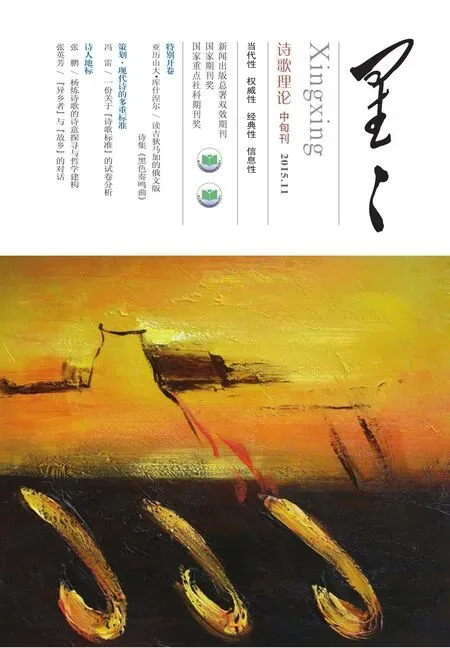一份關于“詩歌標準”的試卷分析
馮 雷
一份關于“詩歌標準”的試卷分析
馮 雷
主持人語:
本期關于詩歌標準討論的文章是一個較為特別的文本。北方工業大學中文系的馮雷老師在他的文學史考試中設置了一道關于“詩歌標準”的題目,對象是中文系一年級的本科生。這類似于一種田野調查,可以較為準確地反映當今年輕的文學讀者(或準文學讀者)關于詩歌的理解與看法。在收到的73份試卷的基礎上,馮雷老師進行了歸納、總結、分析,呈現了90后一代關于詩歌理解的客觀、真實狀況,討論了當前的若干詩歌現象與話題,有趣、有針對性,同時引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王士強
“詩歌標準”是個眾說紛紜的話題,人們對“詩歌”的理解、對“好詩”的想象都不盡相同。不過目前撰文參與到這個話題中來的,大多是“學院派”的專家,他們的意見往往會受到知識背景、師承關系的影響和塑造,因為過于成熟、周全而不免顯得“把一個簡單的問題搞復雜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一個復雜的問題搞簡單”又會怎樣呢?
上學期期末,在“現代文學史”期末試卷的最后,我特意設置了一道“材料與寫作”的大題。給出的材料共有九條,前八條分別是胡適、沈從文、知堂(周作人)、絮如(梁實秋)、卞之琳、何其芳、廢名、穆木天、戴望舒關于新詩的若干評論。最后一條列了六首詩,分別是趙麗華的《傻瓜燈》、烏青的《對白云的贊美》、汪國真的《熱愛生命》、北野的《馬嚼夜草的聲音》、謝文娟的《鯽魚湯》,還有余秀華的《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題目的提示如下:
“好詩標準”、“詩歌標準”一直是近年來詩歌批評界關注的重點話題之一,2008年《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015年《星星》詩刊都曾推出過專欄,集中討論這一話題。這個問題既關涉到當前的詩歌創作、詩壇現象(例如余秀華、汪國真等的詩歌,例如“梨花體”、“烏青體”、“羊羔體”等),也和現代詩的理論建設、詩歌歷史期待、文體秩序相關。
請你結合上述材料,圍繞“什么是好詩”、“詩歌的標準是什么”,談談你的理解和想法。
除去自擬題目、字跡工整、字數范圍等等之外,題目特別要求學生:“1、對文獻材料應有適當的引用、解讀,不必逐條分析。2、對詩歌作品有適當的判斷、評價、分析,談談你的好惡。”
參加考試的73人都是中文系本科一年級的學生,“現代文學史”是必修課,考試采取閉卷的方式。設計這道題的首要用意,在于引導學生閱讀并借助史料,進行書面的學術討論。當然也希望借此可以了解“90后”對于現代漢語詩歌的大致態度。這些學生已經學過了“現代文學史”,還沒有接觸“當代文學史”,對“當代文學”知識場域還比較陌生,題目給出的作品都是“當代”的,這樣做主要是希望避免學生受到文學史結論的規訓而被動地對一些作品帶有先入的成見。
一
閱卷過程中,我對學生的表述做了些粗疏、業余的統計。73個人讀6首詩,《傻瓜燈》獲得了59個差評,“差評率”達到81%,《對白云的贊美》以43個差評緊隨其后,此外有9人對《穿
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表示不滿,對《熱愛生命》和《鯽魚湯》有意見的各有3人,《馬嚼夜草的聲音》零差評。
有33位同學為汪國真的《熱愛生命》“點贊”,這首詩的“好評率”為45%,北野的《馬嚼夜草的聲音》集得28個“贊”,點名表揚《鯽魚湯》的有17人,表揚《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的有14人,另外《傻瓜燈》和《對白云的贊美》也各獲一個好評。
統計情況呈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
學生們關于詩歌的“差評率”明顯要高于“好評率”,這似乎可以理解為,也許大家說不清楚什么樣的詩可以算“好詩”,但是對所謂“壞詩”卻比較敏感和果斷。絕大多數學生都對“梨花體”和“烏青體”持批評的態度。學生們認為這兩首詩“語言惡俗而且沒有任何啟示性”(王自晨);“也可以作為一句標語來理解”,“根本上讓讀者直接跳過鑒賞的環節,我覺得這更像是一種言語浪費”(蘇婷婷);“很粗糙很隨便,缺少詩歌本身獨有的朦朧美與含蓄的表達方式,就像只是對幾個簡單的文字排列組合一樣”(許琪);“作者僅僅是采用了分行的布列的詩歌形式,而絲毫沒有意境之美,只是簡單地去敘述自己的喜惡,這樣的文字像一杯白開水,絲毫勾不起讀者的回味欲望”(張園園)。甚至還有一位學生講了一個他在網上看到的段子,“把今天的心情,做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寫成一句話,把標點符號去除,隨意把這句話分成幾行,一首詩就作好了”(楊文硯)。
總的來說,學生們認為“壞詩”缺乏詩歌應有的美感,具體來說無外乎這樣幾個方面:第一,語言粗俗;第二,表達方式過于直白,以至于懷疑是自己沒看懂;第三,內容空洞,思想貧
乏,讀之無物;第四,詩形隨意,僅僅是排列分行而已。或許還應該補充的一點是“取材寬泛”,例如為數不多的學生對《鯽魚湯》和《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提出批評,理由是“詩歌作者們把所有題材都納入了詩歌中”。(王志新)
二
對余秀華的《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學生們的態度似乎顯得有些猶疑,這和作品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爭議的情形很相似。學生當中這首詩的支持者和否定者數量差不太多。肯定者略多一點點,當然這也可能受到了媒介宣傳的影響。批評者的理由基本沒有超出認定“壞詩”的范圍。肯定者則表示“雖然這首詩的題目看上去沒有那么雅致,但至少他的內容不是那么直白的,有些許朦朧之感,也表達了作者真切的感受”(毛麗佳);作品“痞痞的,帶有一點流氓的氣息和口吻,但是就是喜歡這種情懷”(黃典點);“這首詩的題目我不太能接受,但整首詩讀來,我認為可以將‘你’理解為世界,‘世界這么大我想去看看’。這種詩至少是使我們有所聯想與回味的”(陳靜琳);“這個作品極具感染力,作者通過對‘槍林彈雨’、‘無數的黑夜摁進一個黎明’、‘無數個我奔跑成一個’這些描述表達作者內心的渴望,雖直白,但熱情澎湃”(崔宇陽)。另有不少學生是在談及“好詩”的時候順帶一提,并未對這首詩做過多的評析。
將近一半的學生認為汪國真先生的詩是“好詩”,最起碼《熱愛生命》這首似乎還不錯。比如有的學生認為這首詩“完全可以說是真情實感,讀起來感覺特別有味道,而且很是勁道,讀
完之后仍然值得回味”(秦基偉);“塑造了唯美的意境,給人以心靈的慰藉與啟示,語言明白曉暢,哲理深刻,句式整齊,節奏勻稱(張淏);“用‘遠方’、‘玫瑰’、‘地平線’、‘生命’等意象,表達了對應上下句表達的‘愛情’、‘成功’等情感,并引出了積極向上的奮斗形式”(劉一一);“語言文字錯落有致,長短不一,有一種節奏的美、音律的美,好像古時的長短句”(張子正)。
這里我想就汪國真先生的詩發表一點意見。在我看來,汪氏詩歌的成功之處主要在于其流暢的口語、常見的意象、整飭的詩行、平淺的哲理和連貫、順向的思維方式。學生們對汪氏詩歌的認可基本都集中在這幾點上。不過從我自己的閱讀感受出發,我也并不覺得汪氏的作品可以歸結為“好詩”,特別是讀多了之后。余光中在批評戴望舒的時候曾經提到“就詩的意象而言,形容詞是抽象的,不能有所貢獻。真正有貢獻的,是具象名詞和具象動詞,前者是靜態的,后者是動態的,但都有助于形象的呈現。詩人真正的功力在動詞和名詞,不在形容詞;只有在想像力無法貫透主題時,一位作家才會乞援于形容詞,草草敷衍過去。” 這一點移植到汪氏的詩歌上我覺得是非常有效的。汪氏的詩歌總體上看起來顯得修飾過剩、文采過重,細究之下形容詞的確用得過多。再加上他的詩基本上是不及物的,脫離了具體的生活場景,這都使得他的作品略顯得空洞,而且有流于“新文藝腔”的嫌疑。正如有的學生意識到的那樣,《熱愛生命》“將‘成功’、‘愛情’、‘勇敢’直白地顯現出來,沒有隱藏的內涵,也沒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挖掘”,“沒有余味和回味,顯得過于直白”(漆辛夷);“缺少了一些情感的流變和詩人個性的
書寫”(白楊)。
三
《馬嚼夜草的聲音》和《鯽魚湯》對學生來說可能會顯得有點“冷門”,尤其是《鯽魚湯》,這是我的同門師妹一首沒有公開發表的作品,我曾在一篇公開發表的論文中全文摘錄過。對這兩首詩,學生們盡管吃不準是什么意思,但還是以肯定的態度居多。例如他們認為《馬嚼夜草的聲音》“透過有美感的意象,向人們間接地傳達詩人的情感和內涵”,“這便是朦朧而富有蘊藉的詩”(漆辛夷);“讓我充滿了無限的憧憬和幻想。仿佛感同身受”(苗頎)。關于《鯽魚湯》,學生們肯定了這“是一種委婉而非直抒胸臆的直白抒情”(劉艷妮);“讀者的閱讀可能會感受到更深層的意味,即指的不只是魚,有可能是其他什么”(張子正);“詩形也不畸形,整體上看不呆滯,不遵循舊規律,我認為它們屬于好詩”(黎薇)。可以說,對于這類含蓄、模糊、不那么直截了當的表達方式,學生們基本還是予以謹慎的接受的。
關于《鯽魚湯》不妨補充一個有趣的小花絮。我在論文中認為這首詩的主題是和“革命”相關的,而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林祁教授則認為這首寫的是“性愛”。雖然我們的意見大相徑庭,但都認為這是一首“好詩”。
通過具體的作品分析,有一些學生比較條理、系統地總結了自己的詩歌標準。
比如有的學生主張可以從“詩意的含蓄與直白”、“詩形的
松散與縝密”、“音節的工整與凌亂”三個方面入手,認為詩歌的語言應該講求蘊藉,詩歌的形式仍然有待創造,應當注重音樂性但又不要影響詩歌的自由表達。(劉鴿)
與之相似的主張如“語言文字是否生澀難懂”,“詩人是否能夠成功克制自己噴薄而出的情感”(以卞之琳為例),“是否過于通俗、白話,而讓讀者感受不到一點余味和感想”。(谷海峰)
同樣,有的學生認為“好詩”要“讓人看懂”,“得有真情實感”,“要處理好詩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另外要“有一定的含蓄、含混,要讓人值得玩味兒”。(秦基偉)
還有的學生指出“好詩”要“有較多意象”,“形式與內容要平衡、統一”,“作者在詩中,一定要表現自我”(以戴望舒為例)。(劉一一)
再如有的學生提出“重情、有形、多義”的標準。即“對于情感的重視和表達”,“并非要求現代詩歌如同古代律詩一般平仄對仗的嚴格,而是作為詩歌必須有自己的一套形式所在”,“詩歌蘊含的意思需有一定深刻意義或蘊含多層意義”(周丹丹)。
四
綜合這些意見來看,關于“好詩”,學生們還是非常在意“能不能看懂”的問題,當然在這一點上,學生們的意見還是比較辯證、開放的。他們不喜歡的是那種不知所云、言之無物的空洞,而非詩歌表達的朦朧、暗示以及適度的隱藏。而且,學生大
多強調暗示、含蓄乃是“好詩”應當具備的質素。
在此基礎之上,“好詩”應當大致符合語文寫作的基本規范,比如內容充實、語言流暢;平實也好、秾麗也好,應當體現出一定的文辭和修辭技巧。
第三,情感、意境應當具有感染力,要留有想象的空間,“有了情感還不行,還有有所感悟”(陳靜琳)。
第四,在節奏、音律等形式問題上還是應當有所講究,不能說只要分行排列了就是詩。尤其是詩歌的音樂性問題,很多學生都不贊成材料中戴望舒“詩不能借重音樂,它應該去了音樂的成分”的論斷,認為音樂美“是一首詩歌所必要的條件。詩歌的音韻應與漢字的音韻特點相結合”(蘇婷婷)。還有的學生覺得可以把以方文山為代表的“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詞當做現代詩”,認為這些歌詞“既符合押韻,又能帶給人朦朧美,更符合大眾的喜好”(田中鵬)。
學生們的意見自然不免顯得淺陋、粗疏、無甚新意,我也覺得他們對詩歌的理解和想象還是以古典詩詞和現代文學史上的詩歌為藍本的。不過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意見基本還是落實到詩歌的一些本體問題上的,比如含蓄、文采、形式、意象、節奏等,這或許也說明了讀者對詩歌的文體期待和文化想象,同時也給詩歌標準的討論劃了一個模糊的知識范圍。討論詩歌的標準問題,當然不可能真正為詩歌寫作者樹立可操作的美學規范,而是意在提醒當代的詩人和詩評家注意詩歌、好詩的標準,使大家意識到詩歌和高等數學、量子物理一樣是一門知識,而不要太過隨意和輕率。我曾讀到一位國刊的編輯直言對“十四行詩”不感冒,認為“十四行詩”的本質“在于虛榮和盲目媚外,都是與我
們的母語背道而馳的”。這種態度我覺得是不可取的。我們經常略帶嘲諷地說“比賽留給中國隊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而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時,或許我們也該意識到“詩歌留給我們這一代人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作者單位:北方工業大學中文系)
1.余光中:《評戴望舒的詩》,《余光中集》(第五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519頁。
2.參見拙文:《“80后”詩歌:在成人與成熟之間》,《詩刊》上半月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