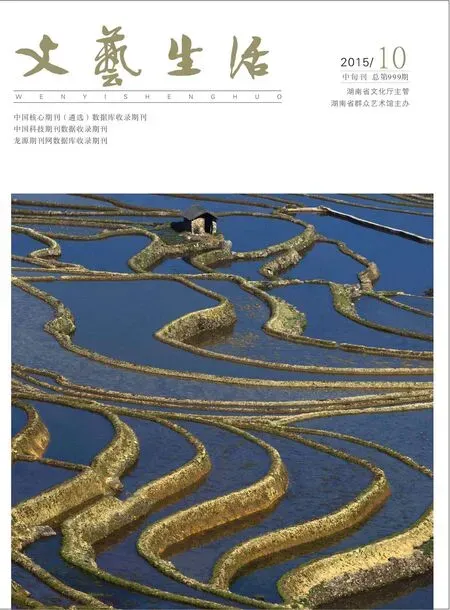矛盾時(shí)代下的文學(xué)典范
——《堂吉訶德》
王浚鑒
(武漢大學(xué)文學(xué)院,湖北武漢430000)
矛盾時(shí)代下的文學(xué)典范
——《堂吉訶德》
王浚鑒
(武漢大學(xué)文學(xué)院,湖北武漢430000)
《堂吉訶德》是我較早接觸的一部外國著作,兒時(shí)在萬千名書中便被它荒誕離奇的情節(jié)所吸引。如今重拾此書,更大興趣偏向于處在文藝復(fù)興大背景下,舊信仰破敗、新思想尚未成熟的思想轉(zhuǎn)型期,這本著作是如何展現(xiàn)人文思想及其文化內(nèi)涵的。人物設(shè)定的匠心獨(dú)運(yùn),故事情節(jié)的暗藏玄機(jī)都無愧于它矛盾時(shí)代黃金產(chǎn)物的文學(xué)地位。這些都將成為再讀《堂吉訶德》新的研究角度。
文藝復(fù)興;時(shí)代產(chǎn)物;矛盾性;藝術(shù)價(jià)值
《堂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于1605年(上卷五十二章)和1615年(下卷七十四章)分兩部分出版的反騎士小說。書中不乏公爵、封建地主、僧侶、農(nóng)民,不同階級(jí)的男男女女約七百個(gè)人物,尖銳地、全面地批判了這一時(shí)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學(xué)、藝術(shù)以及私有財(cái)產(chǎn)制度,真實(shí)而全面的反映了16世紀(jì)末到17世紀(jì)初西班牙的封建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揭露了走向衰落的西班牙王國的各種矛盾,譴責(zé)了貴族階級(jí)的無恥,對(duì)人民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使它成為一部“行將滅亡的騎士階級(jí)的史詩”,一部偉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名著。
文藝復(fù)興轉(zhuǎn)型階段都是充滿矛盾的。文藝復(fù)興是新舊文化之交,是中古時(shí)代思想與近代思想之間的矛盾;是封建主義教會(huì)統(tǒng)治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人文思想、民主自由與專制制度、禁欲主義的矛盾;更有文藝復(fù)興階段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矛盾。《堂吉訶德》中,作者正是借助時(shí)代背景發(fā)掘出矛盾點(diǎn),現(xiàn)實(shí)與想象,真實(shí)與虛幻,智慧與愚蠢,崇高與荒唐,勇敢與膽怯,誠實(shí)與虛偽,理性與瘋癲,建構(gòu)了全書巧妙地框架。本文僅從以下三個(gè)角度切入進(jìn)行研究。
一、主人公堂吉訶德就是一個(gè)矛盾體
堂吉訶德的性格有它內(nèi)在的復(fù)雜性。他性格的顯著特點(diǎn)是脫離實(shí)際,耽于幻想。滿腦子都是騎士小說里描寫的那套古怪的東西,到處都有魔法,巨人和妖怪。同時(shí)他又是一個(gè)理想主義者,他所向往的理想和奉行的原則并不全是騎士制度的產(chǎn)物,其中也包含著人文主義思想。像是他憎恨奴役壓迫,把除奸救苦、除暴安良看作自己的天職,他熱愛自由和公正,敢于為主持正義而忘我斗爭(zhēng)。與此同時(shí),性格的另一側(cè)面便是他行動(dòng)的盲動(dòng)性。辦事不講實(shí)際,單槍匹馬地亂砍亂殺,不管碰到什么樣的敵人,都毫不怯懦,而且從來也不從失敗中吸取教訓(xùn)。反映出他一方面神智不清執(zhí)迷不悟,瘋狂可笑怪誕離奇的性格,又象征著高度的道德原則、無畏的騎士精神、英雄主義的行為、對(duì)正義的堅(jiān)信以及對(duì)愛情的忠貞。他的雙重性格貫穿始末,每一個(gè)魯莽荒誕背后都是一個(gè)英雄主義的初衷。可笑又可悲,可愛又可敬的堂吉柯德形象的巨大概括力,彰顯了他本身的矛盾性魅力。
二、堂吉訶德與桑丘·潘沙的性格矛盾;同時(shí)也是理想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之間的矛盾
如果說堂吉訶德的塑造是成功的,侍從桑丘·潘沙則是另一個(gè)成功典范。他是作為反襯主人公的形象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象征著西班牙的農(nóng)民形象。其性格與主人相輔相成:主人耽于幻想,他處處求實(shí);主人急公好義,他膽小怕事。堂吉訶德充滿幻想(理想主義),桑丘·潘沙則事事從實(shí)際出發(fā)(現(xiàn)實(shí)主義);堂吉訶德代表禁欲主義,而桑丘·潘沙則是享樂派;堂吉訶德有豐富學(xué)識(shí)的鄉(xiāng)村紳士,而桑丘·潘沙只是典型的農(nóng)民形象;甚至細(xì)致到外貌都有堂吉訶德的瘦高與桑丘·潘沙的胖矮做對(duì)比。
朱光潛先生在評(píng)價(jià)堂吉訶德與桑丘·潘沙這兩個(gè)人物時(shí)這樣講:“一個(gè)是滿腦子虛幻理想、持長矛來和風(fēng)車搏斗,以顯出騎士威風(fēng)的堂吉訶德本人,另一個(gè)是要從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祿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們一個(gè)是可笑的理想主義者,一個(gè)是可笑的實(shí)用主義者。但是堂吉訶德屬于過去,桑丘·潘沙卻屬于未來。隨著資產(chǎn)階級(jí)勢(shì)力的日漸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訶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三、《堂吉訶德》在寫法上的矛盾
在塑造堂吉訶德的形象時(shí),用喜劇性的手法描寫一個(gè)帶有悲劇性的人物。它把人物放在一個(gè)個(gè)不同的情景之中,用諷刺的筆調(diào)和夸張的手法,一再描寫人物的荒唐行動(dòng),造成喜劇性的效果。同時(shí),小說著重描寫人物主觀動(dòng)機(jī)與它的客觀后果的矛盾(或適得其反,或迂腐反常,或自討苦吃),在喜劇性的情節(jié)中揭示其悲劇性的內(nèi)涵。這一構(gòu)思也是塞萬提斯的創(chuàng)造,它不僅有利于塑造人物,而且增添了小說的情趣,突出了作品的哲理意味。
《堂吉訶德》乍看似乎荒誕不經(jīng),實(shí)則隱含作者對(duì)西班牙現(xiàn)實(shí)深刻的理解。作者采用諷刺夸張的藝術(shù)手法,把現(xiàn)實(shí)與幻想結(jié)合起來,表達(dá)他對(duì)時(shí)代的見解。作者以史詩般的宏偉規(guī)模,以農(nóng)村為主要舞臺(tái),出場(chǎng)以平民為主要對(duì)象,在這廣闊的社會(huì)背景中,繪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聯(lián)系的社會(huì)畫面。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虛實(shí)結(jié)合,否定中也有歌頌,荒誕中蘊(yùn)含寓意,具有強(qiáng)烈的藝術(shù)性。《堂吉訶德》可以說是傳統(tǒng)騎士文學(xué)的異類,不同于傳統(tǒng)騎士文學(xué)的悲壯典雅。這種另類荒誕、無厘頭的背后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和人生理想,豐富的思想內(nèi)涵,充實(shí)飽滿的人物形象,都在訴說著舊制度給人民帶來的災(zāi)難,成為我們了解和研究西班牙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和風(fēng)俗習(xí)慣的一部百科全書。
I551
A
1005-5312(2015)29-006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