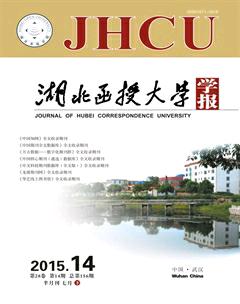從地理語言學和語系的角度審視漢語與英語的差異
熊霄 楊希
[摘要]在全球化和中國擴大、深化開放的語境下,全球使用人數最多的漢語和使用范圍最廣的英語在中國本土發生全方位的碰撞。但是,三十多年來中國民眾、教育機構和各級政府對英語和英語教育的態度和投入稍顯過度與盲目,而且國人習得英語的效果并不是太好。英語教育者和研究者往往忽視了漢語與英語之間天然存在的差異。本文就從地理語言學與語系的角度審視這種天然的差異。
[關鍵詞]漢語;英語;天然差異;地理語言學;語系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14-0123-02
自15世紀大航海時代興起以降,西方諸國憑借堅船利炮逐步登陸中國東南沿海并沿長江向中國內陸滲透。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英語與漢語初次發生大范圍、大規模碰撞。20世紀80年代以降,中國的經濟、文化、政治逐步向外轉型,同時引進國外(西方)的科技與文化。在這種“走出去”與“引進來”的背景下,漢語與英語再次在中國本土發生大規模、全方位碰撞。作為英語研究者,我們有必要提出以下幾個問題:英語的源頭是哪里?其流變與傳播的過程如何?其源頭、流變與傳播如何造成其與漢語的差異?
一、語言的地理差異與跨國界傳播
“地理語言學,也叫語言地理學,該學科以眾多地點的語言事實調查為基礎,利用語言地圖的方式描述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狀況,結合社會文化因素解釋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語言現象歷時變化的過程。”一國之內有不同方言,國與國之間有作為整體的語言之間。語言是國家-民族的身份標識,國家一民族以一定的領土疆界為基礎,故該國家-民族語言受地理空間[包括自然形成的河流山川和(或)國家間的政治邊界]的限制。從一個國家-民族越過邊界進入另一國家-民族的疆域,語言呈現漸進式變化,直至最終出現與源語言有較明顯差別的另一種語言。這既印證了語言是國家一民族的身份標識,也對應“地理差異就成為語言學中最先被注意到的對象”。一個國家一民族的語言界限大致符合該國(民族)地理界限與政治界限(邊界地區存在語言模糊地帶),即從相鄰(陸上相鄰)的A國(民族)到B國(民族),最明顯的差異感來自語言。換言之,語言的差異主要取決于地理差異(空間差異)。從A到Z26個陸上相鄰國家(民族)的理想化模型:若視AL(A國或民族的語言)為源語言,ZL為目標語言,現欲探究兩種語言之間的相似性與親緣性,則須考慮A與Z之間的語言。AL與BL雖有使其保持獨立性的“鄉土根性”,但由于地理空間上相鄰,且語言具有傳播性,兩國(民族)民眾(特別是邊界居民)長期頻繁交往(不考慮政治或軍事隔閡),兩種語言在歷史的沉淀下有相似性或親緣性。如果分別視兩國(民族)的語言為振蕩波,兩個振源向四周輻射,波形互相影響,其效果取決于兩國(民族)的語言疆界,在兩國邊界地區這種效果最明顯,具體表現為邊界地區的語言受到兩種語言的影響,故穩定性較差。AL對BL有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隨著AL在B國(民族)內的深入逐漸減弱,好似離振源越遠波的強度越弱。AL在B的地理空間內因沒有語言環境而弱化為A'L并疊加BL,逐漸異化為(AB)L;當這種被異化語言的波形進入C國(民族),A'L與BL因語言環境的再次改變而分別弱化為A”L與B'L并與CL疊加為(A”B'c)L,以此類推,直至Z國(民族),經過26-2=24個國家一民族地理空間與語言環境的改變,AL已變異為AL24*,同時疊加了24種異族語言,與源語言AL已有很大差異,故AL24*對zL的影響及它們之間的親緣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此過程被筆者稱為“語言波形的漸弱”或“語言親緣性的漸弱”。同時,ZL并非處于靜止狀態被動接受異族語言的影響,其亦遵循語言波形傳播規律向鄰國輻射。根據以上分析,與ZL最具相似性與親緣性的應是其鄰國(民族)的YL,ZL在Y的地理空間內弱化為ZL'并繼續向下一個鄰國(民族)傳播。以此類推,當ZL的變體ZL24*進入A國(民族)時,其與源語言ZL亦有很大差異,其對AL的影響以及它們之間的親緣性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以此理想化模型應用于漢語與英語的關系:英語是英格蘭的官方語言,漢語是中國的官方語言;英格蘭位于亞歐大陸西北端之外的大不列顛島,中國位于亞歐大陸的東端;兩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首都倫敦與北京相距12304.76kin,橫跨歐亞大陸,間隔十幾個國家與幾大文明。根據上文分析,英語與漢語之間通過陸地傳播的互相影響及由之而生的親緣性可忽略不計。所以,在航海與航空技術發達的工業時代之前,英語與漢語之間隔著多重自然與政治屏障而有較大的天然差異。在通信與交通科技發達的后工業時代,兩國(民族)人民直接交流的方式主要是航空運輸,但航空器運輸人數與英格蘭約5000萬人數和中國約13億人數相比,比例太小。過大的地理距離不僅決定了英漢兩種語言的較大天然差異,同時造成了兩國(民族)人民之間交流的不便和對彼此語言的陌生感。
二、語系:英語與漢語
語言的相似性親緣性引出另一概念——語系。“語言系屬分類是指根據語言的發展和演變、直接而明顯的關聯,對語言進行歸類的方法。語言系屬分類主要依據語言語音、詞匯、語法規則之間某些對應關系,把具有相似的語言歸于同一類語群,這種語群稱為同族語言即‘語族;按‘語族之間的某些對應關系,又歸在一起,這類同類語族稱為同系語言即‘語系。”語系分類必然涉及語言及語系比較,“這涉及語言類型學,又稱類型語言學,是通過比較不同語言相同、相異的特點,從復雜的、無限的語言現象中,歸納出少量的、有限的類型,尋找人類語言的普遍現象(即共性),以深化對語言本質、語言特點的認識”。英語非大不列顛的本土語言,該島甚至沒有所謂的本土語言,現代英語是多種語言的融合。其最早的語言為公元前500年左右從歐洲大陸遷徙至大不列顛島的凱爾特人的語言。之后,大不列顛經歷了羅馬人、盎格魯撒克遜人、丹麥人、諾曼人的入侵,每一次入侵伴隨征服者語言的入侵與融合。“民族入侵是語言疊加的一個常見的原因……”。所以,現代英語是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語言——古英語(屬印歐語系西日耳曼語族)為基礎,融合了拉丁語、丹麥語、諾曼語(古法語的北部與西北方言),經過漫長的演變而成。以上這些歐洲語言和英語相似,均以表音的單詞為基礎。例如,“moon”,視之即能根據讀音規則(字母組合、音節、重音)推測單詞的大致讀音,但不能通過其音推斷其義。以表音為基礎的語言其能指與所指之間并無非常明顯的聯系,而是通過約定俗成確定能指與所指的關系。反觀漢語,起源于中國中原地區,數千年來只以中原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其中心從未遷徙他國,可見其純度與穩定性。漢語屬漢藏語系,以表意的漢字為基礎。例如“月”,視之即能根據構字規則(象形、會意、形聲等)推斷其義,但不能通過其形與義推測其讀音。以表義為基礎的語言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但一個字的讀音則是約定俗成的。此外,“關于英漢語的詞義結構…構成英語的語義成分多而細,具有分解性;構成漢語的語義成分則少而略,具有濃縮性”由此可見,英語與漢語的構詞(字)與發音體系完全不同。此外,英語還具有漢語沒有的時態、語態、語氣、屬格等語法體系。而中國大部地區不與印歐語系地區接壤,除了西南部的青藏高原與印度尼泊爾接壤及東北端與俄羅斯斯塔諾夫山脈以南(原屬中國的外興安嶺)地區接壤。但青藏高原為世界屋脊,平均海拔約4000米,與印度接壤的邊境地區屬喜馬拉雅山脈,海拔在7000米以上,為無人區,從而阻隔了印歐語系語言與漢藏語系語言的直接碰撞;中國東北端之外的外興安嶺屬酷寒地區,遠離中原且人口稀少,即使此地區有印歐語系語言存在,對漢語的影響也較小。中國西北部地區與西北邊境之外的地區(包括蒙古和中亞五國)為阿爾泰語系地區,隔開了漢藏語系與印歐語系地區。
結語
傳統的語言學研究和英語教育往往忽視了語言伴隨人而生。人是語言的載體,語言的傳播依賴人的移動。而人的移動受到如大山、大河、氣候、資源等自然條件的限制和國家疆界變化、入侵與戰爭、王朝更迭、殖民與被殖民、經濟與貿易的發展等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對語言的譜系分類究其實與地理語言學一脈相承。一個語言集團在資源豐富的地區定居,如果集團內部政治穩定且無外族入侵,則該集團的語言能得以延續與發展并由人的移動向周邊地區輻射;如政治部穩定或/和有外族入侵,則該集團的語言因為人的被征服或消滅或被驅散而被邊緣化或甚至消亡。本文的結論是漢語與英語由于兩國地理上的差異和傳播上的阻隔以及分屬不同語系,中國人不易習得英語;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舉國學習英語不值得。
參考文獻:
[1]曹志蕓.老枝新芽:中國地理語言學研究展望[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2(3)1.
[2]索緒爾,費爾迪南·德.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3]戴慶廈,朱燕華.20年來漢藏語系的語言類型學研究[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9):131.
[4]姚勇芳.英漢語結構差異在漢詩英譯中的表現[J].中國翻譯,2000(4):24.
(責任編輯:章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