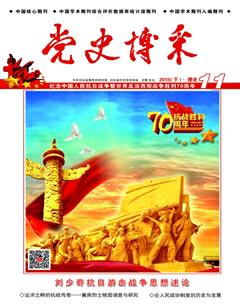“新常態(tài)”語境下“四個全面”的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遵循
田樹洋 田玉嵚
[摘要]以習(xí)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重要精神,研判中國和世界的發(fā)展格局,統(tǒng)籌偉大事業(yè)和偉大工程,相繼提出了“新常態(tài)”和“四個全面”等重要思想。“新常態(tài)”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實(shí)踐,是對中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階段性特征的準(zhǔn)確研判。“四個全面”是新常態(tài)下關(guān)于中國發(fā)展的理論闡釋和價值定位,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馬克思主義的系統(tǒng)觀”、“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觀”,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的歷史起點(diǎn)實(shí)現(xiàn)新的奮斗目標(biāo),順利步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提供了科學(xué)指南和根本路徑。
[關(guān)鍵詞]四個全面;新常態(tài);馬克思主義
一、經(jīng)濟(jì)“新常態(tài)”和“四個全面”
2014年5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中國發(fā)展仍處于重要戰(zhàn)略機(jī)遇期,我們要增強(qiáng)信心,從當(dāng)前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fā),適應(yīng)新常態(tài),保持戰(zhàn)略上的平常心態(tài)。在北京APEC會議上,習(xí)近平首次系統(tǒng)闡述了“新常態(tài)”的內(nèi)涵(國外媒體將之稱為“Pinormal”,即“習(xí)近平常態(tài)”)。同年12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diào)研時強(qiáng)調(diào),要“協(xié)調(diào)推進(jì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全面從嚴(yán)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邁上新臺階。[1]
“新常態(tài)”是我國向世界宣示的決心和政策主張,是對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的深刻領(lǐng)悟和主動作為,主要回應(yīng)了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新趨向,側(cè)重從經(jīng)濟(jì)層面回答如何遵循經(jīng)濟(jì)、社會、自然發(fā)展規(guī)律,推進(jìn)我國經(jīng)濟(jì)持續(xù)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的重要議題。“新常態(tài)”是一個“全面性”的概念,[2]不僅關(guān)乎經(jīng)濟(jì)問題,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關(guān)乎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制度環(huán)境,關(guān)系適應(yīng)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要求的政治體制、法治建設(shè)、社會治理的結(jié)構(gòu)體系,是當(dāng)代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總體布局,從戰(zhàn)略目標(biāo)、發(fā)展動力、制度保障、政治保證四個方面,進(jìn)一步豐富和完善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內(nèi)涵,主要回答了新的歷史時期,如何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xié)調(diào)推進(jì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shí)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戰(zhàn)略問題。“四個全面”闡釋了“新常態(tài)”的中心內(nèi)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義,是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第一個階段性奮斗目標(biāo);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國發(fā)展特色社會主義的強(qiáng)大動力,是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關(guān)鍵一招,;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qiáng)大利器,是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制度保障;全面從嚴(yán)治黨是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關(guān)鍵所在,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保證。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猶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嚴(yán)密結(jié)合,形成動力系統(tǒng),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biāo)的如期實(shí)現(xiàn);全面從嚴(yán)治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堅強(qiáng)領(lǐng)導(dǎo)核心,確保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四個全面”的戰(zhàn)略布局堅定了人民群眾對深化改革前景的信心、對黨緊緊依靠人民進(jìn)行的偉大事業(yè)的理解和支持。
二、“新常態(tài)”語境下“四個全面”的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遵循
“新常態(tài)”是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實(shí)踐,對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階段性特征作出的準(zhǔn)確研判;“四個全面”體現(xiàn)了真理尺度和價值尺度的辯證統(tǒng)一,是新常態(tài)下的關(guān)于中國發(fā)展的理論闡釋和價值定位,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diǎn)。
第一、“四個全面”遵循“馬克思主義歷史觀”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以其頑強(qiáng)的斗志、和平愿景,實(shí)現(xiàn)了民族獨(dú)立、人民解放,步入了國家富強(qiáng)、人民富裕的現(xiàn)代化征程。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新常態(tài)”順應(yīng)了中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要求,“新常態(tài)”語境下“四個全面”是社會主義改革與發(fā)展進(jìn)程中的一次理論創(chuàng)新和現(xiàn)實(shí)關(guān)照,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歷史唯物主義認(rèn)為,在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演進(jìn)中存在著兩大基本規(guī)律: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之間的矛盾運(yùn)動、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yùn)動。這兩對矛盾,在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貫穿始終。其中,作為更為根本的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矛盾,決定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矛盾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然而,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之間的矛盾運(yùn)動又受到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矛盾的制約。站在歷史觀的角度看,“新常態(tài)”語境下的“四個全面”著眼于當(dāng)前和長遠(yuǎn),不僅是對中國發(fā)展的新時期、新階段、新特征“社會主義理性化”的一種理論闡釋、價值定位和社會發(fā)展圖景的清晰呈現(xiàn),而且明確了社會轉(zhuǎn)型時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基本路徑和“社會變遷”的方向。
第二、“四個全面”遵循“馬克思主義系統(tǒng)觀”
馬克思主義認(rèn)為,事物及事物之間是作為系統(tǒng)存在、構(gòu)成的統(tǒng)一體。“四個全面”是對人民期待的根本取向,蘊(yùn)含著系統(tǒng)性改革的“發(fā)展框架”。在“學(xué)習(xí)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fā),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全面從嚴(yán)治黨的戰(zhàn)略布局。這個戰(zhàn)略布局,既有戰(zhàn)略目標(biāo),也有戰(zhàn)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zhàn)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yán)治黨是三大戰(zhàn)略舉措,對實(shí)現(xi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zhàn)略目標(biāo)一個都不能缺。”[3]這為我們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的內(nèi)在邏輯提供了依據(jù)、指明了方向,四者之間相輔相成、相互促進(jìn)、相得益彰。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所強(qiáng)調(diào):“不全面深化改革,發(fā)展就缺少動力,社會就沒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國,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就不能有序進(jìn)行,就難以實(shí)現(xiàn)社會和諧穩(wěn)定。不全面從嚴(yán)治黨,黨就做不到‘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就難以發(fā)揮好領(lǐng)導(dǎo)核心作用。”橫向維度上,“四個全面”體現(xiàn)出“目標(biāo)——路徑”的二分邏輯結(jié)構(gòu)。“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zhàn)略布局的目標(biāo),“全面深化改革”是實(shí)現(xiàn)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強(qiáng)大動力,“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是實(shí)現(xiàn)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制度保障,“全面從嚴(yán)治黨”是實(shí)現(xiàn)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政治保證。改革動力、法治保障、政治保證三者之間全面協(xié)調(diào)運(yùn)轉(zhuǎn),是實(shí)現(xi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偉大目標(biāo)的路徑。縱向維度上,“四個全面”體現(xiàn)出“領(lǐng)導(dǎo)——路徑——目標(biāo)”的三分邏輯結(jié)構(gòu)。“全面從嚴(yán)治黨”是黨緊緊依靠人民、領(lǐng)導(dǎo)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取得偉大勝利的關(guān)鍵因素、根本所在。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之間協(xié)同推進(jìn)、相輔相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yán)治黨具有全面性、協(xié)調(diào)性、整體性,形成邏輯縝密、內(nèi)涵豐富的開放體系,統(tǒng)一于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歷史征程之中。
第三、“四個全面”遵循“馬克思主義發(fā)展觀”
發(fā)展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范疇之一,當(dāng)代中國的根本任務(wù)就是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在改革、建設(shè)的不同歷史時期,黨緊緊依靠人民,基于正在進(jìn)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shí)踐的基礎(chǔ)之上,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十八大以來,以習(xí)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站在時代發(fā)展高度,主動迎接挑戰(zhàn),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chuàng)見的新思想、新觀點(diǎn)、新論斷、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xiàn)實(shí)問題。“四個全面”回應(yīng)推進(jìn)科學(xué)發(fā)展面臨的現(xiàn)實(shí)難題,回答了推動科學(xué)發(fā)展需要怎樣的戰(zhàn)略布局的問題。“四個全面”是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繼承和發(fā)展、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jìn)的科學(xué)理論,是對黨治國理政實(shí)踐、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dǎo)黨治國理政實(shí)踐經(jīng)驗的總結(jié),進(jìn)一步深化了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guī)律和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建設(shè)規(guī)律的認(rèn)識,必將在指導(dǎo)未來的實(shí)踐中開創(chuàng)黨治國理政的新局面。
三、結(jié)語
“四個全面”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dāng)代中國具體實(shí)踐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開拓了當(dāng)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fā)展的新境界,是指導(dǎo)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diǎn)的偉大斗爭最鮮活的馬克思主義。[4]理論上,“新常態(tài)”語境下“四個全面”戰(zhàn)略思想的提出,進(jìn)一步完善了習(xí)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內(nèi)在邏輯。實(shí)踐上,“新常態(tài)”語境下的“四個全面”是當(dāng)前及未來一定時期中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基本遵循。當(dāng)前,我們面對的世情、國情、黨情繼續(xù)發(fā)生深刻變化,面臨的發(fā)展機(jī)遇和風(fēng)險挑戰(zhàn)前所未有。基于中國處所的歷史節(jié)點(diǎn),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判斷,科學(xué)發(fā)展、深化改革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guān)鍵。我們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增強(qiáng)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jī)地深化和推進(jìn)重要領(lǐng)域的改革。十八大以來,以習(xí)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瞻遠(yuǎn)矚、深謀遠(yuǎn)慮,勵精圖治、攻堅克難,帶領(lǐng)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新成就、樹立新風(fēng)尚、開創(chuàng)新局面。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實(shí)現(xiàn)“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總目標(biāo),進(jìn)一步推進(jìn)體制機(jī)制創(chuàng)新,進(jìn)一步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激發(fā)社會活力,促進(jìn)社會公平正義;通過“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黨的領(lǐng)導(dǎo)、人民當(dāng)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jī)統(tǒng)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維護(hù)憲法法律權(quán)威,依法維護(hù)人民權(quán)益、維護(hù)社會公平正義、維護(hù)國家安全穩(wěn)定;通過“全面從嚴(yán)治黨”,確保黨的先進(jìn)性和純潔性,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堅強(qiáng)領(lǐng)導(dǎo)核心。新常態(tài)語境下的“四個全面”為中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進(jìn)入新階段確立了新的向?qū)В瑸樵谛碌臍v史起點(diǎn)實(shí)現(xiàn)新的奮斗目標(biāo),順利步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提供了科學(xué)指南和根本路徑。在歷史歲月的長河中,也正是社會形態(tài)的演進(jìn),使這個古老而偉大民族,又一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釋]
[1]習(xí)近平在江蘇調(diào)研時強(qiáng)調(diào):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yī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新常態(tài)推動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shè)邁上新臺階[N].人民日報,2014-12-15.
[2]竹立家.“新改革觀”與“新常態(tài)”[J].中國經(jīng)濟(jì)報告2015(1):15-16.
[3]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4/c_1114255926.htm
[4]本編寫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2015年修訂版)[M].2015(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