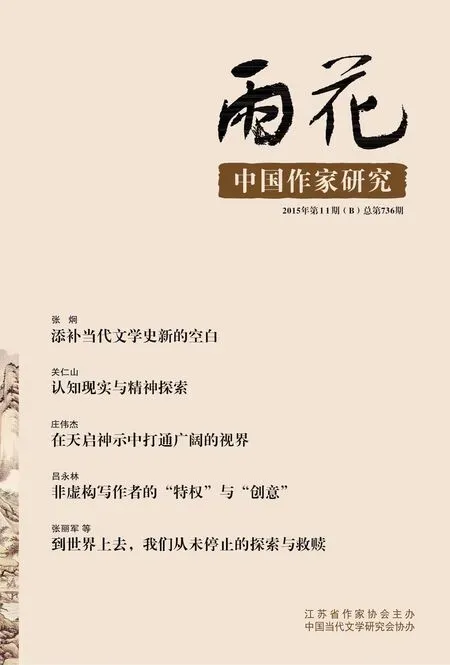苦難、人性與悲憫情懷
——張曉惠《北上海》關鍵詞解讀
■王玉琴
苦難、人性與悲憫情懷
——張曉惠《北上海》關鍵詞解讀
■王玉琴
文學寫作的主體是作家,而其客體總是我們生活著的這個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五彩斑斕而又亂象紛呈。亂花漸欲迷人眼,對于一雙平常的眼睛來說,走過路過也就錯過了,但對于擁抱生活而又積極過濾生活的寫作主體——作家來說,卻絕不可能被表面化的生活所迷惑。他(她)以霧里看花的智慧,將生活中的雞零狗碎與枝枝丫丫,毫不留情地剪裁掉,最終留下人生的底色與心靈的藝術。對于江蘇作家張曉惠來說,一次采風活動中無意中邂逅的一張照片,揭開了60多年一段波瀾壯闊然而塵封已久的大遷徙往事。循著這張陳列在江蘇大豐知青紀念館中的照片,張曉惠揭開了“北上海”50萬畝熱土的冰山一角。跟作家以往聚焦于“私人化”體驗的單篇散文不同,《北上海》是其創作生涯中完全聚焦于一片土地、集中于一類人群的大部頭作品。無論是在張曉惠個人30年的寫作生涯中,還是中國紀實文學史上,《北上海》都堪稱一部傳奇。
“北上海”,作為一個具有地域內涵的名詞,凝聚著特有的文化意義。既然是“北”上海,當然并非上海本土;既然是“上海”,就與上海本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北上海的誕生、成長、發展與衰弱,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國家行為。據史料記載,1949年12月,為了“提純”新中國最大城市上海的城市居民質量,保證新上海的長治久安,上海相關國家部門動用警民武裝力量,突擊收容了上海市區的流氓、強盜、慣偷、毒犯、妓女、兵痞、乞丐及各類游民、難民、無所依托的流浪兒童,約8000人。這批人于1950年被集中收容整編,送到距離上海本土約300公里之外的江蘇大豐荒無人煙的灘涂墾區,實現改造與建設的雙重任務。到了1952年,墾區人數增加到13432人。如果這一批萬人隊伍,完全就是流氓地痞毒犯妓女等各類社會渣滓,則他們承受改造苦難、人生歷練可謂罪有應得,咎由自取。如果這樣,張曉惠以紀實文學之史筆創作《北上海》,其歷史價值與文學意義可能減弱許多。《北上海》根本和真正的立意,是為更多普通而無辜蒙難的北上海建設者、拓荒者、積極改造者而樹碑立傳。因為在初期13432北上海人中,無刑期游民達9270人。對于大多數無以為生的舊上海城市游民來說,這些被后人定義的北上海人更多地承受了時代的政治陣痛,以汗水與血淚為偉大的新中國獻祭。張曉惠站在歷史的肩膀之上,以熱淚、深情與包容,感喟北上海人的脫胎換骨、生離死別,感喟他們的豁達、寬宥以及對北上海熱土綿長的愛戀。北上海式的拓荒和改造,是新中國時代的記憶,是飛地式時空的跨越,具有特有的美學價值與文學史意義。
一、時代匯就的飛地式苦難
飛地是一種特殊的人文地理現象,是一片隸屬于某一行政區管轄,但不與本區毗連的土地。北上海是中國最高級別、最具代表性的飛地。張曉惠作為飛地所在轄區的地方作家,撰寫北上海人在飛地上的苦難史詩,獨得地利與人和之便。
在《北上海》的第一樂章《茫茫鹽堿灘浩浩太平洋》中,張曉惠以詳實的數據與動人的文字,集中、凝重地呈現了北上海人改造的艱辛和時代的苦難。從一無所有、一窮二白,北上海靠著有限的管理人員以及低廉的資金成本,實現著最大化的人員管理、灘涂拓荒與生產生存。由于生存條件的惡劣及各種設施的缺乏,為“提純”上海而來到北上海的各式人等,注定承受著超越身心的痛楚。《綠茵姐姐笑了》以窺斑見豹的方式敘寫了妓女改造的艱辛,除了要跟梅毒等各種性病作斗爭外,墾區管教人員難以招架的是妓女心靈的改造。《白粉大煙鬼的新生》通過阿蘭、陳德福的戒毒故事,詳細呈現了吸毒者煉獄一般的戒毒過程。《蘆蕩中響起的槍聲》通過800多人的越獄故事書寫了犯人改造的艱難,以及犯人管理中的一刀切和管理漏洞。《縱火案揭秘》,書寫了兩個游童阿根、楊小法艱難的一生,也為屈打成招而無辜受死的尹一德、徐超一掬同情之淚。在縱火冤案事件中,阿根和楊小法被急于立功的專案組成員威逼利誘,被迫指正尹、徐二位無辜人士為縱火指使者,自己也身陷囹圄。待到36年后四人昭雪平反時,尹、徐二人早已成千古冤魂,兩位當年只有十四五歲的小小少年背著勞改犯的枷鎖度過了痛苦的大半生,進入了遲暮之年。張曉惠通過對縱火案事件的詳細敘述,呈現時代苦難之一斑,感慨特定年代、特定人事對普通人生活的戕害,激起人們對法制意識和人權意識的反思。
張曉惠書寫的時代性苦難,許多和特定時代寶貴生命的消逝相關。例如50年代墾區管理局辦公室主任鄒魯山,因病痛之軀勞累過度突發腦溢血而死,成了蘇北墾區倒下的第一位拓荒者;1961年為填堵海堤缺口而勞累至死的年青場員李旺財,成為上海農場犧牲的第一位年青烈士;文革時期不堪造反派侮辱折磨、雙雙自盡而死的土壤學專家趙逸文夫婦,成了理想的殉道者;70年代為保衛農場集體資產而被當地居民陷害至死的上海知青大海,死后農場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但并未被認定為烈士……每一個生命消逝的背后,都是一段凝集著苦難與奉獻、赤誠與犧牲的故事。張曉惠以深情筆觸記載北上海人的死亡事件,隱喻著北上海近50萬畝荒灘變為良田的改造,凝聚著汗水、血淚、生離與死別。在北上海這片50萬畝的荒原之上,前后生活過各式犯人、游民、知青、場員10多萬人。正是北上海人的血淚耕耘,才實現了北上海滄海桑田的變化。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與天地相爭、又與天地相往來的苦難史。北上海本來就是新中國改天換地之后新建的墾區,意在改造荒原,也改造舊社會大多數素質低下的舊上海游民。除舊布新的改造過程,意味著陣痛與撕裂,也意味著死亡與新生。張曉惠通過苦難書寫與死亡追述,反思和總結北上海人櫛風沐雨、脫胎換骨的過程與代價,感喟“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力爭“為曾經的創傷、痛苦乃至罪惡做一個注腳”,其歷史紀實與文化反思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二、苦難歷練中的多元人性
《北上海》是一部建構在真實歷史上的苦難史,也是一部善惡交織的人性教科書與情愛傳奇。在一片50萬畝的荒灘土地上,前后生活過10多萬人的茫茫北上海,挑戰了怎樣的人性?北上海人又以怎樣的精神力量應對蚊蟲肆虐的千古蠻荒、人性中的貪婪丑惡還有身心俱疲的磨難?
從弗洛伊德心理學角度考察人性,人有兩類本能:愛欲和死亡本能。愛欲表現為善良、慈愛、寬容等積極光明的行為。死亡本能則表現為殺戮、貪婪、自毀等邪惡極端的行為。可以說,一窮二白、條件艱苦的北上海是一塊人性的試金石,人性的善惡、易變、復雜、多元在這塊試金石上畢露無遺。《北上海》這部作品呈現了這方土地上的苦難與死亡,更言簡意賅地探討了復雜的人性。在作品的第一部分,張曉惠提及了毒犯、妓女、慣偷等人的改造。北上海人的改造,最切實最直接的方式是管制和勞動。面對著超越體能的勞動改造,曾經的毒犯吳強、花鵬飛等人,都以異樣的方式對抗著嚴明的改造紀律。吳強為了對抗勞動改造,先后以裝病、絕食的方式對抗挖溝、刈草等墾區勞作,趁刈草之時故意用鐮刀割斷了自己的腳筋并栽贓管教干部,心甘情愿地成為一名殘疾人。上海灘流氓花鵬飛為了對抗改造,用褲帶將自己吊死在廁所中,使自己成為800多犯人蓄意逃跑的導火線。張曉惠在文中這樣感慨,“生活就是這樣,猝不及防的殘酷撲面而來。它往往會讓好的更好,差的更差,惡的罪不可赦。尤其是在一個制度不健全的社會,在一個無序又躁動不安的年代。”艱辛的勞動、毒癮的侵蝕、管教中的粗暴以及人生的絕望,使得人性死亡本能中的貪婪、殺戮與自毀行為屢屢發生。張曉惠借《北上海》,直陳出人性的復雜與改造的艱難,從冰山一角反映出“提純”人性的艱難險阻,從另一個維度凸顯出墾區管教者、建設者的犧牲、艱辛與雄偉。
死亡本能的另一面是愛欲與人性之善。無論條件怎樣艱苦,怎樣陷入絕境,久經歷練的北上海人終以希望之光生存、繁衍并生生不息。在《北上海》中,在書寫絕境與絕望的同時,張曉惠以溫馨之筆濃墨重彩地凸顯了人性中的善與愛,使得那些誕生于極致痛苦中的純良友善與心心相印,迸發出激動人心的力量。在《最后的上海寶貝》章節,張曉惠書寫了葉靜、王三山與金桐的故事。王三山是一個殘疾的黃包車夫,他在葉靜毒癮發作時收留了她,最后為她累垮了一條命,留下“你把那個東西戒了吧”的遺言。金桐為了幫助體弱的葉靜,將自己輕松的統計員工作讓給她。艱難困苦中的互幫互助,誕生了惺惺相惜的愛情,無論是金桐和葉靜,還是在戒毒過程中互幫互助的陳德福和阿蘭,抑或“丹鳳眼”和阿良,高蜀蓮與電工劉偉棟,這一段段滋養于北上海土地上的同命相憐的愛情,減輕了惡劣生存條件中的苦,化育了人性中本然的惡,蘊育了清寒絕境中的美,帶給北上海別樣的風情、新生和希望。個人改造中的新生和愛情催生出的新家庭,使得孤絕清寒的荒野灘涂,成為家園和希望的象征。張曉惠在10多萬北上海人中,精選幾則獨具風情的戀愛故事,道出了人性中的善良、友愛、純情和堅守,表達了人性積極力量的永恒與至善。
在述說善惡兼具的人性化故事的同時,張曉惠借詳實數據展示了北上海人開天辟地的力量。從1950 到1953年,北上海人興建草房2000多間,開墾荒地9600多畝,鞋廠、木器廠、鐵器廠、學校、醫院相繼建成。其中最為重要的是,9200多名原先的游民、游犯經過身份的重新認定和勞動改造,成為具有各項政治權利和自由人權的“場員”。通過歷史紀實與文學虛構互相結合的創作手段,張曉惠融歷史記載、人性探究與人文關懷于一體,展示了北上海的悲歡離合、愛恨情仇,讓讀者對于塵封既久的北上海往事,有了真切的文學體驗,再現并提升了人們對于那一段歷史的感知、認識和理解。
三、生命至上的悲憫情懷
《北上海》30萬字,敘述了四個板塊的北上海人的故事。從游犯游民改造、場員情感世界、農場知青經歷到墾區管理者的奉獻犧牲,《北上海》自始至終,滲透著作家切己的生命感悟,表達著生命至上的悲憫情懷。這種悲憫情懷,超越了地域、政治與歷史局限,具有自省、反思意識以及清醒的人文精神,可謂柔性與硬度兼具,感性與理性辯證交融。
《北上海》最重要的敘述視角,是以第一代北上海人——田崇志的視角切入的。為什么從田崇志的視角觀察北上海60多年的北上海農場史?這與田崇志個人的人生經歷及他40年一日不間隔的日記相關。“爸爸不在身邊的時候,你每天都要記日記,十來個字也可以,百十個字也可以,將你和妹妹每天的事情都記下來,這樣,爸爸不在你們身邊,再見面的時候,看到你記的日記,爸爸就知道你們是怎樣過來的。”田崇志的父親田中瑞是一名國民黨中將,在1949年逃亡臺灣前夕,交代年僅12歲的兒子田崇志擔負起照顧妹妹的責任并每天寫日記。自1949年與父親分別到1989年父子再會,12歲的少年田崇志變成了50多歲的老人,40年日記記載著時代的進程、個人的成長、生命的失落與人生的感喟。田崇志母親與小妹跳江而死,父親逃往臺灣,作為敵對陣營國民黨子女的田崇志兄妹,成為“提純”對象,和1000多名其他游童被送到墾區集中管理。田崇志40年來一日不隔的日記,成為張曉惠創作《北上海》最重要的契機。
從追蹤田崇志的日記人生開始,張曉惠對北上海人的生命感悟及悲憫情懷,由始至終地貫穿于《北上海》全篇之中,是文章中重要的亮點與文學內涵。例如文章的一開始,作者寫到1000多名毫無家庭照顧的游童被遣送墾區時感慨:“今日之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出讓這批孩子來到墾區的理由。何況,這些孩子的父母有許多曾在抗日戰場上浴血奮戰、戰功赫赫……還有一些從小因貧窮受盡磨難的孤兒和流浪兒童……大上海,即使是建國初期急需除舊布新、百廢待興的上海,無論從財力還是物力上,也是有能力撫育和教育這批從六七歲到十二三歲的孩子的吧!”在文章之中,張曉惠提及致殘的人群三年中從397人增加到845人,一個冬天曾經鋸掉過18條腿4只腳。面對著后天勞動導致的傷殘,作家如此感懷,“也許,這樣的數字對于那個時期、那個年代,相對于12000多人的新生改造……不算一個特別大的數字與問題。但對于一個個具體的只有一次生命的人呢?”面對時代造就的命運不公,張曉惠在文章最后的感慨無奈而沉重:“命運對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太不公平甚至太殘酷了。歷史從不為一個個具體的人生埋單,時代也不為一個個具體的生命負責。”在每一段歷史的背后,張曉惠或以數字或以特定的散文化敘事,書寫北上海人遭遇的生存與生命危機,質疑特定時期的時代政治,感慨生命力量的強大與人類心靈的深邃,探討人的尊嚴和理想化生存的可能性。
四、結語
歷史是靜默的,惟有后來者的觸摸才能讓無語的往事煥發生機,產生以史為鑒的認識價值。沉寂了60多年的北上海,終以其紀實文學樣貌,面呈讀者,并很快產生了異乎尋常的反響——與北上海密切相關的人物專題片《日記人生》已經開播,《北上海》書評也時見于報刊,《北上海》紀錄片也正在拍攝之中。歷史、現實與文學之間,既有一條看不見的鴻溝,更有一條割不斷的血脈暗流。惟有傾心聆聽與心力灌注,才能在認識之后進而審美感知,讓真實的歷史成為不被遺忘的、有價值的歷史,才能在先輩們開墾過的土地上,澆灌出脫胎換骨的、更加璀璨的文明花朵。
(作者單位: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