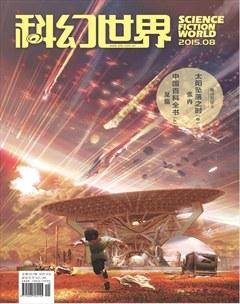中國百科全書(4)
夏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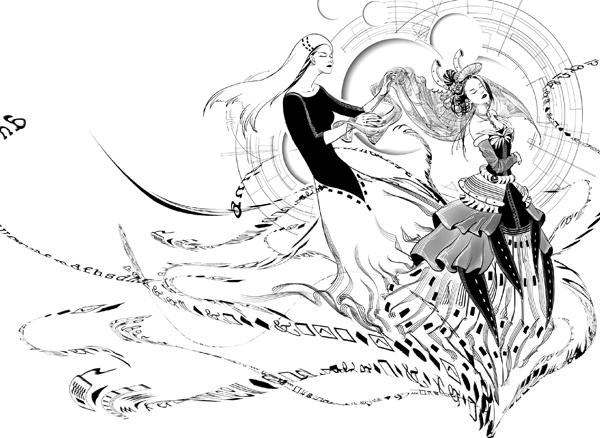
巴別亂
咚咚,咚。
咚咚,咚。
清脆的敲擊聲將我從閱讀中打斷。我抬起手腕看了一眼iWatch,兩個時鐘同時跳出來。此刻中國是下午,倫敦那邊還不到早上七點。
滑動指尖,小蠻的臉浮現在屏幕上,一頭短發亂蓬蓬的。
我打開表情符號欄,在對話框中輸入一個鐘表和一個問號。
(起這么早?)
她發來一張動態圖像:一個小人兒從床上滾到地上,又從地上滾到床上。
(睡不著。)
我也發去一張動態圖:一個小女孩在哭,一只小怪獸摸著她的頭安慰她。
她發來一個小機器人,臉上顯示出“3、2、1”的倒計時,然后點火飛向空中,旁邊加上一個問號。
(你能早點兒過來嗎?)
我發去一個“OK”的手勢,一個噴水的蓮蓬頭,一只吹風機,一支唇膏,一個鐘表。
(好的。我收拾一下,你等我一會兒。)
梳洗打扮完畢后,我來到球幕室中,穿上灰色連體感應服。衣服材料柔軟而富有彈性,緊緊包裹住腰部以上的部分。一切準備就緒,我抬起腳,用鞋跟在傳感地板上敲了三下:
咚咚,咚。
這是我自己設定的指令,靈感來自《綠野仙蹤》中那雙神奇的銀鞋。
周圍的iWall亮起來,映出栩栩如生的影像。我仿佛置身于一間光線柔和的房間,里面亂糟糟的,墻上貼著各種電影和唱片海報,衣服和毛絨玩具堆得到處都是。小蠻穿著睡衣窩在床上,頭發濕漉漉的,臉上貼著面膜,屁股下面坐著一只被壓扁的熊貓靠墊,百無聊賴地啃著指甲。
我模仿她啃指甲的動作,雙手交叉,比出一個大大的叉。
(不許咬指甲!)
她卻哈哈大笑起來,笑得直在床上打滾兒。我轉過頭,在一面落地穿衣鏡中看見了自己的模樣:白白的、雞蛋一樣光滑的臉上投影出我的面部五官,每一個表情都惟妙惟肖;脖子下面是胖墩墩的身體和兩條手臂,我舉起雙手,依次動了動五根手指,鏡子里那個圓頭圓腦的身影也同時做出一模一樣的動作。
iRobot最初被設計為遠程遙控家政機器人。它沒有腿,靠底座上的輪子移動,胳膊和手臂卻像真人一樣靈活,能削蘋果,能端茶倒水,能做飯、洗碗、繡花、寫字、彈鋼琴……除此之外,它還能派上很多意想不到的用場。最近我看到的一則新聞上說,一位有飛行恐懼癥的暢銷書作家,計劃通過iRobot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城市舉辦長達一周的巡回簽名售書會,卻因為腱鞘炎發作而不得不提前終止。
技術永遠都是雙刃劍,讓人快樂也讓人煩惱。
為了今天這個特殊場合,小蠻專門用假發和拖地禮服裙把iRobot裝扮起來,禮服裙的長度經過她親手剪裁調整,以配合機器人的身高。我移動身體重心,試著讓iRobot前后左右移動。香檳色的塔夫綢下擺剛剛好貼地,又不會被輪子掛住。
她蹲下身幫我整理裙擺,比出一個“OK”的手勢,同時向我投來問詢的目光。
我回給她兩個大拇指。
小蠻曾經是玩偶設計師,裝扮機器人對她而言并不是什么難事。她用陶泥做出各種各樣憨態可掬的卡通形象,然后在燒制好的玩偶上繪畫,粘貼配件,再加上服飾和發型,賦予它們獨一無二的個性和表情。我最喜歡的是她送給我的一只陶瓷河馬,作出撅著屁股向遠方歡快奔跑的姿態。河馬身上用丙烯顏料畫滿我最喜歡的向日葵,臉上沒有眼睛鼻子,只有一張大大的紅唇,仿佛在咧嘴大笑。
住進“百鳥之家”后,她一度停止了工作,直到半年前才又慢慢重新撿起。她最近的作品是一款沒有臉的白瓷娃娃。你可以將朋友的照片或者卡通頭像投影到娃娃臉上,根據對方iWatch上傳輸過來的呼吸、心跳、體溫、步速等各項數據,娃娃可以模擬出微笑、焦慮、低沉、疲憊、緊張、熟睡等幾十種不同表情。這款沉默寡言的娃娃出乎意料地大受歡迎,賣得很好。
整理完裙擺,小蠻又指了指我的胸部。我低頭審視,發現她很用心地在禮服裙里縫了兩塊硅膠墊,好把胸部撐起來。我捏了捏硅膠,感應服手套里面傳來微妙的壓力變化,帶來一種細膩柔軟的觸感。
(怎么樣?)
我擺出嫌棄的表情,雙手夸張地在胸前比畫。
(太小啦,我哪有這么平!)
小蠻大笑著,指一指堆在旁邊桌子上的各種零碎材料。
(要不再幫你加工一下?)
我搖搖頭,雙手在胸前合掌,做出葉子形狀,然后手掌張開向上,舉到她面前。
(算啦,今天你是紅花,我是綠葉,我是來陪襯你的。)
她重復“花”的手勢,放到臉旁邊。
(我是花?)
我點點頭。
她伸直胳膊,在旁邊高出她一頭的高度上比畫了幾下,拇指輕點。
(那他呢?)
我比畫了一坨扁扁的東西。小蠻配合地把她打開的雙手放在我的手上面。
(一朵鮮花插在……)
我們兩個笑成一團。
據說笑是人類與同類交流的最古老方式之一。嬰兒在學會說話之前,就先學會了笑。因此在人類社會的每一種語言中,笑的意思都是一樣的。
許多年前,當我在大學里第一次讀到一篇關于“巴別綜合征”(Babel?Syndrome)的文章時,并沒有想到將來有一天,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會因此而被分開。
文章作者推測,巴別綜合征在人類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很久。舊約《創世紀》第十一章中那段有關“變亂口音”的描述,就是對這種病大規模爆發的最早記錄: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
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
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后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
我們下去,在那里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為耶和華在那里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Babel在希伯來文中正是“變亂”的意思。
最近十幾年的醫學研究證明,巴別綜合征是一種名叫LDR的病毒引起的。這種病毒的潛伏期長達幾年甚至十幾年,發病卻很迅猛。進入發病期后,病毒首先感染大腦的前額葉皮質腹部區到胼胝體膝部區,這些區域都與人的行為有關,因此初期癥狀是抑郁、消沉、沉默寡言、離群索居。發病三至四個月后,病人突然變為亢奮、話多、性欲旺盛、創造力強。很多病人會在這個階段留下令人驚嘆的詩歌、小說和其他各種藝術作品,對這些作品的研究,如今已逐漸發展為藝術研究中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然而,這也是病毒感染力最強的時候,哪怕只是當面交談,都有可能因為接觸病人的唾液而被感染。
再過大約一個月后,病毒開始感染語言功能區。首先受到影響的就是頂下小葉中靠近外側裂后方的角回(Angular?Gyrus),這個區域是處理來自視覺皮層信息的重要部位,決定人的讀寫能力。在此過程中,病人逐漸出現閱讀和書寫障礙。一些研究表明,對于雙語或者多語掌握者來說,不同語言的讀寫能力退化速度各不相同。總體而言,非表音文字會比表音的字母文字退化得更快,而與是否母語或者學習掌握的先后順序及熟練程度等因素關系不大。
很快,病毒開始感染位于大腦左半球顳葉后上部的維尼克區(Wernicke's?Area)。這個區域負責將大腦聽覺皮層傳來的聲音信號與記憶中的詞庫進行對比,找到對應詞語及其所代表的意思,使得人能夠“聽懂”一個詞。在病毒影響下,病人聽人說話時所接收到的信息會逐漸發生微妙的偏差,從而對理解他人語言造成一定困難。在有些病人聽來,元音“A”的發音會變得更加扁平,而“P”“T”“K”這些清輔音則變得渾濁;有些人會把音調聽錯,或者把兩個音節聽成一個,其造成的結果是,原本熟悉的語言聽起來像是外語或者方言。但也有少數相反的例子,譬如一位在紐約上東區長大的銀行家患病之后,漸漸聽不懂電視新聞里的英語,卻反而感覺家中墨西哥保姆所說的英語變得好懂很多。
接下來,病毒感染位于第三額葉回后部的布洛卡區(Broca's?Area)。這一區域負責發出指令到軀體運動皮層中掌管咽喉舌肌的神經元,并通過這些神經元支配相應的肌肉運動,使人能夠流暢地表達語言。LDR病毒對這一區域的影響是最神秘的,其機制到現在尚未完全搞清楚。在其他人聽來,病人的口音會越來越奇怪,最終變得難以理解。每一位病人的口音變異方式各不相同,有些人會喪失發后鼻音或者舌尖擦音的能力,卻能夠發出另外一些在大多數語言中都很少使用的異常音素。最終,每一個病人說話的口音都會完全不一樣,并且只有病人本人能夠聽懂。
過去幾千年中,人們并不知道巴別綜合征是由病毒引起的,而通常認為是病人瘋了、中邪了或者被魔鬼附體。很多病人甚至因此被燒死或者活埋,少數人則被當作神的代言人供奉起來。那些活下來的病人會在余生中說著誰也聽不懂的話,無法跟世界上任何一個人交流。天長日久,他們就真的在孤獨中瘋掉了。
文章結尾處,作者憂心忡忡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有一天,這種病在全世界范圍大規模爆發怎么辦?
那會是人類的末日嗎?
兩年前的一個冬日午后,我獨自坐在家里看電影,iWall上的影像突然中斷,一個眉清目秀的男人帶著標準的職業微笑用英語向我表示歉意,隨即他告訴我小蠻在倫敦被確診的事。由于我們半年之內有過親密接觸,存在一定被感染的可能性,他說,醫務人員將在一小時內上門為我做診斷,在此之前,他建議我不要出門跟人接觸。
三個月前,小蠻放圣誕假回國。我們在這間屋里,一起做飯、吃飯、聊天、喝酒,夜里同睡一張床,一直聊到天色微明,就像我們小時候經常做的那樣。
“她在哪里?我能不能跟她說句話?”我問。
“等診斷結果出來,我會再跟您聯系。”
我仿佛聽到他微笑背后沒有說出來的潛臺詞:
If?lucky?enough,?you?will?meet?her?soon.
如果幸運(不幸?)的話,你們很快就能見面了。
我試著開門,門果然打不開,我已被iRoom管理程序鎖在房間里。我不知道該如何打發這一個小時,就去廚房給自己調了杯酒,回到沙發上,想把電影繼續看下去。iWall上光影明滅,男女主人公相聚又別離,訴說著愛恨情仇,但他們所說的一切仿佛突然都對我失去了意義。
人一生有那么多時間浪費在說話上。說話太容易了,像吃飯喝水一樣平常,大多時候我們并沒把它當回事。
我關掉電影,打開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在書中第243至363節,維特根斯坦討論了“私人語言”是否可能存在的問題。他論證道,根本不存在一種只有說話者自己懂得卻無法被其他人所理解的語言,語言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種屬于眾人的公共智性活動。
如果我將一種感覺命名為“愛”,但卻無法向第二個人描述這種“愛”是什么感覺(心跳、臉紅、舌尖的酸甜、手心的溫暖、香氣四溢的吻),我只能對自己說:“我將牢牢記住,這就是愛。”那么我又如何能夠斷定,將來的我是在以正確方法使用這個詞,而不是錯誤地相信自己正確使用了這個詞呢?
如果隨著時間流逝,一些新的感覺出現了(熟悉感、安全感、親昵、厭煩、斤斤計較),我又如何能夠比較并且判斷,它們是否依然是我記憶中所命名的“愛”?
既然不能向其他人求證,只能一廂情愿依賴自己的判斷,那么我又如何知道,天長日久,我命名為“愛”的那些感覺,是否已不知不覺被另一些感覺所替代(倦怠、焦慮、虛無感、深夜的心悸、面對未來的不知所措)?
動物之間有激情和纏綿,但只有在人類發明了語言之后,才有了“愛”的概念。如果全世界七十億人,每個人都只擁有一種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無法理解的“愛”,那么是否意味著愛的終結,或者,人類的終結?
我想象自己墜入一道黑漆漆的深淵,將我與所有人遠遠分隔開。
我想象擁擠的街道上,人們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當我開口說話時,卻發出渡鴉般尖利的悲鳴,惹得滿街人哈哈大笑起來。
我想象全世界最后兩個人在城市廢墟中相遇,面黃肌瘦,衣衫襤褸,手中緊握磨尖的鐵棍。他們絕望地相互叫嚷,卻不知道是該沖上前殺個你死我活,還是該扔下武器彼此擁抱。
我緊握雙手,咬緊牙關,坐在屋里等待。一個小時從未感覺如此漫長。
醫務人員如約而至,一身白色隔離服,包裹得嚴嚴實實。抽血,化驗,測量各種數據,問繁瑣的問題。長久等待之后,醫生宣布我沒事了。然后他摘下面罩,上前給了我一個擁抱。我感覺到陌生人身體的溫暖,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醫生離開后,我聯系到之前那位英國職員。他告訴我,小蠻已經住進一家專為巴別病人開設的治療中心(具體位置不方便透露)。我可以聯系醫院負責人,根據他們安排的時間進行遠程探視。
iWall上出現了小蠻的影像。她沒有化妝,臉色比記憶中更加蒼白,頭發長了一些,酒紅色短發下露出黑色的發根。
除了略顯消瘦之外,她看上去并不像一個病人,然而她的眼睛里卻有一種惶恐的神色。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們第一次見面。那時候她還是一個胖胖的、有些口吃的小女孩,穿著褪色的花裙子,獨自坐在游戲室一角打量周圍嬉笑玩鬧的孩子,像一只膽怯的小老鼠。現在那種眼神又回來了。
我們沉默著相互看了一陣。然后我伸出手,在iWall上面敲了三下。
咚咚,咚。
那是我們小時候的暗號。無數個晴朗的清晨或者放學之后的傍晚,我們跑到對方家去玩兒,總是用這個節奏敲門:咚咚,咚。那是只有我們兩個才知道的暗號。
小蠻蒼白的臉上露出笑容,也舉起手來敲了三下。
咚咚,咚。
“好久不見,你過得怎么樣啊?”我開口問道。
“丄岡乜の厛L咔啊§滒”她回答。
醫生鼓勵我經常去跟小蠻說話。臨床經驗證明,多說話對病人的治療很有幫助。如果病人完全放棄語言交流,就會更容易陷入抑郁、絕望和神志不清中。
巴別病人的語言并非不可理解,只是需要更多耐心去傾聽、分辨、理解和模仿,就像學習一門外語。我錄下每一次談話過程,她的語音、神態、肢體動作,借用軟件分析,找出其中的規律,整理成詞匯表,反復背誦記憶。每次聊天,我都會發現一些新的變化。誤解和誤讀時有發生,有時候出人意料,惹得兩人一起捧腹大笑;有時候則帶來尷尬、沉默和不愉快。
有時候我們也爭吵,用彼此聽不懂的語言。我不明白她為什么突然對我吼叫,只好提高嗓門壓過她的聲音。我們指手畫腳,步步緊逼,血涌上額頭,雙眼變得通紅。她突然沖過來把iWall關掉。我呆立在那里,氣得渾身發抖,黑漆漆的玻璃表面只映出我自己變形的身影。我用雙手狠狠砸墻,像瘋子一樣尖叫,直到怒氣隨著疼痛流出體外。喘不上氣,我靠著冰冷的鏡面慢慢坐下來,把頭埋在雙膝中間。
為什么我們再也聽不懂彼此的話語,為什么不能夠像從前一樣?
Some?day?our?words?change?so?do?seasons.
我走進書房,打開書柜最上面一層,翻出一只陳舊的鐵皮盒。盒子里裝的盡是舊物件。那些搬了無數次家卻從來不舍得扔的東西,那些在影像時代早已淪為古董的東西:我們八歲那年夏天一起寫的童話故事、手繪新年賀卡、上課互傳的小紙條、作文課上她寫給我的評語、我借給她的書中留下的批注、課本上的涂鴉、夾在生日禮物中的卡片……
那是曾經只屬于我們兩人的世界,那是曾經只有我們兩人懂得的語言。
我想起很多年前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們倆并排坐在高高的屋頂上,她跟我說她的棉衣破了一個洞。傍晚光線早早就變得暗淡,卻又一直不肯真正黑下去。我向遠處望,看見一整個龐雜紛亂的世界,在我們腳下說著聽不懂的語言,像無邊無盡的汪洋。
我想起更早之前,我家附近有一小片綠地,我和小蠻常去那里玩耍。我們收集各色花籽播種下去,來年卻只看到牽牛花綠森森的藤蔓爬了滿地。
我想起曾經怕過的那一條大黑狗,總是蹲在院門里沖我們狂吠,現在它必然是老了、死了,不知道埋在了哪里。
我想起無數個夏日清晨,我沿一條小路跑去她家里玩兒,小路陰暗寂靜,泥土濕潤,草叢里的露珠總是沾濕我的腳。無數次我對自己說,如果有一天我選擇不走這條小路了,如果我像其他人一樣步伐穩重地走在水泥大路上,那時候我便長大了,可我真不愿意長大。
現在我的家、她的家,還有那些小路大路全都變成了荒廢的工地。
我想起我的夢,夢里我回到那些早已不復存在的地方,一些凌亂的片段,沒有邏輯,只有栩栩如生的種種細節,每一朵花每一株草,每一只昆蟲嗡嗡的鳴叫與細小閃光的翅膀,它們已不在這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存在,只在我夢中出沒。我總在夢中慢慢地、慢慢地走著,去找我的家,去找那些曾經玩耍過的地方,然而耳旁總有個聲音在說不,你已經從這里搬走了。突然之間我醒來,發覺自己在千萬里之外另一座城市的床上,我在夢中行走了千萬里。
我坐在滿地紙片中間,像小孩子一樣委屈地哭起來。
咚咚,咚。
不知從哪里傳來熟悉的敲門聲。
咚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
聲音不再響了,只有我獨自坐在空寂的房間里。外面天光漸漸暗下去,寂寥的金紅色燈火,浮起在城市天際線上。
我去洗手間用水抹了把臉,回來打開iWall,看見有幾條小蠻發來的消息。信息中沒有語音也沒有文字,只有幾張筆觸簡單的圖畫,像是匆匆忙忙涂抹而成。
第一張畫是兩個小女孩,一個短發,一個長發,面對面張大了嘴在吵架,從她們嘴里冒出許多意義不明的字符,像火星一樣四處飛濺。
第二張畫是兩個小女孩背對背,誰也不理誰。
第三張畫,小女孩中間有一張嘴,嘴上面打了個大紅叉。
第四張畫,兩個女孩頭上各自多出一對蜜蜂般的觸角,一些波浪般彎彎曲曲的線條,把兩對觸角連在一起。
(重要的不是說什么。)
(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彼此懂得。)
我明白自己錯在哪兒了。我把小蠻當作一個病人,我認為她的語言是有缺陷的,需要被治愈。我擔心不能與她溝通,擔心理解錯她的意思。我害怕她的病情繼續惡化,讓我永遠失去最要好的朋友。我要幫助她。我要拯救她。
但小蠻并不覺得自己是病人。她只是說話的方式與我不同,僅此而已。就好像別人都告訴我,小蠻小時候是個胖胖的、口吃的小女孩,但我卻從來不記得。我只記得跟她在一起度過的那些快樂時光,記得無數個清晨或午后,我們坐在僻靜無人的角落里一起講故事。我們總是迅速領會對方的意思,一句話沒說完,另一個人就搶先說出下半句。我們的語言交織在一起,像螞蟻揮動觸角打招呼。雖然我們說話的音調、節奏迥然不同,但我們懂得彼此。
那之后我們依舊保持聯系。我們會發照片和視頻給對方,也學會了用各種表情符號來聊天。有時候聊天軟件中的表情不夠用,我們就自己畫,這比語音聊天要方便得多,也有趣得多。我們仿佛回到了小學時,用自己發明的圖畫語言來寫小紙條,偷偷傳遞秘密情報:短發小女孩是她,扎辮子的小女孩是我;帶圍墻的房子是“學校”,戴眼鏡拿教鞭的人是“老師”……
我也逐漸了解到她在“百鳥之家”的生活。比起醫院,那里其實更像一個療養院。大多數人都找到了不需要說話便可以投入精力去做的事情:畫畫、雕刻、做手工、演奏樂器、園藝、田間勞作……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大家會花一個晚上的時間彼此陪伴。雖然每兩個人之間的語言都不一樣,但人們還是找到了各種各樣的方式來交流:手勢、表情、肢體動作、圖畫、敲擊聲、口哨聲、簡單的哼唱。仔細觀察這一切,使我一再為人類的適應力和創造力而驚奇,我真切地體會到,人是一種社會動物。
語音變亂,讓我們分散在地上,但我們依然想要在一起。
我也觀察到憤怒和憂傷、絕望和恐懼、爭執和沖突,那里并非總像田園牧歌一般和諧。這樣的生活,說不上來是更好還是更壞,或許只是與我熟悉的生活不同,僅此而已。
三個月前,我收到小蠻寄來的一張卡片。卡片里畫著六個月亮和六個太陽,下面是一座白色小屋,屋頂上落著五顏六色的小鳥。小屋旁邊站著一個白裙女孩和一個黑衣男孩。白裙女孩身邊還有一個長發女孩,手中捧著一枚戒指,旁邊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6月6日,我在“百鳥之家”舉行婚禮。你來當伴娘好嗎?)
小蠻的未婚夫來自臺灣,學法學的,在倫敦讀書時發病,住進“百鳥之家”,他們因此相識。這段愛情故事,我一直沒機會聽當事人親自講起。但我相信那一定很精彩。
(你喜歡他什么?)
小蠻舉起右手食指,伸進左手食指和拇指圈成的圓環里。
(性福?)
她大笑著,抓起身旁一個抱枕向我砸過來。
(不是?)
她再次重復那個動作,手指轉動,然后做了一個開門的動作。
(他是你的鑰匙?)
小蠻點點頭。
(嗯……那他的鑰匙,有多大?)
我們一起哈哈大笑,一邊笑一邊各自撿起身旁的抱枕,向著iWall上亂砸一氣。
有一兩次,小蠻邀請我一起討論婚禮細節,這讓我有機會看到他們兩個在一起時的樣子。他們用一種頻率變化豐富的鼻音配合手語交流,指尖不時在對方身上輕點,每一種觸碰都有微妙的意義變化,像兩只蜜蜂在花叢中舞蹈嬉戲,優雅、輕盈、敏捷、流暢。看到他們幸福地笑成一團,我不禁有些失落。
這是一個用他們兩人的語言建造的世界。亞當與夏娃的世界。
咚咚,咚。
我抬起頭,看見iWall那一邊的小蠻向我舉起手中的畫夾,上面是她為婚禮喜糖盒畫的各種設計稿。
(哪個好?)
我毫不猶豫指向南瓜馬車。
小蠻得意地大笑起來,一邊向身旁的未婚夫扮鬼臉,一邊在另外幾張圖樣上畫上一個又一個大大的紅叉。未婚夫無奈地聳一聳肩膀表示“聽你的”,然后他笑起來,我也忍不住大笑。
在每一種語言中,笑的意思都是一樣的。
我幫小蠻梳頭、盤發、化妝、熨婚紗。iRobot的手很靈巧,能夠準確傳遞每一個最微妙的動作。只可惜我的手有些笨拙。
我幫她修好指甲,隨即卻在畫什么圖案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小蠻想把指甲涂成黑色,上面畫上小小的黃色笑臉,我覺得這簡直是胡來,從沒見過哪位新娘子是這么畫指甲的。兩人剛剛開口叫嚷了幾句,就忍不住一起哈哈大笑起來。語言不通,雞同鴨講,誰也不可能說服誰。
我指一指她,雙手比一個很大很大的圓,然后張開手掌,左手指尖點住右手大拇指,其余四指握拳。
(今天是你的大日子。你是老大,你說了算。)
她自己畫了左手五個指甲,我幫她畫了右手。畫好之后,她滿意地把雙手舉在臉旁邊沖我做鬼臉。
(丑死了。)
(敢說我丑?)
(好好,不敢。反正你丑成什么樣子都有人娶你。)
(打你哦!)
(打不著!)
她撲過來撓我。從小到大每次說不過我,她都會出此下策。透過感應服,我感覺到腰間癢死了,我笑得喘不上氣。
(我送你的禮物呢?)
(在這里。)
她從抽屜里拿出一只扎緞帶的盒子,這是我一周之前寄給她的。
(打不開?)
(誰知道你搞的什么鬼,快點打開!)
(好好,女王大人。)
我扯開緞帶,盒子上浮現出一張嘴、一把鑰匙和一個問號。
(口令?)
我把盒子捧到嘴邊,輕聲說道:
“小蠻,祝你幸福。”
她聽不懂這句話。
但是那一瞬間,相隔著半個地球,兩顆淚珠同時從我們兩人的眼角掉落下來。
盒子應聲而開,里面是一條細細的鉑金項鏈,墜子是小小的鑰匙形狀,上面鑲滿碎鉆。
我繞到她身后,幫她戴上項鏈。化妝鏡里映出兩個身影。
(別哭,別哭,快把眼淚擦擦,不然妝都花了。)
(好看?)
(當然,今天整個世界上你最好看。)
(真的?)
(真的。等一下你絕對把他美哭了。)
(哈哈,那你可得拍下來。)
(沒問題,全程錄影,留給你們將來的孩子看。)
(我可不想生孩子,萬一小家伙跟我們兩個都說不到一起怎么辦?)
(你想太多了。將來的事情,將來再說。)
鐘聲響起。我掀開落地窗簾一角,看見陽光灑在茵茵綠草上,賓客們已在位子上等候。幾只鳥雀落在草地中央,一步一啄,然后歡快地拍打翅膀飛到天空中去,灑落一地銀鈴般的啁啾。
這真是一個好日子。
據說,今天主持婚禮的是一位真正的神父,也是“百鳥之家”的成員,一會兒他將用啞劇的形式來“表演”結婚誓詞。
(無論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是貧窮。)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語言,就是我的語言。)
(你準備好啦?)
(有點兒緊張。)
(緊張什么,有我在。)
她推開門,深吸一口氣向前凝望。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回過頭向我舉起手里的捧花。
(你可一定得接住啊。)
我雙手同時比出“OK”的手勢。
鳥兒在屋檐下嘰嘰喳喳唱著。芬芳的夏日陽光中,我陪伴我最好的朋友,面朝整個等待她的世界走去。
【責任編輯:楊 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