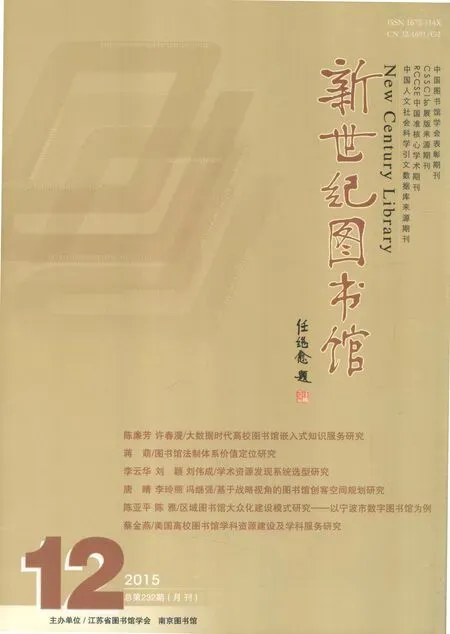方寸之間,東西之別
——從藏書票與藏書印看東西方書籍文化的異同
李曉源
方寸之間,東西之別
——從藏書票與藏書印看東西方書籍文化的異同
李曉源
藏書票與藏書印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是作為藏書所有者的標記,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論文從藏書票和藏書印的功能演變,形式特點,使用規范以及產生原因等角度進行闡述,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東西方書籍文化的不同取向與觀念上的內在差別。
藏書票藏書印書籍文化藏書家
藏書票與藏書印都因藏書而生,與書籍和藏書者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僅以賞心悅目的藝術造型帶給人們一種美的享受,而且所表現的書籍文化也具有深遠的人文意象。藏書票縮現了西方的歷史文脈與人文情愫,而藏書印則印證了中國文化的特質與精神內核。
1 東西方藏書家的不同選擇
同為愛書之人,為何西方的藏書家選擇了藏書票而中國的文人墨客選擇了藏書印呢?這主要與東、西方書籍的裝幀形式有很大關系。西方的洋裝書用紙堅硬厚重,表面粗糙滯澀,能夠雙面書寫和印刷,并配以硬殼紙為封面。這種質地的紙不便于蓋印章,卻非常適合粘貼藏書票,就像在堅硬的墻壁上粘貼一幅精美的圖畫,既平整而又易于保存。而與之相反,中國的古籍以傳統線裝為裝幀形式,講究用紙柔、薄、綿、韌,閱讀時常卷成軸狀,便于把卷吟誦,如果貼上藏書票,既有礙于單手持卷,而且兩種不同質地的紙張粘在一起,形態上格格不入,工藝上干戈難調。而印章和中國古籍的用紙與雕版刷印的工藝卻是同出一轍,綿軟的宣紙與鈐下的朱泥呈現出一種工藝淵源上的默契與色彩配比上的鮮明。
2 藏書票、藏書印的功能及其演變
2.1 表示歸屬權
初始,藏書票和藏書印都是藏書者用以表示對于書籍的所有權。五百年前,德國人給自己的藏書加上一個寫有“某某藏書”字樣的紙簽,以此表明書籍為誰所有,這便是最初的藏書票。藏書票上通常有拉丁語Ex libris,為“予以藏之”之義。1730年德國一家修道院的藏書票上有這樣一句話:“我是維森布倫修道院的合法財產。注意!依法把我還給我的主人。”[1]以擬人的手法提醒人們這本書的歸屬權。無獨有偶,在中國唐代,唐太宗曾自書“貞觀”二字并命玉工刻成聯珠印章[2],加蓋在內府藏書之上,以示這些珍稀典籍為皇家藏有。歷代文人墨客也會在自己的藏書上鈐印姓氏、別號、書齋、堂名等藏書印章以示所有權。因此,有時一本流傳久遠的古籍善本,輾轉易主,上面的印章少則幾個,多則數十枚。從這些累累藏印之中便可以得知這本書的遞藏序列,了解其潛在的庋藏歷史,同時也成為鑒定此書版本源流,考證藏書者生平事跡的一條重要史證線索。
2.2 家族的榮譽與訓誡
西方藏書票圖案多以家族紋章徽志為主要內
容,是家族榮譽的象征。那時在歐洲人們非常講究血統,紋章不僅反映了書籍第一代主人的身份,而且使書籍所有權在家族中作為遺產傳承給下一代[3]。例如創作于1470年的《天使捧紋章》書票據考證就是勃蘭登勃家族的紋章藏書票,臺灣藏書票研究家吳興文稱它為“紋章藏書票的鼻祖”[4]237。在歐洲徽章是貴族的標志,有一整套嚴格的紋章制度,如果不了解紋章學常識,是很難知曉紋章式藏書票其中的含義。比如英國第一位憲政君王喬治五世的藏書票,以一頭戴著王冠的獅子和掛著鏈子的獨角獸共同捧著一面勛章的王室紋章為圖案。勛章的左上和右下是三只獅,頭向右、舉起右前足行進,代表英格蘭;右上獅以后腿撐地,全身躍立揚起前爪,代表蘇格蘭;左下是代表愛爾蘭的豎琴,整體剛好構成大不列顛與愛爾蘭王國[5]。從這枚典型的紋章藏書票中,人們能夠深切感受到英國王室至高無上的權力。以此可見最初的藏書票在社會上還是威信和身份的象征。
而中國的藏書家似乎更注重對子孫的訓誡,希望自己收藏的書籍后人能夠珍視。既有“傳家永保”“子孫勿失”四字款的藏書章,也有字數較多,諄諄教誨子孫的藏書印。明代藏書家“汲古閣”主人毛晉,有一方56個字的大藏書印章,印文為“趙文敏于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如何,后人不賣,將至于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屋,當念斯言,恥非其有,無寧舍旃”[6]10。又如清代藏書家王昶,其藏書印記云:“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極勞勖。愿后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墮。如不材,敢棄置。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庵傳誡。”[7]216還有文字最多的藏書印,即明代王祖嫡錄司馬光誡子惜書的一段話,共計223字,此印文云:“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余卷,公晨夕取閱,……,汝為志之,信陽王氏四部堂識”。在這些藏書印的內容里,既有長輩對晚輩諄諄教導,也有對不屑子孫的謾罵威脅,從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藏書家對后世子孫的苦心與無奈。正如葉德輝先生所說“每嘆子孫能知鬻書,猶勝于付之奚媵覆醬瓿褙鞋襯”[7]217。
2.3 個人的精神世界
18世紀之后,隨著歐洲教育的普及和出版業的發展,藏書不再只是貴族和教堂的專屬特權,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也可以擁有屬于自己的藏書。20世紀初,藏書票從貴族化轉向平民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平民請設計家制作和使用藏書票已很普遍。藏書票的內容也開始從紋章型向圖畫型轉變,不再只是家族財富和權勢地位的象征,更多反映的是藏書者的興趣與愛好,藏書票更趨向個性化,也更追求藝術的表現力。從單純的風景人物、飛禽走獸、花鳥蟲魚等圖案,到關于表現讀書、書房的場景,還有寓言故事和神話傳說的畫面,題材十分廣泛。比如美國著名目錄學家喬治·薩根特的藏書票中,不僅有票主平時使用的古書、卷紙和羽毛筆,還有自己家鄉的老宅,將記憶中美妙的片段挽留在方寸之間[8]57。還有歷史學家克里森將本人晚年的學者形象置于書票之上,背后的地球儀,擺滿藏書的書架和桌面上零散的文獻參考書,正是他一生“活到老學到老”的真實寫照[8]58。至此藏書票和藏書印趨同于表達藏書家個人的精神世界。
中國藏書家多以一些詩文名句作為印文,以此表現自己的志趣。如明代文學家許自昌的藏書印分別有“美人兮天一方”“吟詩一夜東方白”“半畝梅花”[9]。又如清初藏書家蕭夢松,有一印曰:“杜門謝客,齋居一室,氣味深美,山華野草,微風搖動,以此終日。”[10]何等的超然物外,飄逸灑脫!另有表達治學勤奮的勵志藏書印,其文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需學也。非學無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怡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反也。”[11]更有比較極端的表達,如袁克文的“與身俱存亡”藏書印,有一種玉石俱焚的感覺,過于慘烈。倒是雍正皇帝的“為君難”,似更值得回味。
2.4 藝術品
隨著人們對藏書票和藏書印的關注越來越多,藏書票和藏書印被抽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品。19世紀下半葉,藏書票迎來黃金時期,出現了許多藝術珍品,包括丟勒、霍加斯、馬奈、畢維克、比亞茲萊、波納爾、基爾希納、馬蒂斯、高更、科柯施卡、畢加索、埃舍爾、肯特等藝術家都曾參與創作。既有畫家一幅幅手繪的作品,也有版畫家創作的藝術品。特別是版畫藏書票的種類繁多:根據制版工藝,有凸版(木塊雕版印刷)、凹版(銅版印刷)、平版(膠印、石印)、漏版(絲網印刷);根據印刷色數,有單色印刷和雙色、多色套印。精湛的繪畫藝術和巧妙的設計理念使藏書票作為藝術品收藏的風尚開始在歐洲流行。1966年7月28日,由歐洲各國的藏書票愛好者成立了“國際藏書票協會聯盟”,簡稱FISAE[4]238,現已發展到包括德國、西班牙、法國、意大利、荷蘭、丹麥等四十多個國家,會員上萬人。盡管藏書票的藝術性越來越強,實用性逐漸衰退,但是與“書籍”“閱讀”有關的創作素材仍然是藏書票中一個永恒不變的主題。
在中國,藏書家對藏書印也十分講究,經常會請一些制印名家為自己制印。如著名國畫家、金石家陳師曾先后為魯迅刻過“樹人所藏”“俟堂”等5方印章[6]10。由于藏書印在印學中與經典文本息息相關,必須嚴謹周正、端莊雅致,可以發揮的空間有限,所以藏書印不僅要求內容富于深意,而且要求形狀精巧別致,尺寸以不超過書籍行格為佳;筆畫忌諱毛糙,筆體摒絕率意,整體要求呈現出珠圓玉潤的典雅型視覺效果。例如,陳巨來所治的圓朱文印“上海圖書館藏”,筆體線條流暢,古風純然,堅挺有力,靈動之氣充滿印面。陳巨來自己為書齋所治的滿白文印“更生藤齋”,筆畫豐碩,生字上部留紅極寬,其余排布均勻,可謂“緊處密不透風,疏處寬可走馬”。還有隨性印,如宋代賈似道有印文為“悅生”的葫蘆形藏書印。另有比較特殊的藏書肖像章,如袁克文有一枚,印面主體是袁氏潛心展讀線裝書的情景,上部是“皕宋書藏主人廿九歲小景”十一個篆書小字[12]。從宋代開始,許多鑒賞家搜集名家篆刻的精品印章,編印成冊,集成具有獨立藝術價值的印譜,供大家研究、鑒賞和臨摹。其中大量的閑章與肖形印在此就是作為“花押”或“藏書印”而存在的,例如: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養正樓鈐印本《孫氏養正樓印存》,其中肖形印占了14枚,古器物形6枚,人物2枚。藏書印藝術性的體現由此從文字向圖形轉化。
3 藏書票、藏書印的表現形式
盡管藏書者使用藏書票和藏書印的目的是相同的,但是它們卻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形式,而且代表著兩種人文氣質。
首先,從“社會分工”上來看,藏書票多以圖形語言來表達,利用的是版畫藝術制作的工藝,多以私人委托專門藝術家為之定制而成。而藏書印多以文字形式來表達,運用的是篆刻藝術手法,雖然也有授意,他人定制的,但更為普遍的是藏書家本人設計制作的藏書印。因為中國的傳統文人本身就有著書法家、學者、畫家等多重文化身份,反映出近代西方學科的專業化與東方通才教育的差別性。
其次,從“媒介效應”上來講,文字與繪畫也呈現出不同的媒介效應。西方的藏書票所呈現的多為表象的圖形語言,是具象的熱媒介,有較強的視覺沖擊力和感染力,讀者僅需要“觀看”就會被蘊含的文化感受。與之相比,東方的藏書印所呈現的多為表意的文本語言,是抽象的冷媒介,有較強的參與力和深入感,讀者需通過“思考”揣測印中的文化意境。
第三,從“心靈接受史”上來論,對于讀者,藏書票的文化門檻較低,無需要有很高的文字、文學、文化修養就能感受其精神面貌;而藏書印的文化門檻較高,需要有很高的文字、文學、文化修養方能領會其精神內核。這是因為圖像自身是歷史記錄中表達方式最直觀的,而文字本身是保存文化的工具,其本性是最保守的[13]。
第四,從“符號學”上審視,圖像語言為主的藏書票傳達的是感性的“模糊信息”;文本語言為主的藏書印傳達的是理性的“準確信息”。模糊信息的圖像所具備的開放性正好是西方文明的特征,準確信息的文本所具備的閉合性正好是東方文化的特質。
最后,從“修辭學”上分析,雖然都有方寸之間,氣象萬千的意境,但是西方藏書票的藝術特色是圖文并茂、情景交融的,多以具象思維成就表達形式,與西方拉丁語系的表音文字在音畫互動中構成修辭上的“蒙太奇效應”;而東方藏書印則多以文字為基礎,將文字筆畫的線條幻化于萬千,構成朱白對比,以文為本,以義取象,展示出抽象形式之美,與東方象形文字在形意互見中構成修辭上的“互文效應”。兩種文化基因在共同目的的驅使下構筑出別樣的書籍文化景觀。
4 藏書票、藏書印的使用
藏書票的規格通常在10~20cm2之間,一般浮貼于書皮或扉頁上的右上角或中央。藏書票的尺寸大小與書籍之間的關系是有一定規律的。如果一部尺幅很大的書籍配一幅很小的藏書票,或者藏書票尺寸過大,占滿整個扉頁,顯然都很不合適。藏書票的內容與藝術風格更需要與書籍相配,如果選取恰當,藏書票不僅對書籍起到裝飾作用,更似為書籍打開了一扇小小的天窗,開辟出另一個神秘的時空,樂趣無窮。
另一方面,藏書印在書籍上鈐印的位置也十分講究。有鈐于扉頁著書人名下,或正文初頁板框右上方天頭處,或目錄頁下,也有鈐于末頁左上角或卷終結尾處。此外,在整個鈐印過程中,印泥色明朱厚,紙張綿軟細膩、技術嚴謹熟練,三者默契的結合,才能達到印面清晰端正的完美效果。如果藏書印本身明麗規整,位置選蓋的恰到好處,不僅展示出書主人對書籍的恭敬之心和自身的文化底蘊,也是對書籍的一種裝飾。
5 藏書票、藏書印的象征意義
藏書票和藏書印作為書籍所有者的標記,不僅成為書籍風雅的裝飾,而且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東西方文明下不同的書籍文化取向。藏書票的形式圖文
并茂、風格多樣,有的清新淡雅,有的寓意深刻,有的莊重大方,有的輕巧可愛,通過從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的古典哲學或詩歌中獲取畫像(例如法國高蹈派詩人及象征主義派詩人在其作品中的插圖),或者利用主題雙關及組合各種不同元素構成某種文化內涵,從而能夠直觀地反映書籍文化的內容。藏書票作為外在附著性、浮貼式的文化標記裝飾之物,貼用時往往不全部貼死,而只在書票的上方點膠活貼,這種輕便靈活的做法,可以方便日后取下更換或是移用于別的書籍,可以多次使用。一本書籍在不同時段可以更換不同風格的藏書票,但同一時段卻只能規約于一枚藏書票,折射出西方文化中開放、外向、直接、崇尚獨立和自由的人文精神。
而藏書印是內在嵌入性、印記式的文化標記或銘志之物。雖然一枚印章可以反復鈐用,然而一旦鈐印之后,印文即與書籍融為一體,成為永久烙印,伴隨書籍壽命始終而不容更改。后人收藏也只能在前任主人的藏書印上方空白處,次第蓋上自己的印章,這種牢靠穩定的做法,可以讓后人依照藏書印的次序,辨識出書籍傳承的歷史線索。另外,由于中國的文字屬于象形文字,除了文字的內涵之外,字體本身也構成一種象征意義。藏書印通過字義與字形“互文”的方式來反映中國藏書家的一種價值觀,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印章來銘屬一本書籍,這與以不同的漢字字體來規約一種文義的文化現象相似。正如中國文化趨向于“和而不同”——意義相和而符號形態各異。中國文人每次用印都異常嚴謹審慎,要靜讀其書卷內容,玩味其印文字義,考究其字體形態,精審其印面大小,講究其印泥色澤,然后才用印規定位,在重壓之下鈐留一枚銘文般的朱泥紅印,這一系列頗具儀式感的身心狀態,不僅對應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戲劇性體驗,而且賦予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契約式體證,其中還包含了“一沙一世界,剎那即永恒”的宗教感悟,成為中國文人生活的一種寫照,也代表了東方文化的內斂、自省、投入、中和及其含蓄之美。
6 余論
藏書票和藏書印雖然具有不同特點,但是都表達了藏書者對于書籍一份真摯的情感。這就像東西方之間的文化雖然有很大差異,但是人們對知識的熱愛與追求卻是一樣的。如果書籍是一座知識的殿堂,西方的藏書票就像是為這座殿堂鑲嵌了一扇具有美麗風景的窗戶,讓愛書者的心靈與書內的風景相通相映;而中國的藏書印卻是愛書人在廟堂之上奉入的虔敬貢品。用“禮儀性”融入廟堂,并化為廟堂中的一部分,讓藏書者、傳承者、愛書者、讀書者皆能登堂入室,羅列其中,共瞻文化之盛。既構成薪火相傳的烙印,也成為文脈相繼的坐標。藏書票反映的是個人與作者的關聯,而藏書印則反映出讀者群與文本的融匯。基于文本內容,東西方有不同的文字屬性,在語素上前者是外向型的發現,后者是內向型的重審。鑒于文脈載體,東西方有不同文人心緒,在語態上前者是游離性的船舶,后者是駐泊性的港口。歷于文明進程,東西方有不同的文化使命,在語境上前者是通道式的窗口,后者是漸進式的地標。對此我們不應苛求于古人,反倒應該去理解文化現象背后的深層次成因,只有充分理解東西方文人對待書籍各自的態度,才能更充分發掘書籍文化的魅力,才能更妥帖地服務于當下的閱讀生活。
[1]江兆云.藏書票鎖語[J].金融時代,2013(03):41-42.
[2]奚椿年.書趣[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93-95.
[3]馬丁·霍普金森.藏書票的故事[M].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12.
[4]李艷萍,賈琨.淺析藏書票藝術的歷史及當代發展[J].文藝研究,2012(05):237-238.
[5]吳興文.我的藏書票之旅[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187.
[6]流云.名人藏書印章[N].江南時報,2009-01-11(10).
[7]葉德輝.書林清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16-217.
[8]子安.藏書票之愛[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57-58.
[9]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674-677.
[10]范景中.藏書銘印記[M].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56.
[11]獻洲.藏書章記趣[EB/OL].[2006-09-04].http://blog. 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594350&Post ID=6658785.
[12]王愛喜.中國傳統私家藏書印[J].檔案與建設,2002(04):48-49.
[13]哈羅德·伊尼斯.帝國與傳播[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30.
李曉源西北大學圖書館館員。陜西西安,710127。
Difference of the Book Cultur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Ownership Stamp and Ownership Seal
Li Xiaoyuan
Ownership stamp and ownership seal reflec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but they are considered the book ownership of the mark and the same function.This paper introduces evolvement of function,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 specification,origination of ownership stamp and ownership seal,which from one side reflected the book culture’s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and Westorientation and on the conceptof the inherent differences.
Ownership stamp.Ownership seal.Book culture.Bibliophile.
G256.1
2015-07-01編校:方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