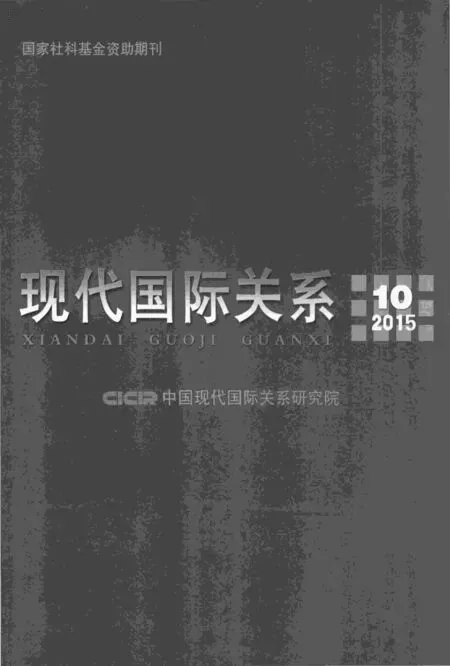現代院論壇“跨太平洋安全:和平共處 包容發展”綜述
付 宇 孫成昊
10月12~13日,由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主辦、主題為“跨太平洋安全:和平共處 包容發展”的“現代院論壇2015”在京召開,來自現代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社科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防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以及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俄羅斯卡內基研究中心、美國笹川財團、日本再建基金會、韓國東西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緬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等50多位中外學者與會,探討了當前亞太地區所面臨的挑戰及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框架的構建。論壇共分三大議題:“‘一帶一路’與地區合作”、“跨太平洋安全:挑戰與應對”、“新型國際關系與跨太平洋安全合作的架構”。
(一)“一帶一路”與地區合作。現代院副院長傅夢孜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出臺與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幾乎同步,是立足周邊又超越周邊的戰略設想,但其主要還是經濟方面的倡議,而非一些西方學者所說的出于中國政治和戰略的需要。而“一帶一路”要全面推進,也要通過有關國家間的共商、共享、共建,真正實現“一帶一路”與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對接。“一帶一路”在推進過程中,將長期面臨規則風險、沿線國家社會政治風險、恐怖主義等地緣安全風險,很難一蹴而就。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李侃如指出,“一帶一路”引發國際社會關注,主要是因為大家并不了解其具體內容,特別是中國尚未對此做出清晰全面的闡釋。“一帶一路”囊括了諸多雄心勃勃的項目,會產生很大的地緣影響,人們關注中國將如何確定“一帶一路”的時間表、對外投資和援助所遵循的標準等。俄羅斯卡內基中心高級研究員加布耶夫認為,“一帶一路”仍面臨許多課題,例如如何與各國發展戰略銜接,以及很多項目在經濟上的可行性不強,如何保證相關國家都能獲利,同時深化各方政治互信和溝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前東盟秘書長王景榮認為,由于南海問題影響,中國和東盟國家進一步加深關系可能會受到影響。2015年11月中國領導人將參加“東盟+1”會議,“一帶一路”是重要議題,希望能更深了解中方推進該倡議的具體安排。
(二)“跨太平洋安全:挑戰與應對”。現代院院長季志業指出,從安全領域看,整個跨太平洋地區正隱約形成兩個陣營。一方面,美國積極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加緊在該地區構建新的軍事安全網絡,加強和調整同盟關系。在美推動下,日本通過新的安保法案獲取集體自衛權,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美日菲澳等盟國間的合作全面強化。同時,美還在這個地區建立新的軍事伙伴關系。另一方面,中國也在加快軍事現代化步伐,大力構建維護自身安全的設施和網絡,包括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加緊鞏固中國自身所掌握的南海島嶼,中俄間的軍事合作也在加強。從經濟領域看,盡管中美雙邊經貿總額還在增加,但雙方深度合作的速度卻在放慢,原定雙邊投資談判不斷推遲。在美推動下,TPP談判協議基本達成一致。同時,中國也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主動構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使這個地區隱約出現了兩大經濟合作體系并存的情況。
與會專家還就美國“亞太再平衡”、南海問題、中美關系等熱點問題展開了集中討論。現代院院長助理胡繼平指出,美國“再平衡”戰略的內容包括很多方面,但目前為止軍事方面的措施仍最主要,影響也最大。過去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沒有采取過軍事行動,但是這種非常克制的做法事實上既沒有得到大國和國際輿論肯定的評價,也沒有得到相關爭議國家善意的回應。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指出,中東亂局、“伊斯蘭國”崛起和烏克蘭沖突等牽扯了美國的精力和資源,使其難以全力在亞太進行全面的戰略部署。美國正進入大選年,不會在對外關系中主動采取重大行動。2017年如果民主黨上臺,美國將在國際機制和安全架構方面采取更多行動,如果是共和黨政府上臺,可能會在加強軍事力量和安全同盟方面加大力度。
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朱鋒表示,解決南海問題上的分歧一定要重視歷史,不梳理歷史就不可能繼續前進。緬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席、總統首席政治顧問哥哥萊指出,南海問題是地區最棘手問題,必須從合理的歷史角度分析爭端根源,避免引發所謂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東盟需要看到,南海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符合其最佳利益。東京財團理事長、前防衛廳次官秋山昌廣認為,目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活動和主張只是從狹義角度堅持國家利益,并不符合中國廣義上的利益,如果中國能促進國際合作將更有利于地區和平與穩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認為,用軍事手段解決南海問題不符合中美兩國利益,中美應采取一系列外交和其他方面努力,重組本地區利益,使其更有利于開展合作。
中國國防部外辦國際安全合作中心主任周波認為,目前中美關系尤其是軍事關系展現良好勢頭,但雙方仍需盡可能開展更多合作,包括戰略交流、加強危機管理、擴展合作領域以及開展更多聯合軍演。哥哥萊認為,中美應減少安全領域的緊張關系,促進其他領域的合作,進行全面經濟對話,同時雙方領導人的政治意愿非常重要。丹麥皇家防務學院戰略研究所副教授萊斯洛特·奧德加德表示,歐洲希望中美合作不僅限于氣候變化問題或反恐,也應包括經濟領域。中國的倡議應該成為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源泉,而中美倡議的結合可以幫助解決安全方面的問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休·懷特認為,中美戰略競爭主要是源于雙方對亞洲發展以及對在亞洲秩序中的作用有著不同理解,美國希望維持主導權,中國則希望地區秩序不再以美國主導權為基礎,從而提升中國的地位和作用。事實上,美國雖然沒有衰落,但中國在崛起,導致大國格局發生變化。所以,如果不對權力平衡進行調整就不應指望中國接受目前的局面,而調整過程應該盡可能透明。
(三)跨太平洋安全架構。季志業強調,亞太形勢的深刻變化,必然要求各國政府和戰略界與時俱進,創新現有的跨太安全架構和理念。美國笹川和平財團理事長、前美國情報總監、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萊爾表示,地區需要新的安全架構,必須依靠行動才能改變現狀,特別是中方要積極采取措施,在經濟合作和政治上都有一定妥協。包道格表示,美國在本地區有自己的安全聯盟,在多數情況下帶來了和平與繁榮,這對美國是好事,也使本地區國家節省很多軍費開支,美國將繼續維持這樣的安全架構。同時,美國限制中國的舉動是危險的,起了反作用,最終徒勞無益。中美之間不一定會出現“修昔底德陷阱”,兩國應找到解決辦法,建立范圍更廣的安全架構,幫助解決相關問題。休·懷特認為,地區安全架構穩定的基礎是國家間穩定的關系,特別是最強國家間穩定的關系。因此,未來跨太安全架構必須以中、美、日穩定的關系為基礎。現代院世界政治所執行所長王鴻剛表示,跨太安全架構旨在解決五大問題:一是安全理念的滯后;二是安全機制的破碎;三是安全熱點問題的集中發酵;四是安全公共產品的缺乏;五是安全爭端對經濟合作的阻礙和限制。布萊爾認為,建設跨太安全架構前可以先建立四種行為規則。一是提前通知重要事項,避免讓對方吃驚;二是強調經濟行動,中國的亞投行倡議、“一帶一路”倡議,美國的TPP都是非常積極的倡議,通過這些倡議完全可以實現共贏;三是軍事行動方面必須小心謹慎;四是政府完全可以控制住海上或空中危機,因此各國要共同進行調查,并基于調查結果采取共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