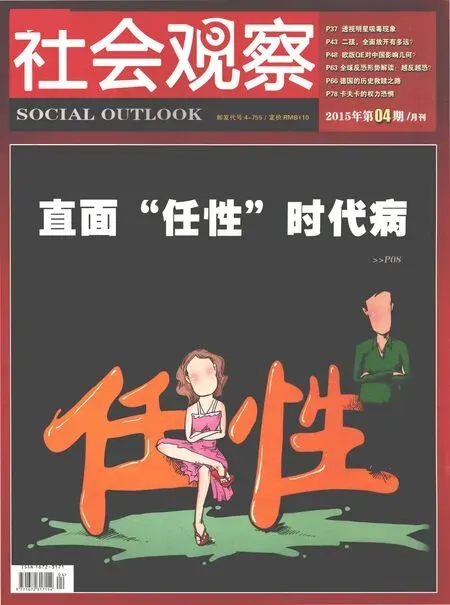中國是否步入“橄欖型”社會?
文/聶慶軼
中產階層多年來一直是個引人注目的議題。政府部門或學界很多人把是否能構建大量的中產階層,形成“橄欖型”社會,作為社會成熟、穩定的標志。然而,誰是中產階層、中產階層界定的依據是什么、我國是否已形成中產階層?對此,一直是有歧見的。
判斷中產階層的依據只能是收入
近年來,判斷分析我國中產階層及其收入狀況主要有兩個理論。
一是“職業分層論”。有人根據職業將國人劃分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從業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無業失業半失業等十個階層。類似的還有“六階層說”、“九級別說”等。根據不同職業歸類分層并據此判斷其收入狀況,是一種方便的、直觀的方法。例如公司白領和車間藍領,他們各自的工資標準、微信交際圈,甚至作息時間等均有差異。同一職業所具有的共同點,經潛移默化會使他們形成類似的偏好、習慣甚至價值取向。某一職業群體容易形成追求自己利益的共同主張,甚至成為某種社會力量。但是作為社會經濟政策,尤其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分析制定基礎,“職業分層法”的弊端是明顯的。

福州第22屆住交會上,一參展商打出“中產階級住房領跑者”概念吸引購房者。 圖/東方IC
第一,除了無業失業階層,同一職業階層內部的收入差距巨大。例如經理,且不說大公司與小公司,即使都是小公司的經理,由于行業、地域、能力等不同,在收入上也有天壤之別。
第二,以職業作為分析收入差異主要依據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方法。在奴隸社會,奴隸是奴隸主會說話的工具,勞動果實全歸奴隸主所有。在農牧業為主的自然經濟社會,地主擁土地資源,農(牧)民耕田放牧謀生。這兩種社會中人們的職業身份往往是通過律法規定和社會習慣限定的。一個人的職業就是其社會地位的標志,收入多少的反映。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職業不再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中產階層主要不是指某種職業階層,而是指擁有社會上中等收入的階層。除去戰亂或經濟管制時期,各個職業之間有溝壑,但沒有政治、社會制度上障礙,職業地位更多是由個人性格、人生態度、努力程度、機會把握、社會關系等決定的。現實生活中我們都看到一個英語教師嬗變為我國首富之一的“馬云神話”。
第三,今天單憑某種職業很難判定其在整個社會中是高收入還是低收入。最典型的是今天城市中服侍照顧嬰兒產婦的“月嫂”。她們吃住在主人家,還可以領取1萬元上下的月薪,如是聲譽好的“金牌月嫂”,月薪可以達到2萬元上下,比我國絕大多數中小私營業主、廠長經理或白領的凈收入高,甚至比一個部級官員的名義工資都高。她們是保姆,可能沒有工作單位為她們繳納“五險一金”,但我們能夠說她們不能進入中產階層嗎?有位名教授還講,“一些出租車司機比我收入還高,但他是工人,我是中產”,這是等級社會傳統思維在作祟。如果僅僅認為私營業主、管理干部、教授等專業人士是中產階層,那么從社會結構來說,中產階層永遠不能成為社會的多數,橄欖型社會永遠無法形成。
二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論”。有人認為,我國現在社會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結構”。兩個階級是指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一個階層是指改革開放后形成的新階層,即私營業主階層、雇傭勞動者階層、職業經理階層等,并強調“私營業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工農階級是勞動階級,新階層掌握擁有資本等生產要素,因而形成“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來的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這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但它與目前我國市場經濟現實距離太遠。
第一,資本只是貨幣等財富的一種存在形式。某人擁有100萬元,他用于購買一套住房改善生活是消費,用于去開辦一個小廠就是投資資本,這都是貨幣的不同運用,今天在階級、階層性質上加以區分沒有意義。
第二,一個農民在城市打工掙了些錢,然后回鄉開個網店雇傭七八個員工,以他的職業變化來區別他是勞動階級還是運用資本獲取經濟利益的新階層,在社會分層中沒有意義。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為他人打工是勞動,辦個工廠進行管理也是勞動,都為社會作了貢獻。把個人不同的勞動預設為對立的性質,再研究它們的矛盾是虛幻的。
第三,一個有資歷的經理在市場上既可以被國有企業,也可以被私營企業雇傭,這只是某經理對收入、職業前景等綜合判斷后的選擇,不會是對階級、階層的選擇。從獲得收入高低角度看,一個人的貨幣是買房子或辦個實業,一個人是為他人打工或自己開網店,是為國有企業或為私人企業當經理,孰多孰少,是不一定的。一個人的資金或勞動力等資源運用方式不能決定其收入高低,也不能決定其是否邁入中產階層。
所以判斷中產階層的標準只能是一個,那就是收入水準。只要一個人的收入在一個國家中處于中等水平,他就是中產階層。這里的收入包括:勞動收入如打工、投資、經營管理、發明創造等和非勞動收入如饋贈、遺產等兩種不同性質的收入,也包括現金、實物、有價證券和經濟利益等不同形式的收入。
中產階層是個地域概念
國家間有收入水平或人文發展的分析指標及相應排名,但是,沒有世界統一的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標準或指標。權威資料上的多個指標顯示我國目前在世界上屬于中等收入國家。
在表中,以每個就業者創造的GDP為標準,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是12041美元,我國是12593美元;人文發展指數中等收入國家是0.630,我國是0.687;居民人均最終消費中等收入國家是1229美元,我國是949美元,略低。考慮到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農村土地等資源商品化不足等因素,綜合起來可以科學地判定,我國是一個較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

中等收入國家的相關指標
但是,全世界的權威專家以及各種統計資料中均沒有制定世界性的、統一的、針對各個國家的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指標。這有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如以高收入國家為標準,例如 2013年人均國民收入統計,排名第1位的摩納哥是183150美元,則其余國家包括美國人都是低收入者;反之,如以低收入國家為標準,例如排名第162位的巴基斯坦是1050美元,則其余國家包括中國人全是高收入者。這不科學,在邏輯上存在“收入狀況悖論”。第二,假如以個人或家庭擁有的實物量為標準,更缺乏可比性。這不僅因為是經濟發展狀況,更因為受到地理、氣候、人口等多種因素制約,很難尋找到恰當的指標商品。如果是冰箱,炎熱與寒冷地區需求并不相同。如果選汽車,它既滿足生產經營活動需要,也提升生活享受的檔次,較能體現一國經濟發展和國民收入的狀況。據估計,美國每千人汽車擁有量約800余輛,中國約100輛,印度約20輛。美國中產家庭一般擁有兩輛及以上的汽車。但是美國有3.2億人,中國約有13.6億人,印度約有12.6億人,如按美國的水準要求中國和印度,哪怕擁有量只是美國的50%,也將造成本國道路難以克服的困難。暫且不論錢的問題,堵車、霧霾等環境成本也將是無法承受的。
所以,中產階層只能是個地域的、相對的概念。美國、中國、印度在本國都有中等收入的中產階層。雖然他們的富裕程度、資源占有狀況存在巨大差距。以高收入國家的標準衡量中、低收入國家的中產階層是不科學的;同時,在中、低收入國家中要求達到高收入國家標準,才確認是中產階層,只能是虛無的假設,并會誤導社會輿論、扭曲社會心理、干擾制定合理的社會經濟政策。
正確認識中產階層很重要
我們把擁有中等收入者均歸入中產階層,而且從地域角度明確其是個國內概念,從收入角度明確其是個相對概念。對這個概念如何理解,不單純是個人看法或學術觀點,而是深刻地影響社會輿論,浸潤社會經濟政策的制定、宣傳。
幾年前,一些有資質的機構提出6~50萬元是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年收入標準(2012年按五等分法統計,中等收入戶一年約7萬元),提出我國有23%的人已跨入中產階層,引起輿論嘩然。有人說,自己一不小心被變成中產階層;有人耍酷似地說,6萬元城市租房都不夠,怎么成了中產?也有人貌似全面地說,應等到多數人生活狀態良好的時候才能有中產,而且關于中產階層的評價標準應該多元化,兼顧財富、權力、聲望等。對23%是中產,有的媒體用“您有惶恐的資格嗎”作為標題來進行討論。另一方面,當知道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制定的印度中產階級標準是:“年均稅后收入在3.375萬盧比到15萬盧比”(約合4500~18750元人民幣);而且宣稱“已有中產階級約3億人”,網上又是吐槽一片。
我們習慣于情緒性宣泄和判斷,對比更富裕的,羨慕妒忌恨,我們不敢說中產;對比更貧困的,驚訝憐憫嘲,你們還想中產?唯獨缺乏的是客觀標準。如果我們連自己是否是中產階層都不能直面看待,如何形成同情扶持相對貧窮者、學習追趕相對富裕者的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鑒于對中產階層、對中低收入者沒有做正確的界定,已影響一些稅收和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宣傳。例如,我國個人所得稅中月工資、薪金費用扣除標準從2005年的800元起步,多次調高,2011年調為3500元。一位財政稅收權威說,扣除標準提高到3500元,對于低端收入群體的減稅力度比較大。事實上,全國城鎮約3億多工薪領取者,2011年只有約2400萬(2014年約2800萬)繳納個人工資、薪金所得稅。這2400萬人中又宣稱有約70%的“中低收入者”,他們的稅率由5%降為3%,大力宣傳這“對中低收入者減稅是一個組合拳”。那么試問,我國其余90%強的工薪者是什么層次的收入者?他們連中低收入者都不夠格嗎?
還有人說,“中國是地地道道的‘圖釘型’社會——中低收入者占就業總人口85%以上”,沒有中產階層。這符合現實嗎?哪有一個國家會有滿大街開著私家車在尋找停車位、節日擠滿全球景點的低收入者。這是理論上的模糊導致輿論宣傳中的混亂,影響形成健康的社會心理。
中產階層就是社會中獲得中等收入的群體。國家日益富強,其中產階層收入水平上升;國家日益衰弱,其中產階層收入水平下降。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中產階層沒有褒貶含義,也不是指私營業主等某個特定階層,就是一個客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