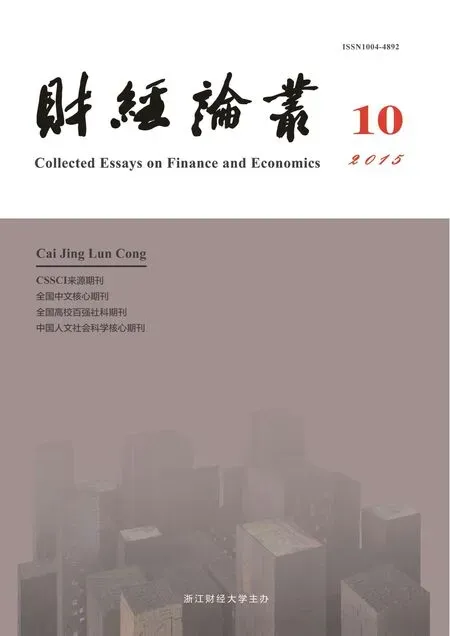制度環境、產權性質與公司慈善捐贈——來自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朱金鳳,Jun Lin
(1.西安外國語大學商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8;2.School of Busines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NY 12561)
一、引 言
企業慈善行為的多層分析模型將企業慈善的動因概括為:經濟理性、社會契約和制度規范[1],其中,制度約束作為重要的外部因素,應當引起充分的重視。特別是在中國這一轉型經濟國家,企業的行為更是呈現制度、文化、社會結構的“嵌入性”特征。然而,長期以來,基于效率視角的經濟理性分析始終主導著主流話語權,強調經濟利益是社會責任的重要驅動因素,忽略企業的制度環境,進而忽視了企業的合法性和制度理性,難以對嵌入具體社會情境的社會責任行為提出有效解釋[2]。制度理論認為企業是嵌入于社會(制度)環境中的,受制度環境的約束,同時也可以通過一定的策略來適應制度環境。“基于制度的戰略觀”[3][4]也強調除了考慮產業和企業層面的因素外,企業戰略選擇還受到更廣泛的國家和社會背景、制度結構等因素的影響,這為我們解釋企業慈善行動的差異性帶來了新的詮釋和啟發。
國內外學者對企業慈善行為內在規律進行了很多研究,但很少有文獻從地區制度環境的角度進行解釋。中國幅員遼闊,由于歷史、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水平等的不同,各地區制度環境大不相同,市場化進程步調不一,宏觀政策差異明顯,這為我們考察不同制度環境下企業慈善表現的差異提供了天然實驗場。同時,中國獨特的政企關系模式和企業產權結構特征也為本研究增添了新的情境。鑒于此,我們將制度環境、產權性質與公司慈善捐贈納入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下,期望對探索公司捐贈的制度動因,認識制度環境在促進企業捐贈中的作用提供有益的啟示。本文主要貢獻及價值體現在:(1)以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證實企業慈善捐贈水平受地區市場環境因素的正向影響。換言之,良好的制度環境是促進民間慈善成長的“沃土”,這豐富了公司慈善驅動機制的文獻,使企業慈善表現差異的探討由企業內部特征拓展到了外部客觀條件,從側重探討捐贈主體(企業)“為什么”(Why)延伸到關注捐贈管理者(政府)“怎么做”(How)。而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改善外部市場條件,正是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有效途徑,這正是在中國捐贈市場處于主導地位的政府應為之事。因此,在實踐層面,本研究對政府在慈善市場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怎樣的作用以及如何扮演好這種角色提供了一定的啟示。(2)有關中國不同性質企業(國有與民營)捐贈差異的判斷主要來自各類直觀統計,管理實證文獻很少,Zhang等[5]雖然證實國有企業的捐贈水平低于民營企業,但卻是基于災難事件,本文基于常態數據證實民營企業在慈善活動中投入了更多的資源,對現有文獻進行了有益的補充。這在管理學意義上促使我們對民營企業家慈善活動背后的行為邏輯與深層含義的深入思考。(3)與民營企業捐贈受到學者們[6][7][8]普遍關注相比,有關國有企業捐贈的研究很少,Zhang等[5]、Li等[9]也僅區分了私有和國有產權,將企業劃分為政府與非政府控制兩類進行實證檢驗,這可能會遺漏同為國有產權但所有權行使主體不同而產生的明顯差異。本文探討了不同政府控制主體下國有企業捐贈行為差異,證實中央政府控股國有企業捐贈水平低于地方政府控股國有企業,這對于理解和規范國有企業捐贈行為,使國企走上一條更為專業化的道路從事慈善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回顧
(一)公司慈善捐贈的動因
Campbell[10]概括了公司慈善捐贈的四種動因:戰略動因、利他主義、政治動因和管理者效用。戰略視角假設企業是利益驅動的,它們可以從理性出發,做出對企業最有利的戰略決策[11],Porter將這種慈善行為定義為“戰略性慈善”,認為企業對那些既能帶來社會效益,又能帶來經濟效益的“互利”慈善領域進行戰略性投資,將對競爭環境的各個方面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從而實現社會公益和企業績效的雙贏[12]。Sanchez[13]等支持利他主義觀點,認為企業慈善是履行應盡的社會義務。Neiheisel綜合利他主義和利潤最大化觀點,提出了企業慈善捐贈的混合模型——政治企業模型,認為企業慈善更多的是對環境或政治氛圍的關注。Haley[14]認為慈善是“社會貨幣”,管理者通過慈善實現管理者效用最大化,獲得更高的聲望、收入,以及得到上層人士的尊敬與贊成。蔡寧等[1]提出企業慈善行動受經濟理性、制度規范和社會契約的三重驅動。張建君[15]以競爭—承諾—服從的概念框架闡述企業捐款的動機。事實上,中國企業慈善行為動因的確更為復雜,高勇強[7]發現中國民營企業慈善捐贈更多的是“工具性”的,慈善捐贈是企業用來分散和轉移公眾視線的遮羞布。Du[6]對中國家族企業的研究證實企業利用慈善活動來轉移公眾注意力,粉飾其環境不端行為。綜上,現實中的企業慈善決策是市場、倫理、制度等多種機制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制度背景的特殊性和轉型經濟的復雜性又使得中國企業的慈善動因表現得更加隱藏和多元。
(二)制度環境與企業社會責任行為
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揭示公司慈善行為的內在規律,證實企業自身特征,例如規模與行業[16]、透明度[17]、廣告支出[18]、產權性質[5][19],政治關系[20][21][22]等都是重要的解釋變量。然而,這些觀察主要限定在組織內部,未將企業置身于整體社會結構中來審視,因而其解釋力是有限的。現實中的企業作為“企業公民”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因此,從企業嵌入的地區社會情境入手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制度環境對企業社會責任行動具有重要解釋力。Fransen[23]指出,不同國家的企業面臨著不同的監管框架,加入不同的行業團體,從而影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Jackson[24]比較了不同制度環境下歐洲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發現自由市場經濟下的企業在CSR各維度上的得分均高于調控經濟下的企業。Lim和Tsutsui[25]對影響社會責任的制度和政治經濟因素進行了跨國分析,發現全球制度壓力在發達國家導致禮儀性承諾(ceremonial commitment),在發展中國家導致實質性承諾(substantial commitment)。可見,國外對制度環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大多是跨國分析,通過比較不同國家、經濟體存在的差異來分析其社會責任實踐的不同。這些研究很難控制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宏觀因素的影響,也不能有效解釋即使在面臨相同(或相近)的國家宏觀制度環境下,同一國家不同區域內的企業社會表現為何也存在明顯差異。實際上,企業的行為除了受制于國家宏觀制度安排外,更嵌入于其所處的地方社會情境中,地區層面的制度進程差異也是影響企業戰略行動的重要因素,特別對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其作用力更強。當前,制度環境在中國情境下的研究主要是探討其對企業戰略和績效的影響[26][27],尚未有制度環境與慈善捐贈關系的實證研究,少數文獻[28]也僅關注了制度環境的調節作用,將制度作為企業慈善行動的一個已知背景條件,未對制度環境的直接作用效果進行系統研究。
三、制度背景與研究假設
(一)制度環境與公司慈善捐贈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并不平衡,市場化進程差異明顯,東部沿海地區在制度環境的各個方面都明顯領先于中、西部地區[29]。制度環境的差異導致政府與市場在經濟運行、資源分配等方面的力量對比存在差異,從而對企業獲得合法性的要求也不同,這必然通過內外部機制傳導給企業,造成企業行為選擇的差異。
首先,制度環境越好的地區,市場化水平越高,企業越傾向于按市場規律辦事,利用市場機制傳遞企業是負責任的“企業公民”的“信號”。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慈善可以提高企業聲譽[30]、保護公司關系資產[31],實現“戰略慈善”的有利經濟后果。這就是說,市場化程度越高,捐贈的價值回報機制發揮的程度越強,這必然激勵企業更積極地參與慈善。其次,法制環境也會影響企業捐贈水平,法制建設滯后的地區,捐贈稅收優惠有限,公益機構的發展也受到限制,透明度、公信力相對較低,監督機制也不健全,從而可能損害企業的慈善參與度。第三,從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看,制度建設落后的地區,政府對要素資源的控制權與支配權越強,對企業干預程度越高。政府會直接進入捐贈市場,向企業發出對口扶貧、賑災捐款等指令性勸募,造成企業“被迫自愿”捐款捐物[32],這必然損害捐贈的“自愿”本質,扭曲捐贈價值回報機制的有效發揮。此外,制度環境的差異還會造成民營企業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從而形成企業財富基礎和慈善供給能力的不同。一般來說,市場化進程越快的地區,民營企業越發達,區域經濟也越富裕,也越能催生出更多的企業家和慈善家。比如,浙江在市場化進程上遙遙領先,浙江的民營經濟也是全國之最,入榜中國慈善排行榜的浙江企業家總數也居全國前列。可見,慈善家和企業家常常不可分割,市場環境越好、區域經濟越發達的地方越可能成為企業家和慈善家的“搖籃”。
同時,伴隨著制度環境的改善,地區文明程度不斷提高,這會改善該地區企業(家)的生存狀況和發展空間,企業家也會更重視自身道德品質的提升,從而形成更積極、正面的財富觀和價值觀,這有助于催生更多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和樂善好施的慈善家。綜上,良好的制度環境為企業從事慈善活動提供了正向激勵和保護,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企業所在地區制度環境越完善,企業慈善捐贈水平越高。
(二)產權性質與公司慈善捐贈
轉型經濟下的中國民營企業長期受制度和政策上的“歧視”,需要采取一定的政治戰略處理與政府監管者的關系,才能保證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因此,和國有、集體企業相比,民營企業把關系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同時也在建立關系上投入更多的資源,以期得到從法律和正式制度中得不到的支持和保護[33]。有政治關系的民營企業也的確獲得了很多好處,比如優惠的融資待遇[34]、更多的稅收優惠[35]和政府補助[36]等。政治關聯巨大的“資源效應”使民營企業有強烈的動機與政府建立關系,慈善捐款便發揮了這種政企紐帶效應,成為強化企業和政府關系的重要途徑[37]。由于中國企業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尋租途徑,以及以慈善捐贈來尋租更為隱蔽,更為安全,有時也更為有效,因此中國企業運用慈善捐贈這種變通的、合法的政治策略向政府尋租更為普遍[33]。李維安等[38]證實,民營企業以慈善捐贈與政府進行資源交換從而獲取債務融資,購買金融資源,這種互惠機制的紐帶是政治關聯。Zhao[39]也證實,企業通過投資于那些有利于加強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慈善或社會責任活動,幫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取得政治合法性,獲得政府的支持與保護。Su和He[40]的研究表明,民營企業通過慈善行為取得產權保護和政治關聯,這種保護有助于提高其盈利水平,并且在制度環境越差的地區這種作用更為明顯。綜上分析,轉型經濟下的民營企業更多地被戰略、利益所驅動,會將更多的資源配置于慈善捐贈活動中。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a:與國有控股企業相比,非國有控股企業慈善捐贈水平更高。
上述分析沒有考慮在國有控股企業中,所有權行使主體的不同所帶來的差異性。實際上,同為國有產權,但實際控制人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企業在慈善動機、決策權配置上也有很大差異。相比地方國有企業,中央企業獲得了更多的得天獨厚的資源和市場準入壁壘,產權也受到天然保護,而地方政府控股企業在跨地區經營時則難免受到行政壟斷的限制,產品或服務遭遇進入壁壘,因而其利用慈善活動獲取合法性的動機更強;其次,公司捐贈中存在代理問題和利益沖突,雖然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權”會增加其利用慈善活動為公司帶來的收益,但管理層也會以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利用慈善活動謀取個人利益。由于中央控股企業管理層受到更為嚴格的監管,比如來自更高權威的審計署審計、重大經營決策等問題要經過更高的主管部門審批等,因此相應約束了管理層的非生產性消費的空間。第三,從捐贈決策權來看,捐贈的基本前提是作為捐贈主體的企業對所捐的財物擁有所有權和支配權,由于國有企業并非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公民”,公眾常以國企沒有“捐款”的權利為由指責其捐款是“慷國家之慨”,并且,由于中央控股企業大多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基礎設施的大型企業,因而受關注程度更高,捐款的負面評價更大①例如,中石油曾向吉林省捐款500萬人民幣治理松花江污染,被指責“慷全民之慨”,“用國家的錢冒名“領功”。2006年國家電網曾捐贈1.2億元,援建希望小學300所,引發輿論的質疑。。正因如此,近年來國務院國資委不斷規范對中央企業捐贈程序的管理,要求企業規范界定對外捐贈范圍,合理確定捐贈規模,嚴格捐贈審批程序,并將對外捐贈支出納入企業年度預算管理,有效維護股東權益②2009年11月國資委發布《關于加強中央企業對外捐贈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規定中央企業凈資產小于100億元,捐贈項目超過100萬元的;凈資產在100億-500億元,捐贈項目超過500萬元的;凈資產大于500億元,捐贈項目超過1000萬元的,都應當報國資委備案同意后才能實施。。這些規范顯然會約束中央控股企業的捐贈自由度。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b:在國有控股企業中,相比地方政府控股企業,中央政府控股企業捐贈水平更低。
(三)產權性質的調節作用
在不同的產權性質下,制度環境對企業行為的影響是不同的。從實踐來看,國有企業的捐贈更多來自政府號召,幫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市場機制的作用相對較弱,而在市場經濟土壤上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家)對市場信息的感知、搜尋和和解釋能力更強,反應也更為敏感。由此,我們認為制度環境對民營企業捐贈行為的影響程度會更大,民營企業利用捐贈的價值提升機制改善外部競爭環境,提高企業競爭優勢的動機更強,效果也更為明顯。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制度環境對企業捐贈水平的正向影響在非國有控股企業表現更強。
四、實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2年連續3年數據進行研究,并進行了以下篩選:剔除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剔除實際控制人不詳的公司;剔除凈資產收益率等主要變量數據缺失的公司;剔除注冊地在西藏的公司,最終獲得4727個樣本觀測值,其中,披露了捐贈額的3954個,占84%,沒有披露的773個,占16%;國有控股樣本2347個,非國有控股樣本2380個,各占50%。本研究中制度環境數據來自樊綱等發布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度報告》,人均GDP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司捐贈數據來自年報附注,其他來自CSMAR數據庫。
(二)變量設計
1.被解釋變量
對公司捐贈水平的度量多采用對管理者的調查和企業實際的披露兩種,由于管理者承諾的捐贈與實際捐贈之間經常會不一致,使用管理者調查數據不能區分企業承諾做什么和實際做了什么之間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從企業實際披露的角度進行度量。指標的選取上,文獻中有使用絕對指標如捐贈額,也有采用相對指標如捐贈收入比或捐贈資產比。中國慈善事業尚處于發展初期,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捐贈評價更多是基于實際捐贈額,而非相對捐贈水平,實際捐贈額也更能刻畫企業的捐贈貢獻度,當前各類企業(家)慈善也都以實際捐贈額作為入榜標準,因此,本研究以年報中披露的實際捐贈額來測量捐贈水平。
2.解釋變量
使用市場化總水平(Market)、政府干預水平(State)、法律和產權保護水平(Law)和一個區域指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來刻畫地區制度環境差異。產權性質上設置是否國有控股(SOE)和政府行政級別(CSOE)兩個檢驗變量,當實際控制人為縣級或縣級以上政府有關機構時,認定為國有控股,否則為非國有控股。進一步,將國有控股劃分為地方政府控股和中央政府控股分別賦值。以公司規模(Size)、盈利能力(ROE)、行業(Indu)、獨立董事比例(Direct)、股權集中度(Top5)、捐贈一期滯后值LDn作為控制變量以控制公司特征因素的影響。變量界定見表1。

表1 變量界定與度量
(三)模型構建
本研究構建以下模型來檢驗制度環境、產權性質與公司慈善捐贈的關系。
模型 1:Dni,t= β0+ β1Institutioni,t+ β2Controli,t+ εi,t
模型 2:Dni,t= β0+ β1Institutioni,t+ β2Ownershipi,t+ β3Controli,t+ εi,t
模型 3:Dni, t= β0+ β1Institutioni, t+ β2Ownershipi, t+ β3Institution* Ownershipi,t+β4Controli,t+ εi,t
模型1用來檢驗制度環境對公司慈善行為的影響,Institution分別用Market、State、Law、GDP代入用來驗證假設1。模型2用來檢驗產權性質對公司慈善捐贈的影響,Ownership分別用是否國有控股SOE和政府行政級別CSOE替代以驗證假設2a和2b。模型3增加了制度環境與產權性質的交叉項Institution*Ownership來檢驗產權性質的調節效應,用來檢驗假設3。
五、實證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限于篇幅,結果未列出),Dn的標準差高達5.0296,說明企業捐贈水平極不平衡,差異度較大。市場化水平Market的最高值為11.8,最低值為3.25,標準差為2.03,說明各地區市場環境存在巨大差異,這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契機。SOE的均值為0.5,說明國有控股企業在我國資本市場上仍占據重要地位(占比50%)。變量GDP、Indu的均值分別為0.62和0.45,表明62%的樣本位于經濟發達地區,45%屬于消費者口碑敏感行業,地區、行業分布具有一定代表性。進一步的相關性分析顯示,制度環境各變量與因變量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這與假設1預期一致。制度環境的四個變量彼此在1%的水平上正相關,相關系數均在0.6以上,說明自變量指標體系的內部一致性,由于存在較高的相關系數,在回歸分析中分別將其代入模型研究。
(二)均值T檢驗與中位數非參數檢驗
對制度環境變量取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兩組,大于中位數的劃分為高組,小于中位數為低組,進行均值差異T檢驗和中位數Mann-Whitney檢驗,結果如表2顯示,制度環境好組的均值和中位數均顯著高于差組,標準差低于差組,且均十分顯著(P<0.01),這與假設1的預期一致。

表2 不同制度環境下慈善捐贈均值差異T檢驗與中位數U檢驗
(三)多元回歸分析
各變量的VIF都在1左右,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由于樣本總量包含773個(占比16%)捐贈額為0的觀測值,樣本出現角點解,以及在對因變量進行對數變化過程中出現0取值的問題,模型1分別對全樣本(N=4727)和捐贈組子樣本(N=3954)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

表3 制度環境與企業慈善捐贈水平多元回歸分析
表3顯示,無論在全樣本還是子樣本下,市場化水平(Market)與捐贈規模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法制水平(Law)分別在1%(全樣本)和5%(子樣本)的水平上與因變量正相關;地區GDP與捐贈規模在5%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政府干預(State)在全樣本下與因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子樣本下T值接近2(T=1.431),P值接近0.1,可以認為在10%的水平上與因變量正相關。結果說明,制度環境對公司慈善捐贈有顯著正向影響,地區市場化水平越高、法制環境越好,政府干預程度越小,區域經濟越發達,企業捐贈規模越大,研究假設1得到很好的驗證。這一結果說明制度環境在促進企業捐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伴隨著制度環境的改善,企業將更多的資源配置于慈善活動中,這對理論和實踐都具有重要啟示。LDn與捐贈規模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企業捐贈行為具有連續性和穩定性。
表4為模型2結果,無論以何指標來測量制度環境,是否國有控股(SOE)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產權性質對公司捐贈水平有顯著負向影響,非國有控股企業捐贈水平高于國有企業,假設2a得到實證支持,這一結論結合Zhang等[5]、李曉玲等[24]的研究,印證了民營企業已成為中國慈善事業的重要力量這一客觀事實。進一步,將SOE替換為CSOE,發現CSOE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政府行政級別也具有重要解釋力,假設2b也得到證實。

表4 制度環境、產權性質與慈善捐贈多元回歸分析
為檢驗產權性質的調節效應是否存在,引入交叉項Institution*Ownership對模型3進行回歸。由于市場化進程總指數(Market)是最具綜合性制度環境指標,因此以其作為制度環境變量,以SOE為產權變量進行調節效應檢驗。調節回歸結果顯示,全樣本下交叉項系數為-0.132,p值為0.064,子樣本下交叉項系數為-0.062,p值為0.039,均十分顯著,這說明產權性質具有顯著的負向調節效應。為進一步分析產權性質調節效應的作用模式,我們對國有和非國有控股企業進行了分組回歸,表5結果顯示,在非國有控股組中,Market、State、Law的系數分別為0.144、0.239、0.048,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GDP的系數為0.279,T值接近于2。而在國有控股企業分組中,各變量的回歸結果均不顯著,這進一步驗證了假設3,即制度環境對企業捐贈水平的正向影響在非國有控股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中表現更為明顯。

表5 制度環境與慈善捐贈:基于產權性質的分組回歸
(四)穩健性檢驗
本研究進行了以下穩健性檢驗:(1)將市場化水平替換為法制水平,構建法制水平與產權性質的交叉項對模型3進行回歸,結果不變;(2)分別以政府干預、法制水平和地區GDP來測量制度環境,對國有和非國有子樣本進行分組回歸,結果顯示,除顯著性略有變化外,基本一致。(3)刪除實際控制人為外資、集體、社會團體、民營企業等的樣本,僅保留了實際控制人為自然人的樣本,即將非國有控股企業界定為狹義的民營企業,將該子樣本與國有控股樣本進行分組回歸,結論不變。總之,穩健性檢驗的結果表明變量的方向并未發生改變,顯著性水平也基本一致,這表明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穩健和可靠的。
六、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證實,企業慈善捐贈受地區制度環境和企業產權結構特征的深刻影響,這對于理解企業慈善行動的深層含義以及轉型制度背景下政府慈善政策的制定具有啟示意義。
(1)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載體,對調節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矛盾,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構建良好的激勵回報機制,保護企業的捐贈熱情,鼓勵更多企業參與慈善十分重要。政府是慈善市場的管理者和監督者,慈善捐贈社會正效應的實現,需要政府的決策安排予以激勵。很顯然,良好的制度環境是企業慈善成長的“沃土”。因此,政府應加強制度環境建設、完善法律法規、減少行政干預、轉變角色定位,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由捐贈市場上的管理者甚至直接參與者,回歸為引導者、激勵者和監督者,實現由慈善事業的“管家”到“引路人”的角色轉換。(2)相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在慈善活動中投入了更多的資源,因此,政府應加大制度創新,通過政策法規激勵民營企業投身公益,變因政策激勵力度不夠的“政策困境”為“政策促進”。(3)參與慈善是民營企業用來建立、維護和鞏固政治關聯,增強企業競爭優勢而采取的一種戰略行動。民營企業應充分利用這一戰略,積極投身公益,為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作為政府,在支持企業參與公益的同時也要加強自身建設,避免企業以慈善這種新型的、安全的利益輸送方式,來構建企業的人際關系平臺,使公益平臺成為一種變相“尋租”的管道,傷害慈善良善的本質。(4)國有企業捐贈水平低于民營企業,這可能與國企歷來面對很大勸募壓力,捐贈金額遠不止報告所統計的數據,以及國企捐款在程序上也更加復雜有關。國有企業捐贈是把“雙刃劍”,政府一方面要鼓勵國有企業積極參與慈善,另一方面也要加強監管,避免國有資產以“慈善”之名流失。政府在對中央企業加強監管的同時,對地方控股國有企業的捐贈管理也不容忽視。只有引導國有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有效維護股東權益,才能使國有資產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企業、政府、社會共同努力,才能“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實現慈善與財富的雙贏及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
[1]蔡寧等.經濟理性、社會契約與制度規范:企業慈善動機問題研究綜述與擴展 [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39(2):64-73.
[2]郝云宏,唐茂林,王淑賢.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理性及行為邏輯:合法性視角[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2,(7):74-81.
[3]Peng M W,Towards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2,19(2):251 -267.
[4]Peng M W,Wang D YL and Jiang Y.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8,39:920-936.
[5]Zhang R,Rezaee Z and Zhu J.Corporate philanthropic disaster response and ownership type: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response to the Sichuan earthquak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2009,(1):51-63.
[6]Du X.Is corporate philanthropy used as environmental misconduct dressing?Evidence from Chinese family-owned firm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4,(4).
[7]高勇強,陳亞靜,張云均.“紅領巾”還是“綠領巾”:民營企業慈善捐贈動機研究[J].管理世界,2012,(8):106-146.
[8]薛爽,肖星.捐贈:民營企業強化政治關聯的手段?[J].財經研究,2011,(11):102-112.
[9]Li S,Song X and Wu H.Political connection,ownership structure,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China:A strategic-polit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4,(4).
[10]Campbell D,Moore G and Metzger M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the U.K.1985-2000:Some empirical finding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2,39(1):29-41.
[11]Seifert B,Morris S A and Bartkus B R.Comparing big givers and small givers:Financial correlate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3,45(3),195-211.
[12]Porter M E and Krame M 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2,80(12):56-68.
[13]Sánchez C M.Motives for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El Salvador:Altruism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0,27(4):363-375.
[14]Haley U.Corporate contributions as managerial masques:Reframing corporate contributions as strategies to influence society[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1,28(5):485-509.
[15]張建君.競爭—承諾—服從:中國企業慈善捐款的動機[J].管理世界,2013,(9):118-129.
[16]Amato L H and Amato C H.The effects of firm size and industry on corporate givi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7,72(3):229-241.
[17]Brammer S and Millington A.Firm size,organizational visibility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An empirical analysis[J].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2006,15(1):6-18.
[18]Zhang R,Zhu J,Yue H and Zhu C.Corporate philanthropic giving,advertising intensity and industry competition level[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4(1):39 -52.
[19]李曉玲,任宇,劉中燕.大股東控制、產權性質對企業捐贈的影響 [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137-145.
[20]杜興強,郭劍花,雷宇.政治聯系方式與民營企業捐贈:度量方法與經驗證據[J].財貿研究,2010,(1):89-99.
[21]梁建,陳爽英,蓋慶恩.民營企業的政治參與、治理結構與慈善捐贈[J].管理世界,2010,(7):109-118.
[22]Jia M and Zhang Z.The CEO's representation of demands and the corporation's response to external pressures:Do politically affiliated firms donate more?[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13,9(1):87-114.
[23]Fransen L.The embeddedness of responsible business practice: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2013,115(2):213-227.
[24]Jackson G and Apostolakou A.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Western Europe:An institutional mirror or substitut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4(3):371 -394.
[25]Lim A and Tsutsui K.Globalization and commitment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ross-National analyses of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economy effect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2,77(1):69~98.
[26]李維安,徐業坤.政治關聯形式、制度環境與民營企業生產率[J].管理科學,2012,(2):1-12.
[27]羅黨論,黨清泉.中國民營上市公司制度環境與績效問題研究[J].經濟研究,2009,(2):106-118.
[28]賈明,張喆.高管的政治關聯影響公司慈善行為嗎?[J].管理世界,2010,(4):99-113.
[29]樊綱,王小魯,朱恒鵬.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9年報告[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
[30]Brammer S,Millington A.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philanthropy:An empir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5,61(1):29-44.
[31]Godfrey P C.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shareholder wealth:A risk management perspectiv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4):777-798.
[32]鐘宏武.慈善捐贈與企業績效[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
[33]Xin,K.and Pearce.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2):1641-1658.
[34]連軍,劉星,楊晉渝.政治聯系、銀行貸款與公司價值[J].南開管理評論,2011,(5):48-57.
[35]吳文峰,吳沖鋒等.中國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與稅收優惠[J].管理世界,2009,(3):134-142.
[36]余明桂,回雅甫,潘紅波.政治聯系、尋租與地方政府財政補貼有效性[J].經濟研究,2010,(3):65-77.
[37]張敏,馬黎珺,張雯.企業慈善捐贈的政企紐帶效應—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13,(7):163-171.
[38]李維安,王鵬程,徐業坤.慈善捐贈、政治關聯與債務融資——民營企業與政府的資源交換行為[J].南開管理評論,2015,(1):4-14.
[39]Zhao M.CSR-Based political legitimacy strategy:Managing the state by doing good in China and Russia[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2,111(4):439-460.
[40]Su J.and He J.Does giving lead to getting?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3(1):7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