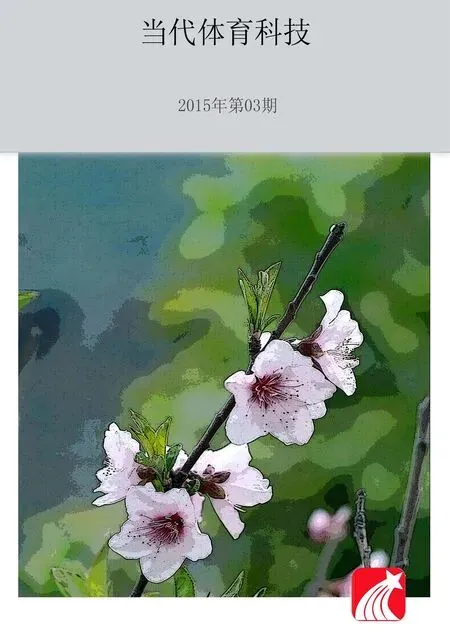文化意識聚焦下的體育休閑化研究
楊晨飛 李華
(玉溪師范學院體育學院 云南玉溪 653100)
人類在自然成長過程中,難免遇到不同的生長周期,而這生長周期隱性地引導人類趨于對內心真實感受的追尋,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從動物本性視角窺看這一過程,會發現人類的脆弱,若將這種脆弱擴大,去探究脆弱的根源,反射出的則是自然界的公平與無情。公平得源于自然界塑造的人類軀體,使得人類具有了與自然界構造相符的行為活動;無情得源于自然界的構造創設,讓人類需從自然界中獲取軀體運作的資本。這看似矛盾的根源,卻驅動了自然界整體的循環,讓存在與被存在成為了自然界的核心問題。人類在自然界背景下存在之始,就開始受到這一循環的困擾,也正是這一循環讓屬于物種的人類逐漸認識到軀體的脆弱,尋找被存在的存在意義成為人類脫離動物概念下物種概念的途徑。
在人類探尋被存在中存在的過程里,為了劃清與軀體物種根源的界限,人類認識到了掠食的殘酷、繁殖的優劣以及雜食的優勢。可是人類雖然劃清了與動物的不同,但卻開始面臨更為嚴峻地問題,即同種之間的存在。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對這種現象有充分的認識,他說:“同種的個體之間的所進行的斗爭幾乎必然是最劇烈的,因為它們居住在同一區域內,需要同樣的食物,并且還遭遇同樣的危險。同種的變種之間的斗爭一般差不多是同等劇烈的。”[1]人類為了避免或克制自身動物性本能的出現,尋求一種舒緩地、隱性地控制機制,成為了解決存在與被存在問題途徑,而這途徑便是人類制度、規則產生的根源。
人類的制度與規則,是對自身動物本能的克制,為避免動物本能再次凌駕于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之上,制度與規則就成為了具有普遍性與強制性的規律。這種規律同自然規律有抽象相似性,可以說這種規律是自然規律下的二級規律,受自然界的限制,又具有人類避免動物性本能所產的意識特殊性。由此可以說,自然界對人類來說是外部的客觀存在(存在),而規律則是人類對內部認識的主觀存在(被存在),它具有對客觀存在的能動作用(認識被存在中的存在)。在認識存在與被存在的過程中,人類主觀對客觀的認識,成為了人類客觀存在的意識,也就是說人類在認識外部環境和自身的過程里,意識逐漸產生,因其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人類自身產生的意識就具有了共同與共通性,也就是普遍意識。普遍意識在外部環境與人類自身二者之間,為尋找一個合理的中間點,制度與規則形成的規律就成為主導人類發展的暫時性普遍意識,即本文所要研究的文化意識。
1 人與文化意識
文化意識,首要問題是了解文化意識具有何種特性。在此,需要對文化意識的特性進行簡要說明。
第一,文化意識絕不是憑空出現。但凡一種文化意識的產生,定有其可尋出的前因與后果。譬如分析一篇文章,不能信手拈得一段,因其它的存在具有承上啟下、承前接后的關系,不懂前因的武判,定會造成分析的失真。在此所要說明的重點是需要審視文化意識產生的背景,既有自然背景,又有社會背景,如上文所說的,客觀存在與主觀存在。
第二,文化意識具有時勢性。正如當今社會存在兩種較為突出社會體制,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若單獨分析二者存在的文化意識差異,是很難辨別地,需要從二者的前因、時勢和意識形態進行分析,因為兩種社會形態歸宗結底在于人類的問題,它們互為因果。有時是先有時勢,才出生意識形態;有了意識形態,時勢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一定大有變動。所以時勢生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又生時勢,時勢又生新的意識形態。
因此,在認識文化意識過程中,時勢與歷程是核心問題,即時間與空間的客觀存在問題。但是,光有時間和空間是不能充分認識對文化意識的,因其所產生的根源在與人,文化意識的問題即是人的問題。正如胡適先生所說的:“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不論對外部客觀存在,還是內部主觀存在,亦或是客觀與主觀存互為交融,其根本仍然是人的意識,因為產生這一思維模式的主體是人的反應。
2 文化意識與體育休閑化
當今社會物質財富相較社會時勢形態呈現膨脹態勢,人類在此環境下的生存,逐漸遠離對于軀體生存的追求,更多的投入到對于客觀存在與主觀被存在的認識之中,所造成的文化意識顯現出人類從理性轉向浮躁的態勢。這種態勢,造就了時勢文化意識的不一。在理性意識下,人類利用所創造的物質資源,創設了更為適宜的外部客觀環境,但是這種創設雖然給人類帶來了便捷,卻又招致了人類動物性本能的釋放。更強力的滿足對于物質資源的渴望,野蠻、暴力頻顯,為了滿足內心欲望,不惜強力改造外部客觀存在以證明主觀被存在的客觀存在感,使人類自身沉溺于成為客觀存在核心的浮躁情感之下。雖然在此看來,這種趨向扭曲了理論性人類意識發展的形態,但是這仍然是具有時勢性的文化意識。
從上述時勢性文化意識形態看,人類也許在盲目中走向了一條錯誤的發展路徑。但是文化意識是從自然界客觀存在中衍生出的概念,它同自然界一樣具有自我代謝與修復的功能。自然界在受到外力改造時,它會呈現出一種自我保護,避免外力對自身的侵擾。此外自然界的自我代謝,從人類的視角看也許是非良性的改變,如物種的滅絕與變異,可是從自然界自我代謝的角度看卻是正確地。一些不良地個體,已不適宜于外部環境的客觀改變,客觀存在總是以一種強制性影響著被存在的存在,因其客觀存在需要自我修復以維持時勢性需求,同時亦證明自然界的客觀存在終是被存在中主觀與客觀存在的根源。這如同“休閑體育”在此時勢環境下所提出一般。
“體育休閑化”是兩種概念抽象后的邏輯組合,已不完全具有兩個概念的獨立價值,更多概念的存在是對時勢文化意識的反應。由此,對“體育休閑化”進行概念分離解析后與主體概念的對比,是證實其具有時勢文化意識影響的重要途徑。
“休閑”(leisure),從詞源上看它是出自拉丁語“licere”(意為被允許)。國內對此理解,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將“lsisure”一詞譯為“余暇”或“閑暇”;另一種是直譯為“休閑”。在《說文解字》和《詞源》對于上述兩種理解的分析指出““余”指多余、剩余;“暇”指空閑,也指無事之時;“閑”是指安靜無事;“休”是一個意會字,意為在大樹的庇護下,頤養活動得以進行并得到精神的修整,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2]從對“休閑”詞義概念的分析上可以看出,它所透漏的是一種內源反省價值。若將其納入時勢文化意識中進行分析,正如上文所述的自然界新陳代謝一般,是人類在時勢文化意識境況下對自身處境的客觀認知。一種社會時勢文化意識被高度提倡,則說明這種文化在時勢下是其極度的缺乏的。因為,人類自我在認識存在與被存在的過程里,同樣具備自然界的自我代謝,在物質基礎高度繁榮的今天,時勢文化意識與物質基礎喚起人類對于所需的極端欲望,極端欲望導致了人類對客觀外部環境存在的侵擾。客觀存在的改變注定會影響內部被存在的客觀存在,亦會激發內部客觀存在的主觀存在。因此,“休閑”并不是憑空產生的概念,而是人類對于客觀被存在中存在價值的反省。
“體育”作為時勢文化意識的一種承載與表現形式,不僅可以解釋不同體育運動的亞文化,而且也可以解釋體育所處的社會。透過某些平凡、不嚴肅的體育現象,闡述社會和人類生活嚴肅、重要的一面。讓所處體育運動過程中的人,在相對獨立的領域內,暫時擱置日常生活。從而使體育成為展現人類個體、群體以及相互之間關系的基本真理。可是,上述以體育推及人類社會生活的推論,又受到來自外力的干擾,即時勢文化意識。由此形成某種特定的形態,亦是產生某種新的內涵形態,均受制于客觀外部存在。
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充分證實,“休閑”與“體育”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意識表現形式,所具有的內涵價值皆不同。在受到時勢文化意識的孕育與洗禮后,二者抽象后邏輯建構,形成符合時勢文化意識需求的價值觀念。但是,不論如何的改造與建構,時勢文化意識產生的種種,終是以“人類”認識為出發點,亦可說終是“人類”的問題。就當下社會對“休閑體育”概念的認識看,“人的自由性不是絕對的,因為在社會條件下,人總是受一定的規范和制度所約束,因此我們所說的自由只是相對于強制性約束和嚴格的規范性而言。”[3]另外,“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任何活動者都可能擁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活動時間、空間,并具有一定的活動能力等條件,但選擇參與什么樣的活動,主要取決于活動者自己。”因此,可以說“休閑體育”是時勢文化意識驅使下人類對于存在與被存在的追尋,“休閑”在于被存在,“體育”在于存在,外部時勢文化意識環境才是“休閑體育”產生的根本。由此,從“休閑體育”來審視與判斷社會發展趨勢,是主觀被存在中的存在對客觀存在的反應,也是客觀存在的真實體現。
3 結論
從人類探求存在與被存在的認知中,逐漸衍生出文化意識。而文化意識在外部客觀存在環境中不斷往復存在于被存在的主觀認知,這種認知成為文化意識時勢性的主要驅動力。當人類在主觀存在影響客觀存在的過程中漸離漸遠了人類在客觀存在中的被存在,反省意識便被這種矛盾激發,形成了時勢性文化意識聚焦。“體育休閑化”便是如此氤氳而生,它不是單獨存在的個體,它是在人類自我循環中,所產生的自我修復,是人類對于時勢文化意識主觀認識后,對于自然界自我代謝恒定規律的客觀認識,但終是人類對于被存在價值的自我反省與探討。
[1](英)達爾文.物種起源[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90.
[2]羅林.休閑體育的認識深化及在我國的發展研究[D].江蘇:蘇州大學,2005:21.
[3]盧峰.休閑體育概念的辨析[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04(5)30: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