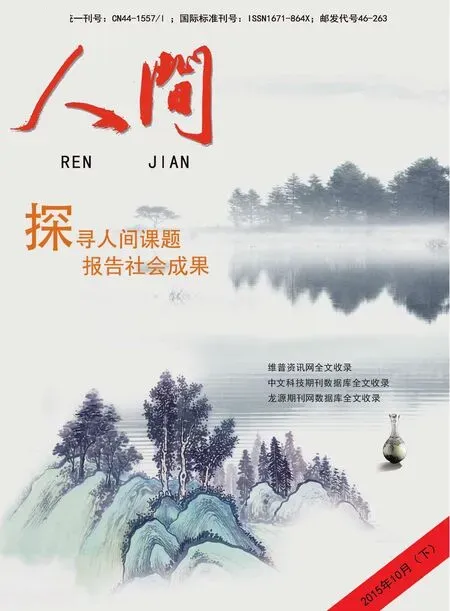萬瑪才旦電影的創作初衷
李榮
(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陜西 咸陽 712000)
萬瑪才旦電影的創作初衷
李榮
(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陜西 咸陽 712000)
藏族電影導演萬瑪才旦是中國當代藏族題材電影中不可不提的冉冉之星。近年來得到了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關注。萬瑪才旦那獨樹一幟的個人風格通過真實藏區的影像在銀幕上展露無遺。本文通過挖掘萬瑪才旦成長環境、內心抉擇和外部環境來分析萬瑪才旦電影的創作初衷,以及萬瑪才旦為呈現真實藏區而做出的種種努力:創建藏人主創團隊、堅持母語創作、大膽啟用非職業演員;鏡頭語言上濃郁紀實風格的長鏡頭使用。對萬瑪才旦電影創作初衷的解讀,可以有助于我們對于萬瑪才旦真實地近乎紀錄的影像風格的理解。
萬瑪才旦;真實藏區;創作初衷
2015年8月5日,改編自萬瑪才旦同名短篇小說的新片《塔洛》入圍了72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競賽單元。萬瑪才旦電影作品首次入圍世界三大國際電影節是其電影風格日臻成熟的體現。雖無緣獎項,但其真誠而質樸的藝術表達,打動了威尼斯電影節《塔洛》首映式的在場觀眾。
一、萬瑪才旦電影的創作初衷及原因
早在2005年,萬瑪才旦接受中國電影的采訪時就說道:“我的電影里,每個生活細節、每句話都拍的很純粹。反映的是當下藏區的生存狀態。”2015年9月,在接受搜狐娛樂記者的采訪時,萬瑪才旦說:“在目前以商業電影為主導的電影市場,做到獨善其身,關鍵是要有個好心態,畢竟創作是自己的事情。”
從2005至2015這十年間的專訪中,不難看出萬瑪才旦電影創作中的某種堅守:懷著對故鄉的無限熱愛,渴望著用自己的方式講述故鄉。正是這一電影創作初衷,激勵著萬瑪的電影創作之路越走越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鑄就了這一創作初衷?
(一)成長環境和內心抉擇是真實表達訴求的內因。
1969年12月,萬瑪才旦出生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一個半農半牧的村子里。這里民風淳樸,日子過得簡單而平靜。“淳樸的民風背后沉積著豐富的傳統文化,年久日深,這種文化便有了堅韌的內核,堅不可摧。而世界卻日新月異,許多新鮮奇異的東西以聲音或者色彩的方式進入小鎮,與傳統文化的古舊和厚重形成了對比,甚至對抗。”1
在處女作影片《靜靜的嘛呢石》中,導演萬瑪才旦就用鏡頭展示了一個簡單淳樸而變化著的家鄉。影片取景于萬瑪才旦家鄉附近的村落和寺院,講述一個小喇嘛回家過年的故事。電影以近似原生態紀錄的方式,為觀眾呈現了一幅藏區深處的風俗畫卷。猶如小喇嘛最后將孫悟空的面具收進自己的袈裟里,然后急速奔向祈愿大法會一樣。傳統和現代的交織互動主線,從一開始就在萬瑪才旦的影片中涌動。“萬瑪才旦就是想通過這個簡單的故事,表現藏區日常生活表面的平靜之下傳統與現代的交織滲透,表現濃厚宗教氛圍下人與人之間的溫情,淳樸的人對信仰的虔誠。其實,這就是他故鄉的真實面貌,那種平淡樸素的靈光。”2
生于斯,長于斯的萬瑪才旦,曾經就讀于青海省海南州民族師范學校,畢業后當過一段時間的小學老師;不安于現狀的他在幾年后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學的藏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后,他成了藏區的一名公務員,每天做著瑣碎而無聊的事情,“與理想距離很遠”;一次偶然的機會,在美國基金會的贊助下,幾經輾轉的他進入了北京電影學院學習,短短兩年的電影學習后,萬瑪才旦就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靜靜的嘛呢石》。這部處女作影片“以真誠的創作態度、樸素的電影語言,形象的展示了藏族宗教世界的日常生活,表現出現代文明與古老宗教的碰撞和融洽。影片風格沉著冷靜、敘事節奏自然流暢,意境深邃。”(金雞獎評委會的評語)在強手如林的2005年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處女作獎的角逐中,36歲的藏族新人導演萬瑪才旦摘得桂冠。
自此,萬瑪才旦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電影為創作手段、以真誠樸素的電影語言為表達方式,成為了藏族文化的守護和傳播者。
(二)“不那么真實的藏區表達現實”是真實訴求的外因。
萬瑪在接受采訪時說過:“經常有一些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講述我的故鄉的故事,這些使我的故鄉一直以來蒙上了一層揭之不去的神秘的面紗……這些人常常信誓旦旦地標榜自己所展示的是真實的,但這種真實反而使人們更加看不清我的故鄉的面貌……我不喜歡這樣的“真實”,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來講述發生在故鄉的真實的故事。”
那些在萬瑪才旦看來“并不那么真實的藏區表達”是什么樣的?通過梳理和回顧藏族題材電影的發展歷史便可以一窺究竟。
新中國電影“十七年”中,我國共拍攝十部藏族題材影片,分別是《金銀灘》(1953)、《猛河的黎明》(1955)、《暴風雨中的雄鷹》(1957)、《五彩路》(1960)、《柯山紅日》(歌劇、1960)、《昆侖鐵騎》(1960)、《紅鷹》(歌劇、1960)、《草原風暴》(1960)、《金沙江畔》(1963)和《農奴》(1966)。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電影大多是以奇麗的民族風情或動人的愛情故事獲得觀眾的親睞,卻始終無法逃離為民族團結服務、為弘揚黨的政策方針服務的窠臼。因此,以當下視點看,“十七年”間創作的藏族題材電影不免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過多的政治傾向;這一階段的藏族題材電影只是服務于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而非真正意義上的藏族電影。
新時期中國藏族題材電影創作也呈現出了嶄新的面貌。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少數民族電影進入一個全新的創作時期,導演關注藏族題材的視角也有所變化,開始了新一階段的探索和開拓,由此,藏族題材電影呈現出多元化的走向。這一時期的藏族電影出現了《冰山雪蓮》(1978)、《丫丫》(1979)、《雪山淚》(197 9);《神奇的綠寶石》(1 983)、《卓瓦桑姆》(舞劇、1984);《女活佛》(1986)和《松贊干布》(19 88);《盜馬賊》(19 86)、《世界屋脊的太陽》(19 91)、《可可西里》(20 04)以及《喜馬拉雅》(2006);《孔繁森》(1995)、《紅河谷》(1996)、《遙望查理拉》(1998)、《極地營救》(2002)等等。這些影片極大地豐富了新時期中國電影關于藏族題材的創作,對于傳播藏族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藏族同胞的生活以可視可聽的方式呈現在大銀幕上時,也部分地消解了藏族在其他人心目中的神秘感。但由于特定歷史環境和民族政策的限制,電影《松贊干布》無法正確地表現西藏及藏族人民的真實生活。田壯壯的《盜馬賊》片中藏族宗教儀式的堆砌和田壯壯自身的漢族身份導致他始終無法逃離獵奇的心理支配。
藏族文化對于“他者”來說本身就是神秘的指代,藏族傳統文化中的宗教習俗以及變幻莫測的地理環境都是對國外導演的誘惑,驅使他們關注藏族,并用自己的攝影機記錄下個人對于這片神秘土地及生活在這里的人的理解。從90年代到近幾年,主要作品大概有以下幾部:《生和死》、《喜馬拉雅比勺魔鬼》、《香格里拉—消失的地平線》、《喜馬拉雅面具》、《西藏七年》、《喜馬拉雅雪人》、《西藏女王》、《小活佛》、《達賴喇嘛傳》、《喜馬拉雅》、《旅行者與魔術師》、《高山上的世界杯》、《色戒》等。
無論是以何種形式來展現藏族人的生活,鏡頭下的藏區以及藏民的生活都帶有導演或多或少的獵奇心態,以及文化“他者”的烙印。時至2005年,萬瑪才旦攜其首部故事長片《靜靜的嘛呢石》亮相,真正意義上反映藏區生存狀態的藏族電影才宣告誕生。
二、 萬瑪才旦電影真實表達訴求的具體表達
作為一個藏族導演兼作家翻譯家,萬瑪才旦仿佛一直肩負著一種民族的使命感。從最初的文學發聲、到2002年處女短片《靜靜的嘛呢石》的問世再到2015年《塔洛》的創作和參展。萬瑪才旦一直扮演著一個藏文化傳播者角色,透過他的小說、翻譯作品和電影作品,向觀眾傳達真正的藏區。他要把電影拍給新一代的藏族人、讓他們了解自己的歷史;以及藏族以外的人看,拋棄以往宗教文化的神秘性和宗教性,而轉而關注藏人的生存狀態。
萬瑪才旦在接受《中國民族》刊物采訪時曾說過:“我是藏族人,迄今最大的夢想,就是拍純粹的藏族電影。”在萬瑪才旦的影像世界里,為了將他熟悉的藏區真實地呈現在觀眾面前,他做出了以下幾方面的努力:
(一)打造一個藏人的創作團隊,以便更好的藏式表達。
“我覺得拍純粹藏族題材的電影劇組都是藏族可能會更好,會更加有默契,對于一些細節的捕捉更有利。” “我現在的方向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拍藏族題材的電影而且以母語為主,沒有這樣一批人可能不行。我有一個可以說是很“周密”的計劃:在兩年內,培養一批藏族的電影人,包括錄音、美術、攝影、制片等。因為語言、文化的隔膜對純藏族電影的拍攝很有影響。培養的人多為二三十歲左右,他們接受過藏族文化的熏陶和教育,自己本身又有素質,定會搞出東西來。雖然現在過得比較清貧、比較艱難,但我們一定會成長起來的。現在,我們第一步已經邁出來了。”談到藏人團隊的組建時,接受專訪的萬瑪才旦如是說。
如今,萬瑪才旦的“周密”計劃已經實現:劇組團隊中,編劇導演由萬瑪才旦擔任;攝影由畢業于北京電影學員攝影系,現在為專業電影攝影師美術師的松太加擔任,參與拍攝了《靜靜地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最后的防雹師》等獲獎影片的拍攝;錄音是由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錄音系的德格才讓擔任,參與了《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和《老狗》主題曲設計和錄音工作;制片是由北京喜馬拉雅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桑杰尖措擔任。這支團隊先后完成了影片《靜靜的嘛呢石》、《最后的防雹師》、《尋找智美更登》、《喇叭褲飄蕩在1983》、《老狗》、《五彩神箭》及《塔洛》的制作;獲得了第2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處女作獎、第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導演獎(《靜靜的嘛呢石》)、第1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攝影獎(《五彩神箭》)等獎項。
這支團隊用藏式的思維和審美,將鏡頭有意的避開藏地風景轉而伸進了藏區的村莊和寺院,展現了一個個淳樸原生態的藏人生活圖景。
(二)堅持母語創作,大膽啟用非職業演員。
這里所說的母語創作即藏語電影創作。“藏語電影”是“母語電影”的一種。是在2004年電影體制改革之后出現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新形式。其特征有:由非國有電影機構投資,主創人員具有少數民族身份,影片的主題奪聚焦在少數民族文化可憂慮的生存狀態,或隱或顯地表達對“現代化”的質疑與對民族文化反思情緒。3 這一名詞的誕生與2005年萬瑪才旦電影《靜靜的嘛呢石》有關。2005年之前的藏族題材影片均為普通話配音,族群的話語隱沒在國家民族的統一表述里。作為第一部采用藏語對白和漢語字幕電影,《靜靜的嘛呢石》在電影意義的敘事里,是劃時代的。
從最初的《靜靜的嘛呢石》到最近的《塔洛》無一例外都堅持母語創作,母語對白讓影片更好地呈現出了原生態的粗糲質感;萬瑪才旦說過:他要把電影拍給新一代的藏族人、讓他們了解自己的歷史。母語電影會讓他們感覺到親切,他們看到和聽到的都是自己真實的生活。藏區外的人則深深沉浸于其中的親切感動、真實如紀錄片一般的風格。正如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田壯壯這樣評價萬瑪才旦的影片:我能夠很強烈地感受到他的那種撲面而來的一種真實!作為雙語創作的作家和導演,萬瑪才旦認為:“藏語在表現力上與漢語的區別在于:藏語的貢獻在佛法佛學上,其詞匯量比較豐富,而文學詞匯則相對比較弱一些。在精神世界的某些方面,藏語比較漢語而言更擅長去表達。”藏語特有的緩慢、停頓的語感正好吻合了高原地區藏傳佛教熏陶下的人們的一種寧靜、舒緩富有哲思的精神生活方式。
熱衷于表現比較廣闊的現實生活面的電影導演,都傾向于選用非職業演員。他們可以在一部探索現實的影片成為現實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又不使自己的生活成為注意的中心。4 對于想要展現藏區真實生存狀態的萬瑪才旦來說,啟用非職業演員是個不二選擇。以處女作長篇《靜靜的嘛呢石》為例,影片中小活佛、小喇嘛、刻石老人與現實生活中的身份是一致的。這樣一來,人物在語言和動作表演等細節上就變得極為自然,片中喇嘛們披袈裟的動作流暢自然、刻石老人刻石動作老練有力、小喇嘛在宗教和世俗生活中的搖擺于好奇,這些都是職業演員們短時間內很難習得的。
此外,在2015年新片《塔洛》中,萬瑪才旦令人意外地選用職業演員作為男女主演。影片講述孤獨的牧羊人“小辮子”(由西德尼瑪飾演)進城辦身份證,并邂逅一名理發店女孩(由楊秀措飾演),與之產生戀情的故事。男主角塔洛的扮演者是西德尼瑪是國家一級演員,在藏區地位的相當于趙本山,在影片“理發”這場戲中,剪掉了留了17年的小辮子。飾演理發店女孩一角的是藏族歌手楊秀措。之所以選擇職業演員甚至是明星,萬瑪才旦認為《塔洛》對角色表演的要求很高,加上自己在創作劇本的時候就想到了西德尼瑪,所以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導演萬瑪才旦關于非職業演員的選擇一方面出于為呈現真實藏區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藏區職業演員稀缺現實背后的無奈之舉。非職業演員也好,職業演員也罷,只要能更好地為萬瑪才旦電影創作服務,都是最好的抉擇。
(三)用鏡頭呈現真實的藏區狀態。
長鏡頭的嫻熟運用是萬瑪才旦電影的顯著特點。
“長鏡頭理論”是法國電影理論家巴贊根據自己的“攝影影像本體論”提出來的和蒙太奇理論相對立的電影理論。巴贊認為,長鏡頭表現的時空連續,是保證電影逼真的重要手段。其特點是強調畫面固有的原始力量,強調生活的真實性,可以“讓觀眾自由的選擇他們自己對事物和事件的解釋”。這一理論符合導演萬瑪才旦關于主張電影反映藏區現實,將自己隱藏在攝像機后面很遠的地方,不輕易表露心跡的初衷。
萬瑪才旦曾在專訪中說過:“我們希望可以拍出大環境中的人物的生存狀態。”通過大量長鏡頭的運用,使觀眾透過鏡頭窺見到了真正原汁原味的藏人生活圖景。
例如:在短片《草原》最后,多洛村長的兒子承認自己偷了措姆阿媽的放生牛之后,父子倆牽著牦牛去找措姆阿媽還牛認錯的長鏡頭使用。導演采用“降”的攝影機運動方式,拍攝父子倆牽著牦牛走向草原深處的背影。前方遠處的大山以及近處仿佛觸手可及的草地映入眼前。這一長鏡頭的運用不僅展現了美好的龍美草原風光,同樣也展現了草原上人們的心靈之美。畫外音的念經設置,更是在結尾升華了導演的創作意圖。
再如影片《尋找智美更登》中,導演一方面通過攝影機遠距離拍攝行進在路上的汽車的長鏡頭,展現出藏區的村莊、寺院、城鎮、學校和機關單位,多角度多方位的展現了真實的藏區圖景;另一方面,將攝影機對準了行進中的汽車內部,將司機、老板、導演、攝像和蒙面女子攝入畫面,隨著老板對自己過往愛情的講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表情。老板的不停講述和沉默的蒙面女,車內坐著的一行人和車窗外忽閃而過的景象形成了動與靜、靜與動的鮮明對比。萬瑪才旦通過長鏡頭內部的場面調度使得看似平常的鏡頭,充滿了張力。
三、結語
不管是從全藏人團隊組建、母語創作、非職業演員的選用還是長鏡頭的使用,萬瑪才旦都曾經歷眾多困難:團隊組建,在萬瑪才旦電影創作旅途中由弱變強;堅持母語創作的萬瑪才旦電影,面臨著邊緣化的現實;非職業演員的選用,也曾在攝制現場面臨一排再拍的尷尬境地;長鏡頭的頻繁使用也曾被影評人批評為:退不了的萬瑪才旦電影。總而言之,不管困難幾何,萬瑪才旦依舊循著他自己信奉的那條道一直走下去。恒久不變的是萬瑪才旦那顆還原真實藏區的赤子之心。
未來,只期待萬瑪才旦電影創作穩穩地走下去,為我們接連呈現出更多打動人心的作品。
注釋:
1.龍仁青《把沉靜賦予紛繁世界——萬瑪才旦和他的作品印象記》 《青海湖》 P28
2.李彥《靜靜的嘛呢石》 P27
3.胡普忠 《藏語電影的生產背景與文化傳播》《民族電影》 P46
4.齊·克拉考爾 《論電影演員》《電影藝術》1980年01期 P44-P45
G632
A
:1671-864X(2015)10-0160-03
李榮(1989—)?,女,漢族,湖南益陽人,現為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2013級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