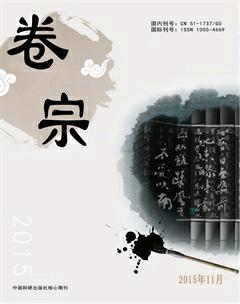小議“夷夏之辨”在中國近代的演變
簡榮平
摘 要:“夷夏之辨”觀念的核心是一種“文化優勢論”,古代中國的文化優勢成就了這一觀念,并使之長期存在,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中的一部分,成為中國處理民族關系、處理外務的準則。近代西方文明的沖擊,使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之上的傳統“夷夏之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開始發生變化。中國人被迫對西方列強重新定位, 具有近代意義的大民族觀逐漸萌生與形成, 傳統的“夷夏之辨”的民族觀、文化觀、種族觀也完成了歷史使命,在革命前進的歷史洪流中歸于沉寂。
關鍵詞:“夷夏之辨”;民族主義
“夷夏之辨”是中國古代儒家的基本政治思想,歷來得到封建統治者的極力推崇,并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嚴格執行。“夷夏之辨”曾一度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融合,加速了中國一體化的進程,其作用功不可沒。但是,歷史發展到近代,由于自身經濟發展的滯后和文化的保守,再加上列強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滲透,打破了中國傳統社會一直所認定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封建專制政體已成為社會進步的桎梏,而西方的先進科技、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和文化體系又在不斷沖擊人們固有的文化定位,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自身和列強的關系,導致了“華夷之防”的疲軟, “夷夏之辨”出現遞嬗。
1 鴉片戰爭前清代的“夷夏之辨”觀念
清朝以滿族統治中原,首當其沖地遭受漢族士人“攘夷”的非難,統治者以理學的君臣、父子之倫和“有德者據天下”作了變通,同時執行民族高壓政策,再加上擁有高度繁榮的封建經濟,所以較快地撫慰了漢族士人心中的不平,沖淡了傳統的華夷觀念,確定了滿族作為華夏正統組成部分的地位。因為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疆域遼闊,己奠定了中華民族現今的格局,所以滿族在取得華夏身份后,“夷”就成為對外國的專指。
清初統治者勵精圖治,休養生息,贏來了“康乾盛世”的蓬勃發展局面,這種良好的發展態勢加重了統治者“天朝上國”的自閉心理。由于受地理知識的局限,統治者不知海外有多么廣闊的文明世界,醉心于自身遼闊的疆域,自認為中國就是世界中心,外邦為夷狄,無力與“上國”抗衡。這種“中國世界中心論”導致清廷自視其大,鄙視外邦,乾隆時修訂的《皇朝文獻通考》對世界就作這樣的描述:“中土居大地之中,浪海四環。其臨邊傍海而居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裔之為言邊也。”把外國看作是“裔”,是邊陲小國,不足與天朝相提并論,只有承襲天朝恩澤的份,所以極度地輕視外國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豐厚的底蘊鋪就了清朝統治者的倫理文化本位心理,他們認定的是儒家的禮儀、典章和聲文教化,對外來文化一味地排斥,認為其一無是處。所以當外國使者來華送來展示其科技水平和工業實力的豐富禮品時,清朝統治者不但總是以“天朝不寶遠物,凡爾國奇巧之器,亦不視為珍異”,“天朝撫有四海……無所不有……并無需爾國制辦物件”等口吻傲視外來文明,持全盤否定態度。而且,統治者僅簡單比較這些東漸勢力的倫理思想和行為習慣,就認為其是未經孔孟教化的“化外之夷”,而根本不予重視,實行傲慢的閉關政策。
清朝統治者的自迷心理導致了閉目塞聽和盲目排外,壓制了外來勢力的東漸。這一時期“華夷之辨”的主旨是“中國中心論”和“倫理文明優越感”,對“華夏”自視過高,而對“夷狄”一味地貶斥。殊不知,國外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正在以日行千里之勢向前發展,中國已漸失其優勢地位,淪落到世界的邊緣。資本的原始積累必然伴隨著血腥的擴張,列強罪惡的腥手終究要開啟中國的大門。鴉片戰爭一聲炮響,驚醒了酣睡的統治者和普通百姓,使他們認清了中國中心地位的失落,開始突破“夷夏之辨”的嚴防,逐步學習西方的器物、制度和心性(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層面的先進文化科學知識。
2 鴉片戰爭時期的“夷夏之辨”觀念
鴉片戰爭中列強的堅船利炮給統治者以強烈的震憾,驚醒了他們“天朝上國”的迷夢,也促使一部分有識之士擺脫虛驕之氣,睜眼觀察陌生的外部世界。以魏源、林則徐、姚瑩等為代表的地主階級先進分子開始從鴉片戰爭失敗的慘痛教訓中認真地分析中國失敗的原因,認為中國失敗的中心原因是技術的落后,技不如人。承認技術落后于“夷狄”,已走出了“中國中心論”的第一步,但他們仍然認為這只是中心初步受損而無大礙,仍可補救,中國的中心仍具有實力,只要學習西方的技術,就能重新自強,反過來就仍能節制諸“夷”,魏源他們就是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作為當時的理論依據是“器變道不變”,中國傳統的倫理規范“道”是不能改變的,而具體的技術“器”卻可以變通,達到自強、衛“道”的目的。所以這一時期雖然“華夷之防”打開了缺口,但學習列強的只限于軍事、制造等器物層面,學習的終極目的是“制夷”,即再度維護中國中心權威。魏源、林則徐他們如此,后來的洋務派、早期維新派亦是如此,都是主張學習西方的技術這個“末”,維護孔孟之道這個“本”。
但是,魏源他們雖然主張學習西方的器物,但已不自覺地超出了這一層面。就魏源所首倡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言,他所學的“技”,即非僅限于器物,與戰艦并列的“養兵練兵之法”,已涉及到軍事之管理、訓練、教育乃至人的素質的改善,他不鄙視西方器技為“奇技淫巧”,而認為“所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反對恪守祖制的泥古不化,主張“變古愈盡,便民愈甚”,他鄙薄那些“徒知侈張中華,未睹寰瀛之大”的愚昧統治者,嘲笑他們:“島夷通市二百載,茫茫昧昧竟安在?,更為可貴的是,他們在悉“夷情”,譯“夷書”的過程中將學習的領域擴展到了對列強的歷史、政治、商務、文化、教育等眾多方面.比魏源稍后的馮桂芬就在他的《校邠廬抗議》一書中,除了“制洋器議”以外還有“采西學議”、 “變科舉議”、“改會試議”諸篇。他指出“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不符不如夷。”當然,他們畢竟是統治階級的一分子,擺脫不了封建禮制的傳統束縛,他們不敢離經叛道,所以在各方面都不敢太深人;另一方面,他們都沒有直接生活在西方的土壤中,只能是膚淺地了解西方的一些基本知識,體驗不到西方的制度、文化在當時的先進性,所以也不可能提出全面學習西方的主張,但做出“師夷”的選擇就已掘開了“華夷之防”的堤壩,日后必然迎來更轟烈的局面,將“華夷之辨”推向崩潰。
作為這一時期“夷夏之辨”只是初步松動,主要還有來自保守派一方強烈壓制的原因。保守派堅決反對學習西方,認為學習西方就是以“夷”變“夏”,就是拋棄祖宗,就是大逆不道。《江寧條約》訂立以后,這些人固然憤慨于割地、賠款,然而更為痛心的還是外國人“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認為“國體之淪失以此為最”。他們振振有詞地說:“《春秋》所最重者,冠履之分;所最謹者,華夷之辨……今督撫之尊,不止大國諸侯,竟下與犬羊之逆,用平行禮.不特褻瀆衣冠,為中外所恥笑,且使各夷聞風效尤,等威莫辨,中國又何恃以為尊乎?”在當時清朝還能維持國家的統治和士林風氣還沒有得到極大開發的情況下,保守派的這些論調仍能在很大程度上束縛士人們的意志,使他們不敢悍然突破“華夷之防”。所以說,在強大的抵“夷”勢力的控制下,“師夷”的效果不佳是在所難免的。然而,無可否認,鴉片戰爭后,向西方學習促進了中國軍工業和科技的發展,也帶來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水平的快速提高。雖然這種發展是畸形的,但為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及后來資產階級力量壯大,并發起維新變法運動打下了基礎。
3 維新變法時期的“夷夏之辨”觀念
如果說在鴉片戰爭時期,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緣于階級立場,還看不到封建專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束縛,對封建王朝存有強烈的依附心,對“夷夏之辨”也表現出強烈的信守。那么,到了維新運動時,由于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并逐漸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已表現出對封建王朝強烈的離心力,表現出對“夷夏之辨”的背叛,他們極力宣揚資本主義在制度和心性方面的優越性,主張從各方面向西方學習,尤其是政治體制,拋棄了“夷夏之辨”的政治立場。
由于西方進化論思想的傳人,在歷史觀領域突出表現為“器變,道也變”。康有為就指出,“道可變,道各不同”,取代了前期的“變器不變道”的觀念。同以 “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鋪就了道器體用一致的道路。這種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歷史觀突破了前期變易歷史觀死守孔孟儒道不變的局限,表現對封建專制的強烈不滿,主張學習西方的民主共和政體和平等、自由、博愛思想,將向西方學習更深人一層,將“華夷之辨”推向逆轉的尷尬局面。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對待西學和外夷的態度上,也更遞進一層。嚴復主張抓住西學命脈來學習,對西方的世界觀、歷史觀、倫理觀等做出了積極的宣揚,他倡導西方“力今以勝古”的世界觀、“開明自營”的功利主義倫理觀、西方的生物進化論,命邏輯學為“一切科學之科學,一切法之法”,幾乎是以西學為食糧,一反洋務派所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羞羞答答的面孔,將傳統的倫理文明淪于被棄之列。
譚嗣同則以全新的態度來處理與“夷”的關系,他將外國資本主義當作“先生”,自己甘作“學生”,他處理西學的態度是:“彼給于我,我將師之;彼忽于我,我將拯之。”幾乎是一種以“夷”化“夏”的心境。他深知“中體西用”論者最大的顧慮是怕被西方文明同化,但他也意識到了中國大勢已與古時不可同日而語,在世界大勢中,中國已處于從屬地位,如果仍強調“夷夏之辨”只能導致笑話。他說“‘語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今中國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數于夷狄,何嘗有一毫所謂‘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猶不可得,逞言變夷狄?”他認為當時中國連并列于“夷狄”的資格都沒有了,還死守“夷夏之辨”,豈不是自欺欺人,取笑于人。可見,在譚嗣同這里,“夷夏之辨”已到了應該拋棄的地步。
由此可見,“華夷之辨”作為封建教義在進人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后,已喪失其存在的合理性,知識分子對其態度的改變反映了歷史的必然要求。
4 辛亥革命時期的“夷夏之辨”觀念
辛亥革命時期,隨著排滿革命風潮的興起,革命黨人心目中的“夷狄”再度成為滿人的指稱。革命派的劉師培認為“夷夏之辨”是百世不易之理。其視滿人為“夷狄”,從事排滿革命的立場十分鮮明。而且他堅持認為“夷夏之辨”主要為種族之別,力證滿族(滿人)不屬中國,說:“滿、漢二民族,當滿族宅夏以前,不獨非同種之人,亦且非同國之人,遺書具在,固可按也。”當然,他也深知滿族統治者與普通滿人的區別,所以強調排滿是為奪取政權,即“今日之排滿,在于排滿人統治權。民族主義即與抵抗強權主義互相表里,固與前儒中外華夷之辨不同也。使統治之權不操于滿族之手,則滿人雖雜處中國,亦無所用其驅除”。也就是說,他所努力奮爭者是推翻滿族統治,建立漢族統治的國家。這代表了眾多革命黨人“排滿建國”的意愿。
平心而論,中國固有的“夷夏之辨”雖也涉種族之別,但核心不是種族問題,而是文化問題。 “夷夏之辨”最初出現時,人們主要是從族類差異來區別夷、夏的。所謂族類差異,既指人種之別,也包括地域、語言、習俗、生活方式等,而且后者漸居主導。人們認為華夏諸國在經濟、文化、道德等方面都高于、優于夷狄,華夏乃“禮儀之邦”,而夷狄則“被發左衽”、未臻開化。孔子雖也講 “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注重族類差異,但更強調“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即以禮(文化)來區分夷夏。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觀點,提出“用夏變夷”,強調“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即只能用華夏文化改造夷,絕不可能以夷變夏。此種 “夷夏之辨”,已超越種族、血統等因素,而視文化因素為最高認同符號,其所體現的是文化民族主義精神。實際上,對于“夷夏之辨”關鍵不在種族而在文化,可以“用夏變夷”,革命黨人并非全然沒有認識。劉師培曾指出,“用夏變夷”的提出,是因孔子認識到世界總有文明普及之日, “使無禮義者化為有禮義”,“特以聲名文物非一國所得私,文明愈進則野蠻種族愈不能常保其生存”,但是目前“據此以蕩華夷之界則殊不然”。也就是說,談“夷夏之辨”時強調種族之別是時勢所需,排滿斗爭的需要,而文化上的“用夏變夷”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長遠目標。兩相比照,革命派更重視眼前的政治目標,所以更強調種族之別。
從后來的歷史進程看,革命派強調種族之別的民族國家認同和相應的現實策略確有立竿見影之效,但顯然不利于民族團結和中華民族整體的長遠發展,所以一當清朝覆滅民國建立,革命黨人便放棄了基于種族之別的民族國家認同理念,轉而倡導“五族共和”,認同“中華民族”。在這方面,孫中山的論述最為經典,他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講中說:“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并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義乃為完了。”可以說,實現國內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創建中華民族新族體,是“五族共和”政策的發展與升華,也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新的奮斗目標。
中華民國的建立,為國內各民族的平等融合與發展創造出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條件。孫中山、袁世凱、梁啟超、、李大釗、常乃德等這一時期都多次使用過“中華民族”一詞,并對其涵義進行了闡釋。與此同時,一些以推動民族平等融合為宗旨的社會組織如“中華民族大同會”和“五族國民合進會”也紛紛成立,為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建立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民國初年,李大釗在《新中華民族主義》和《大亞細亞主義》兩文中,揭示了滿、漢、藏等族趨于一體化的重要歷史文化因素、血統聯系和現實政治條件,呼吁社會認同五族合一的新“中華民族”,主張以此來培養民族精神、統一民族思想。“五四運動”之后,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在政治界、思想界和知識界的最終確立和逐漸傳播開來。孫中山也在此時明確倡揚開放性的“大中華民族”理念。另外,當時中國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等其他政治、思想派別和人物,也都在中國各民族構成一個整體的意義上,頻繁地使用了“中華民族”概念。從“九一八事變”到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人們認識到民族團結的重要性,于是一體化的“中華民族”觀念,滲透到各民族和各階層人民大眾的心中,最終蔚成一個不言而喻、不可動搖的神圣信念。
參考文獻
[1]李寧. 鴉片戰爭前后的中英關系與“華夷之辨”[D]. 安徽大學 2014
[2]李帆. 辛亥革命時期的“夷夏之辨”和民族國家認同[J]. 史學月刊. 2011(04)
[3]賈小葉. 1840—1900年間國人“夷夏之辨”觀念的演變[J]. 歷史教學(高校版). 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