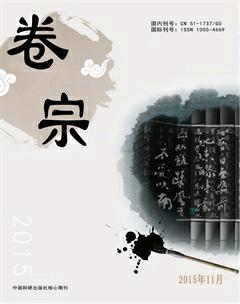新舊之間:一位晚清遺老日記中的思想圖景
摘 要:清末民初是一個新舊交替,中西方思想文化發(fā)生劇烈碰撞融合的時期。身處這一時期的傳統(tǒng)士人在思想上有著新舊元素相交錯的矛盾特征,羅志田指出,過渡時期文化人的思想觀念中往往并有中西新舊“兩個世界”。惲毓鼎就是一位典型的傳統(tǒng)士人,他篤信儒家的道德文章,通過科舉進入官場,長期隨侍光緒帝,對“舊學”、“舊制”推崇之至,且反對迷信西學和改革體制。清廷覆亡,民國肇立后,他以晚清遺老自居,一面固守傳統(tǒng)道德文化,批評民初亂象,一面又受到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影響,逐漸理解并接受了一些新知識和新事物,于是其晚年的思想世界呈現(xiàn)出新舊交錯的復雜圖景。惲毓鼎身前留下的長達120多萬字的個人日記為后人了解這位晚清遺老的真實思想圖景提供了可能。
關(guān)鍵詞:惲毓鼎;守舊派;晚清遺老;思想圖景;新元素
惲毓鼎,字薇孫,又字澄齋,河北大興人,祖籍江蘇常州。光緒十五年中進士,歷任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國史館協(xié)修、纂修、總纂、提調(diào)、咸安宮總裁等職, 特別是擔任起居注官十余年, 成為清宮廷事件的旁觀者和記述者,親眼見證了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期間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其一生影響最大的事件當是其在1907年連續(xù)參倒了軍機大臣瞿鴻禨和兩廣總督岑春煊兩大重臣。惲毓鼎可謂是一位典型的傳統(tǒng)士人,他自小寄居在伯父家,伯父惲彥琦對他實行的是傳統(tǒng)的儒家教育,其思想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后來他以科舉入仕,便將儒家的道德文章奉為立身安國之本。
1 “舊”思想之反映:尊舊學、守舊制、忠舊主
所謂“舊”思想,是相對于清末急劇涌現(xiàn)的以西化為核心的“新”思想而言的。堅持“舊”思想的主體是信奉儒家文化的傳統(tǒng)士人,他們信仰孔孟之道,維護舊學和舊制的尊崇地位,抵制劇烈變革,即使迫于現(xiàn)實壓力,不得不引入一些新學新制,也堅持要以中學為體。這類固守儒家道德思想的傳統(tǒng)士人在民國建立后便被稱為“守舊派”。惲毓鼎便是一位“守舊派”士人,他的日記反映出他的“舊”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尊舊學
洋務(wù)派名臣張之洞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將洋務(wù)思想歸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成為晚清“守舊派”士人抵抗西學沖擊,維護中學正統(tǒng)地位的主要理論依據(jù)。
惲毓鼎也認為學術(shù)應(yīng)以中學為體,過度迷信西學會導致道德敗壞。他認為:“今天下最可憂者,在人心風俗(在上者極力提倡西學,而人心漸與之俱化,一旦泰西有事,恐不免從風而靡耳。總之,不向根本處培植而唯考之以西學為務(wù),是直驅(qū)民離叛也。可恨可痛),其害實自漢學家啟之,使為學、做人分為兩事,而學者不復向身心性命上用工,學校無名教,士林無清議,陵夷澆薄,非一朝夕之故也。向使講學之風猶盛,宋儒之說大行,人心未漓,氣運決不至此!”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諭令廢八股,改試策論,令部臣詳議章程。惲毓鼎上奏指出:“時文之弊,至今已極。……若改為論體,使得镕經(jīng)鑄史,暢所欲言,則有根柢者可以學識見長,而空疏者自無從著手,誠善制也。唯愚意義理之學斷不宜廢。或首場試四書義一篇,五經(jīng)義一篇;次場試史論三篇;三場試時務(wù)策三篇(不必定講西學。凡田賦、鹽漕、錢法、水利、兵刑之類皆是)。”[1]他對改八股為策論表示贊同,但認為不應(yīng)廢除義理之學。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制,惲毓鼎大為憂憤,認為廢科舉可能會導致中華文化的覆亡,指出“若即持此課士,恐十年之后圣經(jīng)賢傳束之高閣,中國文教息滅,天下無一通品矣。”惲毓鼎認為貧弱不是國家目前最大的憂患,世道人心的淪喪才是最令人擔憂的。他在1910年十一月二十四的日記中感嘆:“嗚呼!中國貧弱不足患,而世道人心澌滅潰決殆盡,乃大足患也。”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清廷的統(tǒng)治岌岌可危,惲毓鼎將之歸咎于提出學制改革的張之洞、張百熙等人,認為“今日大局之壞,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壞,根于學術(shù)。若夫?qū)W術(shù)之壞,則張之洞、張百熙其罪魁也。”直接將清廷統(tǒng)治危機歸咎于學制改革。
(二)守舊制
惲毓鼎是舊制度的堅定維護者。他對清末新政持消極態(tài)度,盡管他曾上奏提出保護利權(quán)、修建鐵路、選拔人才等改革措施,但未免已是洋務(wù)派的舊曲重彈。他堅決反對驟廢科舉,認為:“科舉為取士之途,一時未可遽停,八股與策論亦不相上下,應(yīng)俟學堂成效昭然,用人有方,然后議裁議改可也。”他對于官制改革也多有不滿,對之批評道:“自各新衙門之設(shè),求進者麇集輦下。無一定之級,無一定之途,人人存速化之心,習鉆營之術(shù)。此近五年朝局大變象也。破壞廉恥,擾亂志氣,莫此為甚!”認為新設(shè)部門催生了人的鉆營之心,破壞了禮義廉恥的道德感,最終會危害國家。
惲毓鼎堅決維護君主專制體制,反對共和憲政。盡管他曾在1910年向清廷上過《請速開國會以順輿情折》,但那也僅僅是為了讓君主“俯順輿情”,而開國會的目的是為了遏制疆臣的“欺謾”和消弭激烈的“民氣”,最終達到“我皇上操其魁柄,端拱于上,益以見圣主之尊”的作用,表明他并不將開國會與實行民主憲政等同。惲毓鼎反對共和制,認為“共和斷不能久治天下。雖家庭商賈之事,亦須定于一尊,號令歸一,始能行之,何況治天下。”他將清廷最后的覆亡也歸罪于新政,他認為“自來亡國,未如是之速者。其實亂亡之禍,早伏于十年之前。”新政本來是為了挽救清王朝的統(tǒng)治,然而新政的實施卻導致了截然相反的效果,惲毓鼎認為正是新政引起的人心崩潰導致了清廷的速亡:“三年新政,舉中國二千年之舊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與劃除,無事不紛更,無人不徇私,國脈不顧也,民力不恤也。……日晙月削,日異月新,釀成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之大局”,足見他對新政的不滿。正是出于對君主制的眷戀,袁世凱復辟帝制時,惲毓鼎積極響應(yīng),他領(lǐng)銜代表京兆12縣向袁世凱呈遞更定國體的請愿書,后又當選國民代表,并受到袁世凱召見,成為了舊體制的堅定維護者。
(三)忠舊主
“忠”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道德準則之一。惲毓鼎信奉“忠”的道德,對自己長年侍奉的光緒帝有著深厚的愛戴、感恩和忠誠之情。他稱贊光緒帝:“庸詎知天挺英明,豁達大度,奮發(fā)欲有所為”,認為光緒帝“處萬難之會,遵養(yǎng)時晦,以求自全,有大不得已之苦衷哉!”[2]對光緒帝的處境深表同情,一顆忠君之心躍然紙上。
惲毓鼎將接受新式外交禮儀作是對皇帝的不忠行為,因此,他十分反感新式外交禮儀的推行。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允準外國公使親遞國書,由皇帝親自起立受書,這是一個大膽的禮儀變革。可在惲毓鼎看來,皇帝親自起立接受外國公使遞交的國書乃是嚴重的失禮行為,他在日記中寫道:“聞俄國使臣此次勤見,竟等寶座中階,直逼御案,呈遞國書。又各國使臣欲我皇上起立受書。由總署奏請,竟奉俞旨。嗚呼!諸大臣身受國恩,乃令吾君受辱如此,真萬死不足以贖罪矣。”將接受新式外交禮儀視為君主和國家的大辱,也是作為臣子的大恥。
辛亥革命進一步激發(fā)了惲毓鼎思想里的“忠”。武昌起義爆發(fā)后,他以忠臣自居:“余為世臣,誼當以國同休戚,不能比鄉(xiāng)里諸生,唯有竭吾心力為之。設(shè)有不幸,即以身殉之,無置身局外之理也。”[3]他支持其在兵部任職的長子隨軍南下與革命軍作戰(zhàn),及至清廷覆亡以后,其長子還長期在清小朝廷內(nèi)任禁衛(wèi)軍副都統(tǒng)。民國建立后,他以清朝遺老自居,反對民國政府,在1912年的端午節(jié),“仍著清室衣冠行禮”來表示自己的忠心。美籍學者周明之將晚清遺老這種由革命激發(fā)出的“忠”的性格稱之為“潛伏的忠”,這些遺老們在帝制尚存時還有些許改革救國之心,而一旦帝制崩塌,“潛伏的忠”的性格便會被激發(fā)放大,轉(zhuǎn)而抵制新政權(quán)。這個過程被稱之為“忠的再度肯定”。惲毓鼎思想深處的“忠”便是在辛亥革命的激發(fā)下,“再度肯定”而被放大。
2 “新”元素的萌發(fā):接受新知識、新事物
作為一位傳統(tǒng)士人,惲毓鼎的思想底色是“舊”的,尊舊學、守舊制、忠舊主是他“舊”思想的反映。然而其所處的時代畢竟不同了,清末民初是一個新舊交錯,社會發(fā)生急劇變革的時代,受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影響,惲毓鼎的思想世界不可避免地萌發(fā)了一些“新”的元素,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他對新知識和新事物的逐漸理解并接受上。
(一)接受新知識
惲毓鼎早年就經(jīng)常讀《中西紀事》等一些介紹西方文化的報紙雜志,對于西方知識有一定的興趣。
惲毓鼎十分重視學習來自西方的統(tǒng)計學、財政學等實用知識。1908年,他的兒子惲寶銘在法律學堂肆業(yè),他托友人從日本寄回一些新譯出的政法、財政類新書。他將《政法述義》等十余種新書送給兒子,“督其逐次研究”,而“其中《統(tǒng)計學》一種,精要有用,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留以自覽。”并且認為在財政學方面,“今人勝于前人遠甚。”[4]可見其重視西方實用知識的學習。
惲毓鼎對介紹西方政治思想學說的書也很感興趣,他讀完梁纂的《英儒達爾文學說》后,對進化論表示認同,認為“達氏種源論,推明萬物天演競存之理。大凡人物之生,有天然淘汰,有人事淘汰,占于優(yōu)位則勝而存,退于劣位則敗而滅,其理甚精。余驗之萬物,證以中國歷史,確不可易。處今日世界,尤宜熟復斯言。”[5]他在看完梁纂的另一本書《法人孟德斯鳩政學派》第1卷后,認為“孟氏創(chuàng)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quán)鼎立之論,開歐美立憲之宗,誠偉人矣。”[6]對孟德斯鳩的三權(quán)分立學說亦表示贊賞。
惲毓鼎主要通過閱讀一些時人主編的報紙雜志來獲得新知識。他喜歡讀由梁啟超任主筆的《國風報》,他在日記中寫道:“余于近人譯著新書,皆閱不終篇,即生倦?yún)挘殹秶L報》則讀之醰醰有味,益我良多。”1910年由宋教仁等執(zhí)筆,革命派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民立報》,多刊載時事政論、介紹新學的內(nèi)容,十分流行,惲毓鼎對于其中介紹新知識的內(nèi)容很感興趣,認為“此報于政說學理特詳,且具卓識,為南北各報之寇,而摭拾豐富,零金碎錦,多可采之辭。”[7]1911年以后,惲毓鼎又訂閱了專以刊登政治、經(jīng)濟等社會科學著譯文章為主的大型綜合性刊物《東方雜志》,他在日記中稱贊該刊上的文章“理博趣昭,亦頗引人入勝。長年多暇,以此為遣日之資,殊為不惡。”此外他還訂閱了《不忍雜志》、《庸言報》、《亞細亞》、《國華》等報刊雜志,他甚至認為自己通過閱讀報刊雜志汲取新知識“不過一年,即可成政治、法律學問通才。”惲毓鼎在不知不覺間已經(jīng)逐漸接受了新知識。
(二)接受新事物
受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影響,惲毓鼎在清末逐漸接受了政法、財政類經(jīng)世實用的新學教育。在維新思潮漸盛的1897年,他同意家塾先生提出給他兒子加授算學的建議。[8]科舉制廢除后,朝廷以新學招攬人才,他也讓家中子弟學習新學,以新知識來適應(yīng)現(xiàn)實社會的需要,他認為:“科舉雖罷,子弟不能不讀書”,他還命長子“專一研究政法學,為他日致用之道”。1908年他又送另一個兒子入法律學堂肆業(yè),四年后另一個兒子也入新學堂學習政法知識。可見,盡管惲毓鼎尊崇儒學,但當社會需要經(jīng)世之學時,他也會適時地變通,支持家中子弟學習新學,以適應(yīng)時代需要。
惲毓鼎也積極參與新式學堂的創(chuàng)辦活動。如江蘇同鄉(xiāng)會館設(shè)有旅京江蘇籍官紳合辦的子弟學堂,他一直參與江蘇學堂的事務(wù),后來擔任監(jiān)督。此外他還參加一些教育團體的活動。如1909年4月,他參與旅京教育總會,被舉為會長,負責統(tǒng)籌旅京各學堂教育事務(wù)。6月參加中外教育界人士在京成立的世界教育會,“各國學界有名者皆充會員”,他作為中國兩個代表之一,與英、德、美、奧、日本等國8人參與此會。1912年,他又參加教育統(tǒng)一大會,會員110人。成立會上他“登臺演說教育原理,眾多拍掌”,經(jīng)投票公舉,他以一個舊派人物,與新派人物“當代聞人”湯化龍、章炳麟等共4人當選為理事。
此外,惲毓鼎對一些新式文化生活也進行了嘗試,如他雖然嗜好京劇,常到戲園看戲,但也時常陪同妻女家人去看新劇和電影。1907年北京開辟了農(nóng)事試驗場,附有動物園,是北京第一所公家花園,他也時常陪同友人及妻女家人去游玩。這些新式文化活動也增進了他對新事物的了解。
學習新知識,參與新式教育活動,體驗新式文化生活,這些都對惲毓鼎的思想產(chǎn)生了影響,并使之萌發(fā)了一些“新”元素。當然,惲毓鼎始終認為傳統(tǒng)道德才是人心的真正歸宿,但是他也認為在現(xiàn)今時代,如果不了解新學,就不能成為實用性的人才。他在1912年的日記中提到:“身處今日,貴有舊道德,尤貴有新知識,否則將無以自立于社會中。”[9]雖然內(nèi)心仍然堅守著舊道德,但也不能不接受新知識,新舊交錯成為一位晚清遺老思想世界的真實圖景。
3 小結(jié)
惲毓鼎生活在一個西學東漸,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融合的新舊交替的劇變時代。他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和影響,儒家的道德文章在他心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使他成為一位擁護舊制的“晚清遺老”。但時代畢竟不同了,隨著新思潮新事物的不斷涌現(xiàn),他的思想也會受到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影響,逐漸萌發(fā)出一些“新”的元素,理解并接受了一些新知識和新事物,于是其晚年的思想呈現(xiàn)出了新舊交錯并存的特征。由此可見,在清末民初這個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所謂“守舊派”士人也并非完全地守舊,他們在心理和思想層面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他們的思想新舊并存,很難截然區(qū)分。惲毓鼎是這一類傳統(tǒng)士人的代表,然而隨著被貼上“守舊派”的標簽,他們思想中的“新”元素逐漸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湮沒無聞。
參考文獻
[1] 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第77-82頁。
[2]惲毓鼎:《惲毓鼎澄齋日記》[M].史曉風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3頁。
[3]《惲毓鼎澄齋日記》,第160頁。
[4]《惲毓鼎澄齋日記》,第276頁。
[5]《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15頁。
[6]《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62頁。
[7]《復陳新政折》,惲毓鼎:《惲毓鼎澄齋奏稿》[M].史曉風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頁。
[8]《惲毓鼎澄齋日記》,第354頁。
[9]《請速開國會以順輿情折》,《惲毓鼎澄齋奏稿》,第123-124頁。
[10]《惲毓鼎澄齋日記》,第436頁。
[11]《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55頁。
[12]惲毓鼎:《崇陵傳信錄》[M].中華書局編輯組主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0頁。
[13]《惲毓鼎澄齋日記》,第157頁。
[14]《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17頁。
[15]《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96頁。
[16][美]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8頁。
[17]《惲毓鼎澄齋日記》,第381頁。
[18]《惲毓鼎澄齋日記》,第381頁。
[19]《惲毓鼎澄齋日記》,第382頁。
[20]《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36頁。
[21]《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93頁。
[22]《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36頁。
[23]《惲毓鼎澄齋日記》,第662頁。
[24]《惲毓鼎澄齋日記》,第141頁。
[25]《惲毓鼎澄齋日記》,第276頁。
[26]《惲毓鼎澄齋日記》,第450頁。
[27]《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97頁。
[28]《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91頁。
作者簡介
蔡志鵬(1990—),男,漢族,江蘇鹽城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2013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