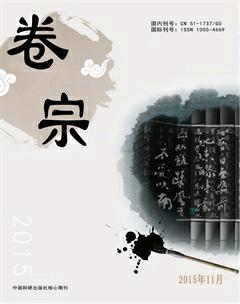德國斯特萊斯曼時期對蘇政策研究
余珮瑤
摘 要: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魏瑪德國外長斯特萊斯曼冷靜的分析了魏瑪共和國所面臨的內外形勢,從德國的實際出發,憑借高超的外交技巧,縱橫捭闔,執行了理智又務實的外交政策:他利用東西方的矛盾展開外交活動,堅持以“蘇聯牌”為爭取德國大國地位恢復的砝碼,起到了輔助對西政策的作用;在1923—1929年間,因為國際形勢和德國地位的變化,斯特萊斯曼的對蘇政策略有不同,但始終保持著對蘇友好的基調,幫助德國在國際競爭中逐步恢復了大國地位。
關鍵詞:斯特萊斯曼;魏瑪德國;對蘇政策
魏瑪共和國時期是德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階段,短促而又意義頗重。它結束了德意志第二帝國,施行了廣泛的改革,在“經濟民主”和社會保障領域開創先河,文化上欣欣向榮,但種種繁華背后掩蓋的紛繁復雜的矛盾糾葛。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斯特萊斯曼在其中閃爍著異樣的光彩,他在“百日新政”以及此后擔任六年外長期間見證了魏瑪德國的興盛與衰亡。
1 斯特萊斯曼時期的對蘇政策
斯特萊斯曼時期的對蘇政策是指1923—1929年間他擔任總理的百日和此后六年外長時期的對蘇政策。這六年里,由于德國在國際環境和經濟條件上的變化,可以1923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魏瑪德國剛剛經歷了魯爾危機,經濟創傷尤為嚴重,而其戰后一直以來的擺脫凡爾賽體系的外交總目標也給斯特萊斯曼提出了新的挑戰,這一階段他的外交政策較為小心謹慎,緊密地配合著他對戰勝國的外交博弈。后一階段,魏瑪德國在國際上地位有所提高,經濟又在穩步恢復發展,使其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在對蘇政策和西方政策上有了更加積極果斷的底氣。而在論述具體階段之前,分析魏瑪德國在1923年之前的對蘇政策以及國家民眾對于蘇聯的態度變化也尤為重要。
(一)對蘇政策的背景
在斯特萊斯曼執掌德國外交之前,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利益集團中對蘇聯的態度迥異。從戰敗到1923年,德國幾經反復,走上了結納蘇俄以擺脫孤立并抗衡協約國的道路。
德國統治集團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敵視是不言而喻的。他們中許多人本不傾向于對蘇友好合作:社會民主黨是強烈反蘇,主張西方政策的;國防軍魯登道夫、馮·德·哥爾茨集團認為對蘇俄除了徹底的反布爾什維克之外,談不上任何政策;工商界中的極右勢力認為,應在俄國恢復君主制來開辟俄國市場,否則談不到對俄合作。
與蘇俄共處與合作,從根本上講是符合德國統治階級的利益。以鋼鐵等重工業壟斷資本十分垂涎于蘇俄廣大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德國軍人集團為了逃避凡爾賽對德國軍備的限制監督并渴望有朝一日洗雪戰敗之恥,以謝克特為代表的多數人主張與蘇俄合作。所以,在德國工業、軍事、外交各界中,自始就有比較強大的主張與蘇俄合作的力量。從1919年起,他們就開始同蘇方人士接觸,試探與蘇合作的可能性。
1922年熱那亞會議,德國在英法事先達成協議的情況下,修改條約無望又處境孤立,深恐協約國與蘇俄達成協議會使德陷于更深的孤立。德國簽署了拉巴洛條約。條約規定,兩國恢復外交和領事關系,相互放棄各項賠償要求,按最惠國待遇發展經濟關系。這是備受壓抑的德國與一個大國簽訂的第一項平等條約,它提高了德國的政治地位,改善了德國的經濟處境,結束了德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列寧說得十分正確:“國際形勢的利害關系迫使他們違背自己的愿望而同蘇維埃俄國講和。”
拉巴洛條約引起了軒然大波,它是德蘇友好里程碑式的條約,為此后拉巴洛時代的蘇德合作奠定了基調。它強烈刺激了西方戰勝國,在其與戰勝國之間的國際博弈中增加了籌碼,惡化了德國和協約國之間的關系,最具代表性的沖突便是魯爾危機。魯爾危機的妥善解決是斯特萊斯曼踏上魏瑪共和國政治領域和外交領域的杰作,并為其此后的對蘇政策基調和細節態度的改變開了頭。
(二)小心謹慎的對蘇政策(1923—1926年)
在1923—1926年間,斯特萊斯曼主要精力放在擺脫凡爾賽合約的束縛和恢復德國政治經濟大國地位上。在此階段里,斯特萊斯曼見縫插針,把握時機,小心謹慎的通過與蘇聯的合作作為與協約國換取賠款、收復邊界等利益的籌碼,謀求英美支持及與世仇法國和解。使德國迅速返回西方陣營乃至重新取得往日的地位無疑頭等重要,而維持發展對東方蘇聯由《拉巴洛條約》開創的合作關系則是次要的,在很大程度上主要輔佐于德國在西方的目標追求。他在上臺后不久,即指示恢復了一度中斷的德蘇經濟談判。1924年5月,德國外交部就對蘇關系明確規定,德國在政治上必須“與俄國保持充分諒解的關系”,經濟上必須“力爭在對俄貿易中至少較他國保持優勢”。
此后,如何對待蘇聯提出的締結兩國政治條約的建議,成為擺在斯特萊斯曼面前重要的課題。隨著西方戰勝國加緊扶持拉攏德國及“洛迦諾政策”的推出,蘇聯日益憂慮不安,認為在德蘇關系上“僅僅以拉巴洛條約為基礎已不足以應付已發生重大變化的世界政治的需要”。
由于德國對西方外交不如意,在萊茵公約和與英國駐蘇大使阿拜隆的談話等問題上使其明白,德國很難指望從西方戰勝國手里重新獲取往日的地位和權益,從而更加意識到維持和利用德蘇關系的必要性。蘇聯從5月起積極謀求改善與法波的關系,既力圖加強自身地位,以此來刺激德國。斯特萊斯曼唯恐蘇聯的舉動會損及德國的外交政策。隨著經濟的恢復發展,出現了工業品銷售困難問題,德國迫切要求進一步開拓蘇聯市場。于是,斯特萊斯曼于5月又突出強調“德蘇關系對于兩國永遠具有重大意義”,并向蘇方一再表示德國“進入國聯不會對蘇產生任何不利,我們不會接受現在形式的國聯第16條款”。于是,恰好在洛迦諾會議期間,德蘇簽訂了經濟條約,調整了兩國間一系列重大的經濟與法律關系。此后,斯特萊斯曼又積極促成兩次對蘇聯1.06億和3億馬克的貸款。而締結政治條約一事,在德蘇經濟條約簽訂后向來訪的齊切林提出一份備忘錄草案,旨在打消蘇聯對德可能參加反俄戰爭的顧慮。3月國聯會議上,由于法波等國從中作梗,使德國加入國聯暫時受阻,斯特萊斯曼才又一次打了“俄國牌”,終于決定迅速與蘇締約。
縱觀1923—1926年間斯特萊斯曼的對蘇政策,尤其是德蘇友好中立條約的簽訂來看,此階段體現了斯特萊斯曼謹慎的態度,他不斷在對西政策受挫時使用對蘇友好政策來刺激和促使協約國的讓步。
(三)積極果斷的對蘇政策(1926—1929年)
隨著德國地位的迅速提高,斯特萊斯曼的外交政策在加緊實現對西方的各項目標的同時維持與蘇合作的基調。斯特萊斯曼在此階段的對蘇外交較前一階段顯得更積極果斷。
斯特萊斯曼在一系列國際事務中積極采取了與蘇合作的方針。這突出表現在對待“東方洛迦諾”及波蘭和立陶宛沖突問題上。1926年秋起,波蘭在英國支持下企圖實施其籌劃已久的“東方洛迦諾”計劃,即建立一個由波蘭領導包括波羅的海三國的聯盟集團以對付蘇聯或德國。但是立陶宛與波蘭之間存在著領土糾紛,并一貫主張由波羅的海三國組成小協約國來維持當地安全,因而堅決反對波蘭計劃,以致波、立矛盾不斷激化。對此,德蘇客觀上有著一致的利益目標——都反對波蘭的擴張意圖。于是,斯特萊斯曼與蘇聯經常保持接觸和交換意見,并對蘭曹一再強調:“我們必須保護立陶宛,并從經濟上加強它。在這方面與蘇聯達成一致是符合我們愿望的。”
斯特萊斯曼還積極支持蘇聯參加國際裁軍會議,爭取恢復德國的軍備平等權。1928年他極力主張讓蘇聯加入非戰公約。年底德國又先后與蘇聯達成了莫斯科經濟議定書和調解協定,在兩國經濟貿易問題上進一步的發展。
1926—1929年階段斯特萊斯曼外交體現了較積極地維持了對蘇合作關系的態度。因此有學者認為德蘇中立條約簽訂后的此階段是德蘇關系發展的“黃金時期”。
2 斯特萊斯曼時期對蘇政策轉變的原因
從最初的對蘇俄的反感情緒,到后來堅持與蘇保持友好關系,斯特萊斯曼經歷了不同態度的轉變歷程。其中自然有其成長經歷和工作經驗的累積,也是其緊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發展和自身素質閱歷提高的體現。
(一)出身與經歷
在斯特萊斯曼的大學時期,經過學習和社團生活的鍛煉,他從內斂的學者成長成了精明的實干家。他了解了自由主義對于德國的重要,也明白了改良比革命更能以最小的社會代價換取最大的社會進步。這種認識逐步的使其獲得了獨立的思考能力和務實的態度,尤其是這種務實的態度,使得其在此后為魏瑪德國爭取國際利益之時,時刻把利益擺在首位,根據不同的階段的形勢變化而轉變對外政策。
在他的五十一年的生命中,有四十年之久都生存在帝國時代,毋庸置疑,帝國時代對于斯特萊斯曼的品質、想法和抱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對于帝國的緬懷和初期對魏瑪共和國反感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更重要的是,在參與政黨的斗爭中斯特萊斯曼認識到,回歸君主獨裁制度并不能實現其強大德國的政治目標,適當的妥協與合作才能擺脫政黨林立造成的混亂局面,于是更穩定地進行他的策略:堅持在現有的體制中爭取更大的國家利益。
這種種經歷使得斯特萊斯曼愈加認識到,為了堅定的政治理想和目標,需要敏銳的洞察力和適當的妥協精神。而在輔助對西政策的對蘇政策中,正是這些素質和準備使得斯特萊斯曼能正確認識國際形勢和自身實力的變化,并適時調整外交策略,為國家爭取更大的利益。
(二)外交目標與意識形態的博弈
鑒于兩國社會制度根本對立,斯特萊斯曼明確表示,從總作戰略上來看,“我對我們與蘇關系估價不太高”,對德國復興來說,與西方戰勝國達成協議遠比維持與蘇合作的拉巴洛政策重要。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只要布爾什維主義在那里長久地統治著,我無法對德蘇結合有許多期待”。他還甚至說過,德國“與共產主義俄國聯姻,無異于與一位欲謀害本民族的兇手同床共寢。這種虛假最終將不可能長久保持下去”。
盡管斯特萊斯曼把對蘇政策置于次要地位,并且具有意識形態上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敵視,卻并未忽視和武斷地中斷德蘇關系。他從魏瑪共和國的現實出發,從國際形勢出發,也十分清醒地意識到,“放棄與莫斯科的聯系是愚蠢的”。德國必須利用對蘇關系這張王牌來抗衡西方,并“為德國的修正政策保持回旋余地和行動自由”。
這充分表示斯特萊斯曼作為一個出色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國家利益面前一切的主觀因素都可讓位,這是務實的外交策略和目標的需求。
(三)國內環境與國家利益
在斯特萊斯曼上臺之前的歷屆政府的消極對外態度,使得魏瑪德國的處境危險,尤其古諾政府與法國沖突的加劇所導致的魯爾危機問題更是使得德國的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人民失去對這個戰后試驗品似的政權的僅有信任,魏瑪共和國陷入了困境。斯特萊斯曼上臺以及此后六年外長期間所要做的就是運用外交手段積極的處理各種事物,改善魏瑪共和國的處境,與此同時盡可能多的獲得國際利益,這種利益不僅在于與西方爭取政治經濟地位的恢復,也在于與蘇聯在部分領域的合作。
這種友好合作的態度是有堅實基礎的。德國統治階級基于利益的考慮,是有極大的與蘇友好合作的意愿的。重工業壟斷資本十分垂涎于蘇俄的廣大市場和豐富的資源;以謝克特為代表的德國軍人集團,渴望有朝一日洗雪戰敗之恥,主張與蘇俄合作;德國還希望在波蘭問題上得到蘇俄的合作。所以,在德國工業、軍事、外交等各界中,一直有比較強大的主張與蘇合作的力量。
這種實力領域的意愿往往會轉化為積極的政治和外交活動的目標。斯特萊斯曼以工業、軍事、外交界的普遍支持態度為后盾,在綜合了國內的利益所向和務實的外交目標追求,選擇了與蘇友好的態度便是理所當然的。
(四)國際環境與外交策略
戰后魏瑪共和國的外交總目標是擺脫戰敗國的陰影和凡爾賽條約在東西邊界、戰爭賠款、軍備限制的束縛,爭取在政治和經濟上恢復到應有的國際大國地位。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斯特萊斯曼運用自己的外交策略和縱橫捭闔的手段,利用了當時國際環境中的各種矛盾,從夾縫中為魏瑪共和國尋得了一條崛起之路。
在當時的國際上有利于德國的矛盾主要有戰勝國之間的意見分歧、戰勝國與蘇俄的對立。由于各自利益的考慮,戰勝國之間的意見分歧嚴重。德國的宿敵法國是竭盡所能地在割地、賠款、削減軍備等方面大肆削弱和壓制德國;英國持續地貫徹歐洲均勢策略,不允許法國太過強勢以稱霸歐洲,威脅到大英帝國的利益,有意識地遏制法國對德國的削弱行為;對美國而言,經濟發展是這階段最主要利益,過分削弱德國會影響其經濟,于是美國自然對法國的極端行為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正是這種意見沖突,使得斯特萊斯曼得以在其中利用英國與美國的意圖遏制法國,獲得了喘息的機會。
另一個環境是戰勝國與蘇俄的矛盾對立。戰敗的德國與受孤立的蘇俄可以說是處在同樣的壓抑的國際地位。戰勝國一方為了孤立蘇俄而極力拉攏德國,蘇俄也意欲靠近德國以獲得國際上些許支持來擺脫孤立地位,于是造就了德國這一處在東西這個鏈條的中間連接部位的極佳博弈位置,充當東西方的傳聲筒。正是斯特萊斯曼洞悉了國際環境中戰勝國、德國、蘇俄之間的關系,在爭取大國地位恢復之時常常利用“蘇聯牌”來獲得戰勝國的讓步。
斯特萊斯曼在從反感蘇俄到傾心合作,從小心謹慎到積極果斷這兩次對蘇的態度政策的轉變中,都充分觀察和深入考慮了國際形勢的利害關系,從而做出相應了政策的變化。
注釋
[1]由于翻譯原因,下文中施特萊斯曼、施特雷澤曼、斯特雷澤曼等皆為同一人,統一為斯特萊斯曼。
[2]愛德華·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M].倫敦,1950,437.轉引自鄭重.施特萊斯曼的外交活動研究[D].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3]黃正柏.試論二十年代的德國外交[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3(1),3
[4]列寧全集,31卷[M].人民出版社,1984,431.轉引自黃正柏.試論二十年代的德國外交[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3(1)
[5]G.羅森費爾特.1922—1933年的蘇聯與德國[M].柏林,1984,121.轉引自姚華.論1923-1929年德國施特雷澤曼的東方政策[J].武漢大學學報,1997(5)
[6]T.施德爾.拉巴洛條約諸問題[M].科隆,1956,53.
[7]A.安德勒.德國拉巴洛政策: 1922—1929年的德蘇關系[M].柏林,1962,152.轉引自徐繼承.淺析斯特萊斯曼的“穩西活東”策略[J]滄桑,2007(2)
[8]G.羅森費爾特.1922—1933年的蘇聯與德國[M].柏林,1984,181.
[9]Jonathan Wright.Gustav Stresemann:Weimars Greatest Statesman[J].History Today.2002,p25.
[10]K.希爾德布蘭特.國際體制中的德意志帝國與蘇聯:正統還是革命? 1918—1932年[M].威斯巴登,197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