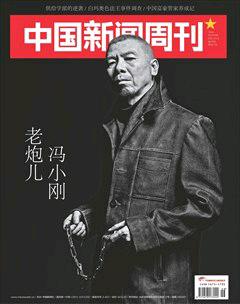中國安保公司“走出去”的困境
王齊龍+郭應喆
11月20日,中國鐵建國際集團(以下簡稱“中鐵建”)3名高管在馬里首都巴馬科麗笙酒店發生的恐怖襲擊中不幸遇難。對于楊明輝來說,這起事件的發生,在讓他覺得痛心的同時,也讓他又想起半年去中非共和國東北部城市比勞的經歷,“啟程前心里忐忑,有闖入虎穴的感覺”。
2015年4月,楊明輝以安防企業德威國際集團(以下簡稱“德威”)首席安保專家的身份,參與到中資企業在中非一項油氣勘探項目復工考察工作中。而在比勞停留的5個多小時,是警員出身的楊明輝2015年多次外勤行動中最為緊張的一段經歷。
兩年多前,中非共和國爆發內戰。此后,比勞被反政府武裝塞雷卡牢牢控制。
“我們是中非內戰后,到比勞當地的第一個中國考察團。內戰后的情況,誰也不知道,中非政府也與當地中斷了聯系。”時隔多月,楊明輝回憶起那次行程仍心有余悸。
但最終,得益于此前在當地的建立的情報網絡,楊明輝一行安然無恙。
楊明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于項目地點位于中非東北角,完全屬于反政府武裝控制區,項目復工所需要的安全保障前提無法由中非過渡政府來提供,只能依靠地方部族武裝,而項目方此前在中非經營的關系網絡發揮了作用。他認為,與項目地的警方、社區及部落等建立良好關系,建立廣泛的信息網絡,將有助于提前獲得危急預報信息。
馬里恐襲慘劇發生后,外界對支持中國民間安保公司“走出去”為中資企業提供更廣泛安全保障的呼聲愈發強烈。
外交與國際關系智庫察哈爾學會12月3日發布的研究報告建議,應該為中國私營安保公司“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為海外中資企業和公民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中國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韓方明還為此撰文稱,“世界級的企業,需要配套世界級的安保公司。應該給予中國的安保公司更多機會,允許他們武裝作業,在實戰中保護中國的海外利益。”

11月20日,在馬里首都巴馬科,警察在發生襲擊的麗笙藍標酒店樓頂巡視。襲擊事件中,有3名中資企業員工不幸身亡。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海外安保的需求也日益增長。
襲擊中資企業多是為了錢
“那是一個土機場,一片平地,連房子都沒有。”飛機還沒落地,楊明輝就觀察到,比勞機場四周有持槍武裝人員把守。
考察團一行6人中,除了楊明輝及另外3名德威安全工作人員外,還包括兩名中資企業的代表。他們此行要與比勞部族長老會面,了解兩家企業合資持有的PTIAL國際公司在當地的油氣勘探項目復工生產的安全性。
中非共和國內戰爆發后,比勞長時間被當地部族武裝控制,而該部族至今拒絕與中非過渡政府和解。PTIAL國際公司在中非東北部的油氣勘探項目也由此被迫停滯,項目人員全部撤離。
進入2014年,中非動蕩局勢有所緩和。是年年底,PTIAL國際公司有了恢復中非項目的想法,并要求負責項目安全工作的德威對項目恢復的可能性展開安全評估。
“我們通過中非政府,聯系上了與比勞部族同屬反政府武裝、內戰前曾建立聯系的恩代萊部族人員,通過他來間接聯系到比勞的部族,傳遞了我們項目方愿意返回當地開采石油、拜訪部族長老的意愿。隨后中轉回來的信息是,他們愿意接待。”楊明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15年3月,項目方同意德威提出的考察方案后,臨時組建的考察團隨即于4月中旬從國內經由法國中轉前往中非。
連年內亂的中非是全球最不發達的地區之一,即便當地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也無力開采。中資企業到當地協助資源開發,為他們創造了致富的途徑。同時,PTIAL國際公司在撤出前曾在當地建設醫院,并雇傭當地人做勘探地點的保安,他們重返當地的決定因而受到了各方勢力的歡迎。當年撤離時未搬走的營地設施和機械設備至今保存完好。
楊明輝稱,安保企業能否在海外武裝作業,得依據東道國的法律。而對保障一個項目的安全而言,除了需要加強人防、物防和技防外,還需要為項目方制定一套完善的公共安全管理機制,理清項目地分支機構各部門彼此間的安保職責,對人員、車輛、物資都需要有相應的管理規定。
他還認為,與項目地的警方等武裝機構、社區及部落等建立良好關系,建立廣泛的信息網絡,將有助于提前獲得危急預報信息。
有著6年境外安保從業經驗的徐磊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相較于針對西方企業展開的襲擊事件含有政治目的,對中資企業等非西方國家企業實施的襲擊,大多是為了錢,“安保工作做到位,將能讓圖謀不軌者心生畏懼,甚至打消念頭。”
根據他的實際經驗,一旦發生武裝襲擊事件,只要自身安保力量能抵御半小時,當地警方一般都能趕到現場,化險為夷。
被“縮水”的安保
2013年5月,楊明輝從警察的崗位上退休。這位三級警監離開警隊后,加入德威擔任首席安保專家。他的首項任務是為中國路橋公司承建的肯尼亞蒙內鐵路項目設計安保服務方案。
楊明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德威原計劃為該項目提供整套的公共安全管理體系方案,涵蓋給肯尼亞政府、項目地安保建設等各方面的花銷,預計為4000多萬美元,不及該項目原總造價預算的138億美元的1%。但項目方認為費用太高,并不接受。
“我們給一大本菜譜,被砍得七零八落。最后只要我們提供風險評估,并在每個營地派駐安全顧問,當助手。”楊明輝說,該項目方案設計前后商談了10個月時間,一直被壓價。
這套“縮水”的安保方案,直接限制了德威工作人員在項目地實際工作開展。
楊明輝說,德威派駐到項目營地的安全顧問及安全官為了建立起廣泛的信息收集網絡,不得不自掏腰包,與當地部落打交道。直到項目開展半年后,德威工作人員收集來的信息起到了安全警示作用,才讓項目方認識到相關措施的重要性,愿意承擔起相關費用。
楊明輝還指出,大型國際企業在海外安保上的投入一般會占到項目預算的2%至5%,甚至能達到6%,但中國企業連0.5%都難以達到。
多名私營安保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部分境外中資企業的安全防范意識不足,在安保方面并沒有持續穩定的投入。一旦襲擊事件發生,將會給境外中資企業造成嚴重的人命財產損失。
曾在中東地區參與安保項目的徐磊表示,在2010年12月“阿拉伯之春”爆發后,中東地區由戰亂引起的社會動蕩愈發嚴重,而中國企業“走出去”越來越多,遭到惡意襲擊的概率也較以往升高。
但讓這位項目經理感到頭痛的是,平日里與中資企業接觸,“攬活”并不容易,“反倒有點安保企業推著境外中資企業往前走的感覺”。
2010年8月中國商務部會同外交部、發展改革委、公安部、國資委、安全監管總局和全國工商聯印發的《境外中資企業機構和人員安全管理規定》明確要求,對外投資合作企業在高風險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時,應建立完整的境外安全制度以確保境外經營活動的安全,包括境外安全管理規定、境外安全成本預算、境外突發事件應急處置預案等。
但楊明輝認為,相關規定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癥結在于海外安全領域缺乏主管部門,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也十分迫切。
“更多的是一種表面工作”
察哈爾學會發布的《私營安保公司:中國海外安全的供給側改革》研究報告還顯示,據不完全統計,過去10多年間,約有70多家中資企業聘用了中國或外國的安保公司,其中包括中國大型的能源企業、工程承包企業、航運企業。
該報告還以2014年中國海外投資存量(6000多億美元)和當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400多億美元)為基數進行估算,假定境外中資企業每年在安保方面的資金投入比例達1%,2014年境外中資企業用于安全方面的開支在80億美元以上。
察哈爾學會研究項目主管、上述報告執筆李少杰認為,私營安保公司的發展正締造一個蓬勃發育的安保市場,也正影響中國海外安全治理的格局。
但李少杰也表示,要推動中國安保企業走出去,還應提供更多支持性政策,包括安保人員持槍立法、安保人員外派涉及到的簽證便利問題。
他還在報告中引述山東一家安保集團負責人的觀點:最大的難點是中國安保行業進軍海外市場缺乏相應的立法(主要是指槍支管理方面的法律問題)支持。沒有立法支持,中國安保人員在海外持槍將面臨違反國內刑法的困境。
對于當下建立中國“黑水公司”的議論,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偉認為,這絕非海外安保的楷模。
“實際上,黑水公司就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雇傭軍,他們在阿富汗、伊拉克開展業務,都是美國主導的一場戰爭下的雇傭行為。這是跟中國當前‘走出去的戰略是不一樣的。這不能作為民營安保公司的典范來比較。”李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離開東道國,任何的安保都不可能很完善地實現”。
近年來,中國民營安保公司“走出去”能力有所提升,但防務研究學者認為,民營安保公司實力仍有待增強。
“目前號稱有海外服務能力的中國安保公司,據不完全統計,可能有二十多家。但大多數主要提供的服務是咨詢、培訓,派出少量的安全官到工地進行一些管理協調。”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研究員汪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實際上這是非常不夠的。說得尖刻一點,這更多的是一種表面工作,如果真正遇到一些嚴重的突發事件,是應付不過來的。”
汪川表示,目前中國僅有不超過4家海外安保公司具備高標準,包括具有國際性行業協會發放的安保資質、擁有持槍許可證、建立自身的情報網絡、與業內的高端安保公司之間有互相配合和合作等。境外中資企業安全保障不能完全依靠于國內的民營安保公司,“在外面的項目可以做本地化的分包,把一些勞務、員工和材料本地化,盡量減少中方人員在海外存在的數量和時間,這是風險控制和風險轉移的一種方式。”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徐磊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