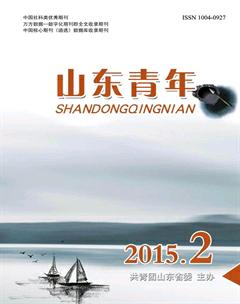淺論《封鎖》中的女性立場
徐丹
摘要:封鎖因愛開始,也終由愛結束。在短暫的、封閉的時空中,一段些許帶有“傳奇”意味的獵艷上演了。小說對于男權社會中,女性,主要是指知識女性被動無力的悲劇命運進行了諷刺與批判。
關鍵詞:封鎖;張愛玲;女性主義;現代文學
“電車停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個‘玲字是冷冷的一小點,一點一點連成了一條虛線,切斷了時間與空間”。
故事發生在戰時的上海,在由于戰爭災難而暫停的電車空間內,一對男女意外地“萍水相逢”了。已婚人夫、銀行會計師呂宗楨,被反印在包子上的字吸引正細細閱讀之時,女主人公吳翠遠,也在一心一意批改學生的卷子。素不相識的二人只因同乘一車并不可能有什么故事發生。要不是呂宗楨一抬頭看見了他討厭的遠房侄子,吳翠遠是不會“被交往”的。為逃避一心想找個好岳家的侄子的糾纏,呂宗楨有意坐到吳翠遠身邊去了,“不聲不響宣布了他的調情的計劃”。
他們的談話漸漸投機到產生愛意,直到涉及婚姻大事。在留下電話號碼后,封鎖開放了。“宗楨突然站起身,擠到人群中不見了,他走了……,電車里點上了燈,她一眼望見他坐在他原先的位置上了。她震了一震——原來他并沒有下車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鎖期間的一切,等于沒有發生。整個上海打了個盹,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
可以說,呂宗楨與吳翠遠的相遇是作者運用敘述技巧有意為之,否則,在電車外的平行的塵世時空中,這二人相交就簡直算是個奇跡了!呂宗楨——“一個整整齊齊穿著西裝戴著玳瑁眼鏡提著公事皮包的人”,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和家庭關系,豐富的社會閱歷,會交際,有城府,即便是在現代社會也是一位極具個人魅力的中年男子;而女主人公翠遠,用當下的時髦話講就只能算是個“經濟適用女”:頭發、長相、裝束都是“千篇一律的樣式”,“唯恐喚起公眾的注意”,“仿佛怕得罪了誰的美,臉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沒有輪廓”,按照父母的期望念完大學之后留校任英文助教。普通的相貌與姿色,空白的戀愛經驗,即便如此,就正常取向的都市女性而言這也是無法遮蔽其對于愛情的深切渴望的。只是或許她還保留著上海知識女性的那份驕傲跟矜持。既不甘心像貧寒人家的女孩樣草草家人,又無法自我奮斗到出人頭地。因此,當面對著呂宗楨的“進攻”時,翠遠初出的震驚和抗拒轉眼便節節敗退,他的花言巧語也能讓她熾熱、快樂,因為他是“一個真的人!不很誠實,也不很聰明,但是一個真的人!”,翠遠需要一個真人,而不是一個好人,不是像她自己和家人那樣的好人,“世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遠不快樂”。這是張愛玲鐘愛的“參差的對照”,于翠遠也是如此。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翠遠愛上了眼前這個陌生的男人,因此才想繼續跟他搭話,想要多了解他一點。男人對婚姻和生活的不滿,女人對愛情的渴望,是他們在情感上產生了這片刻的交匯。翠遠有著地母一般的智慧和胸懷,她看穿了男人卻不去揭穿,充分地理解和寬宥著他。她是宗楨需要的那種能夠“原諒他,包涵他的女人”。
她那少女才有的羞澀令他愉快,使他重燃作為一個單純的男人的尊嚴,那也許是他被磨滅已久的渴望。在此沖動下,宗楨提出了婚姻的話題,卻又因為種種現實的問題很快打起了退堂鼓,對兒女的責任、兩人之間年齡的差距、缺錢的窘迫,對男人來說,隨便一條細節都能夠打敗愛情。但對于翠遠來說,這份真實而自然的感覺令到她愿意拋開了金錢、地位、尊嚴、家庭的。她為宗楨流淚,不但留下了自己的電話,還真切希望對方打來,“如果他打電話給她,她一定管不住她自己的聲音,對她分外的熱烈”。然而,這通電話永不會響起。因為隨著冷冷的鈴聲而來,封鎖解除,他便丟下了她,退回原地。“封鎖期間的一切等于沒有發生,整個的上海打了個盹,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夢醒了,翠遠的愛情也破碎了。
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常常會面臨如此尷尬的境地:平凡如斯卻在偶然的情景下面臨“非凡”的可能性,使她們看到偏離個人生活實際的夢想的曙光,在讓這苦難的現實擊碎夢想,讓女性重新回到冰冷的大地。《花凋》里的川嫦、《沉香屑第一爐香》里的葛薇龍、《半生緣》里的曼禎、《傾城之戀》的白流蘇,還有《封鎖》里的吳翠遠。這種蒼涼是張愛玲鐘愛的“參差的對照”。在《自己文章中》她曾表述過這樣的文藝觀:“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
這種蒼涼感在翠遠的愛情遭遇男人可怕的虛偽和自私后更憑添幾分。呂宗楨雖然是“五四”后接受高等教育的畢業生,但并沒有實現其思想上的解放。為了實現一次拒絕,不惜利用一位素不相識的女性的情感,可見隱藏在其現代開化的外表下拿女性當玩物的封建劣根思想;在短暫的交談后,他發現自己需要一個像翠遠一樣有知識且溫柔、善解人意的女人并毫無保留地向她吐露出自己工作的混沌、家庭的不幸及生活的悲哀,在這里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個正常男人被壓抑的情感的宣泄”,筆者卻感到深層下是女性的受辱和悲哀,翠遠只是一個被需要的人,而不是一個值得去愛去呵護的女人。正如宗楨的結發妻一樣,年輕時的美貌被男人需要,等到人老珠黃即被棄之敝帚;在當下沖動的刺激下,宗楨決定“重新結婚”。似乎這個被世俗封鎖的男人馬上就要沖破所有束縛,為了自己的命運和愛情,開始新生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卻以為了孩子的幸福考量為借口,表示不會離婚,只是娶一個妾。其封建保守的奴性思想此時暴露無遺。張愛玲深刻挖掘出這種麻木的文化人內心殘喘的懦弱、自私的奴性人格。封鎖給了呂宗楨一次釋放情感的機會,同時也赤裸裸的揭露了他的可悲與愚昧:將女性視作男人的附庸,不僅是現代女性的悲哀,更是無覺醒的現代人的無奈。小說與其說是一次失敗的情感遭遇,毋寧說是男人“怕致責任,但求輕松一下的高調調情”。
三
文中多次提及“思想是痛苦的”蘊涵深意且發人深省。我們應當注意小說中出場的其他人物:山東乞丐、公事房職員、長得頗像兄妹的中年夫婦、搓核桃的老頭。他們有人為生計悲歌,有人因工作而勾心斗角,有家庭主婦為了錢發愁絮叨,更有對西學的無知卻不自知,等等。對這些細節的刻畫,無不表現出彼時雖已經過“五四”勵志圖新,但是人最真實的靈魂仍是空虛寂寞,封建殘余仍根深蒂固,如同一只烏殼蟲一樣茍且而活。
電車封而不鎖,與車窗外的真實社會一樣世俗,根本不可能成為惶惶不安的亂世男女渴望的救命稻草。因此,吳翠遠的遭遇就顯得不那么突兀了:女性(包括知識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非理性與無自覺,對自己、他人及所處環境沒有審視性和控制力,在男權主導社會的霸權下,無可避免地遭遇生命的難堪。《封鎖》即是以濃縮的形式來揭示女性生存的悲劇意識和悲涼形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