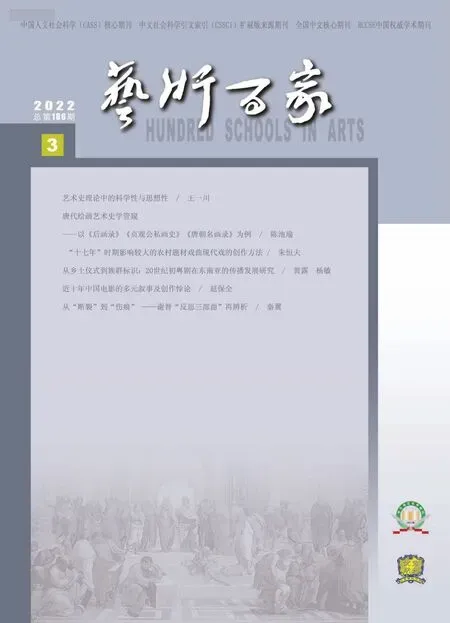步入戲曲:新文藝人的改造
陳宗花
摘 要: 新中國成立后重新建構起來的豫劇演員的主體隊伍,包括幾個來源,其中最主要是經過改造的舊藝人,以及由各文工團轉而從事豫劇活動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新藝人的塑造,不僅是對舊藝人的思想與藝術改造,還包括那些在解放戰爭以及抗美援朝時期已服務于解放戰爭的年輕的黨的文藝工作者。本文以河南豫劇院三團演職人員為例,分析新文藝工作者轉變成地方戲探索尖兵的艱苦歷程。
關鍵詞: 戲曲藝術;20世紀50年代;戲改;藝人改造;河南豫劇院三團;戲曲創作
中圖分類號:J80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50年代是中國戲曲發展的關鍵轉折期,也是一個重要的奠基期,因為大陸從新中國成立后迄今戲曲的基本發展方式、形態、規模都是在這個時期奠定的。50年代重新建構起來的戲曲演員的主體隊伍,包括幾個來源,其中最主要是由各文工團轉而從事豫劇活動的革命文藝工作者,還有經過改造的舊藝人,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戲改過程中,社會主義新藝人的塑造,就不僅僅是舊藝人的思想與藝術改造,還包括那些在解放戰爭以及抗美援朝時期已經服務于解放戰爭年輕的黨的文藝工作者。對舊藝人的改造,豫劇是走在前面的,常香玉代表了一代曾經艱苦地輾轉于舊時代的豫劇演員走向新時代、新社會的渴望與決心,常香玉積極配合改造,并且在為捐獻飛機全國巡演的過程中,受到了強烈的精神沖擊,深刻體會了新的社會觀念、政治觀念與藝術觀念,迅速經歷了精神蛻變,完成了轉變為新藝人的華麗轉身。革命文藝工作者變成地方戲曲藝術探索的尖兵,河南豫劇院三團的演員們也經歷了艱苦曲折的改造歷程,并將戲曲現代戲的探索帶向了一個高峰。豫劇藝人的改造,在全國都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新文藝工作者對戲曲的錯誤認識
來自各文工團的革命的新文藝工作者轉而從事豫劇活動,他們的思想、藝術改造問題長期以來未受到充分重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對新中國成立后豫劇諸多新發展的理解與研究。河南豫劇院豫劇三團的演員隊伍,基本來自于解放戰爭至抗美援朝時期的我軍文工團。全國戰事基本平定之后,為了配合全國范圍內的“文化革命”,一些文工團被要求積極投入到戲改當中,1952年當時在河南省活動的市、專區十幾個文工團整編,一批團員進入河南省戲曲改革的行列當中,其中豫劇三團,基本隊伍就是來源于此。當時河南省選拔60多名條件好、適合演歌劇的同志成立了河南省歌劇團,這批文工團員,大都是1948年至1950年參加革命的青年學生,平均年齡不到20歲,如馬琳、高潔都只有十六七歲,他們普遍具有高、中等文化程度,參加過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運動,一般有兩三年的舞臺生活經驗,是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導下成長起來的的新文藝工作者。①舊藝人進入新社會,是承受著巨大的思想壓力與精神煎熬的,人們往往用脫胎換骨來形容他們蛻變的艱苦歷程,而與之相比,從文工團來的那些所謂的革命的新文藝工作者走上豫劇之路,也并不輕松,同樣經歷了重大的思想裂變。在20世紀50年代末,當豫劇三團成為全國一面旗幟時,這些團員對自己那一段艱苦的思想與藝術轉變歷程也做出了懇切的總結,以當時主要樹立的典型演員高潔、馬琳回顧的最為全面。他們的回憶總結主要圍繞著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新文藝工作者怎樣變成一個為河南人民所熱愛的戲曲演員”②,當時的輿論認為他們的道路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1]。這批文工團員從1952年后轉到地方劇團,這些年輕演員從文工團被調來演豫劇等地方戲,雖然說他們帶著黨交給的重要使命——最初是“在地方戲曲的基礎上發展新歌劇”,之后又改為“以豫劇為基礎,反映現代生活”[2](p.68),同時積極擔負宣傳黨和國家政策方針、教育人民、改造舊戲等重任,但起初他們都覺得不能接受,甚至精神十分痛苦,消極對待,這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源自思想上對舊戲的認識問題。這首先最為突出地表現在對戲曲藝人的認識上。新中國成立前戲曲藝人始終處于社會最底層,長期被侮辱被迫害,并被整個社會輕視、蔑視,新中國成立初期這種偏見仍未消除,這些原文工團員受舊社會歧視戲曲藝人的影響較深[3],人們仍以“戲子”視之,認為“中學生當了‘戲子太丟人”[4]。高潔回憶,不僅自己無法接受,覺得丟人,抬不起頭,而且“那時許多人隱姓埋名,都愿演大花臉,生怕熟人認出自己來”,[5]她自己甚至有過這樣的激烈言論,“叫我當第二常香玉,天天在報上登我的名字,我都不干。我寧愿到話劇團搞一輩子服裝保管”[6](p.193)。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傳統戲曲尤其是地方戲向來不被看重,即使是很多革命干部,黨的文藝工作者們也普遍存在著看不起地方戲的現象,他們并不真正了解地方戲的特點,卻往往出于主觀偏見,以解放區以來的新歌劇,乃至西洋音樂、話劇、歌劇的藝術特質來衡量舊戲曲,因此得出了豫劇等地方戲的藝術層級過低,“粗糙的土里土氣的沒有什么藝術價值”[6](p.193)的結論,認為學唱河南梆子是“新文藝工作者向舊的投降”,是“倒退”[3]。據高潔回憶,“那時我可盲目迷信西洋了。其實,我不但沒看過、沒聽過西洋的藝術,連火車和電影我也沒見過,可就是瞧不起民族戲曲,一心想搞有西洋管弦樂伴奏的歌劇,演員唱的是‘歌,那有多神氣”[1]。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盛行著“用歌劇改造戲曲”的流行傾向,將此視為豫劇今后的發展方向。這種認識在當時頗有市場,體現在豫劇三團初期的編導演作曲等各個方面,《堅持工農兵方向,提高現代戲質量——河南豫劇院三團訪問記》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 建團以后的幾年里,三團演的現代戲大都是重新作曲的,音樂唱腔設計了不少脫離傳統的重唱、四部合唱,不適當地、過多地配備了西洋樂器。這種脫離傳統的作法,在初演《劉胡蘭》時達到了高峰。觀眾們聽了不滿意……說他們演的是“有點豫劇味的新歌劇”。高潔……在那個時候也是熱衷于用歌劇改造戲曲的人之一。有一次演出《人往高處走》,因為這出戲的音樂設計本來已經很“洋”了,劇團的一位負責同志有意識地要她唱那段【慢板】的時候,盡量唱得像豫劇一些。她嘴里答應,心里卻暗暗地想:到臺上我得把洋嗓子亮一手。果然,到那段【慢板】的時候,用洋嗓子一哆嗦,的確也發揮得淋漓盡致,高潔自己心里也夠滿意的了。但是卻引起觀眾的極大不滿:這像什么豫劇![7] 此外,在新中國成立初的舊戲改革中,存在著強烈的否定傳統戲曲的傾向,由否定它的思想意識,連帶否定了它的表現形式,戲劇題材等各方面,如當時有人提出“豫劇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根本不能表現社會主義精神”[4]。這一切在新中國成立初是非常普遍的社會認知。因此這些學生出身、自我標榜為新文藝工作者的原文工團員,無論如何難以接受自己成為戲曲演員的事實。這種沉重的思想負擔使很多演員在劇團初期抱著走著看的態度,未能積極地配合工作,即使之后服從組織原則勉強接受,但思想中的癥結并沒有打開,如高潔稱,“身雖在歌劇團,而思想中卻念念不忘有朝一日有機會我還得離開”,其初期表演的《新條件》雖贏得了一些關眾的支持,但她的心理上,只是在一種顧面子和不能比別人差的自尊心的支配下,努力學習梆子[6](p.193)。
二、在傳統藝術基礎上的新創造 他們的思想轉變是源自整個社會對戲曲的認識變化。隨著20世紀50年代初期戲改中出現的問題逐漸增多,潛在矛盾日益顯露、尖銳的狀況,政府及時作出調整,對民族遺產的地位與價值進行重新估價,并批判蔑視傳統、盲目崇拜摹仿西洋的傾向,文藝界就此問題進行廣泛討論,進行了糾偏。其中豫劇三團就批判了對民族戲曲的虛無主義的態度,以及“用歌劇改造戲曲”的思想[7],這些對出身文工團的戲曲演員們發生了重要影響,逐漸改變了他們的觀念,使他們開始能夠正確地認識到傳統藝術的意義與價值。就在《羅漢錢》演出之后,豫劇三團召開總結大會,組織了高潔等九位同志做了思想轉變的典型發言,其中就“批判了過去對民族傳統的不正確的認識”,高潔后來說,“從那以后,我不但不感到河南梆子粗糙低級,而且認識到它的曲調豐富而優美,具有河南人民樸實健壯的感情。說實話,我已經迷上梆子了”[1]。思想問題解決之后,下面要做的,就是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豫劇表演者、編劇、導演、音樂設計者,等待著他們的是艱苦的學習。豫劇三團掀起了向傳統的唱腔、音樂、劇作、表演藝術等學習的熱潮,當時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兩種方式,以演員培養為例:首先是走出去,高潔向河南省豫劇院院長常香玉學習,馬琳被派到安陽市豫劇團團長崔蘭田處拜師,柳蘭芳到了馬金鳳處拜師;其次是“請進來”,豫劇三團請了很多豫劇名家,如請了吳碧波、張桂花等有名的豫劇演員來團教戲、輔導,還請了豫西調著名老藝人“狗尾巴”和王二順等教男演員唱和表演。“對團里的老藝人,更是要求與他們結成對子,不僅學藝,而且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總的原則就是讓大家“鉆進去”,就是要“鉆到豫劇的傳統中去,掌握豫劇的演唱規律”[8]。這一學習熱潮對編劇、導演、音樂設計、演員、樂隊等水平提高都起到了極好的效果。演員馬琳在崔蘭田處受益頗豐,她在1958年的《演現代劇點滴體會》一文對此作了細致回顧: 黨為了進一步培養我們,1956年初在工作百忙中抽調我到名演員崔蘭田同志那里去學習,可以說,這給我這幾年更深的學習遺產打下基礎。我的嗓子條件不太好,再加上沒有技巧,不會用氣,音位不對,所以經常啞嗓子。這時我就針對著自己的缺點,首先學習如何用氣。在過去,我練氣是練氣,唱是唱,兩者不結合。崔蘭田同志教我結合著唱來練氣,氣是基礎,沒它就不能發聲。嗓子不耐用的原因,就是掌握不住呼吸,一句唱詞該換氣不換,一下子唱完,累的不得了;有時候一張嘴,一口氣放完,使別人聽起來沒有抑揚頓挫。老師教我要叫氣出來得均勻,該放時再放,一句唱中,氣要換的得當,要巧,不能叫別人聽出來。我就結合著她唱的《桃花庵》中罵道姑的幾句戲來練,這幾句戲低音中音多。完全須要吐字清、氣足、有技巧才能唱準。通過這幾句的練習對我幫助很大,我體會到只要把氣用對,音自然就能出來。在音的練習上我抓住重點,先練張口音,就是“啊”音,叫人聽起來很松很亮,我就結合著《秦香蓮》中幾句出來練習,其中有一句“……欺結發”的“發”字,是個張口音,又是個長拖腔,高低音很完全,按拍節計算至少有20拍子,用這句來練這個就非常合適,如果位置音掌握得對,這么長的一個拖腔,你就能唱得很省勁而且音很宏亮。這戲有重點地一個音一個音的練習,效率很大。當我回團再演出《志愿軍的未婚妻》時,即使日夜演兩場,嗓子也沒有什么問題。幾年來我一直是按照這個方法練習,結合自己扮演的不同角色的性格情感的需要來運用唱腔。[9] 演員高潔刻苦學習的情況在當時各類報道中也得到突出宣傳,高潔“特別用心學習常香玉、崔蘭田、桑振君、張桂花等名演員的唱腔和發聲方法。常香玉的真假聲相結合的唱法她也用心學習。同時,她也向藝校的聲樂教員和中央實驗歌劇院的同志學習,研究中國和西洋的發聲方法……由于她的好學好問,真心熱愛梆子這種藝術,劇團里的師傅也十分樂于幫助她,如告訴她怎樣先吐字后行腔的辦法,克服她在演唱上字音不清的缺點;還要求她學各種地方戲曲,在老師和同志們的幫助下,她學過了京戲、評戲、陜北民歌、云南民歌、河南墜子、曲子、山東琴書、四平調等。為了更好地掌握河南梆子唱腔的味兒和特點,她努力學習標準的河南語音,劇團的同志們也隨時隨地糾正她的口音”[1]。導演、編劇、音樂設計、樂隊也在這場學習熱潮中獲得很大進步。楊蘭春為熟悉豫劇,“在舊書攤、老藝人那里淘換來許多傳統豫劇劇本,一本一本全背下來,他還經常到處去看戲,用心琢磨豫劇從文學到藝術的特點、規律”。王基笑、梁思暉“原來都是搞西樂的,現在搞上了豫劇音樂,也是先鉆進去”,最終“這幾位編劇、導演、音樂設計,終于都成了豫劇通”。對于樂隊,豫劇三團要求“原來搞西樂的,不論拉小提琴、吹黑管兒,一律先學民樂……張夫力……由小提琴手改拉中胡、打小鑼,每人都會好幾樣樂器。他們邊學習邊實踐,努力掌握豫劇的曲調、板頭、節奏”[8]。在深入學習傳統藝術基礎上,他們才開始了真正的藝術創造。《堅持工農兵方向,提高現代戲質量——河南豫劇院三團訪問記》中以《銳意追求藝術的革新》為題主要介紹了豫劇三團在唱腔與表演上的革新,豫劇三團主要任務是演現代戲,他們認為“要用為群眾喜聞樂見的傳統藝術形式表現新的生活內容,就必須從生活出發,在傳統藝術的基礎上大膽地、有步驟地進行革新”,文章首先介紹了他們在唱腔上的革新歷程: 開始,為了更好地表現人物的思想感情,也是為了適應群眾的欣賞習慣,在革新唱腔的時候,采用了“不抓全劇抓幾段”,“兩頭不動中間動”的方法。一出戲的腔基本上是按傳統唱法,其中少數幾段重點唱腔,則根據人物性格和感情的需要,在傳統唱法的基礎上加以革新發展。一些經過加工的腔,常常是開頭用傳統唱法,中間稍作變化,結尾又回到原來板路的旋律上來。這樣,經過革新的唱腔,逐漸被觀眾所承認了。然后,再進一步進行較大的革新。一九五八年以后,他們對唱腔的革新發展,一般是在這樣幾種情況下進行的:某些傳統唱腔缺乏表現力,加以變化和發展;為了適應內容和人物感情的需要,唱詞同傳統唱詞的七字韻、十字韻、五字韻不符時,就必須突破傳統,創造新腔;傳統唱腔難于表現人物的特定感情,有時將過門音樂和曲牌音樂改變為唱腔;為了更準確地表現內容,也需要從生活出發,結合傳統,吸收其他劇種或曲藝的曲調,創造新的唱腔。此外,他們還嘗試著吸收一些歌曲的形式,如領唱、伴唱、齊唱、合唱等等,表現群眾勞動的場面,烘托舞臺氣氛。他們對唱腔革新的基本要求是,使人聽起來“既像梆子,又是新的”。endprint
豫劇三團的同志們說,唱腔的革新必須以傳統的腔調為基礎,否則就不像豫劇了,而這樣是會脫離群眾的。這幾年來,唱腔的革新和發展的幅度很大,大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因為它的基調是傳統的唱腔,所以觀眾承認它是豫劇,并且受到他們的歡迎和熱愛。
當然這些改造是表演、編劇、導演、音樂設計等人員共同完成的,不少成功的唱腔都是“首先是作者根據劇本的要求,先‘哼出一個腔,然后再經演員、樂隊的同志共同研究、加工而成”,在《訪豫劇三團演員高潔》中也介紹了高潔對三仙姑(《小二黑結婚》)、“能不夠”(《袁天成與能不夠》)等一些角色唱腔的大膽改造嘗試。而豫劇三團以傳統為基礎的表演上的革新也是引人矚目的,楊蘭春說,“現代戲的表演,不在于傳統程式運用的多少,最根本的問題是,既要從生活出發,又要有傳統戲曲表演的強烈的節奏感”。他以《朝陽溝》拴保娘與《小二黑結婚》二黑娘的出場動作為例加以說明,如拴保娘“上場的表演動作是高興地在擦桌子、茶杯,這些表演看起來同生活中的動作并沒有什么太多的差別,可是每一個動作都要講求圓、美,落在鑼鼓點上”,他總結說,“這樣的表演是生活的,又是戲曲的,效果十分強烈”[7],用這個方法,他們創造出了劉胡蘭踩鍘刀的著名的亮相動作。樂隊在熟悉了豫劇的旋律之后,也進行了大膽積極、具有創造性的改革探索,他們“增加了些樂器,豐富了河南梆子的音色。河南梆子的弦樂器,一般有板胡、二胡、三弦。板胡是主奏樂器,但它的音色不很柔和,有時出現噪音,為了彌補板胡的不足,他們把西洋樂器大、中、小提琴加上,改用特殊指法拉出河南梆子味……有些戲里……加上笙、笛兩種樂器進行伴奏”[3],“對豫劇原有的民族樂器,他們也變化使用,如他們取消了拉二胡的手指頭帽,把原來不倒把的拉法,改成倒把,增強了樂器的效能,最后組成了他們獨特的民樂、西樂混合的豫劇伴奏樂隊……積累經驗,鍥而不舍,取得了受到觀眾歡迎的好成績”[8]。
三、勞動鍛煉與藝術的提升 學習傳統只是培養這些新文藝工作者成為合格社會主義戲曲工作者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后對于新藝人的要求,已經不能再滿足于技術層面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要為廣大工農兵服務——這里主要是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即向工農兵學習,并成為其中一員的重要政治意義。同時戲曲要表現新社會、新時代,真正理解工農兵,并能準確全面地表現他們,這也是一項重要的現實任務。但新中國成立初期,很多戲曲團體演職人員對下基層,尤其是下農村存在很多抵觸情緒,他們普遍認為只有到省里、北京演出,才能提高,在當時看來,這是由于他們的思想感情沒有徹底轉變為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7]當然他們也不太懂得體驗生活在戲曲表演上的重要性,以為只要掌握了傳統技術,表演什么的都是不在話下。[JP2]
這種傾向很快得到了扭轉,理論基點自然是延安文藝整風以來的思路與經驗——即革命藝術與革命生活是一體的。革命藝術是對革命生活的提煉與升華,這就要求通過上山下鄉,勞動鍛煉,同勞動者一起生活、一起勞動、一起斗爭,從而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當立足點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自己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同時也被他們接受為其中一員后,群眾才把你當做知心人,也才能了解、熟悉和觀察、體驗到自己所要表現的對象。不過,這個時期他們已經和延安時期很多藝術家有所區別了。延安時期很多藝術家走向民間,多數情況下只是懷著樸素的政治層面思想改造的理念,單純地認為走向民間、融入群眾、提高覺悟就是革命藝術取得成功的萬靈丹,還未能從藝術創作理論、演劇理論等層面明晰地體會到,這也是表現人物必須下的基本功夫。而20世紀50年代不少藝術家,尤其是豫劇三團,已經受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理論體系的影響,在下基層思想改造過程中,實際上已經能夠有意識地將體驗派的觀察與學習等戲劇訓練層面的因素加入其中,使自己表現在農村的藝術體驗與思考迅速成熟。這就促使他們在很短時間內,不僅在思想感情上與農民打成一片,而且將農村體驗馬上轉化為戲劇動作、情緒、程式、場景等表達方式。最后豫劇三團在表現現代生活方面在全國迅速異軍突起,成為全國戲劇界的標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當時的各類報道與采訪,較多地集中于他們如何在農村勞動鍛煉,改造自己的思想,體會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這些活動如何幫助他們在表演時準確地表現出應有的思想感情等。如馬琳回顧塑造銀環這個人物形象經驗時,著重談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她坦承劇中主人公銀環的思想轉變的過程,很大程度上與她自身的思想轉變經歷極為相似,這使她能夠深切體會人物的內心世界,因此能將銀環思想轉變的過程,“在感情和動作上,掌握得比較準確:急躁、怕困難、嬌氣等動作作起來比較有自信”;但同時,她在表現轉變后的銀環時卻有些力不從心,“就我的演出來說,后幾場戲就沒有演好。她在轉變后的勞動熱情、革命干勁,我就表現不出來”,她總結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感情問題”,即“人家在困難面前提的口號是‘千難萬難難不住英雄好漢,而我一遇到困難就灰心;人家是把月亮當成太陽,三天任務一天完,鼓足干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我工作上稍有成績就自滿,這兩種思想感情怎么能相比呢?”她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從這里我更體會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9]楊蘭春曾舉過馬琳在朝陽溝體驗生活時的一個例子,講述她思想轉變的過程,馬琳隨農村老太太拾糞,開始嫌臟戴手套,后來受到老太太感染,脫掉了手套,楊蘭春說,“這戴手套與脫手套之別,是她思想感情的變化,脫手套的舉動,是她內心深處一大飛躍”。[10](p.144)為了保證與群眾的密切聯系、思想感情的一致,豫劇三團形成了規律性的下鄉制度,“堅持每年下鄉三四個月的時間,晚上為社員演出,白天參加生產勞動……生產搞得好的富裕地區要去,自然災害嚴重的地區或者偏僻的地區也要去。還要抓住時機,不放過在農村開展的各種政治運動,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放過一個運動,不僅生活留下一段空白,也失去了進一步改造思想感情的機會”。[7]1960年第9期《戲劇報》還以《思想藝術雙豐收——記河南豫劇院三團在上山下鄉中的收獲》為題,對他們“大躍進”時期的勞動鍛煉的經驗,以及這一經驗對于《冬去春來》創作的重要影響等問題作了專題的細致報道。當時各類報道與采訪,仍堅持著思想改造、認識生活就能提高藝術的看法,如他們做出這樣的總結:“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人的思想感情變了,覺悟提高了,藝術創造也隨之提高了。三團十一年走過的道路,證明了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改造自己、認識生活,才有可能進入創造過程”[7]。中共河南省豫劇院委員會在對豫劇三團工作進行總結時,得出了這樣的明確結論“深入生活,參加實際斗爭,和工農兵群眾相結合,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演好現代戲的根本途徑。”[11]在對高潔采訪后,記者也做出過這樣的總結,“技術應該是從生活中得來的,從學習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里吸取來的”[5]。很明顯,對于演員們有意識地將體驗派的觀察與學習等戲劇訓練加入勞動鍛煉、思想改造當中的經驗,當時的報道與采訪者并不敏感,實際上很多演員也沒有上升到演劇理論認識的高度,基本上是在楊蘭春等的演劇思想指導下進行的訓練及實踐。豫劇三團下鄉絕非單純勞動鍛煉,收集積累素材,下去時都曾專門提出過要求,如“參加生產勞動時,對每一種生產工具都嘗試學習操作,這不僅為了在舞臺上能夠做得像,還可以從操作某種工具之中,掌握住特有的勞動節奏和當時的自我感覺”。此外,在對豫劇三團各類報道與采訪中,還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描述:演員排起戲來如魚得水,在臺上一舉一動都有生活依據,做起來十分自信、自如,往往是導演一點,演員們便能聯想到一系列生活形象。[7]之后很快設計出戲劇場景與戲劇動作,并進一步地程式化固定下來。在這些報道中,只是在說明,由于深入生活,在農村尋找到了各種體驗,到排練表演時就能夠隨時喚起、調動出這些體驗,但從體驗立刻能轉化為戲劇動作、情緒、程式、場景等表達方式,就不是僅僅體驗生活就能做到的,這是有意識的戲劇訓練的結果。
(責任編輯:陳娟娟)
① 葉遙《一個堅持演現代戲的好劇團——河南省豫劇院三團訪問記》,《人民日報》,1963年4月25日;楊蘭春口述、許欣等整理《楊蘭春藝術道路紀實(節選)》,《中國戲劇》2000年第2期;張邁《三起三落終不倒——河南省豫劇院三團堅持演現代戲三十年》,《戲劇論叢》第2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頁。
② 游默《豫劇的青年紅旗手——記“群英會”特邀代表、河南豫劇院三團青年演員馬琳》,《戲劇報》,1959年第24期。另參見高潔《學習豫劇并運用它來表現現代生活》,《論戲曲反映偉大群眾時代問題》第2輯,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193頁。[ZK)]
參考文獻:
[1][ZK(#]游之牧.豫劇演員高潔的成長[J].戲劇報,1958,(14).
[2]張邁.三起三落終不倒——河南省豫劇院三團堅持演現代戲三十年[J].戲劇論叢,1984,(02).
[3]葉遙.一個堅持演現代戲的好劇團——河南省豫劇院三團訪問記[N].人民日報,1963-04-25.
[4]河南省豫劇院三團.在學習傳統、大膽革新的路上——河南省豫劇院三團堅持演現代戲的收獲與體會[J].奔流(戲劇專刊),1963.
[5][ZK(#]弟.訪豫劇三團演員高潔[J].人民音樂,1958,(07).
[6]戲劇報編輯部、戲曲研究編委會編.反映偉大群眾時代問題(第2輯)[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7]劉珂理、游默、胡金兆.堅持工農兵方向,提高現代戲質量——河南豫劇院三團訪問記[J].戲劇報,1964,(01).
[8]劉乃崇、蔣健蘭.一個堅持演現代戲的戰斗集體——訪河南豫劇院三團[J].人民戲劇,1982,(12).
[9]馬琳.演現代劇點滴體會[J].戲劇報,1958,(14).
[10]楊蘭春.楊蘭春傳[M].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
[11]中共河南省豫劇院委員會.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發展社會主義新豫劇——河南省豫劇院三團堅持演現代戲的體會[N].河南日報,1964-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