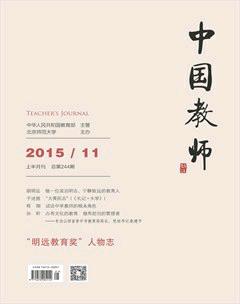“大畏民志”(《禮記·大學》)
王文修+于述勝

專欄主持人
于述勝,1964年生,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學術史研究。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宣傳出版委員會副主任,《教育學報》執行主編,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常務理事。
某日,有新聞報道了一樁家庭官司。老父以兒子、兒媳未盡贍養義務,欲索回已贈與孫子的房屋;兒子、兒媳則堅稱自己已履行贈與合同而拒絕返還。調解無果,遂爭訟于法庭,大有反目成仇之勢。學者頗為感慨,遂言之于師。
學者曰:如今,爭端和官司太多了!馬路上相撞,爭;鄰里不和,吵。就連贍養老者,也要打官司,讓本應充滿溫情的家人之間,也情同陌路,勢如水火。這種社會現狀,該如何改善?
師者問:君以為該如何?
學者曰:我認為應制定更嚴明的法令,再培養一批能“片言折獄”的好法官,父子爭訟之事當會大大減少。中國古代對不孝之子女懲罰很嚴厲,《唐律》甚至規定不孝養老人即可定死罪。
師者曰:法固不可缺,中國的古語“辟以止辟”—以懲罰制止邪僻之行即強調法令的必要性。古代圣賢亦主張明于典法:舜即位后則命皋陶“明於五刑,以弼五教”①,即嚴明五種刑法以輔助五類教化;《周禮·秋官·司寇》載有獄官審案的“三刺”“五聽”之法①。
但法只可懲已發之惡行,難養中心之善德。對此,老子早已洞悉,故言“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令繁苛,既是盜賊多有的表現,也是不斷造就盜賊的原因。老子此言非反對以法為治,而是指出獨行法令的局限性。政令刑罰僅能治標,不能治本。“依法治國”,必以“以德立國”為本。
學者問:如何“以德立國”?
師者言:治訟之急務,在于使百姓深深畏服于天道良知,即“大畏民志”。
學者曰:請聞其詳。
師者曰:“大畏民志”一語,出自《禮記·大學》。其言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謂聽訟時,我和別人一樣,以律斷之,不參雜私心雜念。儒家亦十分注重審案過程中之公正廉明,如《論語》中孔子贊子路能“片言折獄”,即因子路為人忠信,斷案公正,故其裁決令人信服。“無訟”乃儒者在公正廉明之外,對刑法的進一步要求。在孔子看來,比判斷好訟案更根本的,是讓人們皆有誠敬之心、親愛之情而不起爭訟。而最好的訟斷,不僅要弄清是非曲折,更應該讓爭訟者重歸于好,此即“必也使無訟乎”。其義與《尚書》之“刑期于無刑”相類。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之“情”,既是“情意”也是“情實”,乃人們情感意向之真誠無欺。“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并非斷案者不讓其申辯,而是爭訟者自感情虧理屈、無顏啟齒。如果大家都無情,只講自己的私心私欲,怎么能“必也使無訟”呢?只會訟越來越多才是。禮樂者,所以興起人們親親之情,誠敬之心,故能少用刑法。刑政所以保護人們其情、其心,非僅保護合法權利也。
故“大畏民志者”,乃使民深深地畏服于天德良知、人倫之道,使民對自己喪情失性之舉時刻保有戒慎恐懼之心,故不忍、也不能狡辯。僅僅畏懼刑法的懲罰,其導致的結果是無畏,對于所以為人之道并無敬畏之心,遂無所不用其極,以非為是。斷案者明察秋毫、裁斷確當,讓爭訟者不敢混淆視聽而畏懼被加重懲罰,亦僅為“小畏”。吾等宜深思“大畏”“小畏”之別。
學者曰:《論語》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句能否和“大畏民志”聯系起來理解?
師者曰:然,其義正可與“大畏民志”互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僅以政刑去牽引百姓,百姓只想著逃避罪責,而內心不感到羞恥,可以說“無畏”也。孔子贊賞的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以德和禮教化民心,百姓才會“有恥且格”。對于“格”的理解,一種主流的解釋是“來”,即老百姓來歸順的意思。我則傾向于《論語正義》中的觀點,將“格”釋為“正”,即《孟子》中所說的“格君心之非”之意,“有恥且格”也就是每個人都有羞恥感而格正己心之非。“大畏民志”同于此意。“大畏”,不是說懼怕外在的法令,而是心畏服于天德良知。故我認為:《大學》所謂“大畏民志”,與《論語》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脈相承。
學者贊嘆:先生“大畏民志”一解,可謂發前人之未發。
師者曰:不然,我之見解非首創,并不是憑空得來,乃發于明儒王船山之說。
學者復問:使民眾畏服于天德良知,固然是治理和教化的更高境界,但果能實現嗎?
師者曰:孔子即曾以身先之,后世儒者亦多有明“大畏民志”深義而身體力行者。《孔子家語·始誅》就記載了孔子治訟的故事:孔子為魯大司寇,遇父子爭訟。孔子將那父子一同抓來,還關在一起,整整三個月也不審理其案。在別人看來,孔子此舉即使不是昏官,至少也是不夠勤政的。結果三個月后,父親主動提出:俺爺兒倆的官司不打了。孔子遂赦之。關在一起三個月,卻讓那父子倆在患難與共中喚醒了其親親之情。
魯執政大夫聞知此事,頗為不快地說:“司寇欺騙了我。他曾告訴我:‘治國必以孝為先。對于此案,我的意見是殺了那個不孝子,讓百姓引以為戒而克盡孝道。這不是很好嗎?可孔子為什么不治其罪而釋之?”
冉有把季孫氏的話告訴了孔子。孔子喟然嘆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乃無理之舉。三軍大敗,不可斬殺將士;法令不當,不可據以定罪。”這是因為,君上德教未行,罪不在其民。怠于政事而勤于誅殺,這是兇狠的表現;征斂賦稅沒有節制,這是殘暴的表現;不顧目標是否可行卻要求人必須達成,這是苛虐的表現。兇狠、殘暴、苛虐是治國理政的三項弊端,無此三者,方可以用刑。
學者曰:我想,孔子此語是批評季氏和國家失職,未能廣施禮樂教化吧?
師者曰:不錯。文中孔子又引《詩經》之語,“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以明輔佐天子治國理政之人,其本職在于不迷百姓心志,使威權在手而不輕用、刑罰完備而不輕施。其間隱含著對于季孫氏為政尚刑不尚德的嚴厲批評。
學者復問:老師前面提到后儒亦有以真情化解紛爭者,能否舉一二例子?
師者曰:明儒王陽明亦有一則治訟趣事。《傳習錄》中記載,陽明的鄉里有一對父子爭訟,來請他裁斷。陽明勸說之辭未盡,父子相抱慟哭而去。陽明弟子柴鳴治感到很奇怪,遂問于師:“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冶對先生的回答更感驚訝,復問何故。陽明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曾撫養舜,卻不知自心已為后妻所移了,還自詡慈愛,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因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得到天倫之樂時(瞽瞍底豫),又不過復得其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后世稱舜是個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個慈父。”
學者贊言:這段兒說得太精彩了,依我看,陽明先生甚得舜之孝心。人果能效法舜而常思己過,恒念父恩,爭訟必漸遠離。
師者復曰:陽明后學羅汝芳亦繼承儒家的德治(教)之道。《明儒學案》說他“知太湖縣,擢(提拔)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為治”。以講會鄉約為治,使鄰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這體現的就是儒家德教為本、政刑為末的思想。
據《明史·羅汝芳傳》記載,羅汝芳任太湖知縣時,常召集縣學諸生講學,公事多決斷于講學中。后來他入京朝見皇帝時,曾力勸當時的宰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以至于四方聽講者達數千人。他自己曾創辦開元講會,令在押犯人到會聽講。最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對兄弟爭奪財產的記載:“民兄弟爭產,汝芳對之泣,民亦泣,訟乃已。”作為裁斷者,本應“置身事外”方能泰然處之,但近溪子(羅汝芳)卻感同身受,臨訟而泣。其所以落淚,乃因親兄弟對簿公堂,只為一點點家產,民之困窮可知;他更因自己身為父母官、不能救民于水火而內疚。爭訟者為其深情所感動:羅大人與我們兄弟只是陌路相逢,尚有此深情;吾等骨肉至親,何至爭訟如此?
學者贊曰:汝芳以己之真情,喚起其兄弟的骨肉親情。我聽了也深受感動啊!老師常言:“有至情方有至理”,今日品此語,真是“至情”又“至真”之言啊!
師者曰:良知人人皆有,非圣賢獨具。然孔子、陽明之所以超出吾輩者,乃因其能體良知而力行,以德化民、成就美俗。若果人人能保護此仁心而不失,“親其親長其長”,家齊國治何難之有!
“大畏民志”贊
親親是良知,人人皆性之。
利欲致爭訟,智昏情亦滅。
小畏畏刑措,大畏畏失性。
政刑止吾訟,禮樂起吾情。
儒者使無訟,情通理還明。
大畏民志者,克臻齊治平。
參考文獻:
[1]孔安國, 孔穎達. 禮記正義[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孔安國, 孔穎達. 尚書正義[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責任編輯:任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