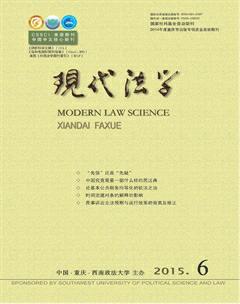“先信”還是“先疑”
摘要:政府部門面對一個具體的公民時,是先信任他,還是先懷疑他,這不僅關系到彼此合作的狀態,也影響到國家與公民關系的政治架構。前者可稱之“先信”,后者可稱之為“先疑”。在“先信”之下,除非政府辦事部門能證明該申請人是不誠信的,否則不得拒絕。而在“先疑”之下,除非該申請人能證明自己是誠信的,否則政府部門對于其請求事項可以拒絕。“先信”采用信用減分制,“先疑”采用的則是信用加分制。“先信”是“信任+嚴懲”,“先疑”則是“懷疑+監督”,從而“先信”提升了社會信任,而“先疑”則加劇了社會的不信任。一個國家是采用“先信”還是“先疑”,往往與其工業文明和民主化程度有著較強的關聯性。
關鍵詞:先信;先疑;如何證明我媽是我媽;信任;誠信
中圖分類號:DF03
文獻標志碼:A
最近,一則“如何證明我媽是我媽”的新聞,讓國人好不困擾,就連李總理都憤怒地質問道:“證明‘你媽是你媽,這怎么證明呢?簡直是天大的笑話!”這的確是笑話,人們從直覺上和經驗中都不難作出判斷,但從理論上如何破解則并不容易。其實,“我如何證明我媽是我媽”可以轉換成另一個問題,即“你如何證明我媽不是我媽”。同樣一個問題,由誰來證明,這往往涉及到信任與懷疑的制度選擇的問題。
信任是合作的開端,去政府部門辦事,公民與政府辦事人員彼此雖然是陌生人,但仍然必須要求有最低限度的信任基礎,這種信任基礎主要集中在公民是否可信,以及如何證明其可信的這一問題上。具體言之,如果這種證明是由公民自己來完成,那么,在公民不能充分證明自己是可信時,得推定公民是不可信的;反之,如果這種證明是由政府來負責,那么,在政府不能證明公民是不可信時,得推定公民是可信的。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理念類型的思考問題的方式,前者可歸為“先疑”式,后者可表述為“先信”式。兩種模式孰優孰劣,可從誠信的舉證、信任風險的化解、以及信用的監督等三個方面作嚴格的邏輯推演,并在推演的基礎上,挖掘制度選擇“先信”與“先疑”的根本制約因素。目前,中國政府正在致力于公民誠信體系的構建,相信這種推演與挖掘對政府信任公民與否的制度選擇有著極強的啟示意義。
一、誠信的舉證
在普通的人與人關系中,彼此之間是否信任,以及如何信任,這不是制度所關心的內容,至少不是制度所關心的重點。但是,當一方是政府部門,而另一方是普通公民時,那么兩者之間就不是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是反映了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關系。如考試制度中主考方與考生之間,海關制度中海關與旅客之間。此類關系中的信任問題,對于政府部門來說,在應某個公民申請時,是首先信任他,還是首先懷疑他,這在雙方合作關系實際發生前,制度必須預先做出強制性的規定。因此,“先信”和“先疑”構成了制度選擇的起點。
無論制度是選擇“先信”還是“先疑”,目的都是為了促進政府部門與公民之間的合作關系。但同時,“先信”或“先疑”也都有可能面臨公民不誠信的問題,因此,對于公民誠信與否的證明就成為問題的中心。無論是“先信”還是“先疑”都要求就申請人是否可信提供證明,只不過證明的途徑有所不同而已,其不同可以作如下邏輯演繹:
第一,申請人是否可信,該申請人自己最為清楚,所謂心知肚明,因此,理論上由該申請人來證明自己值得依賴是最合理的要求。但是,“可信”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并含有評價的性質,從證據學上看,這一概念因其抽象性和評價性,是很難獲得直接證明的。相反,政府的辦事部門,其證明對象則是該申請人的“不可信”,“不可信”相對于“可信”,雖然也是具有評價性的概念,但卻容易轉化為一個具體的事實概念,政府部門只要證明該申請人存在某一不可信的相關事實,即已滿足證明的要求,因而是可證明的。“不可信”概念容易轉化為事實概念的這一性質表明,制度選擇“先信”相比于“先疑”更為合理。
第二,當然,“不可信”向事實概念的這一轉化也提醒了我們:“可信”或許也可以作這樣的轉化,即將可信的評價與可信的事實聯系起來,由該申請人提供其可信的事實,從而導出可信的價值判斷,比如他可以列舉出支持自己可信的事實。但是,支持“可信的事實”相對于“不可信的事實”,范圍是不確定的,或者說,支持“可信”的待證事實是無限的,其證明結論永遠是接近可信,而不可能證實可信。因此,由申請人來證明自己是可信的制度安排,在增加申請人證明負擔的同時,理論上永無可能獲得證實的結果。例如,對于身份的證明,申請人提供了身份證,但這并不能有效證明身份證是自己的,也不能有效證明提供的身份證是真實的。申請人提供的任何證明,都可以無限地質疑下去,如此等等,不可窮盡。相對而言,政府辦事部門的證明對象則是申請人的“不可信”,其待證的不可信事實范圍是有限的,其有限性理論上為1%,即只要證明其中之一的某一事實,比如對于申請人的身份證明,只要證明身份證與申請人不同一,或者申請人之身份證已失效,或系偽造,證明其一,舉證責任即已完成。因此,從證明的邏輯難度上作比較,政府辦事部門的舉證難度是某公民的舉證難度的百分之一。因而,從證明的難易程度上看,相比于“先疑”,“先信”作為制度的起點更為科學。
第三,所謂“可信的事實”,制度上也可以預先規定一個范圍,將無限的待證事實作有限的范圍限定,從而化“無限”為“有限”。比如可以要求某公民提供某幾種具體的證明文件,或者規定某公民必須通過政府部門的某些檢查和檢驗。但是,這就有三個問題:一是,由制度規定的待證范圍,其實也是人為的,雖然可以在規范上確定“有限”,但并不能解決事實上的“無限”,其證明的結果仍然是接近可信,而無法證實可信。二是,或許通過列舉某申請人必須提供的證明文件的這一做法,能夠保證其進入制度程序前的可信,但卻不能確保該申請人進入制度程序后,能夠持續保持可信。比如考生參加考試,主考方雖然可以要求某公民提供身份證、準考證等來確信其身份,但并不能設計出萬無一失地杜絕考生在此后考試程序中一切可能發生的舞弊行為。因此,關于“可信”的證據,理論上只能保證過去,不能保證未來。三是,當某公民進入程序后,政府部門制度上即便可以設計出完善的各種檢查和監督的技術,但是這一做法會導致證明程序的無限延伸,從而與效率價值相悖,并且由于在理論上的不可窮盡,而始終不能完全確保申請人的可信。endprint
第四,法律判斷要求涇渭分明,而世界并非如此,世界之非確定性得由推定的方法來求得法律的確定性。依此法理,假如由政府部門來負責證明申請人是不可信的,而政府部門又不能證明,則只能推定申請人是可信的,即推定其為清白之人。相反,假如由申請人來證明自己是可信的,而他又不能做到,則應推定其不可信,即推定其為不清白之人。由于前已論及的原因,理論上某公民并不能滿足證明的要求,那么,不只是某個具體的申請人得被推定為不清白之人,人人得被推定為不清白之人,如此,社會民眾人人都是嫌疑犯,刑法的無罪推定也將喪失根基。正因此,清白免證可以看作是一項公民權利,人人均得假定,故無人需要證明。并且,“若有人向他人提出證明義務,則他也把自己拉進了義務的圈套”(因為他不承認免證的假定,也要自證),從而陷于邏輯上的悖論。雖然不可避免的,“所有人都清白”的假定讓少數不清白且善于欺詐的人得益了,但是如果不讓他們得益,那么大多數人就得放棄自己的身份安定的權利,而這并無必要且多有害處。因為,更多的人身份不確定,并不意味著欺詐必然不得益,然而將清白者說成不清白卻是肯定的。
兩相比較,從某個人是否可信的證明上看,制度選擇“先信”相對于“先疑”,在邏輯上無疑更科學、更合理。不過,也許有人會質疑,法律本來就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如果要求政府部門首先得信任公民,那么,兩者就相互矛盾了。筆者以為,法律“人性惡”預設是以抽象的人性為基礎的,而政府部門對公民得“先信”是面對具體人而言,抽象人性之假設與具體人格之對待是不同性質和不同層面的法律問題。正如刑法懲罰的對象是有罪的犯罪分子,但當具體刑罰施之于具體人時,得推定其為無罪一樣,即刑罰假定的人的惡是抽象人的惡,無罪推定假定的人的無罪則是具體人的無罪。因此,要求政府部門對公民得“先信”,此與法律“人性惡”的假定并無矛盾。
制度選擇“先信”相對于“先疑”,在邏輯上更為科學合理,還不只是停留于舉證責任分配的層面上,而且還因為舉證責任的分配,直接影響到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的關系架構上。在“先信”之下,除非政府部門能夠證明公民的請求存在欺詐或隱瞞的情形,政府辦事部門不得拒絕公民的合法請求。如果政府部門不能提供證據,即使心存懷疑,仍不得拒絕。其政治意義具體有四:
一是使政府的不作為變得不可能。怠政與消極現象只存在于“先疑”之下,因為“先疑”可以為不作為提供堂而皇之的理由。但在“先信”之下,政府被置于公民日常活動的監督之下,政府內部層級監督的非及時性被彌補,并且行政效率得到了保證。雖然“先信”也有可能導致個別公民的個別欺詐行為僥幸通過,但是,這與“先疑”下所滋長的官僚主義危害比較起來是值得的。并且,本文后面將要論及,公民基于公民自己失信成本的考慮,欺詐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二是使政府的腐敗行為被抑制。政府部門的腐敗行為往往發生于“先疑”制度下,“先疑”導致了權力的擴張。在“先疑”之下,政府部門居于主動地位,而公民的地位則具有從屬性,這就使得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基于尋租的意圖,在懷疑的名義下,可以隨意刁難公民。“先信”則限定了權力的范圍,在“先信”之下,公民居于主動地位,政府部門非有證據不得拒絕,因而其尋租的空間被壓縮到了最小,這恐怕也是西方國家的政府官員相對于中國政府官員更清廉的原因所在。
三是使政府行為被公民有效監督。在“先疑”之下,公民是政府嚴密監管的對象,政府可以不斷地質疑公民的誠信,視公民為“刁民”,“你如何證明你媽是你媽”就反映了政府工作人員居高臨下的監管態度。相反,在“先信”之下,由于政府部門非有確實證據,不得對公民作不可信的推定,“如何證明我媽是我媽”就成功地轉化為“你憑什么說我媽不是我媽”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被置于公民的監督之下。顯然,這種監督的有效性遠甚于政府的內部監督。
四是使公民的真正主人翁地位得到了凸顯。因為,在“先信”之下,政府辦事部門非經充分證據支持,不得否認公民的誠信,于是公民的安全感和自尊感得到了提升,而這反過來又進一步提升了公民的誠信表現。但在“先疑”之下,公民始終于處于被政府辦事人員質疑與不信任的地位,從而加劇了公民屈從于公務員的從屬地位。因此,也就可以這樣說,“先信”與“先疑”關于舉證責任的分配,原本就是由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關系架構所決定的,是權利與權力關系的自然反映和必然延伸。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先信”代表了權利本位,而“先疑”則反映了權力本位,孰優孰劣,判然有別。因此,制度選擇“先信”,而不是“先疑”,這不只是因為要考慮到舉證責任的技術因素,還因為其包含了極強的政治因素。
當然,需要補充的是,“先信”與“先疑”的區分,盡管概念上可以做到涇渭分明,但現實中并不是絕對對立。以考試為例,即使是采用典型的“先信”式的西方國家,雖然在考試時并沒有嚴密的監考制度,但考生也得提供必要的身份證明。這說明,“先信”并不是絕對的盲信。當某公民證明自己可信并不困難時,或者,政府已經將證明文件事先頒給了公民時,那么,公民出示證件并不與“先信”的理念與做法相違背。因為,“先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民無法自我證明。當公民自我證明并不困難時,這一原因已經被消除。
二、風險的化解
信任關系具有以下性質:一、時間差與不對稱性。承諾與兌現具有時間差,信任者與被信任者存在某種不對稱性。二、不確定性。具備了確定性,就不存在風險與應對風險的方式了,也就不叫信任。三、沒有足夠的依據。信任屬于傾向和愿望。因此,信任實際上是一方對另一方信守承諾的概率估計,是對對方是否值得信任的一種估計。”在信任關系結構中,我們說一方信任另一方,是說一方將自己的未來命運托付于另一方,并對自己的這一托付充滿信心。
因此,信任的同時伴隨著信任的風險。信任包含一種判斷,即由于授予他人對某些利益的決定權,也接受了他們潛在不良意愿所造成的易受損害性。一旦付出信任,也就意味著要承擔潛在傷害所帶來的風險,以換取相互合作的好處。當一方信任另一方,也就意味著一方的信任容易被另一方所利用,因為一方對于另一方的信任,僅僅是增加了對方的適應性,而減少了自己的主動性,從而增加了自身遭受對方攻擊的風險。信任別人,也就是給別人留下了傷害自己的機會。但信任本身表明自己并不相信對方會傷害自己。因此,“先信”與“先疑”,對于信任方來說,其風險是不一樣的。假定制度選擇“先信”,那么,政府辦事部門就要冒信任的風險;而如果制度選擇“先疑”,那么,政府辦事部門則將風險降到了最低的程度,而由公民承擔不合作的損失。因此,“先信”與“先疑”相比,對于具體的政府部門而言,前者風險大于后者,規避風險的理想辦法似乎應該選擇“先疑”。endprint
雖然制度不可以通過安排來消除風險,但是可以通過安排來分攤風險。由誰來承擔風險,是由公民還是由政府來承擔,制度是可以預先做出安排的。一般來說,擁有資源的人,比如擁有權力、財富和信息的人都更能夠付出信任,那是因為他們有足夠能力承擔信任破裂的風險。相反,那些缺乏資源的人往往不能付出信任。因為錯誤的信任可能導致災難性后果,而自己又缺少足夠保護自己的手段,因而他們只能高度地節省信任資源。因此,與其讓公民承擔不合作的損失,不如由政府承擔信任的風險,因為后者承擔風險的能力遠遠大于前者。
而且,雖然對于政府部門而言,“先疑”的風險遠小于“先信”,但是其風險的“小”是以彼此不合作或減少合作作為代價的。因為人是理性的和自利的,在單次囚徒博弈中,選擇背叛而不是守信是最佳的策略,從而,“先疑”導致了合作的終結或至少帶來了合作的困難。因此,我們說“先疑”的風險比“先信”低,這種比較只在單一的和孤立的關系中才有意義。而如果相互作用的時間是無限的,那么人們就會選擇合作。相互作用的時限越長、越無限,就越有可能產生理性的自利行為,以維持合作的均衡。因此,如果在制度上將人的信用納入一個連續的系統來考察,那么就能激發人們的合作,而不是背叛。
幸運的是,人生并不是單次的生命博弈。“如果我們的生命博弈真是單次囚徒困境,我們永遠也不可能進化成社會性動物。”人類社會關系的連續性與關聯性為“先信”的采納提供了社會基礎,而“先信”促成合作的優勢也因此得到了凸顯。換言之,結合合作所帶來的收益這一點,“先疑”在降低了信任風險的同時,也導致了合作收益的喪失。與此相反,“先信”在承擔信任風險的同時,也會因此帶來合作收益的獲得。畢竟,制度的目的是促成合作大門的開啟,而不是促使合作大門的關閉。因此,將風險與收益聯系起來考慮,我們也會發現,“先信”相比于“先疑”,由其促成了合作的收益,而應該成為制度的首選。英國企業家文森勛爵歸納的商業成功的戒律之一就是“相信每一個人,除非你找到不再相信的理由為止。”這雖然是商業定律,但也是關于信任的定律,不只對商人有益,也對政府有用。
當然,“先信”的合作收益只是理論上的,它必須能夠化解風險,或者能夠化解大部分的風險才有實際的意義。以加拿大渥太華坐公交車為例,如果你逃票,一旦被發現,你就會被罰款300加元(相當于人民幣1800元)。同理,你向銀行聲稱你的信用卡被盜刷,銀行雖然“先信”你,但如果事后發現你的聲稱是假的,那么你在銀行就有了信用不良的記錄,而這將關系到你的未來。在加拿大入關時,你如果攜帶了需要申報的物品,你可以聲明沒有,海關也會“先信”你,但是,一旦發現你的聲明是虛假的,你就進入了黑名單,其相應的懲罰措施是,你以后的每一次過關,都必須提前4個小時抵達海關,將你所有的行李一一打開,逐一排查,讓你煩不勝煩。因此,“先信”并不是無條件的,它伴隨的是后續的對于“失信”的嚴厲懲罰,雖然檢查是偶然的,但后果卻是嚴重的。
“先信”不是絕對的和無條件的,“先信”作為政府辦事部門與公民發生關系的制度起點,它首先表明的只是在官方對于公民的起始態度,但它并不是一個從一而終的態度。一旦發現某公民有失信的行為,政府辦事部門對于該公民的信任即已減少,甚至喪失。因此,“先信”與“先疑”的區別就在于,“先疑”對公民信用的考察,重點是放在了關系開始之前,而“先信”則是將考察的重點放在了關系開始之后。具體來說,對于公民信用的考察,“先疑”采用的是信用加分制,而“先信”采用的則是信用減分制。
如果公民一生的信用分值是100分的話,那么,“先疑”就是將一個人的信用分數在起始時給定為0分,以后隨著其信用良好記錄的增加而相應增加其信用分數,這種增加,理論上在其死亡時可以達到滿分100。而“先信”在起點時就給定一個人100分,以后隨著其失信的增加而相應減少其信用分值,這種減少,理論上可減至0分。看起來,兩種計分方式,只是方向相反,并無實質上的不同。但仔細推敲其實際運用的效果,信用減分制可以有效地抑制機會主義,而信用加分制則可能會刺激機會主義。
信用分數的起點是0,還是100,這對于人的心理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對此,心理學上的稟賦效應理論可以提供較為充分的解釋。所謂稟賦效應,是指“為了捍衛自己已有的東西,我們愿意付出的資源和精力多于去奪取別人東西的投入。就比方說狗吧,較之跟其他狗搶骨頭,狗寧肯在保護自家骨頭上花更多的精力。所有權的稟賦效應跟厭惡損失存在顯而易見的直接聯系,避免損失之痛帶給我們的動力,比追求收益之喜強兩倍。在進化的設計下,人們更在乎已經擁有的,對有可能擁有的東西反而不那么上心。”也就是說,在稟賦效應的支配下,人們對于自己已經擁有的愿望遠勝于自己可得到的,已經擁有的失去所帶來的痛苦遠甚于可得而未得所帶來的遺憾。因此,當人們已經擁有信用100分時,人們會因為倍加珍惜的心理,而時刻小心自己的行為,唯恐自己已經擁有的信用分數的流失。相反,當人們的信用分數只是0時,雖然理論上一個人可以經過努力獲得更多的分數,但偶然的失信,只是不可再加,但不至再減。換一句話說,擁有100分,其失信的成本較高,而只有0分的人,失信的成本非常之低,所謂失去的是鐐銬,得到的可能是世界。因此,前者的機會主義被抑制,而后者的機會主義則被激活。難怪在加拿大,有朋友告訴我,說謊會意味著你未來的路會越走越窄,究其原因,就在于加拿大對人的信用采用了減分的方法。因此從這一意義講,“先信”也就不僅僅是表明官方對公民的一種態度,也內含一種工于計算的精明策略,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一個人說謊與欺詐的本能。
無論是信用加分,還是信用減分,總分都是100,但由于統計的方向相反,對于人的誠信的激勵作用就不一樣。從理性上分析,一個人表現得誠信與否,與人的利益具有很大的關聯性。美國學者亞歷山大·J·菲爾德說過,“可信賴性并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人性品質,對他而言,只有當可信賴比不可信賴更有好處的時候,人類才是可信賴的……有些人是誠信的,僅僅在如果誠信或者誠信的表現能夠比不誠信獲益更多之時。”對比“先信”與“先疑”,無疑,“先信”的利益引導性遠強于“先疑”。因此,人們真的沒有理由去責備中國人的說謊習性,只是中國人缺乏有效引導誠信的利益機制罷了。endprint
在“先疑”之下,如果人的一生信用滿分是100,那么一個人得經過一生的努力,持續地堅持誠信,拒絕任何機會的引誘,才可以獲取。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因此,人們會因為要獲得100分極其困難而放棄努力,積善的努力被壓抑。而即使至死,經過一生比拼,獲得了100的信用滿分,這一滿分對他的人生也失去了意義,至多是可以在死后被追認為道德模范而已。但在“先信”之下,出生即已拿到100分,以后只要持續保持即可。因此,出生時即已獲得的100分就具有人生意義,它在其一生中能夠發揮正能量,幫助他贏得信任,從而贏得人生的各種機遇。換言之,“先信”起始的100分比“先疑”最后得到的100分,其發揮的作用是不一樣的。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西方國家,“活雷鋒”時時可遇。
事實上,無論是采用加分制還是減分制,都包含了對人性弱點的擔憂,擔心在未來的合作關系中,對方有可能會失信。只不過,信用加分制因為過度的擔心,而不敢首先付出信任,因此關閉了合作的大門。而信用減分制,其實也不是因為陌生人有可信任的理由,因為,“我們不能把對陌生人信任的基礎建立在他們的可信性上,因為我們無法知道他們是否誠信。我們只是在假定他們是誠信的。”但是,假定對方是誠信的其實是一項非常劃算的策略,一方在可承受風險的前提下,首先釋放出信任,利用稟賦心理,就會激發起對方抑惡揚善的效應。因此,在單一的和孤立的關系中可能面臨的失信風險,在信用減分制的引導下,卻被悄然化解。真可謂,小技巧,大智慧。
在“先信”制度安排下,信任除了表明官方對公民信任的政治態度外,也具有策略方面的意義。因為,政府部門對公民的信任也不是建立在該公民具有可信性的基礎上,而這正是信任的策略主義和信任的道德主義的區別所在。所謂道德主義的信任,我以為,是指“應該”信任,是基于倫理上的要求而產生的無條件的信任;而策略主義信任則是指信任對于我而言是能夠最大化利益的一種手段,因而是有條件的。“先疑”是在對方充分展示了其可信性依據后才付出的信任,這就是一種道德主義的信任。道德主義的信任在熟人社會中非常典型,一方因為對對方的熟悉、了解或情誼而對對方付出的信任,這種信任不僅有社會學的根據,更重要的是有倫理學上的要求。但是,對于陌生人,人們不會因為你不信任他而在道德上非難你,而你決定信任陌生人,也只是基于概率的計算與功利的權衡,因而也就可以看作是一種策略。正是這樣一種信任策略的成功運用,“先信”贏得了“先疑”所不能獲得的合作收益,從而極大地化解了信任的風險。
三、信用的監督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信任和不信任是一對并行不悖的“奇怪組合”,人們在合作和信任的同時,還需要保留對交往對象的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信任并不代表著就可以放棄謹慎、安全保護和監督。如果沒有“不信任”這種獨特的否定思維方式,那么,信任就可能是迷信、盲信。盲目信任更多的是減少而不是增加人們的信任。因此,“先信”在信任的同時也對“不信任”配套了應對的機制。
“先信”制度在交易中大大地簡化了識別的負擔,從而減少了世界的復雜性。因為,“信任的存在,緩解了行為者們的擔憂、疑慮、警惕和戒備,并從監視他人日常行為細節的高代價措施中擺脫出來。”但是,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行動者們則必須靠正式的監視和強制。也就是說,懷疑和不信任要求監督,并且還特別依賴于監督。因此“先疑”相比于“先信”,必須同時有監督制度與之配套,才能保證“先疑”運行的可能。
一談起中西方法律制度的不同,人們大都習慣于認為,西方制度設計嚴密,而中國設計出來的制度則總是漏洞百出,有空可鉆。在這一幾乎是意識形態的話語作為前提的推導下,我們無不是強調制度建設的完善,并且制度建設的核心又無不是強調嚴密的監督制度,讓機會主義者無機可循。因此,在中國人的潛意識思維里,一提到如何防范公民的不誠信行為,就一定會想到加強監督。比如,一談到禁而不止的制假販假,人們想當然地就是要求增加政府的監管。事實似乎也是這樣,比如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如果行人知道有監控探頭,恐怕就不會一走了之。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近幾年來,監控探頭廣泛運用于各種場合,人們的一舉一動都納入了監控的范圍當中。我們先不說這種無處不在的監控是否會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利,單就監督成本以及監督是否有效的問題,就值得反思。
有一個關于和尚分粥的故事,說的是有七個和尚,每餐每人一碗稀飯。但是,由誰主持分稀飯卻是一個不放心的問題,因為資源的有限性與權力的擴張性必然導致分稀飯者利用權力營私舞弊。西方人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是“分者最后端”,有效地化解了不公正的難題。但是,按照中國人的思維卻是通過監督的方式來加以解決。先是試圖找到一個“大公無私”的老劉來主持分配;發現老劉并不可靠后,又找到另一個也是“思想覺悟高”的老李去監督老劉;發現老李也有問題時,又派“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老張去監督老李。這就是中國人的監督情結。這種層層架屋的監督方式除了導致監督成本不斷上升外,其致命的缺陷是陷入“誰來監督監督者”無限循環的怪圈中。層層架屋的監督方式始終是將希望寄予監督者的道德品格上,制度的運作成功依賴于監督者的“道德自律”,因而也就決定了這一監督方式從根本上來講就不具有經濟性和有效性。西方“分者最后端”的處理方式可以看作是“先信”的方式,對任何一個分粥的人首先都持信任的態度,但這種信任并非是無條件的,而是將問題交給分粥人自己,利用其自身利益的相關性進行自我引導。中國的處理方式則可以看作是“先疑”的方式,首先是對任何一個分粥人都持不信任的態度,而指望通過強化監督的方式來應對分粥人可能的權力尋租。也可以這樣總結,“先信”是采用“信任+嚴懲”的方式,而“先疑”則是采用“懷疑+監督”的方式,前者簡單,后者復雜。
依靠復雜的外部監督的做法,從經驗上來看效果并不理想。有海外生活經驗的人知道,在國外許多超市里,顧客出入相當的自由,沒有看到如中國一樣有許多的監控探頭,但也沒有報道有高于中國超市的失竊率。特別令中國人不可思議的是,政府部門,行人也可以隨意出入,可以進去躲避風雪、可以進去如廁、可以進去問路,并沒有人過來質疑你。出入政府大門的輕松,與中國政府一些大門武警持槍守衛的緊張構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并沒有證據表明,這些國家的辦公大樓經常遭受不明真相的群眾圍攻或者恐怖主義分子的突然襲擊。由此也可以發現,這些國家的政府部門對于公民的信任與中國的一些政府部門對于公民的懷疑,形成了相當程度的反差,并且,其產生的效果也形成了相應程度的反差。endprint
國家對于公民的信任,是建立在公民自我約束的基礎上,而中國一些政府部門對于公民的信任,則是通過強化對公民的監督來保證。前者節省了成本,信任本身就是社會資本形式,因而可以減少監督與懲罰的成本。或者說,“先信”的監督是自我監督,而“先疑”的監督則是外部監督。理論上來說,自我監督實質上沒有監督,但是,當自我監督與自我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時,自我監督就具有了鮮活的生命力。自我約束的監督主體是自己,其失信的結果由自己承擔責任,賭一次如果失敗,就可能影響一生。因此,公民基于自身利益可能失去的擔心,就能很好地約束自己,只要借助于偶然的、不確定的檢查,自我約束就可以取得最大化的收益。外部監督的監督主體是政府,由于個人失信的成本不高,至多是可增加的信用分數不增加而已,但是,賭一次如果成功,就可能一本萬利。兩相比較,自我約束的監督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相當于建立了一張嚴密的監督之網;而外部監督則因為監督資源的有限性,而導致監督的低效性,一旦外在監督松懈或缺失,立刻就激活了機會主義。
理論與事實已經很好地證明,絕對依賴強力的控制,而不依靠信任,往往會產生一種巨大的資源分配不當,這種分配不當不僅是無效率的,而且最終也是無效益的。正因此,法律首先得假定公民誠信的,而不能假定公民不誠實的。當法律首先假定某公民是不誠實的,法律得依靠監督,而一旦監督松懈,那么,惡行就可能發生。因此,假定公民不誠實的法律,導致了公民的賭博和投機的心理。制度原本就假定自己是不清白的,導致努力證明自己的清白因其十分困難而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相反,當法律假定公民是誠信時,公民在日常行為中就不需要努力去證明自己的清白,但一旦自己的行為不慎,即失去清白,在社會上將寸步難行,毀滅一生,因而也就有效地遏止了冒險鉆營與投機取巧的動機。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采用“先疑”制度的國家,一遇到問題,總強調監督,而由于不可能解決“誰來監督監督者”的問題,因而也就永遠解決不了公民失信的問題。從“先信”與“先疑”的成本與效益的對比中,簡單而便利的“先信”制度取得了依賴于復雜的監督設計所不能取得的收益。
“先信”與“先疑”由于對監督制度依賴的不同,還導致了政府與公民之間信任關系也呈相反的走向。在“先疑”之下,公民是政府嚴密監管的對象,政府不斷質疑公民的誠信,視公民為“刁民”,而公民則總是試圖擺脫政府的監督,雙方的關系為貓與鼠的關系,互不信任,相互敵對,越監督,越想擺脫監督,所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而要保持雙方平衡關系的穩定性,只得依賴于暴力與權術的運用,欺騙、隱瞞、壓制、恐嚇等各種手段輪番上陣。相反,在“先信”之下,公民對于自己的誠信表現,自己做主、自我約束,政府部門非有確實證據,不得對公民作不誠實的推定,因而不是政府監督公民,反倒是政府被公民所監督,此與“先疑”的監督方向恰好相反。“先信”所決定的公民對于政府的監督,與前面論及的因信用證明而內含的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架構關系在邏輯上是高度一致的。而這對于打造誠信政府,遠比某些政府高呼執政為民的口號,其意義來得更為有效和更為實際。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說“先信”是“信任+嚴懲”,而“先疑”則是“懷疑+監督”,這種區分只是相對意義上的,并不是說,“先信”完全排斥監督,“先疑”完全排斥嚴懲。準確的意思是指,“先信”的重心是嚴懲,而不是監督,監督在“先信”那里并不重要。“先疑”的重心是監督,而不是嚴懲,嚴懲在“先疑”那里并不重要,因為“先疑”的目的主要是防范,如果防范的目的能夠達到,嚴懲也就不必要或不重要了。
四、制度選擇的根本因素
如果說一個國家的社會誠信的高低,與“先信”還是“先疑”有著一定的因果關系的話,那么,為什么仍然會有一些國家舍棄“先信”不用,而選擇“先疑”,其選擇是否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人類信任史的演化來做一分析。
人類的歷史也是信任進化的歷史。在自然狀態,人與人之間是分離的和孤獨的,叢林規則是人類生存的唯一法則,因此,信任作為社會媒介無由產生。但是,社會則是人與人聯合的行為。在社會關系中,人與人之間是一種結合而非分離的關系,因此,信任作為人們聯合的媒介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信任首先發生于親屬之間,一個人“最容易信任與我們同一種族的人。”親屬關系以生物性親緣關系為基礎,使得愛與信任的發生幾乎是出自本能。這種在親緣關系中普遍可見的信任資源,在陌生人社會就變得稀缺了。因為,在陌生人社會里,彼此之間首先是相互懷疑,而不可能是相互信任,只有在懷疑被推翻的基礎上才會進一步試著交往,因而,在陌生人社會里,首先采用的是“先疑”而不是“先信”。但是,由于懷疑要完全被推翻,在理論上并不現實,而那些傳統的以牙還牙、放逐、名譽受損等非正式懲罰在陌生人社會里要防止機會主義行為時往往是無效的。因此,在陌生人社會里,守信往往成為最差的選擇,而背叛才是首選的策略,從而經常不免陷于“囚徒困境”中。人類社會自進人國家時代以來,逐漸建立起“系統信任”,以彌補陌生人交往中的信任資源的不足。從此,“人格信任”和“系統信任”兩種信任共存共榮,相輔相成,支撐著社會生活的展開。不過,即便是這樣,“先信”并不是隨著國家強行推行的“系統信任”而自動產生。
“先信”的產生與工業文明有一定關系。因為,“先信”實行的信用減分制,其有效運作的條件是,能夠對人的信用表現進行連續性和普遍性的考察,計算機聯網所帶來的信息共享為此提供了便利。在農業文明時期,人們聚族而居,安土重遷和血緣關系導致了人際交往的長期性和連續性。在這樣的熟人社會里,一個人生于斯,長于斯,彼此知根知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建立在可信任的人格基礎上。由于農業文明時期的人口幾乎不流動,因而,將個人信用的信息作連續和普遍性的考察,并無意義,并且因為缺乏考察的技術支持,也無可能。但在工業文明時期,人口流動的頻繁,信用的重要,以及技術的越來越完備,都為“先信”的采用提供了需要和可能。不過,這種需要與可能,只是就重要性和可能性而言的,真正在制度上強制政府對于國民的“先信”,則是與國家權力來源的正當性有著密切的聯系。endprint
非民主國家,其政權獲得的正當性理由并不充足。“我們如果追溯任何國家的最初起源,我們就將發現,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帝系或共和國政府最初不是建立在篡奪和反叛上的。而且其權利在最初還是極其可疑而不定的。只有時間使他們的權利趨于鞏固,時間在人們心靈上逐漸地起了作用,使它順從任何權威,并使那個權威顯得正當和合理。”政權獲得的非正當性,滋生了當政者的緊張、疑慮、恐懼和不自信的心理。唯恐其他人會采用同樣手段奪取其政權的心理陰影一直揮之不去。因此,政府對于任何一個國民從心理上總是抱有懷疑和警惕的態度,從而,其選擇的制度只能是“先疑”而不可能是“先信”。相反,民主國家,由于其政權的獲得來自人民的同意,只對人民負責的權力觀念決定了政府對其國民一定會持信任的態度,并且根據社會契約的要求,也必須持有信任的態度,從而“先信”而不是“先疑”成為其制度選擇。如果這一推理可以成立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民主國家的政府普遍信任其國民,而極權國家,則對其國民總是采取高度不放心的態度。在這樣的國家,國家的暴力機器,甚至其軍事力量主要也是防止國民的謀反。
“先信”與“先疑”不僅是一種制度,而且還是一種生活方式。一旦政府被法律強制地“先信”國民,并且隨著“先信”所帶來的可見利益,一些經濟強勢集團,如大型公司等,基于長期合作的需要,并有承擔對方失信風險的能力,也會逐漸效仿采用“先信”的策略。如此一來,社會信任的風氣也就蔓延開來,并形成良性循環,就像“先疑”所導致的社會普遍不信任的風氣蔓延形成惡性循環一樣,當“先信”被普遍采納,信任會導致更多的信任,社會誠信度不斷走高,在這樣的社會里,人們生活得安全、踏實,并充滿自信。在加拿大,你可以先看病,后付費,在許多停車場,雖然沒有收費員,也沒有欄桿,但人們也會在自動售票機上自覺購票付費。同理,當“先疑”被普遍采納,不信任也會帶來更嚴重的不信任,社會誠信度不斷走低,在這樣的社會里,人們生活得緊張、恐懼和不自信,即使是去醫院看病,患者視醫生為藥販子,醫生則把患者當潛在的原告,彼此相互提防。
在“先信”被普遍采納的國家,信任不僅存在于政府部門對于公民,公民與公民之間,甚至公民對政府也會持高度信任的態度。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民主社會的司法所具有的公信力,只要沒有發現法官存在違法的確鑿證據,對于司法,民眾都會持信任和尊重的態度,而其懷疑態度只是停留在制度設計之前,而具體制度一旦通過民主而制定,其具體運作的結果,國民大都會采用“先信”的態度,除非有相反的證據。“先疑”則不然,懷疑的指向不只是指向制度設計,而且還指向制度的運作,對于來自官方的任何不利己的決定,在沒有證據的情形下,首先就推定官方是在刁難自己,即使是對于司法判決,也首先是質疑,而不是尊重,討價還價,無所可信。因此,雖然本文主要討論的是政府對公民的信任問題,但是,我們并不能否定,各種信任關系彼此存在緊密的關聯性。并且,因為政府對于公民的信任關系在整個社會中處于絕對主導和支配的地位,因而政府與公民的信任關系,實際上也就決定、至少影響到其他信任關系的展開。理解這一點,我們就會發現,民主國家盡管沒有在制度上要求公民之間必須持“先信”的態度,但“先信”卻已經成為民主國家的一種普遍現象。這表明,信任結構的相關性是何等的緊密。
中國的農業文明時期漫長,工業文明并不發達,并且民主化進程的歷史也十分短暫,遠沒有進化到西方民主國家的程度。特別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每個朝代的政權從起源上分析,都或多或少缺乏正當性,因而當權者也大都基于他人覬覦自己地位的擔心而時刻警惕顛覆政權的陰謀詭計。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一直將國民與政府視作相互對立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關系。因此,“先疑”不只是一種制度選擇,而且還成為社會的一種普遍心理,人人相互提防、相互疑懼。在這樣的文化支配下,中國人際信任關系還帶有等級性,更多的是信任權力與高位。這種對于身份和權力的依賴,打上了封建社會官僚制度和計劃經濟時代單位制度的烙印,它的反面就是對同類人的不信任。此外,中國人際關系的不信任也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有關。因為,“資源分配得越平等,就越能提高對他人的信任感。”相反,在一個資源分配不均的社會里,“富人和窮人很少有理由相信他們擁有共同的價值,因此他們會警惕他人的動機。”歷史與現實的因素決定了中國“先疑”現象的普遍性。
“先信”對于國家權力民主化嚴重依賴的原理表明,如果拋開這一依賴性因素,民間單一的和孤立的“先信”行為,其結果非但不能激勵人的誠信,相反首先付出“先信”的一方反倒會淪為他人不誠信的獵物。前段時間,網絡上流行一則很火的故事就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九十年代,剛進人中國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歐美的設計為標準。按美國安利規定,產品實行“無因全款退貨”。這項在西方實行的很好的制度,卻在中國遭遇到了滑鐵盧的失敗。精明的中國人很快以其“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國人:很多中國人回家把剛買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額退款。在上海,剛剛開業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門口排起了退款的長長隊伍,絡繹不絕,人潮涌動,一時間,令安利的美國人大吃一驚。最后,安利因虧損,不得不修改了在中國的銷售規則:產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則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國)改變了其公司制度,轉變了原先安利(美國)的營銷模式,開始逐步與“中國特色”接軌。
我們不要嘲笑國人的貪婪和不誠信的習性,而應該從歷史與現實中去尋找這一習性的真正原因。當然,強調這一點,并不是要為國人不誠信的表現進行辯護,更不是認為,中國在社會誠信的改善方面,就無所作為。事實上,制度對于文化的演進,總是可以起著較為直接的引導作用,而這也正是本文寫作的目的。如果法律首先強制政府率先對于公民信任,或許可以開啟一個良好的開端,從而影響并引導其他信任關系的建立。目前,中國政府正在致力誠信體系建設,我們有理由期盼,隨著中國民主化的不斷進步以及相關制度的日益完善,那種“如何證明你媽是你媽”的笑話,也將隨著“先信”在中國的開花和蔓延而最終絕跡。
參考文獻:
[1]宮本欣,法學家茶座(第6輯)[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2]鄭也夫,信任論[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
[3]埃里克·尤斯拉納,信任的道德基礎[M],張敦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4]亞歷山大·J·菲爾德,利他主義傾向——行為科學、進化理論與互惠的起源[M],趙培,等,譯,長春:長春出版社,2005:26.
[5]麥特·里德雷,美德的起源——人類本能與協作的進化[M],劉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282.
[6]邁克爾·舍默,當經濟學遇上生物學和心理學[M],閭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166.
[7]馬克·E·沃倫,民主與信任[M],吳輝,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8]周安平,人民監督員制度的正當性與有效性質疑[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7(2).
[9]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M],趙磊,等,譯,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147.
[10]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韓朝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32.
[11]翟學偉,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86.
[12]休謨,人性論(下)[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597.
責任編輯:龍大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