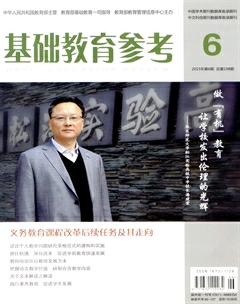關于文本解讀之解讀
竇銀強,四川省高中語文特級教師。從事高三語文教學近三十年。教育理念為“語文即生活”:其“語段高效閱讀法”、“文本三層解讀法”、“生活化作文”等在省內外有較大影響:教育部“2010新課程高中語文培訓”骨干教師,獲“2009感動四川十大教師”、“優秀教師”、“師德先進個人”等稱號:在報刊發表文章470余篇,主研課題12項,學術專著5部。
平時我們閱讀文學作品,總是依據自己的生活經歷或閱歷,與作品中的人物對話,總能在作品人物的不同命運和遭遇中,或多或少地找到自己的影子,從而和作品中的人物產生心靈上的共鳴,獲得自己的獨特感悟。這就是文學欣賞中多元化解讀的魅力所在。正如莎士比亞所言:一千個人眼里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但有些文學作品一旦進入教材,就要承擔起語文教學的憑借功能、示范功能、教育功能和發展功能;就要完成教學大綱賦予的具體教學目標和任務。因此,教師就不能隨心所欲地多元化地欣賞文本了。也就是說,不能用文學欣賞,替代負有具體教學目標和任務的語文文本解讀。
一、“本”來面目:閱讀教學非文學欣賞
語文閱讀教學中的文本解讀,是語文課程資源的核心部分,文本是語文閱讀教學活動的媒介和載體;而文學欣賞中的文本解讀,文本是廣義的語言材料,讀者可依據自己的生活經歷或閱歷進行多元化解讀。
語文閱讀教學中的文本是狹義的文本,即語文課本。重視對語文課本的解讀,是語文學習的一個重要途徑。語文閱讀教學中的文本解讀,就是通過對文本的具體分析,來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從而通過文本的不同表現形式去理解文本內涵,與作者產生心靈上的共鳴。其“解讀”之意在于——通過對課文(即文本內容)的具體分析,通過教師和學生對文本的具體感知、理解、解釋、體驗、建構、評價和反饋等環節,完成具體的教學目標和任務,這是培養學生學會搜集整理信息、認識客觀與自我世界、發展思維能力、獲得審美體驗的重要載體和途徑。
基于此,我們只有明白文學欣賞較之語文教學與研究的異同,才能將閱讀教學中的文本解讀落到實處,進而有用、有效地推進閱讀教學的文本解讀。
二、瞄準教學目標,具體而準確地解讀文本
只有學生借助文本中的語言文字符號,準確領會作者的思想內涵并練就出一定的閱讀技能,才能達成閱讀課的教學目標。因此,要設計并實施好這一系統工程,我們不妨從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抓住文本內容中的關鍵詞語、句子等具體的語言材料,去梳理文本的內涵和藝術本質。這是“一種技術,但它是一種有思想引領、有思想貫注的技術”。因為文本的思想是通過具體的、有感情的、有色彩的詞語、語句向外傳遞的,故梳理文本內涵時,面對這些語言材料,要有“高度的敏感和警覺”,要“在漢語中出生入死”,要能夠“沉入詞語”中,“從語言出發,再回到語言”。這些指導思想很具體地說明——應該怎樣規范自己的文本解讀行為,以便在實際操作時會時刻保持敏感性,推敲詞語,不斷思考文本的價值,審視文本的意義。
同時,解讀文本的過程還是知識儲備的過程。在閱讀過程中,要關注和留意文本中的鮮活語言材料。比如,鋪敘美好的親情和友誼;描摹美麗的景物和感人的場面;關注現實生活的熱點;熱愛有品位的文化藝術;省察價值取向、道德情操;歷練人生觀念、思想方法;了解前沿科學技術的發展;展望、預測美好的未來。文本中的許多鮮活語言材料,恰恰體現了作者對生活、對人生的感悟和反思,而讀者在解讀的過程中,往往結合了自己的生活經歷,灌注了自己的思想,慢慢地與文本的語言材料融為一體。所以,從文本里走出來的讀者,已在不知不覺、潛移默化中有了新的知識儲備。
二是根據文本的特質,確定該文本在本冊、本單元或本課閱讀教學中的教學任務。教學大綱將具體的教學任務分解到不同層次的每一個學年、學期;而每一個學期的教學任務又被分解到每一個單元、每一篇文本上。所以,我們解讀文本內容時,先要將文本解讀的重點、難點準確定位。然后再考慮運用什么樣的手法(可以從標題、線索、情節、形象人手)去抓住文本的關鍵詞、語句等具體語言材料,加以梳理、整合,解讀文本的思想內核和表現形式,從而確定文本的教學重難點;體現其教學價值時,要以體現層次性(即針對不同教學對象或考慮教學對象的個體差異)的原則來設計教學的重難點、教學方法及手段。
魯迅先生說過:“《紅樓夢》,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但類似的文本一旦進入教材,就具有了以下“四性”。
憑借功能。文本是語文教學內容的載體,是借以實現語文教學目標、發揮語文教育功能的物質基礎。語文教學加強基礎、傳遞文化、培養能力、養成習慣、進行思想教育和情感陶冶等方面,都離不開文本這一憑借物。如解讀文本內容、提取文本關鍵詞,便是培養學生概括能力、提取關鍵信息能力的最佳途徑。借此,還可以讓學生形成一些閱讀的判斷技能,如把握好概括文本內容的關鍵詞既可以是雙音節詞,也可以是四字短語或多音節短語;關鍵詞一般是名詞、動詞、形容詞,絕不會是虛詞;提煉的基本步驟一般是:壓縮內容——提取主干——篩選比較——整合表達(可用“誰怎么樣”的格式準確概括文本內容)。
示范功能。語文教學挑選典型規范的作品作為文本,意在通過定向、規范的語文訓練,使學生集中、高效地學習語文知識,培養語文能力。文本除了課文內容和語言形式的示范功能外,還包括訓練的難易深淺在內的示范功能。
教育功能。語文是表情、達意、載道的應用性工具,這就決定了學生在學習文本的過程中,離不開情、意、道的內容。教學具有教育性,語文教學的教育功能主要就是憑借文本而實現的,因為文本蘊涵著極其豐富的對學生進行思想情感、道德意志教育和精神陶冶的內容。
發展功能。現代教學論認為,教學與發展是互相聯系的。如文本為學生語言能力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使學生的語言不斷從貧乏走向豐富,由幼稚走向成熟,由呆板走向生動。又如,文本作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載體,對學生的政治品質、思想品質、道德品質,以及情感、意志、性格等個性心理品質的發展,也有著熏陶漸染、潛移默化的作用。
因此,要解讀好文本,首先要粗讀,即解讀文題。因為文題的審讀突出了思維焦點;通過文題可提煉出作者的寫作意圖;此外還要弄清文題是涉及的什么話題(這就需要從文本中去提煉,從關鍵詞語、語句、語段中去提煉,從行文結構、語法邏輯關系中去提煉,從文本相關材料中去提煉)。其次是精讀。要從文本具體內容解讀中實現思維發散——從眾多文本的行文思路中確定:文本寫了些什么(可采用發散收攏法、因果法等篩選信息、歸納要點)以及文本為什么要這樣寫,從而實現思維突破(文本眾多材料中哪些是我需要的?哪些語言材料可轉化成我的知識儲備)。這時候就需要突破現有思維,在對文本內容的識記、理解中,挑選文本恰當的語言材料,運用到自己對自然、人生、社會的認識中去,即由揭示文本的主旨,到自己如何更好地表現主旨,最終實現整合建構。通過自己的新構思,強調創新思維的整合(人無我有,人有我新)——通過文本合適的結構安排組織好文章(列提綱法、畫結構圖法),從而建構具有自己個性化的、今后該如何操作的方法和措施。這就是教學中解讀文本所體現的發展功能。
三是走進文本,把握好文本解讀與文學賞析的關系。依據文本內容恰當確定教學目標(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要扣住文本后的思考與練習,來確定閱讀的具體方法和措施。反之,如果游離文本,不去整體把握文本,而抓住文本其中的一點內容就斷章取義并無限拔高、升華主題;或者教師以自己對文本的理解,代替了不同層次學生對文本的理解;或者教師把對文本的評價、文學賞析當作對文本的解讀,就忽視了文本的教學價值。當然,能適當地運用當今文學鑒賞、文藝批評的方法去解讀文本,是很好的解讀方法和技巧,但角度選擇一定要恰當,定位要準確。
站在學生的視角去解讀,是語文課堂教學與自我文學欣賞最大的區別。自我文學欣賞是一種自由度很高的閱讀活動,讀者往往會用自己的角度和經歷重新解讀作品,與文本的文字產生共鳴并對自身產生影響,閱人便是閱己,讀文便是讀心。而在語文閱讀教學過程中,文本解讀是一種定向閱讀,同樣的一篇文本,放在不同的年級段,是帶有不同閱讀任務和不同教學價值的。這就要求教師一定要站在學生的視角去解讀,循序漸進,由淺入深,逐漸為學生搭建起解讀文本、培養閱讀能力的知識架構。但是,許多教師在解讀的時候,往往又不自覺地以自己的經歷或與文本類似的經歷,來替代文本本身的具體情境,從而走進了文本教學的誤區——可以說,這是當下學生文本理解能力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是跳出文本,但不能脫離文本,且要正確處理文本解讀與文學評價的關系。閱讀教學中往往要緊扣文本,但又不能拘泥于文本。要針對教學對象的不同層次、認知水平,來恰當確定知識與能力培養目標。學生對文本的解讀,往往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并以此聯系自己以往的閱歷,去拓展、深化自己的視野,這就需要跳出文本,逐步演變成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即由閱讀感悟、模仿領悟,形成能力而循序漸進。但如果教師在解讀文本時,脫離文本內容去展示個人才華,天馬行空地無限拔高文本主題,或不著邊際地旁征博引,以顯示自己的文學功底之深厚。那么,學生本身就沒有真正走進文本里去,又怎么跳得出來呢?
所以,要跳出文本,首要的是要細讀文本。在細讀文本的過程中,至少要經過三次以上的反復研讀,由淺入深,由表及里,才能把握文本、接近文本的本質。初讀時,語文教師最好研讀“白本”,即丟掉《教學參考》《教案設計》之類現成的東西,自己先走進文本里去探究一番,整體把握“是什么”,才能有自己的主見,而不是人云亦云,應付了事,甚至道聽途說,以訛傳訛,誤人誤己。
其次要精讀。深入到文本里去,對敏感的詞語、句子要追根溯源地搞清“為什么”。當然,這里會遇到許多疑惑,會發現很多文本背后的意蘊是初讀時所不能理解的。此時讀者就只有延著作者的思路,和作者進行心靈溝通、交流乃至碰撞,才能逐漸接近文字的本真。
最后才是跳出文本,對文本的理解需要再次反思。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幾位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中,在談到《紅樓夢》時說:“《紅樓夢》我至少讀了五遍。”這說明對一篇文本,至少要讀三遍以上方能談得上熟悉。初讀的閱讀積累和精讀的考證閱讀,導致讀者的認識根基已經較為深厚,這時就需要再回頭去審視文本的內涵和學生理解程度的差異。兩相映照之下,文本的教學價值便有了棲息的土地——教師舍去一些,留取一些;學生走近一些,伸手拿走一些。這樣的文本解讀才是閱讀教學的本真。因此,只有經歷“把薄書讀厚,再把厚書讀薄”的過程,才能達到閱讀教學中文本解讀的最佳境界——跳出文本。
三、堅持“三要”原則,做實文本閱讀教學
弄清楚教學文本與普通文本解讀的區別后,我們就要在實際教學中把握好解讀的原則,把文本教學更加高效地落到實處。
第一,要與編者對話,揣摩編者之用意。教師只有把握好編者的編寫意圖,了解課標的理念和要求,依據文本所在單元的教學要求和目標,才能進行準確的文本解讀,才能把握文本的價值取向,才能合理、有效地使用文本,有的放矢地進行閱讀教學。同時,解讀文本要從文本的整體到局部、由局部到詞句去篩選、歸納、整合,缺一不可。因為文本的具體語言材料是有生命、有溫度、有色彩的。
第二,要與文本作者對話,體會文本作者的思想。“與作者對話”,是教師品味、探究文本的過程。教師要將自己的情感傾注其內,使自己的思想與作者產生共鳴。只有當教師深入到教材的字里行間去,真正走進作者的情感世界,體會作者的思想以后,才能把握文本意義及實質性的重點內容,給文本價值取向準確定位。走進了文本,領悟了文本,才能在課堂上引導學生合理地解讀文本,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美國教育家杜威說:“一個真正把握教學內容,吃透教材結構的人,才能靈活自如地運用探究學習方法。否則,任何的生搬硬套,不論動機如何良好,只能導致兩種結果——犧牲學生和敗壞這種理論的聲譽。”故教師要依據文本引導學生自然地走進文本,理解文本,再走出文本,去沐浴文本精神的陽光和鳥語花香。
第三,要與學生對話,照顧到不同層次學生的閱讀感受。文本解讀的最終目標是引導學生走進文本,“閱讀是學生的個性化行為,不應以教師的分析代替學生的閱讀實踐。”不要把學生的讀書收獲全都當做是對文本的正確理解,而全然不顧文本的價值取向;同時,又不能一意孤行、理所當然地把教師的個人認識和感受強加于學生。
只有從不同學生的層次、角度來解讀文本,才有利于課堂上及時、有效地引導和調控,使學生能及時調整自己與作者的對話,更正確、全面、深入地理解文本的意義。
綜上所述,文本一旦被賦予了教學的目標價值,教師就一定要以教學的眼光來審視文本,以教學的口吻來解讀文本,以教學的思維來激活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