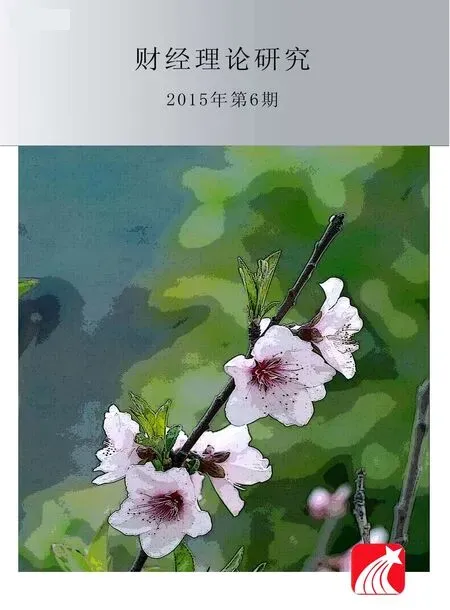地方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
傳導機制與實證研究
劉 偉1,2,王 嬌2
(1.重慶工商大學 管理學院,重慶 400067;2. 重慶工商大學 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重慶 400067)
?
地方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
傳導機制與實證研究
劉偉1,2,王嬌2
(1.重慶工商大學管理學院,重慶400067;2. 重慶工商大學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重慶400067)
[摘要]文章在分析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機制的基礎上,利用中國地方省份1995-2012年面板數據和可靠的計量方法,實證分析地方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檢驗結果顯示靜態面板數據模型與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結果基本一致:地方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社會保障支出、農林水事務支出和科教文衛支出均是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影響因素,地方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社會保障支出和農林水事務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是擴大效應,科教文衛支出則有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本文研究表明,不同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非常復雜,可通過對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社會保障支出、農林水事務支出和科教文衛支出進行深化調整,在政府公共支出資源配置上適當向農村地區傾斜,才能有效調節城鄉居民間過大的收入差距。
[關鍵詞]地方公共支出結構;城鄉收入差距;省級面板數據;靜態與動態面板估計
一、問題提出
作為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手段之一,公共支出一直被認為在促進社會收入公平分配、調節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公共支出絕對規模一直處于擴大的態勢,近年來占GDP的比重呈快速增長的勢頭,由1995年的11.2%增加到2012年的24.3%,在宏觀調控和資源配置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正在逐漸拉大卻是不爭的事實,城鄉居民收入比由1997年的2.47上升到2009年的3.33,雖然2010-2012年有所回落,但收入比依然處于3.1以上的高位水平。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引起理論學者和決策者的極大關注:為什么作為最重要收入再分配手段之一的公共支出在其規模逐年擴大情況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呈不斷擴大的趨勢(見圖1)?如何理解中國公共支出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城鄉收入差距長期持續保持擴大的現象?如果直觀地以公共支出規模的變動來解釋城鄉收入差距持續大幅擴大未免太過于簡單和表面化,且難以確切把握城鄉收入差距的內在規律和背后深層次原因。從社會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公共支出結構直接體現的是政府所控制的社會公共資源的流向,而政府公共支出的不同流向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所產生的促進或抑制程度是不同的。同時,近三十年來地方公共支出占總公共支出比重逐年上升,2013年達到了85.35%,表明地方政府在調節各省社會經濟等方面上的公共經濟資源在增加。因此,探討省域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社會保障支出、農林水事務支出和科教文衛支出等公共支出結構變量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除此之外,系統分析不同公共支出結構變量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可以為政府部門制定相應的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公共支出政策提供啟示意義。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第三部分為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第四部分為實證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結論及政策啟示。

圖1 1978年-2012年財政支出與城鄉收入差距變動趨勢①
二、文獻綜述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許多學者從金融發展、城鎮化、對外開放和勞動力市場等不同視角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原因展開了詮釋,但研究結論不一致。而有關公共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研究上,研究結論同樣存在差異。一種觀點認為公共支出有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縮小,認為傾向于基本公共服務的公共支出會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比如公共教育和醫療衛生支出會通過給低收入群體帶來較大的收入效應(寇鐵軍等,2002),[1]傾向于農業投入以及科教文衛支出增加的公共支出能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陳安平和杜金沛,2010)。[2]我國城鄉公共投資差距縮小或收斂會促進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楊飛虎等,2014)[3]。另一種觀點認為公共支出并非有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縮小。主要在于城市偏向的教育經費投入政策導致了城鄉公共教育水平差異,進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公共教育水平差異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貢獻程度達到將近35%(陳斌開等人,2010)。[4]而隨著財政分權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政府的生產性支出和公共產品支出更偏向于城市部門,從而更容易引起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陳工和洪禮陽,2012);[5]另一方面,城市偏向的財政再分配政策導致初次分配扭曲、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重下降,從而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雷根強和蔡翔,2012)。[6]而從支出功能層面上看,公共教育支出和社會保障制度并沒有很好地發揮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沒有起到調節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形成了“逆向調節”的負效應,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劉渝琳和陳玲,2012)。[7]近10多年來,政府嘗試通過擴大農村公共支出規模來促進農民收入增長以緩解城鄉間收入差距,但由于政府重視程度不夠和目標偏差,以及結構上農業科研和農村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支出過低,使得農村公共支出在降低城鄉收入差距上的作用并不夠顯著(沈坤榮和張璟,2007)。[8]
雖然國內學術界在有關公共支出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是關于國內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問題的研究則比較薄弱、系統性不強,主要體現在:一是缺乏系統性,大多只研究某一類型的公共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而關于從公共支出視角探討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尚缺乏系統研究;二是實證研究比較薄弱,大多停留在簡單的定性分析上;三是從現有實證研究結果來看,學術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我們認為國內初級階段的公共支出結構,可能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試圖從以下兩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拓展:首先,構建包括一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農林水事務支出和科教文衛等變量的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計量模型,著重分析公共支出結構變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其次,采用靜態與動態的面板計量方法實證分析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三、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傳導機制
從社會公共資源配置視角而言,公共支出結構直接關系到地方政府所控制的社會公共資源的利用與分配,而政府對公共支出資源的不同配置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所產生的促進或抑制程度是不同的,從而會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產生影響效應。
(一) 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從支出的用途和屬性來看,一般公共服務支出(2006年前為行政管理支出)②包括辦公經費和人員經費兩部分。其中辦公經費主要提供較為完善經濟發展環境的支出,人員經費幾乎全部是行政人員的工資性收入,而行政人員大部分屬于城鎮居民(李金玲,2008)[9],直接受益對象主要為從事行政管理的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難以從該項支出中獲得直接的收益。同時在公共財政收入一定的條件下,如果用于行政管理的費用過多,政府就不得不壓縮用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教育、科技、醫療等方面的支出,很多民生問題被擱置,得不到應有的改善,從而影響整個公共產品配置的效率不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尹利軍和龍新民,2007)[10],從而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
但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有效的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可以保證政府機構的正常運轉和政府職能的實現,從而提高政府機構的運轉效果,促進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和城鄉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從而會有利于改善社會收入分配狀況。同時,有效的一般公共服務支出能夠提升公共資源的配置效率,會根據城鄉之間的經濟發展現實來配置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及時調節城鄉居民的收入分配狀況,防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因此,從這個視角來看,有效的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二) 社會保障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福利經濟學和凱恩斯學派等均認為社會保障是調節城鄉收入差距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主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以及社會保險基金征繳和給付的方式實現。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成熟的社會保障制度在社會分配上的調節作用顯著。但是,社會保障制度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賴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通常而言,覆蓋面越廣,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就越明顯;覆蓋面越窄,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就會越弱,甚至有可能導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由于戶籍制度與城鄉分割的原因,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中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存在差異安排,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保障支出幾乎只覆蓋城鎮居民。雖然近年來政府加快了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在農村啟動了醫療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擴大了對農村居民的覆蓋面,但除了東部沿海一些經濟發達地區開始進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試點外,其他大多數農村地區尚未建立與城鎮同樣待遇的社會保障體系,大部分農村居民尚未享受到城鎮居民同樣的基本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中城鄉之間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差別較大。2011年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年人均補助標準分別為935.9元和130.1元,城鎮居民獲得的補助約為農村居民的7.19倍;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平均標準和補助標準的城鄉之比分別為2.01倍和2.26倍(邢偉,2013)。[11]因此,城鄉間社會保障資源分配嚴重失衡,有可能導致了城鎮居民獲得的轉移支付收入和福利收入遠高于農村居民,進而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三) 農林水事務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農林水事務支出(2006年前為支農支出)是國家公共財政對農業一種直接的支持方式,也是再分配過程中國民收入對農業的一種凈流入。一方面,農林水事務支出通過提供農村經濟發展所需的農村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準公共產品、準公共服務來改善農業生產、生活條件以及創造市場交易的外部有利條件,有助于直接或間接地增加農民收入(張車偉,2003)[12];另一方面,農林水事務支出通過對“雖然經濟效益差、但社會效益好”的農業公共性投資項目及大中型農業基礎建設項目進行投資,不但能夠促進市場上的資金、勞動力和技術等各種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流動,而且可以促進這些要素在農業內部各行業之間合理配置,從而有利于提高農業發展水平,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冉光和和唐文,2007)[13]。因此,理論上可能存在“農林水事務支出增加→農村公共服務水平提升→促進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邏輯機制。
但如果農林水事務支出長期存在使用效率低的問題,上述邏輯傳遞機制并不一定能起作用。有不少學者的研究就認為我國農林水事務支出存在使用效率低的問題③,直接影響到農村公共服務品數量與質量的提升,從而導致農林水事務支出難以轉化為農民收入的增長。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農林水事務支出就不能有效的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四) 科教文衛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科教文衛支出主要包括公共科技支出、公共文教支出和公共衛生支出,我們分別來討論三者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1.公共科技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源泉。因此,各國政府通常選擇運用公共財政支出手段支持科學技術的發展,進而帶動和引導整個國家的科技投入、通過科技進步來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穩定發展。從這個層面來講,公共科技支出能夠通過引導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普及應用,促進城鎮與農村經濟共同發展來使城鄉居民獲得收益,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從而有利于改善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狀況。
但科學技術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科學技術研究尤其是基礎科學研究最大的特征是投入規模大、周期長與風險高。因此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條件下,企業對科技研究投資是非常謹慎的,而政府為了國家的長遠經濟發展戰略,往往會對企業的科技研發投資進行適當的干預,使整個社會的科技資源配置與國家發展戰略相匹配。而在當前世界經濟社會活動空間分布已經進入以城市為主的時代里,政府在城鎮產業和農村產業的科技投入就會不一致,會更傾向于城市的集聚,城鄉的經濟發展就會出現差異,從而使城鄉居民從科技投入與進步上獲得的受益就會不一致。比如,我國自建國以來所推行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林毅夫和劉培林,2003)[16],國家科技投入偏向于城鎮工業發展,而農業的技術研究與開發能力有限,對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增收產生不利的影響,這樣的狀況就有可能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
2.公共文教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根據舒爾茨和貝克爾的人力資本理論,普通教育、職業培訓、繼續教育可以積累人力資本進而提升勞動者自身的能力與素質。而能力與素質是決定個人收入高低的關鍵因素,生產能力與素質高的勞動者可以從事高技能的行業,獲得較高的收入,相反,勞動技能和素質較低的勞動者只能從事純體力消耗的低收入工作。因此可以看出,受教育、培訓程度高低決定著勞動者收入的高低,公共文教支出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主要通過人力資本傳導途徑:公共文教支出增加→積累人力資本水平→提升勞動力能力與素質→進而影響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
很顯然,政府對城鄉教育資源的不同配置將會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出現差異。如果教育支出尤其是基礎教育支出和基本技能的職業培訓傾向于低收入群體,擴大教育、培訓在低收入群體中的普及性,增加低收入群體家庭成員受教育的機會,提升低收入群體的勞動素質與技能,進而增加收入,那么該項支出就會縮小因受基礎教育程度不同而產生的收入差距。但如果公共教育經費投入偏向城鎮和城市各級重點學校,就會導致城鎮學校教育質量遠高于農村、城鎮居民獲得的教育和再教育機會遠高于農村居民。因此,由城鄉教育差異所導致的城鄉居民人力資本水平不同將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3.公共衛生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早在1909年Irving Fisher在《國家健康報告》中把健康作為一種國家財富的形式,認為不健康會帶來“因為早亡而喪失的未來收益的凈現值、因為疾病而喪失的工作時間、花費在治療上的成本”的損失[17]。通常,越健康的勞動力能夠獲得的就業機會就越多,就越能提高個人的勞動生產率和延長工作時間,獲得的勞動收入報酬也就越高(潘思思,2007)[18]。另一方面,健康勞動力意味著疾病發生的概率減少,這不僅能夠節省疾病治療的支出,而且能夠減少患病的時間成本,勞動力有更多的時間參與工作、提高收入水平。根據舒爾茨和貝克爾的人力資本理論,健康是人力資本投資和積累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因素④,是其他形式的人力資本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對個人家庭收入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公共衛生支出作為居民健康水平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⑤,其支出增加有利于居民健康水平⑥的改善(Mayer和Sarin,2005[19];王俊,2007[20])。因此,公共衛生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傳導機制可以歸納為:公共衛生支出→居民健康水平→人力資本積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相對而言,我國農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經濟回報更大(劉國恩,2004)[21],不少學者認為營養和健康是制約農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張車偉,2003)[12],健康狀況在對農村家庭獲取非農就業收入乃至增加家庭收入方面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魏眾,2004)[22]。從這個角度來看,公共衛生支出有利于調節城鄉收入差距。
四、模型設定、數據來源與檢驗方法
(一)模型設定與數據
根據上述公共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機制分析,不同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效應不同,我們需要通過實證分析來判斷上述影響的傳遞機制是否成立。為此,本文構建以下計量模型(見式(1)):
yit=βXit+φKit+vt+εit
(1)
其中i和t分別表示省份和年份;vt是難以觀測的個體效應(individual effect);εit是擾動項。yit表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Xit表示所選擇的各種公共支出結構變量。根據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職能理論,收入分配是公共財政的三大職能之一。[23]其中,公共支出主要通過社會保障支出、公共教育支出、支農支出等轉移性支出和購買性支出來調節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閆坤和程瑜,2010)。[24]因此,我們選擇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在《中國統計年鑒》上,2006年之前稱為行政管理支出,2007年后改為一般公共服務)、就業與社會保障支出、農林水事務支出(也稱為支農支出)和科教文衛支出(科學技術、教育、文化體育與傳媒、醫療衛生支出的簡稱)作為各省的公共支出結構變量。Kit表示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一組非公共支出宏觀經濟變量。
討論公共支出結構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效應,通常而言,學術界都以各項公共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來衡量公共支出的結構。但這種衡量方式會導致計量模型存在異方差。而為了消除異方差,本文采納對城鄉收入差距和公共支出結構變量取對數值的衡量方法。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差值的對數值表示。公共支出結構變量中的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就業與社會保障支出、農林水事務支出和科教文衛支出均以其支出的對數值表示。控制變量本文選擇的是各省的經濟增長率和各省的城鎮化率。其中,經濟增長以各省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值表示;學術界通常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城鎮化率,但由于有些省份連續多年的城鎮人口統計缺失,所以本文以城鎮就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的比重來表示各省的城鎮化率。
數據采用上以我國1995年-2012年省級面板數據為主。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宏數據庫。由于數據缺失問題,本文的面板數據樣本不包括西藏和港澳臺地區,同時將重慶和四川的數據合并。具體變量的統計性描述見表1。

表1 變量統計性描述
(二)檢驗方法
估計方法的使用上,為防止單純使用一種估計方法而導致檢驗結果可信度不高的問題出現,我們依據上述所構建的模型,運用我國29個省份1995年-2012年間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該模型。考慮到不同模型設定可能導致不同的結論,本文將同時實證檢驗靜態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以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在靜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上,分別采用Pool OLS回歸方法、固定效應方法(FE)和隨機效應方法(RE)來實證分析地方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上,分別采用差分廣義矩估計方法(diff—GMM)和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sys-GMM)兩步估計實證分析地方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五、實證分析
(一)靜態面板數據模型估計
本文在式(1)基礎上,構建如下的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靜態面板數據模型,見式(2)。
GAPit=β1GGFWit+β2SSBZit+β3ZNZCit+β4KJWWit+β5urbit+β6gdpit+vi+εit
(2)
GAPit表示各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GGFWit表示各省的一般公共服務支出;SSBZit表示各省的就業與社會保障支出;ZNZCit表示各省的農林水事務支出(支農支出);KJWWit表示科教文衛支出;gdpit表示各省的經濟增長率;urbit表示各省的城鎮化率。其他變量解釋與式(1)相同。
本文采用混合橫截面估計(Pool OLS)回歸方法、固定效應方法(FE)和隨機效應方法(RE)等回歸方法對式(2)進行在靜態面板模型設定,估計結果見表2,其中列(1)、(3)、(5)為未納入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根據表2的估計結果,在未控制變量和有控制變量的情況下,估計結果均表明一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農林水事務支出和科教文衛等公共支出結構變量幾乎都顯著進入模型。其中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社會保障支出和農林水事務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顯著為正,表明三者支出增加會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而科教文衛支出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顯著為負,表明增加科教文衛支出會有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兩個控制變量中城鎮化率的影響效應不顯著,經濟增長率表現為正效應,表明經濟增長率提升反而擴大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表2 靜態面板數據模型估計結果
注:括號內為t值,***、**和*分別表示為1%、 5%和10%的水平下顯著.
(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估計
宏觀經濟變量在長期內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實際中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動既取決于當前的經濟形勢、也受過去經濟狀況的影響。因此,本文通過引入了滯后被解釋變量(lagged variable)城鄉收入差距的滯后值來建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但這一方面會使被解釋變量受其一期滯后值影響而導致自相關問題,或者收入差距和一些解釋變量之間很可能是同時決定的,從而導致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另一方面在動態面板數據計量模型中,由于滯后被解釋變量的存在,使得利用OLS和GLS得到的估計量是有偏的和非一致的。因此,本文采用Hansen(1982)提出的廣義矩估計(GMM),遵循Arellano和Bond(1991)、Blundell和Bond(1998)的估計方法,通過差分數據轉換和引入合適的工具變量來有效控制被解釋變量的自相關及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進一步檢驗動態面板數據結構下一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農林水事務支出和科教文衛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25-27]動態面板數據結構方程構建如下式(3):
(3)
其中變量解釋與式(2)相同。通常研究者一般采用一階差分 GMM 方法(diff-GMM)和系統GMM方法(sys-GMM)來估計這類具有動態性質的模型。但在時間維度較短的情況下,sys-GMM估計量將優于diff-GMM估計量(Bond et al.,2001)。[28]因此,考慮到模型的動態性質和所收集到數據時間維度較小的特征,本文在 Bond et al.(2001) 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分別用diff-GMM 和sys-GMM方法來估計上述方程。在計量分析中,差分GMM和系統GMM的兩步估計還要進行Arellano-Bond test for AR(1) and AR(2)檢驗,考察一次差分殘差序列是否存在二階自相關;同時通過Sargan過度識別約束檢驗方法對所使用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檢驗原假設是所使用的工具變量與誤差項不相關。
估計結果見表3。其中列(7)和(8)采用混合橫截面估計方法,列(9)和(10)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方法估計,列(11)和(12)采用差分GMM估計模型,列(13)和(14)采用系統GMM估計方法。其中差分GMM估計和系統GMM估計的GAPit-1估計值落在混合橫截面估計和面板固定效應估計的估計值之間⑦,可見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對照表2和表3,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結果與靜態面板數據模型的結果基本一致,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社會保障支出、農林水事務支出和科教文衛支出均是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影響因素,一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支出和農林水事務支出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為顯著的正效應,表明地方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社會保障支出和農林水事務支出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影響因素,其支出的增加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但是相對而言,社會保障支出與農林水事務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彈性系數較小。科教文衛支出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為顯著的負效應,表明增加科教文衛支出會有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兩個控制變量經濟增長率和城鎮化率均對收入差距存在顯著的正效應,也表明地方各省經濟增長率和城鎮化率也是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
(三)對估計結果的總結
根據靜態與動態面板數據的估計結果,我們認為模型的估計結果是無偏和穩健的。檢驗結果顯示靜態面板數據模型與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結果基本一致:公共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非常復雜,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社會保障支出和農林水事務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是擴大效應,科教文衛支出則有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

表3 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估計結果
注:①Hausman FE v. RE為對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做Hausman檢驗,根據結果選擇固定效應;②AR(1)和AR(2)分別為Arellano-Bond test for AR(1) and AR(2)的p值;③括號內為t值,***、**和*分別表示1%、 5%和10%的水平下顯著.
六、政策啟示
根據實證結論,要有效調節城鄉居民間過大的收入差距,可通過公共支出結構進行深化調整。首先,在一般公共服務支出上應從嚴控制行政經費數額和行政人員的膨脹,精簡政府機構和提高辦事效率,加快政府公務用車改革和公務接待費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支出的使用效率。其次,在社會保障支出上應加快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與完善,推動城鄉、區域之間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與整合,重點提高對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補貼水平,健全社會救助體系和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逐步形成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待遇調整體系。第三,在農林水事務支出上,應注重提升其支出效率,可通過對農業行政事業機構的調整,控制并減少農業行政事業單位的事業費開支,嚴格執行支出預算專項專用,并定期公開相關信息和接受社會監督,把農林水事務支出真正用到支持對農民的種糧補貼和農業的生產上。第四,在科教文衛支出上,應當提升公共財政支出中科教文衛支出的比重,加大對農村地區科教文衛支出的支持力度,以此來提升農村人力資源水平,促進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縮小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
[注釋]
①城鄉收入差距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表示.
②2007年財政收支分類改革對原有預算科目進行大幅調整和歸并,行政管理支出調整為一般公共服務.
③孫文祥和張志超(2004) 、解堊(2006) 和陳思霞(2009) 的研究闡述了這一點[14]-[15].
④根據該理論,舒爾茨認為教育、健康、培訓和遷徙是人力資本的主要構成內容.
⑤在有關公共衛生支出與居民健康之間關系的研究上,國內外學者主要以Grossman健康需求函數和健康生產函數為基礎,從公共衛生支出對居民健康水平的影響和公共衛生投入對居民健康公平的影響這兩方面展開的.
⑥學者們主要采納嬰兒死亡率及兒童死亡率指標來衡量居民的健康水平.
⑦學者們通常認為對被解釋變量滯后一階的估計值而言,Pooled OLS 估計高估了真實值,而Fixed effects 估計則低估了真實值.雖然兩個估計均為有偏的,但卻決定了真實估計值的上界和下界.
[參考文獻]
[1]寇鐵軍,金雙華.財政支出規模、結構與社會公平關系的研究[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2,(6):17-23.
[2]陳安平,杜金沛.中國的財政支出與城鄉收入差距[J].統計研究,2010,(11):34-39.
[3]楊飛虎,魏驍,高遠.我國公共投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J].財經理論研究,2014,(5).
[4]陳斌開,張鵬飛,楊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資本投資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J].管理世界,2010,(1):36-43.
[5]陳工,洪禮陽.財政分權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J].財經研究,2012,(8):45-49.
[6]雷根強,蔡翔.初次分配扭曲、財政支出城市偏向與城鄉收入差距——來自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2,(3):76-89.
[7]劉渝琳,陳玲.教育投入與社會保障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聯合影響[J].人口學刊,2012,(2):10-20.
[8]沈坤榮,張璟.中國農村公共支出及其績效分析——基于農民收入增長和城鄉收入差距的經驗研究[J].管理世界,2007,(1):30-42.
[9]李金玲,宋效中,姜銘.我國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的實證分析[J].內蒙古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6).
[10]尹利軍,龍新民.行政管理支出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優化策略[J].改革與戰略,2007,(11).
[11]邢偉.城鎮化背景下促進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與整合[J].宏觀經濟管理,2013,(7):28-30.
[12]張車偉.營養、健康與效率——來自中國貧困農村的證據[J].經濟研究,2003,(1):3-13.
[13]冉光和,唐文.財政支出結構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實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7,(8):75-77.
[14]孫文祥,張志超.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的影響[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4,(12):3-9.
[15]解堊.財政分權、公共品供給與城鄉收入差距[J].經濟經緯,2007,(1):27-30.
[16]陳思霞.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財政支出結構優化研究[J].群文天地,2009,(3):80-83.
[17][美]享德森.健康經濟學[M].向運華等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
[18]潘思思.健康人力資本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影響[D].杭州:浙江大學,2007.
[19]Mayer,Susan,E.& Sarin,Ankur.Some Mechanisms Liking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nfant Mortality[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5,(60):439 -455.
[20]王俊.中國政府衛生支出規模研究——三個誤區及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07,(2).
[21]劉國恩,William H.Dow,傅正泓,John Akin.中國的健康人力資本與收入增長[J].經濟學(季刊),2004,(4).
[22]魏眾.健康對非農就業及其工資決定的影響[J].經濟研究,2004,(2).
[23]理查德·馬斯格雷夫,佩吉·馬斯格雷夫.財政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24]閆坤,程瑜.促進我國收入分配關系調整的財稅政策研究[J].稅務研究,2010,(3).
[25]Hansen,P..Large Sample Properties of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Estimators[J].Econometrica,1982,(50):1029-1054.
[26]Arellano and Bond.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J].R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58):277-297.
[27]Blundell,R.and S.Bond.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143.
[28]Bond Stephen,Anke Hoeffler & Jonathan Temple.GMM Estimation of Empirical Growth Models[D].CEPR Discussion Raper,2001.
[責任編輯:張曉娟]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Study on the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 Structure Affect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
LIU Wei1,2,WANG Jiao2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2.Research Center of the Economy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Take advantag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1982-2012 and reliable panel measurement methods, this paper study the effect of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 composition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xpenditure for general public services, expenditure for social safety net, expenditure for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water conservancy, expenditure on culture, education, science and health are the main factors effect urban-rural income gap; expenditure for general public services, expenditure for social safety net, expenditure for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water conservancy are the main reason to the expansion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while the effect of expenditure on culture, education, science and health in a narrow trend.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djust large urban-rural income gap.
Key words:composition of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urban-rural Income gap;provincial panel data;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中圖分類號]F01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863(2015)06-0056-09
[作者簡介]劉偉(1973-),男,廣西北流人,重慶工商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慶工商大學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兼職研究人員,博士,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后,從事公共支出與收入分配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2&ZD100);國家社會科學基金(09CJY029);第54批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2013M540696);2013年重慶市博士后科研項目特別資助(Xm201360);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11YJA790091)
[收稿日期]2015-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