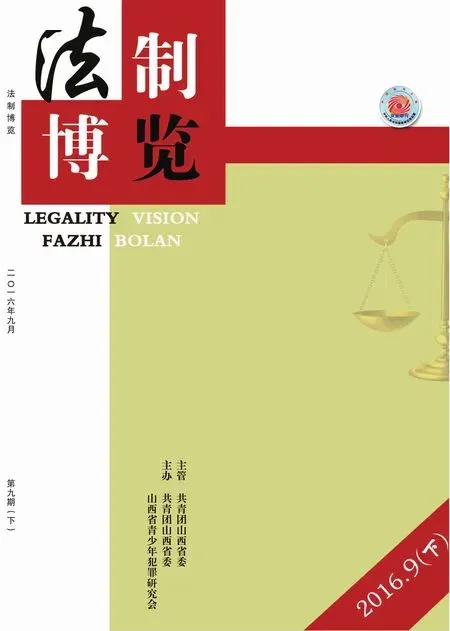論尋釁滋事罪疑點(diǎn)問題的認(rèn)定
劉春德
天津市北辰區(qū)人民檢察院,天津 300499
?
論尋釁滋事罪疑點(diǎn)問題的認(rèn)定
劉春德
天津市北辰區(qū)人民檢察院,天津300499
認(rèn)定尋釁滋事罪的主觀要素不應(yīng)以是否有流氓動機(jī)為條件,并且將流氓動機(jī)當(dāng)作該罪的要件可能無法起到區(qū)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效果。尋釁滋事罪的客體為雙重客體,即個體法益和公共秩序。判斷某一具體行為是否為“尋釁滋事”可以采取雙替換的方法,首先替換行為人,其次對被害人進(jìn)行替換。某一毆打他人的行為只要同時滿足雙替換的要求,就可以認(rèn)定該行為具有主觀“隨意性”,屬于“尋釁滋事”行為。
流氓動機(jī);法益;隨意性;雙替換
關(guān)于尋釁滋事罪的構(gòu)成要件和具體類型,兩高公布的專門司法解釋有明確規(guī)定,但實(shí)踐中對其具體適用上仍遇到許多困惑和爭議,值得進(jìn)一步研討。
一、尋釁滋事罪的主觀特征——是否必須具有“流氓動機(jī)”
尋釁滋事這一詞如何理解,依照2013年兩高《關(guān)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解釋》)規(guī)定,行為人為尋求刺激、發(fā)泄情緒、逞強(qiáng)耍橫等,無事生非,實(shí)施隨意毆打他人、追逐、攔截、辱罵、恐嚇?biāo)说刃谭ǖ?93條規(guī)定的行為的,認(rèn)定為“尋釁滋事”。從《解釋》規(guī)定來看,該罪要求行為人具有明顯的流氓動機(jī),而眾所周知,現(xiàn)行刑法已刪去流氓罪的條款,作為從流氓罪中分離出來的尋釁滋事罪是否也理所當(dāng)然地要求行為人必須具有流氓動機(jī)呢?持肯定觀點(diǎn)的學(xué)者認(rèn)為,尋釁滋事罪是從1979年《刑法》規(guī)定的流氓罪中分離出來的,因此原流氓罪的本質(zhì)特征和特點(diǎn)在尋釁滋事都有所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尋釁滋事行為是典型的流氓行為之一。①持否定觀點(diǎn)的學(xué)者認(rèn)為,尋釁滋事罪作為危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的一種,主要是因?yàn)榇祟愋袨榧葥p害了個體的權(quán)益,又?jǐn)_亂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安定,……在行為多樣化的當(dāng)下,認(rèn)定尋釁滋事罪的主觀要素不應(yīng)以是否有流氓動機(jī)為條件。②所謂“流氓動機(jī)”或者“尋求精神刺激”是沒有具體意義,難以被人認(rèn)識的心理狀態(tài),具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內(nèi)容,將其作為尋釁滋事罪的主觀要素,并不具有限定犯罪范圍的意義。③筆者對這一問題持否定意見,首先流氓動機(jī)這一詞匯已被淘汰,其具體涵義模糊不清,現(xiàn)行刑事法律也未有對該詞語涵義的解釋,若在司法實(shí)踐中繼續(xù)適用,有可能導(dǎo)致司法辦案人員無所適從,裁判結(jié)果五花八門。其次,將流氓動機(jī)當(dāng)做該罪的要件可能無法起到區(qū)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效果,因?yàn)橹灰菍?shí)施隨意毆打他人、強(qiáng)拿硬要公私財(cái)物等行為的,皆能夠評價為出于流氓動機(jī),并且在公共場所,至于行為人是基于流氓動機(jī)毆打他人,抑或是基于報復(fù)動機(jī)實(shí)施毆打,對法益的侵犯,即對于他人身體安全和公共場所秩序的侵犯基本沒有區(qū)別。這里借鑒張明楷教授的觀點(diǎn),要求尋釁滋事行為人必須具有流氓動機(jī),表明過于重視主觀因素,而認(rèn)定犯罪行為,應(yīng)當(dāng)以客觀方面要素為根本,應(yīng)當(dāng)將客觀要素作為較重要因素,特別在區(qū)分此罪與彼罪情形下,應(yīng)先著眼于客觀要素。回歸到尋釁滋事犯罪,行為人的行為是否侵犯了刑法保護(hù)的法益,不能只因出于流氓動機(jī)隨意毆打他人或者強(qiáng)拿硬要的,才認(rèn)定為尋釁滋事,出于其他動機(jī)實(shí)施該行為的就不認(rèn)定為尋釁滋事,而應(yīng)首先從客觀行為著手分析予以認(rèn)定。
二、尋釁滋事罪客體特征——所保護(hù)的法益
尋釁滋事行為包括四種類型,其保護(hù)的法益也相應(yīng)分為不同類型。“隨意毆打他人”型保護(hù)法益是社會一般交往中的個人的身體安全,或者說與公共秩序相關(guān)聯(lián)的個人的身體安全;“追逐、攔截、辱罵他人”類型保護(hù)法益為一般人在公共生活、公共活動的行動自由與名譽(yù);“強(qiáng)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cái)物”型保護(hù)的法益為個人財(cái)產(chǎn)和與財(cái)產(chǎn)有關(guān)的社會生活的安寧;“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型保護(hù)法益是不特定人或多數(shù)人在公共場所活動的自由與安全。④不難看出,雖然該觀點(diǎn)將尋釁滋事保護(hù)的法益分為不同類型,但每種類型保護(hù)法益均包括兩部分,即個人與公共秩序,并且個人部分須是與公共秩序相關(guān)聯(lián)的,也就是說所保護(hù)的重要法益為公共秩序部分。尋釁滋事罪這一法條在我國《刑法》中規(guī)定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一章的擾亂公共秩序一節(jié),這也意味著,公共秩序?yàn)樵撟锏闹饕腕w。同時,由于尋釁滋事行為法律規(guī)定有四種類型,該四種類型表面上看首先侵犯了具體個體的利益,因此個體利益也理應(yīng)得到刑法的保護(hù)。概而言之,筆者認(rèn)為,尋釁滋事罪的客體為雙重客體,即個體法益和公共秩序。這一點(diǎn)也可以從尋釁滋事罪的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中得到印證,如兩高《關(guān)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guī)定,行為人因婚戀、家庭、鄰里、債務(wù)等糾紛,實(shí)施毆打、辱罵、恐嚇?biāo)嘶蛘邠p毀、占用他人財(cái)物等行為的,一般不認(rèn)定為“尋釁滋事”。因?yàn)檫@些行為侵害的法益單是個體利益,并未對公共秩序法益造成侵害。“尋釁滋事罪必須同時侵犯社會法益和個體法益,而且這兩個法益必須相對獨(dú)立,即在行為侵犯個體法益的同時必須額外造成對社會管理秩序的破壞。”⑤
三、“隨意毆打他人”類型中“隨意”的判斷
由于“隨意毆打他人”這一類型的尋釁滋事行為在實(shí)際案例中較為多發(fā)和常見,而目前不論是理論界還是實(shí)務(wù)界對“隨意”的理解存在爭議,因此有必要進(jìn)一步分析探討。在司法實(shí)踐中,對如何認(rèn)定“隨意”上通常以“無事生非”和“事出有因”進(jìn)行判斷,認(rèn)為如果行為“事出有因”就不應(yīng)該認(rèn)定為尋釁滋事。筆者認(rèn)為,這一說法有些偏頗和武斷。實(shí)際上,行為人實(shí)施毆打他人時,大多并非毫無行為人自己認(rèn)為的“理由”,而是有其所自認(rèn)為的理由。“任何故意犯罪行為都有其產(chǎn)生的主觀原因或動機(jī)”。⑥如果簡單的以行為人是否事出有因?yàn)闃?biāo)準(zhǔn)進(jìn)行判斷,有可能致使大多數(shù)造成被害人輕微傷的案件無法追究刑責(zé),從而使得該種類型的尋釁滋事犯罪束之高閣。行為人“無事生非”毆打他人認(rèn)定為“隨意”較好理解和認(rèn)定,沒有分歧。關(guān)鍵是“事出有因”的行為,這里可以從“因”的內(nèi)容是否合理以及因果關(guān)系兩方面分析,如果行為人毆打他人的原因內(nèi)容荒唐,邏輯混亂,并不為一般社會公眾所承認(rèn),即所謂的“強(qiáng)盜邏輯”,且該原因與毆打行為的實(shí)施一般意義上并不具有引起與被引起的必然因果關(guān)系,那么行為人所謂的“因”與“無事生非”無異,應(yīng)認(rèn)定為“尋釁滋事”。“隨意性的認(rèn)定,要從一個正常人的角度分析其是否也會實(shí)施該行為,如果一般人不會實(shí)施該行為,那么其行為具有隨意性。”⑦判斷某一具體行為是否為“尋釁滋事”可以采取雙替換的方法,首先替換行為人,即把行為人替換成一般的社會人員,如果其在相同環(huán)境下依舊會或者可能會作出同樣或者類似的行為,那就說明行為人的行為不具有“隨意性”,不屬于“尋釁滋事”。其次對被害人進(jìn)行替換,由于尋釁滋事行為要求行為對象是隨機(jī)的、偶然的,所以該對象即被害人具有可替換性。假如將原有被害人替換為其他人,實(shí)施毆打的行為人仍不會停手、停止毆打行為,那足以說明行為人主觀方面具有毆打他人的“隨意性”,屬于“尋釁滋事”行為。某一毆打他人的行為只要同時滿足前述雙替換的要求,就可以認(rèn)定該行為具有主觀隨意性,屬于“尋釁滋事”行為。
[注釋]
①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shí)務(wù)研究(中)[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
②徐衛(wèi)東.認(rèn)定尋釁滋事罪需注意三個要點(diǎn)[J].當(dāng)代法學(xué),2010(6).
③張明楷.尋釁滋事罪探究(下篇)[J].政治與法律,2008(1).
④張明楷.尋釁滋事罪探究(上篇)[J].政治與法律,2008(1).
⑤徐衛(wèi)東.認(rèn)定尋釁滋事罪需注意三個要點(diǎn)[J].當(dāng)代法學(xué),2010(6).
⑥張明楷.尋釁滋事罪探究(上篇)[J].政治與法律,2008(1).
⑦買忠香.尋釁滋事罪“隨意毆打他人”之辨析[J].中國刑事法,2010.10.
D924.32
A
2095-4379-(2016)27-0125-02
劉春德,天津市北辰區(qū)人民檢察院,助理檢察員,研究方向:檢察理論及實(shí)務(w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