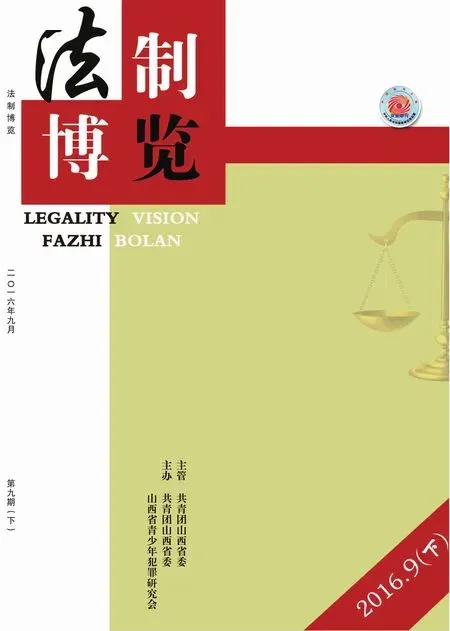法律解釋作為法律發(fā)展的中心
郁 洵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上海 200042
?
法律解釋作為法律發(fā)展的中心
郁洵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上海200042
法律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性是西方法律傳統(tǒng)的重要特征。雖然我國與西方的法律發(fā)展不盡相同,但由于受我國到了法律發(fā)展危機的侵襲。法律解釋憑借特有的優(yōu)勢,成為了化解危機的最優(yōu)方案。因此,法律解釋應作為法律發(fā)展的中心。
法律發(fā)展;法律危機;法律解釋
一、法律發(fā)展的危機
“我感到我們正處在法律價值和法律思想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在這種危機中,我們整個的法律傳統(tǒng)都受到挑戰(zhàn)。”[1]伯爾曼這一滿懷憂患的論斷警醒著世人:西方法律價值和法律思想所鍛造出的千年傳統(tǒng)已經(jīng)被人淡忘,曾經(jīng)的法律制度、法律價值和法律概念面臨著巨大的威脅。我們發(fā)現(xiàn),政治勢力可能在法官選任過程中系統(tǒng)地進行意識形態(tài)測試以篩選候選人。[2]
(一)西方法律發(fā)展危機的表現(xiàn)
外部因素與內(nèi)在邏輯的共存與競爭意味著,如果政治等外部因素強勢地驅(qū)使法律前進,那么法律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性將會受到排擠而趨向邊緣化,人們便會將對法律本身的注意力轉(zhuǎn)移到外部因素上,放棄對于法律的尊重。伯爾曼的憂慮正在于此。
(二)西方法律發(fā)展危機的后果
也許有人會用這樣的社會法學觀點,為外部因素的干擾而辯護:法律是滿足社會需要的重要手段,人類社會在近百年來急劇變化,法律亦隨之發(fā)生變化,此乃理所當然之事。但是,這一看法未能準確地說明法律的功能,因而也無法意識到法律發(fā)展危機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因為,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在變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種可以大致確定的預期,以便利人們的相互交往和行為。[3]
(三)中國的法律發(fā)展危機
西方學者對于西方法律發(fā)展的憂慮,引發(fā)了我們對于中國法律發(fā)展的思考。中國究竟有沒有遇到與西方相類似的危機呢?通說認為,基于中西方的這些區(qū)別,斷言西方法律發(fā)展所面臨的危機會在中國產(chǎn)生,恐怕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法律發(fā)展就不會面臨危機:首先,在法律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對其超長時間的了解導致人們對歷史上法律表現(xiàn)出的局限性極其熟悉,還導致一種安全感,這促成人們患上對其益處的健忘癥。其次,法律體系是靜態(tài)的,盡管它能對外部因素造成的些許限制,還遠遠不能凸顯出動態(tài)的法律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性。最后,西方法律文化的沖擊對中國法律發(fā)展的影響。結(jié)合以上三點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法律發(fā)展所面臨的危機甚至比西方更為深重。
二、化解危機的三種方案
“一個社會每當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危機之中,就會本能地轉(zhuǎn)眼回顧它的起源并從那里尋找癥結(jié)”,[4]西方還可以從自身的歷史中尋找化解危機的方法,而中國將如何應對呢?可結(ji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而提出三種化解危機的方案。
(一)限制政治權(quán)力
政治權(quán)力是妨礙法律發(fā)展內(nèi)在邏輯性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能否采取措施限制政治權(quán)力以保護法律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性呢?政治權(quán)力以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還是側(cè)重于在靜態(tài)的法律體系下限制自己的權(quán)力,而并非意味著在動態(tài)的法律發(fā)展中就一定會尊重法律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性。因此,以限制政治權(quán)力為中心,樹立法律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性,不符合政治權(quán)力的特性,不適合作為化解危機的方案。
(二)擴大司法權(quán)力
在維護法律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性時,司法權(quán)力有顯著的優(yōu)勢。然而,應當注意到:第一,司法本身即具有被動消極的特征,不利于其如同政治權(quán)力一般,主動出擊,大包大攬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第二,司法權(quán)力的管轄事項是有限的。一旦當事人將其爭議提交法院,他們極有可能參加到了一種零和游戲中,必須要分出輸贏勝負。[5]另外,盲目擴大司法權(quán)力,使其參與到自己無力解決的社會事務,甚至會導致司法權(quán)力與政治權(quán)力相混同,非但起不到確保法律發(fā)展內(nèi)在邏輯性的作用,反而為政治權(quán)力干預司法權(quán)力打開了缺口。
(三)依靠法律解釋學
法律解釋肇始于古羅馬。《十二銅表法》見證了法律解釋與法律發(fā)展的緊密聯(lián)系。古羅馬法學家在解釋《十二銅表法》的過程中,引申出大量的多種多樣的連編纂者都夢想不到的法律準則。就這樣,直到一千年后《國法大全》頒布,《十二銅表法》也未曾更改過一詞,但人們總能從中讀出新鮮的精神。[6]解釋發(fā)展了《十二銅表法》,使其與社會的發(fā)展保持同步。而在當代,法律發(fā)展所遇到的危機,也可以利用法律解釋加以解決。中國的法律發(fā)展應當以法律解釋為中心。
三、法律解釋的三重優(yōu)勢
可以預見,法律解釋將憑借著這三大優(yōu)勢推動中國法律發(fā)展,而法律發(fā)展也只有以法律解釋為中心才能使外部因素、內(nèi)在邏輯形成合力,平穩(wěn)地渡過危機。
(一)解釋原則的優(yōu)勢
一般認為,解釋原則有合法性與合理性兩種。兩種解釋原則的適用孰先孰后,涉及了政治權(quán)力與司法權(quán)力的范圍。正確理解解釋原則,能夠修正限制政治權(quán)力、擴大司法權(quán)力的危機化解方案。
解釋的合法性原則是指立法居于司法之上,因此法官的法律解釋必須受到法律文本的約束和限制。但是它具有很大的缺陷:第一,崇尚立法至上。第二,不能認識到良法惡法的區(qū)別。第三,脫離現(xiàn)實情況。
解釋是否超出法律的限制,這一問題往往只有憑借合理性的判斷才能回答。法律不可能成為絕對的指南,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應在何時選擇這條或那條既有規(guī)則解釋或指引判決。而法律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性之所以重要,也是因為穩(wěn)定人們的預期,使大家接受一種相對合理的變化。因此,解釋的合理性原則應當位于合法性之先,只有依靠合理的解釋才能發(fā)展法律。
(二)解釋主體的優(yōu)勢
雖然法律解釋主體非常廣泛,可以包括法官、學者、其他法律職業(yè)者乃至于普通人。但是法官在法律解釋上占據(jù)主導優(yōu)勢,這使得法律解釋不會成為學者的專利。具體來說,法官之所以在法律解釋上占據(jù)主導優(yōu)勢,是因為:第一,從思維上看,在進行法律解釋時,法官面對的是現(xiàn)實案件,而非像學者一樣進行沉溺于大量的虛擬案件之中。第二,由于法律解釋活動蘊含主觀色彩,因而不同學者可能會在同一解釋問題上給出南轅北轍的答案,這會動搖人們對于法律解釋的信心。第三,只有法官的解釋才能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因此,法律解釋的適用主體應當是法官。通過法官的法律解釋才能真正聯(lián)結(jié)立法、司法和法學三個維度,促使法律有機發(fā)展。
(三)解釋方法的優(yōu)勢
可以說,法律解釋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但是它借助了一套獨特的方法將自己的價值判斷包裹起來,這就使得法律解釋避免了外部因素對法律發(fā)展的直接干預。它仍然重視既有法律,同時注重法律對外部因素的適應,真正維護了法律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性。
四、結(jié)語
法官的法律解釋具有獨特的優(yōu)點,能夠調(diào)和法律發(fā)展中內(nèi)在邏輯性與外部因素的矛盾,穩(wěn)定人們的預期,化解中國法律發(fā)展所面臨的危機。中國法律發(fā)展,應當抓住法律解釋這個中心。因此,法律的發(fā)展需要依靠漫長的司法實踐、依靠一代又一代法官在具體案件中的法律解釋。
[1][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tǒng)的形成[M].賀衛(wèi)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38,39.
[2][美]塔瑪納哈.論法治——歷史、政治和理論[M].李桂林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138.
[3][4]朱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7.
[5]王利明.從足球裁判看司法公正[N].人民法院報,2012-09-04.
[6][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23.
D920.0
A
2095-4379-(2016)27-0194-02
郁洵(1989-),男,江蘇淮安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2012級法學理論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