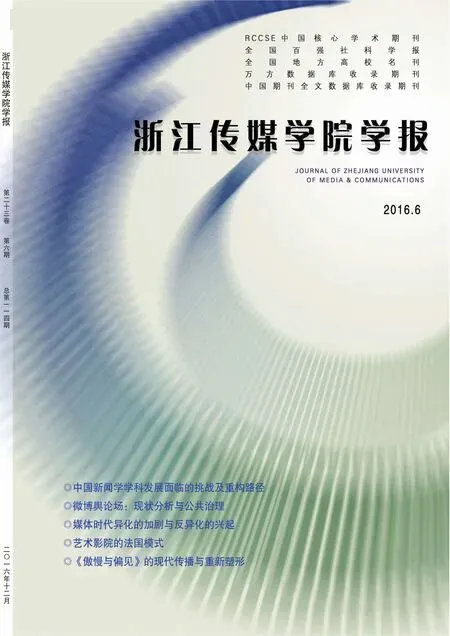媒體時代異化的加劇與反異化的興起
應力浩
?
媒體時代異化的加劇與反異化的興起
應力浩
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系統地闡述了在工業社會中出現的勞動者與勞動產品和勞動本身的分離現象對勞動者造成的影響。法蘭克福學派的幾位學者將異化理論與大眾媒體進行了聯系,并指出在大眾媒體時代產生的“文化工業”對人類所造成的思想上的異化。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社會中又產生了不同于傳統勞工的“電子勞工”。而“電子勞工”的出現又與“電子異化”的形成產生了關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被迫受困于三重異化的裹挾。但是,凱爾納從黑格爾思想中所提煉出的反異化理論又給異化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新媒體中所包含的互動元素及其隨之而來的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似乎也從某種程度上證實了具有反異化特征的行為在當今社會已經開始規模化出現。
異化;反異化;馬克思;文化工業;新媒體;批判理論
自從馬克思提出他的異化理論以來,關于人類異化問題的討論一直是哲學界研究的焦點。而異化理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內容延展性也使其成為了理解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力量。以法蘭克福學派為首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也將異化理論與資本主義環境下大眾媒體的發展和演變過程聯系起來,并用極具說服力的論述證明了兩者之間所存在的關系。而隨著新媒體時代的來臨,媒體在規模和數量上的指數性增長也讓不少學者擔心,媒體對人類的控制將會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人類異化的形式和維度也會相應地發生巨變。受到多重異化包圍的人類似乎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自己的身體和意識,這也似乎與黑格爾思想中主體精神和客體最終趨向同一的理想狀態越走越遠。與此同時,新媒體中包含的互動性元素卻又在某種程度上給受眾的自我覺醒(反異化)提供了可能。本文所要討論的核心內容即是異化同反異化這一組看似矛盾的關聯體之間所存在的某種辯證關系。
一、異化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我們一般認為,是黑格爾、費爾巴哈以及馬克思創造并發揚了異化理論。事實上,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里,就對異化的概念提出過思考,他指出,現代社會中所存在的各種約束和制度,使人類逐漸喪失其本性,變得越來越不自由。[1]幾年后,在《社會契約論》里,他擲地有聲地說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反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隸。”[2]盧梭已經發現了社會中所出現的某些與異化相似的特征,然而他本人思想的矛盾性和復雜性使得他不能將異化以完整的理論形式推出。不過他卻敏銳地捕捉到了現代契約社會對人類自由的侵蝕。隨著生存技能的提升以及生存壓力的減小,人類從安全性和穩定性角度出發,自愿決定脫離自然狀態并讓渡出部分“天賦”權利予社會,使自己得以在一個相對安穩的環境中生存。然而處在這個文明和進步社會中的他們卻失去了更多的自由,他們變得不能完全控制自己。
首位將異化以明確理論提出的哲學家是黑格爾,他把在原始狀態下統一的主體意識(精神)與客體(自然界)的分離過程稱為異化。[3]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對“異化”本身持有相對中立的態度,他相信異化只是一個過渡階段,盡管主客體之間正在經歷或已經產生分離,但隨著主體自我意識的加強(盡管他認為這一過程極其漫長且艱難),兩者之間的對立狀態將逐漸消除,并最終重新趨向同一。也就是說,黑格爾的異化理論包含了三個階段,即主客體之間的“同一”、“異化”與“反異化”過程。費爾巴哈則批判了黑格爾具有唯靈論傾向的異化理論,他認為異化的主體應該是以實體存在的人,而黑格爾理論中所謂的絕對精神只是人異化后的產物。[4]
盡管馬克思本人并不贊同費爾巴哈宗教式的異化理論,他卻認可了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異化理論的批判以及他將人作為異化主體的研究方向。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馬克思系統地描繪了在私有制條件下所發生的“異化”對作為勞動者的人類所帶來的變化:(1)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2)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活動相異化;(3)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即人同自由自覺的活動及其創造的對象世界相異化;(4)人同人相異化。[5]簡言之,勞動者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將不可避免地失去對其生活和命運的控制權。通過異化理論,馬克思對私有制條件下的追求資本積累的社會(馬克思在此時尚未開始使用資本主義這一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身處于其中的勞動者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控制。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工業化和私有制的發展對作為人類本質的勞動產生了巨大的抑制作用,人類的本性遭到了破壞。一方面,馬克思的異化理論進一步發展了黑格爾的異化理論中的“異化”過程;但另一方面馬克思和黑格爾對于“反異化”過程的理解卻大相徑庭。馬克思并沒有徹底否認反異化的可能性,但對他而言,反異化只可能出現在顛覆性革命后或社會制度發生徹底變革后。也就是說,馬克思拒絕了黑格爾的在社會常態狀況中由主體主觀出發的反異化行為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發表他的異化理論后,并未在日后對其加以過多的補充和修正。事實上,作為馬克思的早期重要理論之一的異化理論,在其中后期的作品中甚至鮮有被提及(因與主題關系不大,本文將不討論為何馬克思選擇揚棄這一重要理論)。相比于黑格爾的異化理論,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在思考深度和理論完整性上都略勝一籌,但是與黑格爾的異化理論相類似的是,從本質上說,他的異化理論依然具有相當程度的形而上特征。
二、大眾媒體與異化
馬克思的后輩,匈牙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在20世紀初期重拾起了異化理論并將其與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對接,并提出了物化(reification)理論。他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中日益泛濫的商品形式進行分析,討論了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商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辯證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作為行為主體進行勞動活動所產出的“勞動產品成了商品”[6]。人的勞動所得脫離了人的控制范圍,最終與其對立。而作為勞動成果產出的商品,類比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關系,則成了人的物化形式。也就是說,勞動產品成為了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呈現方式,勞動者則因此變得等同于勞動產品。根據盧卡奇的觀點,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本應享有他們勞動后產出的勞動產品,即商品的支配權。而現實狀況下這種支配權的缺失恰恰證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與勞動本身所發生的異化。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討論的是人類勞動在工業化私有制條件下所發生的與其本身的分離現象,即因勞動客體化而產生的與主體的分離,而物化理論討論的則是人類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發生的商品化現象,即因勞動商品化而產生的與主體的分離。因此,從根本上說,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并沒有跳出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的基本框架。物化并非是異化的變體形式或深化,它只是異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具體實現方式。也就是說,物化從屬于異化,而異化包含了物化。
不得不提的是,正是由于盧卡奇的積極嘗試,一系列具有深刻見解的相關研究在20世紀中涌現出來。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學者的批判理論核心思想正是綜合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及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對處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大眾媒體進行了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創造了“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這一概念以抨擊日益墮落的大眾文化。[7]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的大眾媒體更像是一系列的生產車間,在這些車間里生產的不是實體產品,而是大量具有標準化、普遍化和商品化特征的媒體和文化產品,諸如電影、廣播節目和娛樂雜志等。而這些不管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具有明顯趨同性特征的文化產品,卻極大地影響了受眾對文化的理解。每個人所獨有的個性和特點在大眾媒體時代成了幻象,“因為每個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7]。可以說,資本主義嘗試用大眾媒體所制造和生產的“文化工業”對人類的思想進行控制,且已經取得了一定效果。人類的思想變得工業化、產品化以及資本主義化。而當一個人變得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他一定是被異化了的個體。本雅明則比較了機械復制時代大量涌現的與原作相似度極高的復制品同原作之間的關系,認為再高明的機械復制品也無法代替更不可能超越原作的價值和功能。原作永遠是獨立于復制品的,因為在機械復制過程中,藝術家在原作創作過程中以及觀者在欣賞過程中所產生的“靈韻(aura)”消失了。[8]而這種“靈韻”正是源自于藝術家的靈光一現以及觀者因距離而產生的對作品的敬畏感。隨著技術的發展,復制品可以在外觀和形式上無限接近原作,但由于“靈韻”的缺失,復制品永遠只能是缺乏精神價值的復制品。簡言之,相比于原作,復制品只是行尸走肉。更重要的是,復制品的泛濫不僅使原作在實用價值上受到了折損,更使得觀者失去了基本的欣賞和審美能力。馬爾庫塞強調了大眾媒體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他悲觀地指出:大眾媒體以及隨之而來的廣告創造了大量對人類而言毫無意義的需求。這些無意義需求的生成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思考和行為方式。人類逐漸失去了基本的理解能力和批判能力,最終人類被改造成了“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9]而所謂的單向度的人,通常具有思想單一化、知識匱乏化、政治冷漠化等特征,而這些特征正是大眾媒體對人的異化產生的結果。
結合幾位法蘭克福學派學者的觀點,大眾媒體的興盛造成的惡果是:個體獨特性的磨滅,大眾審美觀的扭曲以及求知欲和思考能力的缺失。相比于馬克思時代的異化,大眾媒體帶來的是人類在思想上的進一步異化。
三、新媒體與電子異化
卡斯特選擇使用“信息資本主義(informational capitalism)”一詞來指代在信息時代出現的范圍更廣、更為高效且具有全球化特征的資本主義體系。[10]這個體系通過不斷創新信息技術而變得日益強盛,而日益強盛的資本主義體系反過來又進一步促成了信息技術的革新。富克斯由此提出了“電子勞工(digital labour)”的概念,他指出,在信息資本主義社會中,被定義為“在互聯網通訊技術支持下對資本積累有必要作用的個體”的電子勞工已經出現了。[11]換言之,處于新媒體時代的人類,在原有的傳統勞工基礎上,又增加了一種新的屬性。表面上,由于工業化所帶來的生產效率提升,我們投入到傳統勞動的時間相比過去減少了,但事實上,我們投入勞動的時間總和可能是增加了,因為網絡社會的虛擬空間也成了我們的工作場所。在正常工作時間,我們在工作地點進行勞動;到了閑暇時,我們則在網絡上進行勞動。安德烈杰維奇在分析我們的網絡行為時指出:“我們編寫的每一條信息,我們上傳的每一個視頻,我們購買或瀏覽的每一個商品,我們的時間—空間路徑以及我們的社會互動模式都成了可以用來分辨、預測和管理我們行為的數據。”[12]根據這種觀點,我們在網絡上進行的每一個行為,都屬于電子勞動的范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將馬克思針對傳統勞工的異化理論與新媒體(社交媒體)時代所出現的電子勞工進行聯系。通過和馬克思的傳統異化理論對比,我們可以對電子異化做出系統性的總結:與傳統勞工類似的是,電子勞工受到了“電子異化”,因為他們無法控制交流過程,無法控制用于進行交流的工具,無法控制在傳播過程中創造的信息以及無法控制交流過程的對象。
從某種程度上說,法國的社會理論家波德里亞的“仿像(simulacrum)”理論就是本雅明的“靈韻”論在后現代主義視角下的發展和延續。波德里亞的仿像理論具有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仿造(counterfeit),主要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到工業革命前。由于缺少工業化的支持,仿造追求的是對原型最大程度的手工模仿。仿像的第二等級是生產(production),出現于工業時代或者說是本雅明所提到的機械復制時代,即具有現代性特征的時代,在這一等級里,原型通過工業化被重復生產。第三等級是仿真(simulation),出現在我們所生活的數字時代,具有后現代特征。在第三等級里,無所不在的仿真品使得整個世界變得仿真化。大眾媒體通過仿像創造出了一種超真實(hyperreality),也就是無數個不同于真實世界的完全由仿像構成的“新世界”。[13]在大眾媒體的影響下,真實與仿真變得難以辨別,甚至說,真實被大量充斥的仿真所掩蓋、所取代。被仿真世界吸引的我們與真實之間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遠,我們被仿真所異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波德里亞的仿像理論與新媒體進行聯系,我們可以發現一種存在于真實世界與新媒體所創造的半真實或虛擬世界之間的身份(identity)混亂現象。我們在虛擬世界創造的身份,與我們的意識或者說是我們的存在本身是不一致且分離的,而這種由二元身份交錯所導致的非正常狀況造成了一種新的異化形式的出現,即人的虛擬身份與他本人的異化。與主體在現實世界中的身份不同,虛擬身份更像是由主體通過仿真所創造出的在另一個(虛擬)空間里的自我呈現形式,不管其真實性如何。
四、反異化的可能性和標準
凱爾納綜合分析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并給出了極富洞見的有關反異化(de-alienation)的解讀。凱爾納的貢獻在于,他發揚了黑格爾的異化理論中不被許多人(特別是馬克思)所重視的后一階段過程,即“反異化”過程,并將其應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他認為,對于身處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個體勞動者來說,一方面,如馬克思所說,他們在勞動過程中被異化且失去了對自身的控制權;但另一方面,由于不斷的技術革新給社會及個人帶來的資本和知識的積累,資本主義的內在本質將逐漸被勞動者理解和看透,而這也將帶領他們走上反異化的道路。[14]簡單地說,對于凱爾納而言,異化和反異化其實是同時進行的,從某種程度上說,異化的開端實際上也是反異化的開端。而從異化理論的本質來看,凱爾納的解讀也是具有說服力的。對于馬克思及其之后的學者而言,不管最終結果如何,他們提出與異化有關理論的原初目的就是為了提醒勞動者(媒體概念中的受眾)密切關注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異化狀況。而一旦他們的提醒被勞動者(或受眾)接受和認可,使他們開始認真思考關于異化的問題,并付諸行動,那么這些理論就轉化成了一股可以削弱異化現象的力量。也就是說,提出異化理論的目的就是為了反異化,異化理論本身就具有反異化傾向。
而富克斯和賽維尼亞尼對新媒體語境下“電子反異化”的可能性持明確的否定態度。他們斷言:只有當處在某個社會中的個體能有意識地減少其工作時間并將這些時間應用于人類工作(human work)的時候,才出現了電子反異化過程,而這在當前的全球環境下是不可能實現的。[15]然而,他們的觀點是武斷的且他們的用詞是模糊的,他們所謂的人類工作(human work)與非人類工作(unhuman work)的界限本身就難以明確定義。如果某個行為個體主動放棄某項報酬或利潤更高的工作,轉而將精力放在一些非盈利性質的公益行為上,我們就完全有理由將這些行為與具有反異化特征的人類行為進行聯系。費舍爾則認為社交媒體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流行已經造成了反異化現象的出現。但與此同時他又謹慎地指出了一種因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使用者和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之間所存在的某種辯證互動關系而出現的矛盾困境。一方面,新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言論的自由表達,思想和意識的獨立和解放可以被認為是“電子反異化”的一股強大勢力;而另一方面,為了能維持并擴大資本主義社會,信息資本主義體系似乎是在主動向新媒體尋求幫助。新媒體中包含的這些“電子反異化”因素對于社會的邊緣群體、被統治群體,以及其他弱勢群體來說具有巨大吸引力,他們渴望被聆聽,而社交媒體為他們則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由此,費舍爾得出的最終結論是,由社交媒體產生的反異化所帶來的實際結果是更強大更有效的剝削(exploitation)。[16]
費舍爾的問題在于,他還是低估了實現“反異化”過程的標準。如果某行為僅具有言論自由、思想和意識的獨立和解放這些元素而不具有其他元素,那么該行為至多只能算得上是“類反異化的(semi de-alienational)”行為或是通往真正反異化過程的中間行為,但它們與真正的反異化行為仍有明顯的差異。顯然,我們不能把那些在工作中埋怨工作時間過長、工作強度過高、工資過低甚至威脅罷工的工人看作是“反異化”的先鋒群體。盡管他們的行為里也部分包含了某些言論的自由表達、思想和意識的解放等諸多因素,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一旦他們的某些訴求得到滿足,他們的反抗行為就會停止。
綜合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凱爾納對反異化的解析,我們可以認為,標準的反異化行為是需要滿足一定條件的:行為主體的行動必須是主動的且有清晰自我認識的,是可以通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各種規則來進行、以自我實現為目標的具有正面價值的行為,且根本目的與資本的積累不相關聯;有可能在與他人的聯系中影響他人的行動目標,進而使整個社會的結構或構成產生變化。簡單地說,反異化行為包含三個關鍵點:首先是行為個體具有主動性,其次,行為方式是正向的且以自我實現為前提,第三是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反觀費舍爾論述中所試圖包含的“反異化”群體:盡管他們的行為具有一定的主動性,但是從他們的思想、訴求以及他們想要達到的效果來看,他們的行為總的來說還是被動且盲目的,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具有報復傾向的;他們的行為也不具有自我實現的特征,而僅是對內心不滿的抒發;盡管他們的行為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造成影響,但這些影響也不至于對整個社會結構造成破壞性沖擊。因此,他們不能被認為是開始或已經發生意識覺醒的群體,而是屬于被壓抑太久的群體。
五、新媒體中的反異化行為
2013年,一位名叫Vugar Huseynzade的瑞典小伙被阿塞拜疆的職業足球俱樂部FC Baku聘用,成為球隊新一任的主教練。當時,他年僅21歲,且沒有任何與職業足球相關的背景;他唯一與足球有關的經歷是,他是電子游戲“足球經理(football manager)”的資深玩家。據報道稱,在應聘過程中他憑借著從足球經理游戲中學到的豐富的足球技戰術和球隊運營管理知識擊敗了法國傳奇球星帕潘,最終得到了這個職位。[17]在這個例子里,我們有必要對波德里亞的仿像理論進行重新的思考。事實上,Huseynzade并沒有被電子游戲中的仿真世界所蒙蔽,他在游戲中的虛擬身份也并沒有與他本人產生分離,應該說,兩者在本質上是相互融合的同一整體。盡管在空間上與他本人存在距離,他的虛擬身份更類似于他本人在另一維度的延伸。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他通過在游戲中的虛擬身份獲得的信息和知識作為支持,他根本不會有機會獲得這份工作。Huseynzade在新媒體中進行的行為(玩電子游戲)是主動的且具有明確目的性的,而借助新媒體這一平臺,他也成功地實現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可以說他是主動尋求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制度的幫助以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而不是反過來。因此,他的行為具有一定的反異化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自我實現行為只是針對其本人,并不具有明顯的社會性,也不會對現存制度造成沖擊。也就是說,對比標準的反異化行為,他的自我實現程度仍然是有限的,他的反異化行為還是狹隘的。
隨著web2.0時代的到來,詹金斯關注到了一種自下而上的源自草根的“參與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18]在“參與文化”語境下,大眾通過社交媒體產生聯系。依托社交媒體,一些具有共同愛好的個人可以在線上及線下自由地進行互動聯系。他們為喜愛的影視節目錄制粉絲視頻(fan video),為受歡迎的電子游戲制作非官方補丁(modding),根據原作撰寫粉絲版本的小說(fan fiction writing)。原來大眾媒體環境下生產者(producer)和消費者(consumer)之間的差異變得模糊,未來學家托夫勒的創用者(prosumer)概念或許在新媒體時代真的出現了。參與文化中的參與者的行為具有主動性,而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角色的不斷互換似乎也說明了現存社會正在發生的某種轉型。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行為并不具備明顯的自我實現特征。加入到參與文化中的個體,他們的粉絲行為多數還是屬于娛樂和玩票性質。而且,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角色模糊,并沒有使社會出現結構性變化;生產者和消費者仍然存在于社會結構中。由此可見,參與文化中的個體,盡管他們的行為具有較強的反異化特征,但仍不能屬于徹底的反異化行為。
在觀察了新媒體時代的新聞行業后,吉爾默提出了“我們即媒介(we the media)”的概念。[19]他注意到,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媒介融合降低了曾經高度職業化的新聞行業的準入門檻。在新媒體時代,只要有一臺智能手機,人人都有機會成為媒體人。一旦我們捕捉到某條有價值的訊息并通過手機或其他工具在互聯網上進行發布,我們就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受到大量的關注。“我們即媒介”這一概念是具有革命性的。將這一現象與前文所述的反異化行為所需條件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一些自媒體時代的草根“媒體人”,他們的行為是主動的且具有自我實現性的。他們中的很多人提供新聞素材的目的只是因為認為自己有責任去向其他人以及整個社會分享或呈現他們認為重要的新聞,而與物質因素完全無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行為挑戰和威脅到了傳統媒體的地位。傳統媒體將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并做出針對性調整以迎合時代的發展規律,類似于“文化工業”性質的文化產品在當今時代將變得很難生存。因此,“我們即媒介”行為是有理由被看成標準反異化行為的。
六、結 語
本文分別從“異化理論的起源與發展”、“大眾媒體與異化”以及“新媒體與異化”三個層次系統分析了異化理論的發展軌跡以及異化在不同媒體時代對行為主體所造成的影響。縱觀異化理論的發展史,我們所受到的異化不管是從強度還是從廣度來看,都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在當今的信息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已經被三種不同形式的異化所包圍:(1)工業社會中發生在傳統勞動身上的勞動者與勞動產品和勞動本身的分離;(2)大眾媒體時代中文化工業所產生的知識缺失性異化;(3)信息資本主義時代電子勞動所產生的電子異化。異化強度的增加也使得不少學者對人類在新媒體時代覺醒的可能性抱有非樂觀的態度。然而,結合凱爾納對反異化的闡述以及新媒體時代出現的許多與異化具有相異甚至相反特征的事例,我們可以發現,事實上反異化的強度似乎與異化的強度之間存在某種能動關系。異化的確正在影響我們,而我們也正在通過反異化行為予以回擊。又或許,這些具有反異化特征的行為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人類本身就是一種適應性極強的生物,更大強度的異化所造成的結果是更大強度的反異化。通過新媒體技術,越來越多的人有機會進行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影響,相互協作,異化的未來也因此變得越來越不明朗。在新媒體不斷發展的今天,斷言異化會壓倒反異化或反異化會戰勝異化都是不明智的。但至少,歷史的發展證明,法蘭克福學派的悲觀主義異化思想還是過于消極了。我們沒有必要過于悲觀,當然也不能盲目樂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還是要相信人類自己。
從某種程度上說,狄更斯可以算得上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預言家之一,他在《雙城記》里的開篇名言是:“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歲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20]或許是對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描述,或許對每個時代都是。
[1][法]讓-雅克·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M].李常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11-150.
[2][法]讓-雅克·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
[3][德]格奧爾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38-79.
[4][德]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M].榮震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42-66.
[5][德]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57.
[6][匈]喬治·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M].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47.
[7][德]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3.
[8][德]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0:5-14.
[9][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6.
[10][西]曼紐爾·卡斯特.網絡時代的崛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22.
[11]Christian Fuchs.ClassandExploitationontheInternet[A].T·Scholz.DigitalLabor:TheInternetasPlaygroundandFactory[C].London:Routledge.2013:Ch.13.
[12]Mark Andrejevic.EstrangedFreeLabor[A].T·Scholz.DigitalLabor:TheInternetasPlaygroundandFactory[C].London:Routledge.2013:Ch.9.
[13][法]讓·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M].車槿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61-112.
[14]Douglas Kellner.NewTechnologiesandAlienation:SomeCriticalReflections[A].L·Langman.TheEvolutionofAlienation:Trauma,Promise,andtheMillennium[C].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47-68.
[15]Christian Fuchs,Gerhard Sevignani.What is Digital Labour?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J].TripleC,2013(11):237-293.
[16]Eran Fisher.How Less Alienation Creates More Exploitation?Audience Labour on Social Network Sites[J].TripleC,2012(10):171-182.
[17]Dan Ripley.MeettheManWhoHonedHisGeniusontheFootballManagerComputerGame[EB/OL].Daily Mail,http://www.dailymail.co.uk/sport/football/article-2340324/Football-Manager-Vugar-Huseynzade-got-FC-Baku-job.html,2013-06-12.
[18]Henry Jenkins.Fans,Bloggers,andGamers:ExploringParticipatoryCultur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
[19]Dan Gillmor.WetheMedia[M].Sebastopol,CA:O’Reilly Media.2006:ⅩⅤ.
[20][英]查爾斯·狄更斯.雙城記[M].石永禮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1.
[責任編輯:趙曉蘭]
應力浩,男,碩士生。(寧波諾丁漢大學,浙江 寧波,315100)
G206.2
A
1008-6552(2016)06-00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