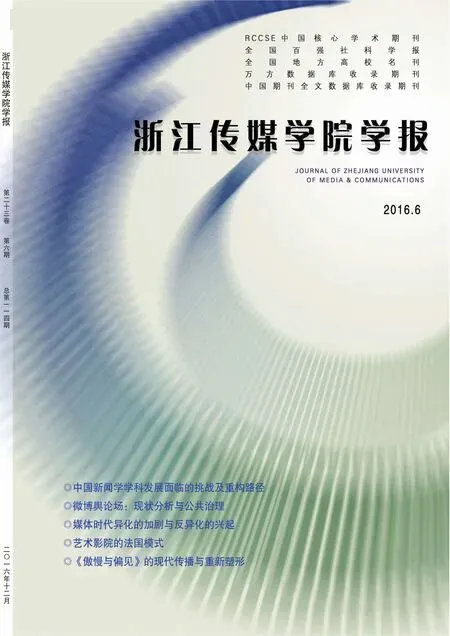文學傳媒的“媒化”運行機制研究
——以《大公報·文藝副刊》為例
林曉華 邱艷萍
?
文學傳媒的“媒化”運行機制研究
——以《大公報·文藝副刊》為例
林曉華 邱艷萍
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生產、傳播、接受過程中,以報紙文藝副刊為主體的文學傳媒起著重要作用。現代文學作品在進入報刊發表階段之后,必然要經歷“媒化”進程。文章以《大公報·文藝副刊》為研究對象,考察《大公報》的媒介定位與受眾策略對于《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潛在規制,進而分析《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輯在保持較高文學水準的同時,如何運用媒介營銷策略來調節和配置文學資源,并取得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文學傳媒;《大公報·文藝副刊》;“媒化”機制研究;社會效益;經濟效益
一、文學傳媒“媒化”運行機制研究方法的思考
中國現代文學的傳播平臺為報紙副刊、文藝期刊、文學出版三分天下。其中,報紙因為最接近大眾趣味,是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傳播渠道。曹聚仁認為:“中國的文壇和報壇是表姊妹,血緣是很密切的。”[1]報紙的文藝副刊作為文學傳媒的主體,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生產、傳播、接受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王本朝指出:“現代職業作家的創作機制,報紙雜志的傳媒機制,讀者接受的消費機制……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體制力量,同時也可看作是中國文學追求現代性的標志之一。”[2]其中關于“報紙雜志的傳媒機制、讀者接受的消費機制”的提法,正是文學傳媒與現代文學互動、共生的重要論斷。
文學作品在進入報刊發表階段之后,必然要經歷“媒化”進程。所謂文學作品的“媒化”,指進入媒介的文學作品,除了在文學水準上過關之外,還需要符合文學傳媒的定位、價值取向與選題標準等,方能得到媒介的接納,從而進入傳播與流通環節。本文以《大公報·文藝副刊》(以下簡稱“《文副》”)為研究對象,探討文學傳媒的“媒化”運行機制。將“《文副》”作為個案研究,從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上看,基于以下考慮:
首先,文學傳媒研究需要綜合運用多學科知識、立體透視的研究理念。亨利·雷馬克指出:“我們必須進行綜合,除非我們要讓文學研究永遠處于支離破碎和孤立隔絕的狀態。”[3]可能是《文副》的文學成就太過耀眼,以往《文副》的相關研究成果不少,但大都是《文副》所推出的作家研究,或是發表于《文副》的文學作品研究。這些研究突出了《文副》的文學性,但是《文副》作為文學傳媒所具有的傳媒特點,特別是文學作品進入《文副》后,“媒化”運行機制如何發揮作用,鮮有提及。“文學”與“傳媒”成了無法粘在一起的兩張“皮”。本文對于《文副》“媒化”運行機制的研究,綜合運用文學、新聞學、傳播學的學科知識,首先分析《大公報》本身的媒介定位與受眾策略對于《文副》的規制,進而考察《文副》編輯部是如何運用各種媒介營銷策略來調節和配置文學資源,以取得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其側重點在于將《文副》作為一個標本,深入研究“文學”與“傳媒”之間的互動、共生關系,從而在研究理念上樹立全局性的眼光。
其次,個案研究應是文學傳媒研究的起點。文學傳媒具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是作為傳播文學的平臺,具有文學性;二是文學傳媒作為專業媒體,具有媒體特性。由此,一方面文學傳媒不是文學作品集,但另一方面,文學傳媒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眾媒體,文學傳媒的定位、讀者策略、運行機制、傳播路徑都與一般的大眾媒體有所區別。而且,不同的文學傳媒,由于其社會環境、媒介定位、編輯方針、作者資源的不同,其文藝副刊也呈現出不同的風格。
因此,若只從表面掃描,可能會有些整體印象,但容易顯得空泛與粗疏,一如黃發有先生所言,“借助幾本圖書雜志、幾部影像作品,就可以縱橫馳騁地大談文學傳媒的歷史源流與當代走向,進行流于空泛的現象描述與草率的價值評判。”[4]所以,文學傳媒研究需要扎實的個案研究,深入到典型文學傳媒的內部,獲得真實的、一手的材料,從而了解其內部的運行機制和外部力量對于文學的滲透和影響。所以,將多學科透視與個案研究結合,有利于文學傳媒研究從點到面,從局部到整體的推進,對于正在生長中的文學傳播學與文學接受史這兩大學科會形成有力支撐。
二、《大公報》的媒介定位對《文副》的規制
作為母報,《大公報》的媒介定位與受眾策略對于《文副》有著重要的影響,并直接規范、制約著《文副》的運行。《大公報》為民國第一大報,是“文人辦報”的典范。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創辦人英斂之在創刊號上發表《〈大公報〉序》,聲明辦報宗旨為“開風氣,牗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從1902年到1926年,《大公報》三易其主,但其“引進西方先進文化,開啟民智”的精魂卻薪火相傳。
1926年9月,新記《大公報》復刊號上刊登了由張季鸞執筆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不黨、不私、不賣、不盲”。以“獨立辦報”為主要宗旨的新記《大公報》,其讀者群體包括知識分子、官吏、公務員等。這其中,重要的讀者群體之一是知識分子,當時主要是大學師生。那么,怎樣才能做到吸引眾多的大學師生來閱讀《大公報》?針對這一讀者群體,《大公報》的媒介策略是開辦了幾個重要的專業副刊,請各個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擔任副刊主編或撰稿人。

《大公報》的專家團隊及其所辦副刊
以上學者既是當時名重一時的社會名流、大學者,又是所在領域的意見領袖。意見領袖是指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同時對他人施加影響的“活躍分子”,他們在大眾傳播效果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或過濾的作用。各個領域的著名學者以副刊主編或撰稿人的角色在《大公報》上發表文學作品或最新研究論文,這對于大學師生及知識青年們來說,具有強大的號召力。
我們重點來看《大公報·文藝副刊》。“新記”《大公報》先開辦了副刊《藝林》,后來又開設了《小公園》與《文學副刊》。《文學副刊》首任主編是“學衡派”代表人物吳宓。吳宓先生是當時文化界、學術界的重量級人物,由他來主編《大公報》的《文學副刊》,其影響力和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但吳宓思想上較為保守,遠離新文學。對此,《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曾說過:“我就是嫌這個刊物編得太老氣橫秋。《大公報》不能只給提籠架鳥的老頭兒看。”[5]
在1930年初,白話文與新文學已成氣候,《大公報》必須要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大公報》負責人決定更換編輯,轉換副刊風格。1933年,《大公報》邀請沈從文、楊振聲兩人擔任《文副》主編。此時的沈從文已經是一位在文壇名氣響亮的作家。沈從文追求文學的獨立姿態,與《大公報》自身“大公無私,不偏不倚”及“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理念不謀而合。
《文副》有一個非常強大的作者團隊。既有成名作家老舍、巴金、周作人、冰心、張天翼、傅彥長、魯彥,又有當時的文壇新秀曹禺、卞之琳、何其芳等人。從《大公報》的角度來說,以大學師生為主體的知識分子,是《大公報》的重點讀者群,通過創辦《文副》這樣的文學媒體,甚至于將《文副》編輯部設立在著名大學里,可以很好地吸引大學師生購買、閱讀《大公報》。其次,一般情況下《大公報》本身的媒介定位對《文副》的辦刊理念來說是潛在的核心框架,而《大公報》對《文副》顯性的規范制約,是以更換主編的方式來體現的。
三、《文副》的媒體調節和文學資源配置
作為報刊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藝副刊具有大眾傳媒的基本屬性:政治性、文化性、商品性。文藝副刊的政治性、文化性,學界已有較多研究,此處不再贅言。文章中的商品性,指文藝副刊既是作為一種面向讀者的文化產品,也是一種需要投向市場的商品。因此,文藝副刊在運營過程中,需要運用多種媒介營銷手法,來取得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在中國現代文學生產過程中,報紙文藝副刊的“媒化”運行機制發揮著重要作用。現代文學作品在進入媒介之后,“媒化”機制隨即發生作用,對文學作品甚至于對作家本人按照媒介標準進行運作:選題、策劃、修改、包裝與宣傳。比如,副刊編輯的“把關人”作用,會對現代文學作家的創作形成引導與規范,這種引導和規范對于部分“以文為生”的作家來說更為直接,也更明顯。文學報刊將一些作家作品放置于重要的版面位置進行發表,這種“今日頭條”式的議程設置會吸引最多的關注度,當然也對其他安排在不起眼版面位置的,甚至于沒有發表于報刊的文學作品形成遮蔽效果。選擇一個作家,對其進行包裝與宣傳,會將一個無名作家變成文學明星,從而在后續作品發表時實現報刊與作家的雙贏,收獲更多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
現代文學作家、作品在“媒化”之后,事實上即是兩種標準:文學標準與媒介標準。既是文學作品,也是文化商品;既是作家,又是文化名人與媒體明星。典型如魯迅,魯迅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成功的作家,但又是一個失敗的編輯。魯迅一生主編或參編的報刊達數十種之多,但我們也看到,魯迅主編或參編的報刊沒有一個取得過真正的市場成功。人各有所長,報刊運作需要有專門、專業的技能,是一門特殊的、復雜的學問,創辦文學報刊對于現代文學傳播來說,非常重要。魯迅在編輯事業上相對不那么成功,恰恰說明了當時文學傳媒市場的競爭相當激烈。文學傳媒作為一種特殊商品,能否得到市場認可,除了文學本身的高水準之外,還得通曉媒介營銷與媒介競爭的知識,方能取得成功。
1933年,沈從文開始主編《文副》。沈從文一直提倡純粹的文學,追求文學的獨立,但是他在主編《文副》時,既是作家,又是報紙編輯。一方面要符合《文副》的文學性,另一方面,也要符合《大公報》本身的市場定位與編輯方針。在追求文學理想的同時,沈從文必然要注重讀者的口味與趣味,關注市場反應。由此,他不得不在“文”與“商”之間謀求平衡,尋找最佳結合點。
(1)首發式打名人牌。名人效應,是名人的出現所達成的引人注意、強化事物、擴大影響的效應,或人們模仿名人的心理現象的統稱。沈從文主編的《文副》第一期于1933年9月23日出刊,所推出的作家、作品均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其陣容堪稱豪華。這一期有楊振聲的小說《乞雨》、林徽因的《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新詩《倦》、沈從文的《記丁玲女士·跋》等作品。卞之琳是當時詩人代表,林徽因是青春偶像派作家,楊振聲時任國立青島大學校長,又曾主編《高小實驗國語教科書》和《中學國文教科書》,在師生中有較高知名度。至于沈從文自己,他從一個沒有文憑的文藝青年,成長為名作家、大學教授,本身就是一個勵志榜樣。所以,1933年《文副》第一期以這樣的豪華組合亮相,可謂先聲奪人,有強大的市場號召力。
(2)引發文學論爭以保持關注度。《文副》首打名人牌,效果固然極好,但讀者歷來喜新厭舊,新鮮勁一過,注意力就會分散。文學論爭本是一種業務探討,但文學論爭若是出現在大眾傳媒上,就具有了新聞性,容易引起讀者的興趣和圍觀。一個月后,沈從文在《文副》第九期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文學者的態度》,引發了“京派”與“海派”之爭。在《態度》中,沈從文認為“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績上努力,他們(文學的票友與白相人)則在作品宣傳上努力。”他反對做文學的“票友”和“白相”人,認為文學創作應當遵守自己“事業的尊嚴”,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超脫于政治、商業之外。《態度》引發了一場為時一年、牽扯人數近百的論戰。上海是當時中國文壇的中心,不僅有張恨水、周瘦鵑,更有魯迅、茅盾等大作家。蘇汶、姚雪垠、曹聚仁、胡風、徐懋庸等先后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場或態度。最值得關注的是魯迅前后寫了多篇文章參與論爭,最重要的是《“京派”與“海派”》《南人與北人》。而作為論爭的發起者,沈從文是最為活躍的,他在《文副》上先后發表了十幾篇文論,包括《論“海派”》《打頭文學》《知識階級與進步》《關于“海派”》等。
當然,若說這場文學論爭是沈從文有意挑起,以便通過商業炒作來推廣《文副》,這未必是其初衷。但是繼《文副》首發式上打名人牌之后,時隔一月,“京”“海”之爭又再次讓讀者聚焦于這份文藝副刊,從而有效地提升了讀者的關注度和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卻是客觀事實。此后,《文副》還參與過“反差不多”、關于大眾語和通俗化的討論。參與這些論爭,一方面是《文副》編者希望藉此表明自己的文學立場;另一方面,在客觀上,通過對文壇熱點事件的參與,又可以來提升《文副》的讀者關注度與市場熱度。
(3)開展讀者活動:文學評獎、編選出版作品。《文副》的媒介營銷還包括設立文學獎金、編選出版《〈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等方式。這些動作,一方面可以吸引作者與讀者參與刊物活動,另一方面盤點、展示辦刊實績,很好地擴大了《文副》在文藝界和讀者群中的影響。
經過努力,沈從文將《文副》辦成了高水平的純文學副刊,其定位和風格完全有別于通俗、甚至于部分是低級趣味的海派市民期刊。由此,爭取到了高校師生和文藝青年這個龐大且具有引領效應的讀者群體。到1935年6月“刊物固定讀者大約二十萬人”,在當時的確是一個擁有相當規模的受眾群體的副刊了。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文副》得到了市場的高度認可,并在文藝界發生了重要影響。
1941年,《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最佳新聞事業服務獎”獎章,總編輯張季鸞總結其辦報成功的八字方針為“文人論政、商業經營”。《文副》作為《大公報》的子刊物,如果說“名家辦刊、商業經營”是沈從文主編《文副》的成功秘訣,不能不說這是比較貼切的。名家辦刊是亮點,使得《文副》能夠保持較高的文學水準,而商業經營則是底色,是《文副》取得市場成功的保障。
通過對《文副》“媒化”運行機制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在文學傳媒與現代作家作品的互動、共生中,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就逐漸地萌芽、生發出來。
[1]曹聚仁.文壇五十年[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2.
[2]王本朝.中國現代文學的生產體制問題[J].文學評論,2003(3):93.
[3][美]亨利·雷馬克.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A].張隆溪.比較文學譯文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29.
[4]黃發有.文學期刊與當代文學環境[J].天津社會科學,2014(5):98.
[5]朱麗.沈從文與《大公報·文藝副刊》[J].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3):68.
[責任編輯:高辛凡]
2013年西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重大項目培育項目“民族地區信息傳播的深層模式探究與理論體系的建構”(13SZD08)的研究成果。
林曉華,男,新聞學博士,副教授。(西南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四川 成都,610041) 邱艷萍,女,文學博士,副教授。(西南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四川 成都,610041)
G219.2
A
1008-6552(2016)06-006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