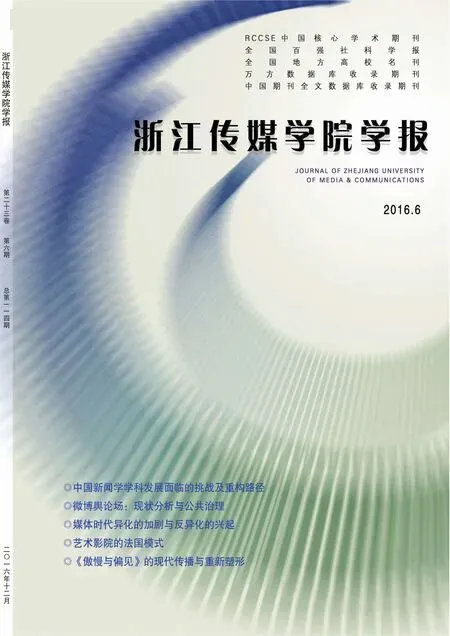媒介、空間與城市意象的地域化:當代電視劇中蘇州意象的表達
張夢晗
?
媒介、空間與城市意象的地域化:當代電視劇中蘇州意象的表達
張夢晗
當代電視劇中的城市意象常常是作為某種象征和隱喻而存在的。它的聚合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意象本身具有高度代表性;二是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得到公眾的認同。作為地域化城市意象的代表之一,當代電視劇中的蘇州意象主要表現為水鄉、古城等自然意象和蘇繡、昆曲等非自然意象。媒介所建構的這一類城市意象與區域歷史文化語境緊密相連,與人的生活狀態、行為特點等密切相關。不同地域的城市意象所呈現的世俗民風、細民瑣事、歷史掌故、人物風貌構成了獨具特色的一方文化。因而對電視劇中各類城市意象流變的關照,可以為我們看待媒介、人、社會之間的關系提供參照。
當代電視劇;地域化城市意象;蘇州;城市文化
中國當代電視劇一路發展,與城市化進程同脈相連,影像在現實社會的映照下,聚合各類意象,成為反映城市發展的沙盤圖。影視作品中的城市意象首先表現為城市的外在形象,如城市建筑、人文景觀、自然風光等,這些結構性的表征具有較高的辨識度和不可復制性,能夠喚起觀眾對某特定城市的認知。但更進一步來說,城市意象還蘊含著理性層面人們對于某一城市的內在感知,這其中必然包括城市人、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等。當代電視劇中的城市意象在更多情況下是作為某種象征或隱喻而存在的,剝離了原始符號意義的單重功能,一墻一瓦,一橋一路都承擔著敘事功能,蘊含著敘事動力。
一、城市意象聚合的條件及內涵
在界定城市意象的概念之前,本文先交代“意象”這一概念的源起。中國的意象理論早在《周易》“觀物取象”、“立象以盡意”中已有雛形,此后東漢哲學家王充、魏晉玄學家王弼對此也都多有論述。首次將“意”與“象”合為一個新詞并將這一概念從哲學領域引入審美與藝術領域的則是南北朝文藝理論家與批評家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中有“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所謂意象,即“作者的意識與外界的物象交會,經過觀察、審思與美的釀造,成為有意境的景象。”[1]亦即“客觀物象與主體意念的融合和形成的文學基本元素”。[2]譬如桃花的意象之一為“愛情”,流水中的桃花總是和傷逝的情緒相伴而生。
又如在電視劇中,當影像需要表達漂流這種狀態時,在鄉間,可以用看似無意的空鏡頭拍攝浮云游散:飄忽不定的流云,時而聚攏時而分散,搖擺不定地浮現于無邊無際的天空,隱喻著無所依附的“游子意”;在城市,還可以用游蕩的地下鐵來表現:匆忙的腳步,四面八方的流向,地鐵車窗外常年漆黑的背景,車廂內晃蕩不安的節奏,形色各異的人群,暗示著沒有歸屬的城市流浪。
在西方,全面闡釋意象這一概念的學者是康德。康德與劉勰理論的共同之處在于將具象可感性與理性抽象性的統一視作“意象”的根本特性。承認意象自身具有多義性、模糊性,其生成必須借助于想象力。由此可見,意象的抽取不能脫離對具體形態的認知。美國理論家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一書對意象的論述在西方理論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認為,在心理學中,意象一詞表示“有關過去的感受上、知覺上的經驗在心中的重現或回憶。它的功用在于它是感覺的‘遺存’和‘重現’。”[3]這種意象的定義更接近于我們通常所說的知覺表象,較易進行量化與統計研究,因此,西方一部分意象研究尤其是應用型的研究也趨于采用這種“意象”定義,以下討論的美國學者凱文·林奇的研究思路即屬此類。
凱文·林奇(Kevin Lynch)所著的《城市意象》堪稱里程碑式研究成果。城市意象是由美國凱文·林奇對波士頓澤西城和洛杉磯等城市進行了周密的研究分析后,提出的一種城市規劃設計思想。通過實驗訪查,林奇提煉出居民所關注的共同主題,此時的空間意象逐漸聚合成為人們對環境的認知圖式,它想象性地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中,并非一種實質的存在。林奇認為城市中居民對于城市的認知雖然各有不同,但“任何一個城市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意象,它是由許多個別意象疊合而成。”[4]在林奇的研究之中,個性研究和結構研究是其主攻方面,對于意蘊和結構背后意義的討論則基本采取不干涉的態度,這種關注結構本身,忽略多元艱澀意義闡釋的方法,從符號學角度來看,即為側重能指(signifier,意符)層面,避開所指(signified,意指)層面。此外,他還特別強調環境意象是觀察者與所處環境雙向作用的結果。林奇認為城市“既是成千上萬不同階層、不同性格的人們在共同感知(或是享受)的事物,而且也是眾多建造者由于各種原因不斷建設改造的產物。”[4](1)
城市原本就是一件流動的藝術品,在歷史千萬年的激蕩中生出屬于自己的肌理。就如人們想到昆曲、評彈、雙面繡,就想起溫潤清秀的蘇吳江南;想到冰糖兒葫蘆、四合院、胡同兒就想起積淀厚重的北京大都;想到日月潭、烏龍茶、鳳梨酥就想起同宗同脈的臺灣島。這些典型的城市意象正是在人類與城市發展的互動中積淀形成的,正如凱文·林奇所說:“在城市中每一個感官都會產生反應,綜合之后就成為印象。”[4](1)
由此,本文認為城市意象是在認知主體接觸城市客體事物后,對感覺傳遞的表象信息進行加工,在思維空間中抽象成對城市的印象,于頭腦中留下記憶痕跡,用以喚起相對應想象的認知材料。意象可以是單一意象,也可以是多個意象的組合體。形成意象的過程實際也是抽象的過程,但值得一提的是意象是一種承載記憶的結構體,并非瞬間的感覺。
城市意象的形成并非隨意捏合即可成形的,它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本身具有高度的代表性,這個在上文已經談過。二是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得到公眾的認同。這就要談到“公眾意象”這個概念了,公眾意象是“大多數城市居民心中擁有的共同印象,即在單個物質實體、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一種基本生理特征三者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希望可能達成一致的領域。”[4](5)只有在一定范圍內達成相對固定的公眾意見,此意象才可能得以進一步推廣至成為某城的代名詞。例如臺灣行政院新聞局發起“尋找臺灣意象系列活動”,投票選出公眾心目中最能代表臺灣的幾種意象,票選后,布袋戲、玉山、101大廈、臺灣美食成為多數公眾意見的聚合點,此類意象作為公眾意象對城市行銷和文化傳承都大有裨益。
影像表達中的區域化城市意象蘊含著人們對于某一空間的深層次內在感知,這一類特色意象的聚合及表達習慣,并非無章可循。以江南水鄉蘇州為例,要考察這一地區的城市意象,就要聯系多種歷史文化因素。因為時間為每座城市留下區別于他者的區域化意象,而影像則將其糅合化用,傳達出城市自身的品格。
二、電視劇中蘇州意象的提取和形成
(一)當代電視劇中“城里園林,城外水鄉”的意象表達
要在電視劇中體現出蘇州意象,水和園林這兩個元素是絕對不可少的,蘇州的獨特就在這里。世間常贊“江南園林甲天下,蘇州園林甲江南。”古典園林山、石、水、木、樓的錯落,疊山理水,營造了一個“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對人的精神世界產生全方位影響的意象形態系統,處處點染著藝術巧思。蘇州的濱水景觀十分動人,用“市河處處堪搖櫓”,“家家門前泊舟航”形容實不為過。水之美在于“上善若水”,水之韌在于“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談水就離不了船,越是有特色的船,越是容易形成鮮明的意象感。歐洲威尼斯的貢多拉,中國江南的烏篷船,皆成為激發思古幽情的城市“媒介”。無論是園林水鄉,還是蘇繡絲綢,蘇州的城市意象總能將城市人緊張焦慮的心態洗滌平和。長此以往,形成了一種親水舒緩的文化心態。
蘇州“城里園林,城外水鄉”的格局是獨一無二的,也是蘇州城市意象的精華所在。石階、小雨、油紙傘,旗袍、小橋、烏篷船,這些典型的具有蘇州特色的城市景觀,配上清婉的江南小調,傳遞出柔腸百轉的情緒。如《上海往事》這部電視劇尤為偏愛姑蘇城外的小橋流水。劇中,低矮的弄堂門廊,雕花的石墻門墩,屋檐上自生的植物,斑駁的灰墻,古花瓶的碎片,累累傷痕間保留著過往生命的種種細節。當劇中人物“張愛玲”與“胡蘭成”黯然分手時,“胡蘭成”呆呆地坐在石階上,手里握著一柄舊黃的油紙傘。“張愛玲”一襲藍花旗袍,倚在河濱廊柱邊。此時的旁白沒有過多陳述,一條烏篷船緩緩從二人身后的小橋穿過,兩人各在一邊,暗示曲終人散、各自天涯。同時,與之相配合的音樂起調于凄清的江南小調,隨著分別的在即,音調急轉而下,聯排使用附點音符,傳達出主人千回百轉的不定心緒。
作為“姑蘇第一名街”的山塘街有一千一百多年的歷史,其間店肆林立,會館集聚,建筑疏朗有致、典雅別致,不失為展現蘇州城市意象的好選擇。《諜戰古山塘》是一部在真實歷史背景下展開的傳奇故事,劇如其名,全劇圍繞七里山塘呈現。其中有這樣一段充滿濃郁蘇州風味的地道場景:河中,裝載著茉莉花、白蘭花及其他貨物的船只來來往往,各色游船畫舫款款而過。河岸,松挽著頭發的婦女們在河邊洗菜,最有趣的是在河中搖著小船做買賣的小販,有賣米的、賣柴的、賣海棠糕的、賣油鹽醬醋的,住在樓上的人們如果想買東西,甚至無需下樓,只要用繩子把盛東西的籃子吊下去就可以了。這就是以前蘇州人實在的市井生活,雖說現代的蘇州人很少再使用這樣的方式購買物品,但千百年來積淀下來的親水情結是難以撼動的,蘇州“水陸并行,河街相鄰”的格局在該劇中得到全景寫照。
電視劇《諜戰古山塘》中有一個長鏡頭是這樣創造性表現蘇州老院這一城市意象的:一處舊院落,一座年久的小樓,樓前一株大柳,茵著半座院子,樓的四旁爬滿了爬山虎,藤葉密罩,整個樓就像個綠草垛子。寬大的石階上生滿了青苔,一片落葉,葉柄兒纏在那密密的青苔里,不知怎么著了風,嗖嗖地發著顫音。明明是夏日里的景象,卻讓人冷不丁地打一個寒戰;那院落看著一片綠意盎然,卻漫著一陣清冷陰霧,巧妙地配合了神秘緊張的諜戰氣氛。靜謐安詳的老院落和綠油油的顏色同樣可以傳達出陰森的意象,這種聚合意象的方式屬發散輻射式。
而蘇州老院的常見意象聚合反映的則是古樸、閑淡、安寧的民間生存狀態,例如電視劇《褲襠巷風流記》主要描寫的是小巷間的人情瑣事,用身邊的故事、身邊的小人物書寫蘇州人慢悠悠、溫吞吞、閑淡淡的生活態度,從中窺探到蘇州小巷的文化情韻。
(二)當代電視劇中“蘇繡”的意象表達
作為蘇州城市意象的重要節點之一,蘇繡當仁不讓,這一精巧細致的非自然意象在電視劇中常常隱喻著整座姑蘇城的風格。例如電視劇《天堂繡》中,利用一幅幅雙面繡,對接了古今,對接了中韓。作為現代傳奇劇,該片第一集就突出表現了這種現代與傳統的雜糅。影片先是將大量鏡頭鎖定在蘇州現代化意象濃厚的工業園區,金色陽光下,金雞湖畔,韓國女孩全彩熙專心作畫,隨后呈現了令人沉醉的東方水城的特色景觀,鏡頭下的蘇州水網密布、碧波魚躍、雨量充沛,十分符合“水鄉澤國”之稱。男主角鄺良是一位有才干的年輕人,身為熱愛蘇繡藝術的企業家,他的身上也映射出蘇州古老而現代的雙面性格。同時,男主角被定位為一個內心沒有冬天的人,而蘇州也正是這樣一座沒有冬天的城市,沒有冰冷的城市性格,不緊不慢、不急不躁,有繁華更有寧靜,有時尚更有古典,用“蟄伏在鬧市皺褶子里的小街”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了。
在此部電視劇的定位上,導演黃健中目標很明確,希望能將這部作品“作為一個有著深深地方烙印的作品打出去”。他說:“除了紀錄片,中國到今天為止沒有真正的‘都市名片劇’,我希望這部劇能做到這一點。”[5]該劇主要講述一幅丟失已久的國寶級藝術珍品《天堂繡》突然重現人間,引來中、韓、新、美四國眾多神秘人士的追蹤。親人的背叛,隱秘的血緣,商戰的殘酷,權錢的誘惑,引發出撲朔迷離、懸念迭起的復雜經過。柳暗花明、出乎意料的結局雖令人喜出望外,卻讓一場風花雪月的異國戀情留下無限感慨、萬般唏噓。在劇中,導演黃健中還引用了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影響世界的紀錄片《中國》的部分畫面,通過閃回的手法,將《中國》中關于蘇州的畫面穿插在劇情中,通過過去畫面與現代畫面的對比,展現出歷史的滄桑感。
此外,珍貴道具《姑蘇盛世圖》成為該劇的一大亮點。劇中主道具“天堂繡”是借用了蘇州蘇繡工藝美術大師蔡梅英送至2010年世博會展覽的展品。蔡梅英大師的此幅繡品是帶領18位繡娘,耗時5年完成的,與清人徐揚于乾隆年間所繪《姑蘇盛世圖》為1∶1比例,僅繡線、底料就花費人民幣七百多萬元,加上手工價值千余萬。所用蠶絲線總長超過四萬余公里,足可以環繞地球一周。全圖內有各色人物四千多人,房屋建筑二千多棟,橋梁五十多座,各種客貨船只四百多艘,且每個人的服飾道具和動作沒有重復。能夠尋到這部繡品參與《天堂繡》的拍攝,著實為電視劇的觀賞性和蘇州城市的意象行銷增色許多。
電視劇中的蘇州意象整體呈現出溫軟柔美卻堅韌十足的特色,屬長于傳統卻不落窠臼的城市性格。在《笑著活下去》《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橘子紅了》《褲襠巷風流記》等劇中,悠長的小巷、蜿蜒的水街、金燦燦的甜橘、濕漉漉的石板路,展現出蘇州溫軟寧靜的日常意象;在《京華煙云》《啼笑姻緣》《桃花扇》《鐘鳴寒山寺》《陳圓圓》《董小宛》《柳如是》等劇中,精巧的雙面繡,“水磨調”的昆曲唱腔,清香細膩的碧螺春茶,演示出蘇州優雅傳統的文人意象;在《善良背后》《決不離婚》《天堂繡》等劇中,寬敞平坦的大道,鱗次櫛比的風尚建筑,風馳電掣的軌道交通,傳達出了蘇州對接時代的現代意象。
伴隨著中國電視劇的發展,電視劇中的城市意象作為城市形態和城市意蘊的有機結合,被不同的觀察者賦予迥然有別的內涵。[6]城市空間的意象層次是建立在人的空間體驗之上,并以潛意識為背景,兼受文化、生態、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因而城市意象是人對城市空間知覺想象的綜合。但與此相關,在另一方面,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意識、生活方式對人們產生的潛在影響,增加了城市意象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
三、地域化城市意象背后的文化展演
通過對電視劇中城市意象的考察,我們發現城市意象具有地域性歸屬,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電視劇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其間表達的城市意象,可以拿來與文學中的意象表達相類比。“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實際上通過地域文化這個中間環節起作用。即使是自然條件也是后來才越發與本區域的人文因素緊密連接,通過區域文化的中間環節才影響和制約文學的。”[7]電視劇中的城市意象的地域化色彩可以類比為風俗畫,是“由一系列的文化因素構織而成的,這些文化因素的歷史與現實存在便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語境。在這一文化語境中,所有的人、物、事都具有該地域文化的特征和烙印,受這一文化固有的規定性制約。”[8]
城市是有生命的,將其看作一個肌體,俯視下去,縱橫捭闔的街道就是動脈,穿流其間的水域就是流動的血液,順著或曲折或平直的線路分割開來,城市的空間就分成了一個個小豆腐塊。再往細處分,小通道就更加地密集,他們有著形態各異的紋理,于其中記錄著屬于自己的故事。因而,對于城市意象地域化色彩的考察,也離不開對文化的分析。城市的地域性特色,一方面是由于歷史痕跡的傳承,另一方面也與其自身的自然風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總的來說,城市意象的地域化特色可以與城市的個性緊密聯系在一起,有的城市以優美的自然山水見長,也有的城市憑借深厚的文化背景取勝;即使同為風景勝地,也會因地理位置、氣候品格而造就出風格迥異的旖旎風光。正是因為地域化的差異美,才使得電視劇中的城市意象更為引人入勝。
與自然風貌相比,城市意象的地域屬性更多是在歷史文化語境中緩慢形成的,只有民族的,才有可能成為永恒的。地域化的屬性加入“人”的色彩后,就更加豐富飽滿了。如同凱文·林奇在《城市形態》中所評論的:“大部分的人都有在一個獨特場所體會到獨特感受的經驗,人們會贊賞這地方,并同時對其不足之處感到惋惜。僅僅去感受一個地方就能有獨特的趣味:體會光線的變化、感受風的吹拂、享受觸摸、聲音、顏色、形狀等等。……因為一個生動和獨特的場所會對人的記憶、感覺以及價值觀直接產生影響。所以,地方的特色和人的個性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人們會把‘我在這’(I am here)變成了‘這是我’(I am)。”[9]
城市意象不是靜止、獨立的存在,而是與城市人的生活狀態、行為特點等密切相關的。不同地域的城市意象所呈現的世俗民風、細民瑣事、歷史掌故、人物風貌構成了獨具特色的一方文化。從更深層面來看,不同地區的城市意象是由歷史積淀、文化傳承、經濟形態、家族傳統等因素所構成的特定人文形態。城市意象的地域屬性與具體的事件、場景、物品、服飾和習尚密切相關。
在表現江南題材的電視劇中,可以看到溫婉典雅的庭院流水,江南總是一個“詩意的所在”;在講述沖撞糾葛、黑幫打斗的題材劇中,香港常以“罪惡之都”的身份出現,另一方面,香港又以“金融中心”的霸氣面孔,呈現給觀眾一類欲流縱橫、富賈云集的意象;而與此相對照的是臺灣電視劇中的意象組合常呈現出別樣風景,文化尋根的社會氛圍和凝視慢活的生活心態,促使臺灣電視劇常以清新唯美的畫風出現;回歸心靈、守望單純的主題意象即使在臺北這樣快節奏的城市也會以幽默輕松的方式流露出來。
四、結 語
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當代電視劇發展迅猛。作為種種文化現象中的一支,對電視劇中城市意象流變的關照,可以為我們看待城市、人、社會之間的關系提供別樣的參照坐標。城市的陸離變化賦予電視劇創作更多的想象力,電視劇虛實交錯的光影解讀、展演城市,這二者之間交叉難舍的關系共筑了生存空間中人們關注的問題:城市與人、感情渴望與物質追逐、空間與家園、時間與生命。電視劇在城市變化的滋養下,塑造、重組、分解空間,成為反映城市發展狀態的沙盤圖,帶領觀眾在鏡頭的指引下歷經一場未知之旅。這場充滿意外的旅行總能讓閱聽者發現別樣的世界,陪伴人們在特定的時空下品味解讀城市空間。在這其中,意象的營造就成為聚合城市形象的重要方式,點滴片段的透露,流于無形的展開,城市的味道就在電視劇意象之爐下飄散出來。
正如人們透過馮小剛的電影窺見北京,透過侯孝賢的電影遙望臺北,透過王家衛的電影猜想香港,透過陳英雄的電影認識河內。城市是人類敘述歷史的一部鮮活的作品,像一部編年體史書。早期城市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貿易交換的需要,許多農民需要到一個四通八達的要塞處交換自己的產品;隨著交換的頻率越來越高,交換者來不及回到農村,在聚集處繁衍延續,慢慢形成了城市。所以說,城市本身就是人類變遷的一部紀錄片。而電視劇作為一種較新的文化形態,雖然產生時間不長,卻發展迅速。它聚合各類有代表意義的城市意象元素,通過不同的意象排列組合而傳達城市的地域味道,于無形之中展演城市的個性。
[1]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M].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3.
[2]孫耀煜.中國古代文學原理[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187.
[3][美]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M].劉象愚等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298.
[4][美]凱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曉軍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7.
[5]高敏.導演黃健中和電視劇《天堂繡》[EB/OL].http://ent.sina.com.cn/v/m/2010-03-16/11412898686.shtml,2010-03-16.
[6]張夢晗.當代中國電視劇中城市意象的聚合方式及類型表達[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3(4).
[7]嚴家炎.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J].理論與創作,1995(1).
[8]于啟瑩.京味·市井·小說——京味市民小說三家[D].東北師范大學,2008.
[9][美]凱文·林奇.城市形態[M].林慶怡,陳朝暉,鄧華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93-94.
[責任編輯:華曉紅]
2015年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一般項目“信息社會經驗下媒介時間使用與發展研究”(15JDCB05YB)的研究成果。
張夢晗,女,講師,博士。(蘇州大學 鳳凰傳媒學院,江蘇 蘇州,215123)
J905.2
A
1008-6552(2016)06-008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