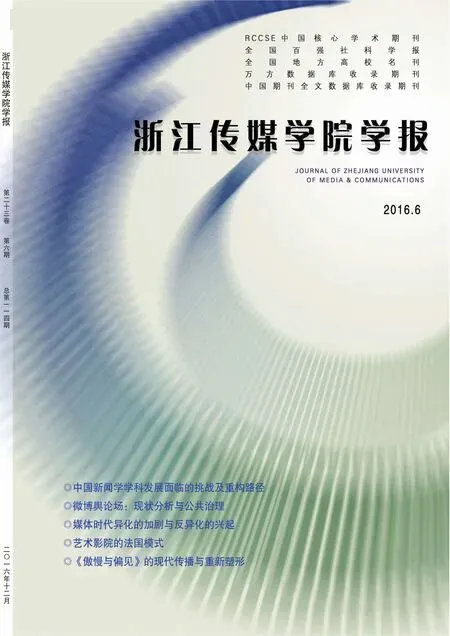雨果美丑詩學觀的經典化
林曉筱
?
雨果美丑詩學觀的經典化
林曉筱
美丑詩學觀是雨果《巴黎圣母院》這部經典的經典性。雨果這一美學原則有著較為悠久的傳統,經歷了“促成和諧”、“揭露諷刺”、“催生崇高”這三個歷史階段。雨果將這些積淀在哲學、美學、文學、倫理學中的觀念提升成為他自身獨特的浪漫主義詩學理念。
雨果;美丑;詩學;經典化
雨果于1830年7月27日開始動筆寫作《巴黎圣母院》這部小說,最終一蹴而就在1832年1月15日完稿,用完了先前買來的最后一滴墨水。雨果欣喜過望,曾打算將這部小說取名為《一瓶墨水的內涵》。這個題目未能最終成為小說的題目,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雨果并非真的枯坐在桌前閉門造車,而是對小說的場景做過一番細致的考察。他在動筆三年前就已經閱讀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和嚴肅的歷史著作,在此研究的基礎上已對15世紀的巴黎歷史了如指掌。[1]
對現實的考察再加上詩意的想象,使得《巴黎圣母院》的問世在評論家圣伯夫看來標志著雨果在創作上達到了成熟期。但這種成熟期并未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巴黎圣母院》“不是大多數人所熟悉的小說,而是他自己的,總是有點荒誕、執拗、高傲,可以說是陡峭的,所有的方面都很別致,而同時又有洞察力、嘲諷,有所醒悟……”[2]圣伯夫雖然沒有明確指出雨果這部作品包含上述幾種特質的原因,但時至今日我們知道,這一連串的特質可以鑲嵌在《巴黎圣母院》的核心美學特質——“美丑對照原則”當中。
雨果本人在《克倫威爾序》(以下簡稱《序》)中首次提出了“美丑對照原則”。整篇《序》正如雨果在開篇時所舉的軍隊的例子一樣,充滿了戰斗氣息。它所要駁斥的是古典主義,乃至古典主義之前,沉積在美學歷史當中的單一美學準則。雨果認為:“古代的純粹史詩性的詩歌藝術也象古代的多神教和古代哲學一樣,對自然僅僅從一個方面去加以考察,而毫不憐惜地把世界中那些可供藝術模仿但與某種典型美無關的一切東西,全都從藝術中拋棄掉。”[3]
雨果在《序》中曾說:“照我們看來,就藝術中如何運用滑稽丑怪這個問題,足足可以寫一本新穎的書出來。通過這本書,可以指出,近代人從這個豐富的典型里汲取了多么強烈的效果……”[3](35)
而今,我們可以說意大利作家艾柯所著的《丑的歷史》則剛好成了雨果所說的“新穎的書”。艾柯提醒我們,丑這個概念在人類的認識和接受的范疇中具有如下前提:第一,“丑”這個概念具有相對性。不僅個體對待“美”和“丑”的因素有所差別,而且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丑”也不可避免地隨著審美標準的變化在逐漸發生變化。第二,這種對美丑的界定盡管有其相對性,但是這種相對性并非無邊無際,難以捉摸,而是可以參考某個“特定”的模型進行定義。無論是柏拉圖所說的“理念”,還是托馬斯·阿奎那定義的“形式”與“材料”的統一,都可以視作人類在對待“丑”這個概念時留下的公分母。第三,自從羅森克蘭茨(Karl Rosenkranz)于1853年發表第一部《丑的美學》(Aesthetic of Ugliness)以來,人類在對待丑時除去政治和經濟的外在標準之外,也會摻雜諸如道德等人類生活的內在價值,繼而影響人們對“丑”的認定和態度。[4]在這三個前提之上,艾柯認為我們要在對待“丑”時注意三種區分:丑本身,主要是指令人作嘔的現象;形式上的丑,涉及的是整體和部分之間關系的失衡,以及藝術對這兩者的刻畫。[4](18-20)
一、“丑”對“美”的補充:促成和諧
古希臘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濫觴之一,我們對“丑”的審視自然要從古希臘時代開始。柏拉圖在《巴門尼德篇》中記載了蘇格拉底和巴門尼德有關“理念”的一番對話,其中包含了蘇格拉底對“丑”的認識。在這番對話中,蘇格拉底和巴門尼德對“公正”、“美”和“善”等概念具有的“理念性”基本達成了一致。但是就“頭發”、“爛泥”、“垃圾”等“一切微不足道、卑賤的事物”擁有理念,蘇格拉底認為是“荒謬的”。究其原因,蘇格拉底認為:“在這些事例當中,事物就是我們能看到的事物。”[5]由此可見,在“理念”的維度之下,卑賤的事物之所以顯得“荒謬”主要在于“可見”,也就是有形。在蘇格拉底的論述中,美和丑相比,趨向于無形,更接近理念世界,而丑則落于塵世,趨向于有形。關鍵在于,這個“有形”和前面所提及的頭發、爛泥、垃圾等相關,更趨向于“局部”。而在《大希庇亞篇》中,蘇格拉底則通過扮演一位曾問倒過他的提問者,就有關“美”和“丑”的問題向希庇亞提問。在希庇亞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連串的類比關系,“猴子”、“人”、“少女”和“陶罐”等顯然都是美的,但是這些物品顯然是在對比中顯現出美的:“最美麗的猴子與人類比起來是丑陋的……最美麗的陶罐與少女相比也是丑陋的。”這些美的事物在希庇亞看來具有兩點共通的特性:“井然有序”和“擁有外形”。[5](36-37)
我們可以發現,先前在《巴門尼德篇》中有關“丑”具有“有形”性的論述顯然和“瑣碎性”相對應,也就是說在古希臘人的眼中,“美”雖然是無形的,但是具有使得事物井然有序的特征,并在“井然有序”的觀念之下,它能夠促成事物完整的形體。而“丑”則相反,丑雖然有形,但這種形態誕生的是失序的、破碎的事物。秩序反應在古希臘人的觀念之中,就形成了對人和物的比例的追尋。“公元前4世紀,波里克利特斯(Policlitus)創作一具雕像,此作由于體現理想比例的所有規則而得《正典》之名。而維特魯威(Virtruvius)是后來才提出人體各部分的完美比例的;臉應該是身長的十分之一,頭是身長的八分之一,軀干是四分之一等等。”[4](23)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看到,美的秩序是在一系列類比的關系下產生的,也就是說美具有通約性。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曾表述說:“……這些事物里都有優美與丑惡。壞風格、壞節奏、壞音調,類似壞言詞、壞品格。反之,美好的表現與明智、美好的品格相接近。”[6](107)基于此,柏拉圖呼吁“阻止藝術家無論在繪畫和雕塑作品里,還是建筑或任何藝術作品里描繪邪惡、放蕩、卑鄙、齷齪的壞精神……”因為這樣做會使得人們“從小就接觸罪惡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臥毒草中嘴嚼反芻,近墨者黑,不知不覺間心靈上就鑄成大錯了。”[6](107)其實,拋開柏拉圖的論述不論,從希臘人所用的詞中我們依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希臘人在表達有關“完美”的理念時,用的是“kalokagathia”,這個詞可以拆解成“kalos”(美麗)和“agathos”(善等正面價值)這兩個部分,夾在一起構成了“完美”。[4](23)由此可見,“美”成了一個超越身體的價值理念,與“善”相連。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在古希臘人的眼中,“美”和“和諧”、“無形”、“善”相聯系,而“丑”則和“失序”、“有形”、“罪惡”相關。這似乎構成了截然相反的一對二元對立,不僅體現在事物的“比例”等可見的維度,也體現在“善、惡”等不可見的抽象價值判斷中。但是,論述什么是美丑是一個方面,而如何表述這種對立則是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因為我們得時刻注意,雨果的“美丑對照原則”本質上也是對美丑關系的一次書寫。這種對“美丑”關系的書寫,可以追述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亞里士多德基于摹仿論指出:“人對于摹仿的作品總是感到快感。經驗證明了這樣一點:事物本身看上去盡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圖像看上去卻能引起我們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動物形象。”[7]至于這種快感的來源,亞里士多德認為在于我們“一邊在看,一邊在認知”。[7](24)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認知”無疑在簡單地羅列“美丑對比”之外,加入了讀者的因素,也就是說讀者在看待“美丑”的時候除去衡量“美丑”的價值判斷之外,會基于作品的摹仿特性而關注到對“美丑”的表現層面。繼而亞里士多德特別指出,作品中“好壞”之分,與對“美”和“丑”的表現有關,因為“‘壞’不是指一切惡而言,而是指丑而言……”[7](28)
盡管如此,古希臘的文學創作似乎沒有拘囿于亞里士多德所框定的事物的“美丑”與表現“好壞”的聯系之中。我們依舊可以在神話傳說、荷馬的史詩,乃至悲劇詩人的創作中看見米諾陶、斯芬克斯、塞壬等人身妖獸的怪物,這些怪物不僅不符合比例,而且其不合比例的方式是某種人和獸的組合,其恐怖形象令讀者觸目驚心,而他們所做的事情,連同那些外貌并不可怕的人(諸如美狄亞、坦塔勒斯等)所做的事情一樣,無論如何也無法和“善”掛鉤。按照古希臘圣賢的標準來看,這些怪物和人無疑是丑的。但不容否認的是,他們的形象卻實實在在地存在于這些偉大的作品當中。這說明“壞”的、“丑”的事物,除去抽象價值衡量之外,在文學、藝術作品的價值當中有著獨特的表現作用。奧勒留則通過一系列事物的類比[8],意在表明人們若對此類丑的事物換一種觀察的方式,那么這些事物必然會產生不一樣的審美效果。這樣一來,以“美”來代替整體,以“美”來獨撐“完美”的理念,在一個隨處可見不完美的世界當中,被“美丑共存”符合“自然”的觀念所革新。
“美”和“丑”在“自然”中的著床,在基督教文化中孕育出了“萬有之美”的全新認識,這種認識在新柏拉圖主義者筆下得到了具體的闡釋。那位托名為戴奧尼索斯的作者認為:“但我們在把‘美的’和‘美’用于統一萬物的原因時,不要在這兩個名字間作區分……美將萬物召喚向自己(當他被稱為‘美’時),并把一切事物都聚集在自身之中。他把他稱為美的,因為他是全然美好的,是超出一切的美者……在那一切美的事物的單純但超越的本性中,美與美者作為其源泉而獨特地在先存在著。從這一美中產生了萬物的存在,各自都展示著自己的美的方式……美統一萬物而為萬物源泉……世上沒有任何東西不分有一定的至美與至善。”[9]顯然這番話中包含著一種相矛盾的成分。如果美是統一萬物的源泉,萬物之中也分有這種至美和至善,那么萬物之中的丑,萬物之中的惡又該如何解釋?換言之,美和丑固然是一對二元對立,既然這組二元對立依然存在,并歸屬于“萬有之美”,那么承載這對對立的容器又是什么?對于這一疑問,圣奧古斯丁的論述為我們提供了答案。他在《懺悔錄》中指出“對于你天主,絕對談不到惡;不僅對于你,對于你所創造的萬物也如此,因為在你所造的萬有之外,沒有一物能侵犯、破壞你所定的秩序。只是萬物各部分之間有的彼此不相協調,使人認為不好,可是這些部分與另一些部分相協,便就是好而部分本身也并無不好。況且一切不相協調的部分則與負載萬物的地相配合,而地又和上面風云來去的青天相配合。”[10]除此之外,這位圣徒在《論秩序》《上帝之城》等著作中多次提及各種事例,用以強調“秩序”和“和諧”。這樣一來,“美”和“丑”不僅統一在了和諧和秩序的維度之中,并且各自有了對秩序的不同價值。從某個側面來說,這種觀念使得“丑”的事物具有了和“美”的事物一樣的價值表現功能。
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基督教的文字和藝術作品當中大量出現了許多丑陋的形象。這些形象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基督受難時的鮮血場面,以及迫害基督的人的丑態。
我們可以在大量描述基督受難的繪畫和文字作品中看到有關耶穌的種種“丑陋”畫面:鮮血、傷痕、荊冠,甚至是耶穌的尸體。前文我們已經看到,“美”和“丑”已經在新柏拉圖主義者心目當中獲得了統一于“和諧”的可能性,而在基督教文化中,這種可能性進一步就成了人性和神性的合一與和諧。人性代表著耶穌“道成肉身”的人的一面,而神性則代表著他身上的上帝之子的神性。由于存在這種兩分性,黑格爾認為古典藝術往往不能勝任這一表現功能,“因為個別主體與神的和解并不是一開始就直接出現和諧,而是只有經過無限痛苦、拋舍、犧牲和有限的,感性的,主體方面因素的消除才產生出來的和諧,有限和無限的在這里緊密結合成一體。”[11]由此可見,耶穌作為人性一面所遭受的鮮血場面,無疑是作為肉體的“丑”的部分在向精神中的“美”的部分的一種轉化,是肉體向精神升華過程中的必要且間接的犧牲。
至于迫害基督的人,黑格爾認為可視為基督的敵人,他們“判了神的罪,嗤笑他,使他受苦刑,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們被表現為內心上是惡的,而這種內心的惡和對神的敵視表現于外表則為丑陋,粗魯,野蠻的形象和兇狠的歪曲。”[11](299)這樣一來,外在于基督的那些方面,可以視作是對基督精神上“美”的直接催化。
至此,我們可以說,在基督教文化中,丑不僅和美統一于秩序當中,而且具有和美一樣的表現價值。和古希臘相比,這種丑的認識具有如下特點:丑不再是參照美的一種缺失和失衡、失序,而是作為整體參與秩序的構建;丑不再是肉體/精神二元對立體系中單純代表肉體的一個尺度,而是作為一種對美的犧牲和催化,從而兼具肉體和精神的特征,這種特征表現為耶穌神性和人性的統一與和諧。
二、“丑”對“美”的延伸:揭示諷刺
“丑”的形象除去作為研究標本放在哲學家、美學家的案頭之外,更多地是伴隨著笑聲回蕩在民間。這似乎構成了人們面對丑的事物時近乎本能的反應。那么,人們在接受“丑”的事物時會發笑?
其實,本能只是一方面,屬于心理學的范疇。但即便是柏格森這樣的心理學家在研究這一問題時也沒能道破真諦。普羅普認為,柏格森認定人類之所以發笑是受到了自然規律支配這一結論是錯誤的,因為它無法解釋為什么有些事物明明是可笑的,但人們就是選擇不笑。[12]顯然,人之所以選擇不笑,是受到了某種約束本能的作用。這些約束本能的成分和一個人所處的社會、階級、文化等異于自身的因素密切相關。進而,普羅普認為這種異己的因素會激發兩種模式供人發笑:
相似性和差異性。所謂相似性就是一種重復。當一個人刻意地去模仿另一個人的行動,并且重復不停地模仿,往往就引出來讓人發笑的場景。比如小孩子之間經常做的重復某人的話。相似性發笑的前提在于,人們都相信每個個體都是不同的,當所有的不同刻意地趨向共同特征時,往往就會帶來笑的因素。[11](40-43)而差異性因素之所以能讓人發笑,原因在于人們看到了別人身上某種完全不同于自己的一面,確切地說就是某種缺陷。[12](43-44)那么,這兩點對于我們的認識有何幫助呢?
“丑”就是某種缺陷,并且這種缺陷無法復制。這一特點之所以會引人發笑,需滿足兩個條件:“它的存在和形態不使我們感到受辱和激起憤怒,也不引起憐憫和同情……”[12](45)受辱、憤怒、憐憫,這些元素顯然不僅僅是人的一種本能反應,更多地是人在相應習俗和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的價值判斷。這樣一來,我們可以說人對丑之所以會發笑,不僅是由丑態本身所決定的,還裹挾著丑態背后的集體因素。丑的缺陷不僅是丑態的外在,也是對集體所遵循的共有價值觀念的適度違反。普羅普的精彩分析無疑切中了丑之于笑的基本原理,但對于我們所要探究的問題來說,關鍵還不在于對丑與人之發笑本能,或者某種社會習俗促使丑成為笑料這兩個問題進行探究,我們所要關注的是,人們為什么會創造丑,利用丑的樣貌和形態來主動地引起他人的笑?
我們若將以上這個問題與中世紀的狂歡文化結合起來分析將會帶來較為清晰的判斷。在巴赫金看來,中世紀存在兩種生活模式:“一種是常規的、十分嚴肅而緊蹙眉頭的生活,服從于嚴格的等級秩序的生活,充滿了恐懼、教條、崇敬、虔誠的生活;另一種是狂歡廣場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滿了兩重性的笑,充滿了對一切神圣物的褻瀆和歪曲,充滿了不敬和猥褻,充滿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隨意不拘的交往。這兩種生活都得到了認可,但相互間有嚴格的時間界限。”[13]而兩種生活之間的調節則成了狂歡文化主要功能。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狂歡就是一場場“笑的”節日。它為原本壓抑、封閉的民眾精神生活激活了豐富的時間體驗,敞開了話語流通的空間。[14]但若聯系我們所要論述的主題,除去空間和時間這兩個要素之外,處在狂歡化儀式中的人的“軀體”則更為重要。
據西方學者考察,狂歡節(Carnival)一詞由“caro,carnis”(肉體)與“levare”(更替)組合而成。[14](200)由此可見,狂歡的主體是與肉體相關的內容。肉體對宗教、官方話語的反抗通過宣泄欲望來實現。在巴赫金看來,民眾通過身體中怪誕的部分來抵抗宗教生活中的體面,主要通過四個方面來實現:通過展現怪誕來傳遞生命力,繼而體現出希望的內涵;通過敞開身體,尤其展現官方話語所禁忌的部分來達成親密的接觸;挑戰官方的禁忌,繼而達到挑戰話語權威的作用;最終敞開了一種對話的可能。[14](5)那么,所謂的怪誕的身體具體是指什么呢?巴赫金指出:“怪誕形象的藝術邏輯藐視人體中封閉的、平坦的和無生氣的平面(表面),只定格那些超出于人體界限或通向人體內里的東西。山岳和深淵,這就是怪誕人體的凹凸,或用建筑學語言,即地下室里的鐘樓。”[15]由這段話我們不難看出,所謂的怪誕其實就是指身體不符合勻稱、平面的認識觀中的軀體。這種“凹凸”具有更為深刻的隱喻意義:“現代人體規范的特點是……一種完全現成的、完結的、有嚴格界限的、封閉的、由內向外展開的、不可混淆的和個體表現的人體。一切突起的、從人體中鼓凸出來的東西,任何顯著的凸起部位、突出部分和分肢,亦即一切人體在其中開始超越其界限,開始孕育另一人體的東西,都被砍掉、取消、封閉、軟化。而且,所有導向人體內里的孔洞也被封閉。個體的、界限分明的大塊人體及其厚實沉重、無縫無孔的正面,成為形象的基礎。人體無縫無孔的平面、平原、作為封閉的、與別的人體和個體性世界不相融合的分界,開始具有主導意義。這一人體所有的非完成性、非現成性特征,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其肉體內在生命的所有表現,也被排除。”[15](371)考慮到巴赫金構建理論的基本態度,我們可以這樣說,狂歡儀式中身體的凹凸其實是為了展開對話,流通話語的一種手段,這種手段由于借助了軀體的具體展現形式,不僅具備了對話的渴望,也同時展現了由展開身體偽裝所帶來的真誠。
回到我們所論述的問題上來看,怪誕的軀體、凹凸的造型其實就是一種“丑態”。誠如艾柯所言,“丑態”因此具有了兩個關鍵的話語功能:詼諧與猥褻。值得指出的是,艾柯并沒有指明這兩個術語的總結得益于巴赫金的分析,但在筆者看來,艾柯無疑是對巴赫金理論的一次深入總結。在中世紀的語境之下,猥褻顯然來自于官方和宗教話語中的標準,是對正統身體觀念的否定。而所謂的詼諧則是一種渴望交流,表露真誠對話的嘗試,這兩者的關系密不可分。即便如此,我們還需看到,民間這種對丑態的展示多半是自發性的,歸屬于傳統或者集體無意識的范疇當中,它與人們自發創作丑態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我們真正需要考察的問題在于,人們抱著什么樣的目的在創作、生產丑的形象?如若目的是可以探明的,那么所謂的猥褻和詼諧的主旨又在何處?
無疑,喜劇是有關丑態的形象的天然舞臺。出現喜劇的演員可能本身并不是丑的,但卻通過夸張的裝扮,浮夸的演技來模仿丑態,從而達到喜劇表演的目的。這是值得我們考察的一個方面,因為演員是有意識地創作和表現丑態。專攻丑的美學的羅森克蘭茲就曾經指出:“浮夸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是丑事。浮夸是一個人的自由往往已經失去控制的征象,而且每每在不適合的場合,在他不防之下迅速難以收拾而令他恐慌吃驚。因此,浮夸就像一個妖怪,在沒有預警之下放肆妄為,使他陷入尷尬的處境。所以,喜劇演員總是喜歡在丑怪劇和詼諧情節里運用這項因素,至少通過典故來表現……人,不管年齡、教育水平、社會階層和地位有什么差異,全都有這種不由自主的卑下天性,因此此類典故指涉很少有不令觀眾大笑的;低下的喜劇特別喜歡運用與此有關的粗俗、淫穢和瞎鬧,道理就在這里。”[4](138)羅森克蘭茨在這番話中與其說強調了丑進入喜劇的條件,不如說揭示了我們對丑的好奇。并且,這種好奇帶有瞬間性和突襲性,它首先引起的是人們對失控事物的驚恐。但是,我們不禁要問,人們對于驚恐的事物為何會笑?這種猥褻的場景又是如何產生詼諧的效果的?一般來說,觀眾在經歷從驚恐到發笑的這個過程中之所以能放聲大笑,原因或許在于他看到的是和自己無關的驚恐,并且慶幸自己能安全地躲過這種驚恐,繼而將笑當成一種寬慰和對驚恐情緒的舒緩。但是,可想而知這種笑必定是短暫的,也必定是無法重復的。馬克斯·德索就曾指出:“縱使在一般生活中,丑的變形,令人作嘔的東西實際上都能使我們著迷,其原因不僅是由于它以突然的一擊而喚起我們的敏感,而且也由于它痛苦地刺激我們那作為整體的生活……藝術大師們在他們的作品里僅為藝術的目的而體現出這種刺激,人們都認為是合理的。”[16]如此來看,丑態之所以能讓人發笑,并且人們也樂于接受這種刺激,除去我們對他人驚恐的消費,對緊張情緒的舒緩之外,還伴隨著人們接受藝術創作的共識。既然提升到藝術創作的層面,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喜劇的漫長歷史中,丑怪形象之所以能夠長久地發展下來,定有除去讓人短暫發笑之外的原因。
要探索這一原因,我們不妨順著馬克斯·德索的分析,首先來分析一下丑的產生機制是什么。德索認為:“使人愉快的和理想的美的東西產生一點小小的變化可能獲得某種獨立丑的東西。稍微扭曲一個正方形或圓形,或把不相容的兩種顏色混合起來都會產生丑的效果……更重要的則是丑從自身中獲取審美價值的能力……一切種類的美——嚴格的形式美,歡快的色彩美,悅耳的音樂和諧美——都可以說是花費了極大的精力去炫耀其外部,所以就沒有任何余力去表現其內部了……然而如果藝術家欲表達自己內心中深深的思念,表現內心最深處最屬于精神的東西,那么丑便與優雅一起提供了表達的合適方式。”[16](156)由此可以看出,丑若要達到和美一樣的美學功能,首先需要擺脫的是肉體,而進入精神的層面。但很顯然,這里所說的精神層面肯定不再是丑的物體自身的層面,而是來源于被揭示的物體。也就是說,丑開始脫離原本就是丑的事物,對需要表現的對象進行刻畫。丑態所包含的詼諧和幽默發生了對象的轉移,將自己的丑態轉移到原本不那么丑,甚至是美的事物身上,達到一種精神層面的揭示,這就是諷刺。
以丑來揭示美的事物的偽善,所達成的效果是漫畫式的,對丑的功能這一重要轉換,羅森克蘭茨的認識是深刻的:“丑將崇高的轉換為粗俗的,將愜意轉化為可憎的,將絕對的美轉化成諷刺漫畫,在諷刺漫畫里,尊嚴變成強調,魅力變成賣俏。諷刺漫畫因此是形式之丑的極致,不過,也正因為其所反映的事物時受其所扭曲的正面形象所決定的,所以諷刺漫畫不知不覺進入喜劇境界。”[4](154)這樣一來,丑和笑就結合在一起,成為了諷刺。值得注意的是,羅森克蘭茨指出這種喜劇效果受到了正面形象,也就是所要諷刺的對象的限定。但這并不意味著丑的事物就因此失去了自身的特點,恰恰相反,諷刺的效果若要達到理想的效果,必須最大限度地保留自身的特點:“要解釋諷刺漫畫的話,你必須加上另外一個夸張觀念,就是形式與其全體之間的不合比例,也就是否定那個依照形式觀念而本來應該存在的統一。也就是說,如果整個形式的所有部分都做同等的放大或縮小,那么,各部分之間的比例維持不變……就不會產生任何真正的丑。但是,如果有一個部分逸出這種全體的統一,從而否定各部分之間原有的協調,可是這逸出部分以外的其余部分相行之下幾乎消失。這樣,就是不成比例的效果……使形式出現扭曲的那種夸大,必須是一個充滿力量的,牽動整體形式的因素。它所造成的形式失序必須是有機的。這個觀念是諷刺漫畫效果的奧秘所在。透過將整治的某一部分加以不懷好意的夸大,造成的不和諧卻會生出某種新的和諧來。”[4](154)至此,我們可以看到,“丑”通過諷刺的效果,形成了新的和諧,從而在“美”的側面延伸出了新的道路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艾柯認為羅森克蘭茨完成了“丑在美學上的救贖”。[4](152)
三、“丑”對“美”的提升:激發崇高
到了18世紀,人們對丑的認識又有了新的維度。這種對丑的全新認識首先在美學家和哲學家那里得到了理論上的探討。大思想家伯克認為“雖然丑是美的對立面,它卻不是比例和適宜性的對立面。因為很可能有這樣的東西,它雖然非常丑,但卻合乎某種比例并且完全適合于某種用途。我想丑同樣可以完全和一個崇高的觀念相協調。但是,我并不暗示丑本身是一個崇高的觀念,除非它和激起強烈恐怖的一些品質結合在一起。”[17]伯克的上述言論中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首先,他指出了丑自身作為美的對立面,保留了“比例”和“適宜性”這兩個方面。從這一點上來說,伯克回應了羅森克蘭茨的言論。但更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范疇對應關系,那就是丑與崇高的關系。盡管在這個范疇中丑并不直接與崇高劃等號,但丑中所包含的恐怖成分卻能激發崇高。這樣一來,我們對丑的認識就獲得了全新的維度。
其實,伯克的認識是融合在一系列美學思想的變革潮流中的。因為“在18世紀,關于美的辯論,重點從尋找規則來定義美轉為思考美對人的作用。”[4](272)而在康德眼中,美對人的具體作用就體現在美與崇高的關系當中。他指出一共有兩種崇高:數學式的崇高和力學式的崇高。所謂數學式的崇高,“典型的例子就是繁星滿布的天空:我們所見仿佛遠逾我們的感受能力范圍,我們的理性因此假設一個無限,我們的感官無法掌握這無限,我們的想象卻以直覺擁抱它。”[4](276)另一種力學式的崇高,“典型的例子就是暴風雨:我們的靈魂被無限力量的印象所撼動,我們的感官本能自覺渺小,從而產生不安的感覺,但我們意識到我們在道德上的偉大來彌補這種不安——自然的威力無法主宰我們道德上的偉大。”[4](276)具體來說,如若要激發數學式的崇高,則先要有一個超出感官的對象,進而需要用想象力來擁抱。而在力學式的崇高中,靈魂因為無限所撼動,需要道德來進行彌補。“超出感官”和“無限”就是不可見的表征,“擁抱”與“彌補”則是針對這種“不可見”所做出的策略。
相比之下,丑則是可見的,直面的。萊辛在《拉奧孔》中論及“丑”的作用時曾特意指出:“丑要有許多部分都不妥帖,而這些部分也要一眼就可以看遍的,才能使我們感到美所引起的那種感覺的反面。”[18]由此觀之,萊辛所謂的丑的可見特質,實則作為一種區分,可歸在詩歌和繪畫關系的范疇中進行論證。如若從這一論證角度出發來看,萊辛認為詩人在寫作詩歌時,實則是通過描寫丑的形體,稀釋了丑所能引起的反感,“就效果來說,丑仿佛已失其為丑了,丑才可以成為詩人所利用的題材。詩人不應為丑本身而去利用丑,但他卻可以利用丑作為一種組成因素,去產生和加強某種混合的情感。”[18]并且這種混合的情感就是“可笑性”和“可怖性”。而這個可笑的特性是怎樣產生的呢?萊辛認為:“丑陋的身體只有在同時顯得脆弱而有病態,妨礙心靈自由活動的表現,因而引起不利的評判時,嫌厭和喜愛才能融合為一體,但是所產生的新東西卻不是可笑性而是憐憫;那對象如果沒有這種情形,本來會受到我們尊敬,因為有這種情況,就變成逗趣了。”[18](143)逗趣與憐憫之別顯然在于觀看者自身的評判,而若這種判斷的結果和所謂的利害關系相掛鉤時,那么“如果無害的丑惡可以顯得可笑,有害的丑惡在任何時候都是可恐怖的。”[18](145)筆者認為,所謂無害的丑惡實則表明在觀看者心中,這種丑惡是可以被控制的。而有害的丑惡則意在表明,丑惡已經超出了人的可接受范圍之外。但是作為人的一種天性,席勒指出人卻常常會在明明知道丑陋可以激發恐怖的情況下不由自主地去觀看丑的事物:“人性有個普遍現象,就是難過、可怕甚至恐怖的事物,對我們有難以抵擋的吸引力;痛苦和恐怖的場面,我們覺得既憎惡,又受吸引。正義得伸的快意,與不高貴的報復欲,都無法解釋這現象。觀者可能原諒這狼狽無狀之人,最真心同情他的人可能希望他得救,但觀眾都多少有一股欲望,想看他受苦之容,聽他受苦之言。受過教育者如果是例外,那也并非因為他沒有這股本能,而是因為這本能被憐憫克服,或者因為這本能被立法抑制。質性較粗的人,則不受這些細致情緒阻礙,追從這股強大的沖動而不以為恥。這現象因此必定根源于人這種動物的本性,必須解釋為人類普遍的心理律則。”[4](220)
除去這一點近乎本能的特質之外,如若我們聯系康德的言論,不妨做如下補充:人類之所以會去觀看丑惡的事物,除去本性之外,還在于丑的事物因其具有可怖的特性從而具備了一種無法被掌控的特質,在這種無法被掌控的特質的影響下,人們的心靈似乎可以激發出崇高的特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萊辛所指出的丑的事物的“可笑性”和“可怖性”,可以視為人們依據丑的事物對自身的利害關系所做出的兩種不同程度的反應:如若這種丑與自身的利害無關,那么這種丑就是可笑的。進而,如若這種丑對于觀看者有著切身的利益,比如讓人引起痛感,那么這種丑就可以激發出可怖感,但人們并不會就此止步,而是借助類似美的事物所激發的道德或者想象的彌補一樣,借助憐憫來激發出類似的崇高感來。由此,丑就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具有了類似激發崇高的美學特質。
四、結 語
至此,我們梳理了雨果之前的美學家所論述的有關“美”和“丑”在審美中的表現。丑曾作為美的補充,一同表現和諧;也曾作為一種反諷的元素,延伸了美對于和諧的表現;并且在激發“崇高”方面,獲得了和“美”近似的作用。應該說在這種轉變的背后,隱含著古典和近代美學觀念的轉變。而雨果作為浪漫主義的旗手,其出發點也正是站在浪漫和古典的論證上的。
[1]程曾厚.程曾厚講雨果[M].北京:北京大學大學出版社,2008:154.
[2]程曾厚.雨果評論匯編[C].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60.
[3][法]雨果.雨果論文學[M].柳鳴九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30.
[4][意]翁貝托·艾柯.丑的歷史[M].彭淮棟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8-16.
[5][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2卷)[M].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60.
[6][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07.
[7][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M].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4.
[8][古羅馬]馬可·奧勒留.沉思錄[M].何懷宏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27-28.
[9][古希臘]狄奧尼修斯.神秘神學[M].包利民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8:28-29.
[10][古羅馬]奧古斯丁.懺悔錄[M].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94.
[11][德]黑格爾.美學[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298.
[12][俄]普洛普.滑稽與笑的問題[M].杜書瀛等譯.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14.
[13][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M].白春仁,顧亞鈴譯.北京:三聯書店,1988:184.
[14]趙勇.民間話語的開掘與放大——論巴赫金的狂歡理論[J].外國文學研究,2002(2).
[15][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憲等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69.
[16][德]馬克斯·德索.美學與藝術理論[M].蘭金仁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155.
[17][英]柏克.關于崇高與美的觀念的根源的哲學探討[A].孟紀青,汝信譯.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編輯委員會.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5冊)[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60.
[18][德]萊辛.拉奧孔[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42.
[責任編輯:華曉紅]
2010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外國文學經典生成與傳播研究”(10&ZD135)的階段性成果。
林曉筱,男,講師,文學博士。(浙江傳媒學院 文學院,浙江 杭州,310018)
I565.074
A
1008-6552(2016)06-01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