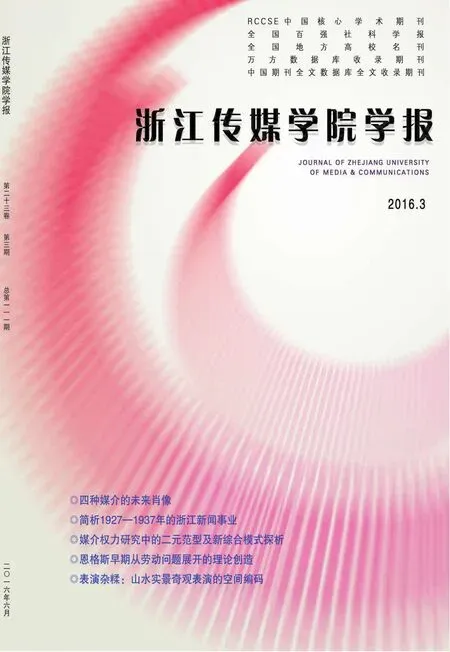民國士人觀影的心路歷程
——基于《余紹宋日記》中觀影筆記的解讀
徐洲赤
?
民國士人觀影的心路歷程
——基于《余紹宋日記》中觀影筆記的解讀
徐洲赤
摘要:清末民初為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解體與轉型時期,電影作為新文化的重要形態,可以折射出新舊觀念和文化對一個社會轉型期士人的影響。《余紹宋日記》中的電影筆記,較為具體地記錄了一個民國士人對電影的接受過程及其觀影心態的變化,尤其對左翼電影的觀感,非常典型地體現了當時士人階層在社會沖突面前的分裂心態和立場。同時,也為傳統士人階層在時代動蕩下的轉型與消亡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照視角。
關鍵詞:士人階層;電影;新舊文化;余紹宋;左翼電影
“觀《死光》影片,甚奇,此光如真實用,人類無噍類矣。”[1]1925年9月21日,民國北京政府司法部官員余紹宋,在北京真光電影院觀看外國電影《死光》后,在日記中記下了他的感受。“無噍類”,無幸存者之意。從1921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的16年間,余紹宋在他的日記中,共記錄看電影經歷53次,記錄電影片名48部。雖然這些記錄比較簡短,作者也非專業電影人士,但作為私人生活史的一部分,自有其獨特價值。
一、余紹宋和《余紹宋日記》
民國文化名人余紹宋有《余紹宋日記》五卷,計170萬字,從1917年至1942年的24年間,基本沒有間斷過,差不多是民國時期最全的私人日記之一。其間歷經張勛復辟、軍閥混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抗日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和階段,既有對大時代的觀察和記錄,也有對日常生活細節的體察和感悟,是研究民國史的重要資料。*學界對《余紹宋日記》的資料運用,主要以民國史研究及書畫史和方志學研究為主,如民國史方面,臺灣學者林志宏著《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胡平生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等著作,論及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政局,均曾援引《余紹宋日記》中相關內容。而當今治中國近代美術思想史的諸多學者,如毛建波、張濤等,均在其專著和論文中大量援引《余紹宋日記》為權威資料。總體而言,當今學界對《余紹宋日記》的研究尚不夠充分。
余紹宋,浙江龍游人,民國時期文人畫的代表人物之一,解放前以書畫名播朝野。曾赴日留學,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擔任過司法部次長、代理總長。北伐后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他告別仕途,回杭州鬻畫為生。后擔任浙江省臨時參議會副議長,當選國大代表。1949年因病去世。余紹宋勤學敏思,天分極高,在民國早期的司法理論和實踐、書畫藝術、方志學等方面均有相當的造詣。
余紹宋從政期間向來厭惡官場做派,堅持不黨不私,看重政治操守。上世紀20年代發生“金佛郎案”和“三一八”慘案,余紹宋因堅持法統而兩度辭官抗議,乃至最終因對政治失望而棄絕仕途。其行事方式與觀念,更接近于儒家傳統的士人理念:進則濟世,退則修身。梁啟超作為其摯友,曾在給張元濟信中對他如此評價:“越園(余紹宋字)雖在司法界屢歷要職,曾不改儒素……其不屑不潔之苦心,非我輩中人莫之能解也。貧士而狷守自守,舍自食其力外無所為計。”[1](626)梁啟超以“貧士”許之,而余紹宋亦以士人身份自許。如他在辭任北京美術專科學校校長的信函中說:“士有如此,不得謂之士。”[1](473)以此強調其行事做人之標準。其士人身份的認定,后世學界也多有認同,如有學者評價:“從其公余生活的諸多面相窺測,余紹宋的身份認同感,更多的是來自于對傳統文士身份的追溯與復現。”[2]
讀《余紹宋日記》可以感受到:這個處于新舊轉換期的舊士人,始終面臨各種蜂擁而至的新文化的沖擊。而民國初年,一方面,軍閥割據,武力稱雄;另一方面,新思想、新文化風起云涌,革命浪潮不斷高漲,立場溫和的舊士人階層趨于沒落、瓦解和分化,在主動與被動間彷徨并各自尋求轉型。
余紹宋在北京和杭州期間先后組織的宣南畫社和東皋雅集,均是民國時期有重要影響力的美術社團。參與畫會的友人有湯定之、陳師曾、賀履之、蕭俊賢、陳寶琛、姚茫父等。他們在藝術趣味和創作路徑上,大多和余紹宋志趣相投,即重視傳統文人畫的純粹性和風骨,較少受新起海派畫風的影響。1923年10月2日,有上海友人勸余紹宋到滬賣畫,“謂可發財。”而他的態度是:“余非不知,但海上畫風太壞,恐敗壞吾書畫耳。”[1](407)
余紹宋對新文化始終有一種距離感,尤其對外國歌舞。1923年8月26日,余紹宋在真光劇場聽外國音樂,“外國女人歌舞殊莫名其妙,但覺目光閃爍,歌聲宛轉激厲而已,聽者七八百人,外國人甚少,卻掌聲雷動。”他覺得這些人大概都和自己一樣,完全聽不懂,“卻使其掌無辜受痛。慨嘆而已。”[1](400)他沒有領會這是西方的文明禮儀,他對西洋舞蹈更是反感。1934年5月10日,“夜同姬人往城站影戲院觀梅花歌舞團演藝,但誨淫耳,一無足取,未演畢即歸。”[1](1171)梅花歌舞團,最初叫“梨花歌舞團”,是20世紀20年代創辦的歌舞團體,創辦人魏縈波女士,擅長西洋古典舞、土風舞及中國戲曲舞蹈。她創作的《七情》(盤絲洞)是一部反封建反迷信的歌舞劇。該劇于1930年初夏在南京、上海公演,轟動一時,得到田漢等的鼓勵、幫助。“梅花歌舞團”還上演進步劇作家歐陽予倩編的歌舞劇《楊貴妃》,以及《國色天香》《草裙舞》《玉兔舞》《西班牙舞》《卻爾斯黛舞》《水手舞》《劍舞》《扇舞》等等,是一個比較專業的舞蹈團體。或許是西洋舞蹈的裸露服飾讓他覺得不可接受,視為“誨淫”。
但如果就此認為余紹宋立場保守、思想僵化,對新文化一味排斥,那就錯了。且看他對《新青年》的態度:“夜看所謂《新青年》雜志,內中主張多荒謬不經,惟思想極新穎活潑,亦有足取者。”[1](97)這是他在1919年2月26日所記的日記。應該說,這個評價比較客觀。我們現在一般把《新青年》當作新思想、新文化傳播的代表,是進步與保守的界標,具有新時代的象征意義。但如果將《新青年》作為衡量進步與反動的標尺,則失之簡單。《新青年》的許多文章為求振聾發聵、矯枉過正,常有極盡偏激與夸張表述之處。如陳獨秀的《敬告青年》主張:“要變易‘家族本位主義’,否定傳統綱常,首先便是反‘孝’。”[3]頗有些駭人聽聞。在時人看來,的確不是說道理的方式。當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汪懋祖致書胡適,說《新青年》的一些文章:“如村嫗潑罵,似不容人以討論者,其何以折服人心。”[4]而余紹宋能夠肯定其“有足取者”,足以說明他并不固步自封,不排斥接納新事物、新思想。1923年11月1日,他首次在日記中對所看電影作了評價:“赴真光看《二孤女》電影,演法國革命時事,可歌可泣。”[1](416)雖簡短,也可見其對電影內容的態度。
中國早期電影事業,差不多隨帝制的衰落、民國的建立同步而來,是新舊文化的交匯體,既有西方好萊塢電影文化的成份,又有早期舊倫理電影中國傳統文化之遺留,更有左翼電影的階級觀念之構建,從中可以強烈感受到新舊觀念和文化對一個社會轉型期士人的沖擊。
二、余紹宋對電影的接受過程及電影觀感之變化
現存《余紹宋日記》從1917年開始,但在1917年到1921年6月的三年半時間里,關于看電影的經歷是空白,唯一提到之處是1919年1月2日:“今晚美國公使芮恩施請看美國戰事影戲,辭未去。”[1](91)1919年時,北京的電影院大多為外國人創辦,如“平安電影院由洋人經營,票價高,觀眾多為洋人和上等華人。”[5]在電影進入他的生活之前,作為一個政府官員,公余之暇,除了作畫,他手不釋卷,尤勤于讀史。如《通鑒》《南史》《北史》《十七史商榷》等,并且因為許多書是善本、孤本,須借閱,邊看邊抄錄,一天要抄兩萬多字,頗為勤奮。他讀書效率驚人,幾卷本的史書,一夜讀畢。如1918年2月14日記:“夜讀《安龍逸史》兩卷,慘然于亡國之感矣。”[1](50)讀書生活之外,用于消遣的是下圍棋和看戲。如1917年4月6日記:“夜蒲伯英邀赴第一舞臺觀梅郎演木蘭新劇,精彩之至,內中以‘臨別’一場為最淋漓盡致。”[1](14)1917年6月5日又述:“飯后招說書者來說《水滸》。”[1](21)有時還不免有傳統士大夫式的荒唐。1921年10月8日,回老家路過蘭溪,“吃花酒兩抬,舊時兩妓已從良,無一相識之人矣。”[1](1165)就這樣,他過著一種符合儒家標準的傳統士人生活。
中國人創辦的真光電影院于1920年被大火燒毀,在中央公園臨時開設分院,余紹宋第一次看電影即在此處,時間是1921年7月24日:“夜與周妾同到中央公園遣悶并看電影,遇雨而歸。”[1](190)但因為中央公園開設的是露天電影院,所謂“遇雨而歸”,即很可能沒有看成。從他沒有提及片名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因為此后余紹宋看電影大多會提及片名。他最早提到片名的電影是《大盜感恩錄》,1921年12月24日和好友江庸(曾任司法總長)一起觀看,晚上九點鐘開映,十一點半結束。
此后,電影進入其社交和家庭生活,成為一項經常性的活動。如1925年一至三月間的記載:“1月14日,陪徐心庵(同鄉好友)看電影。”“22日和江叔海丈(畫友,曾任京師大學堂文科學長、代校長、故宮博物院維持會長)看電影。”“26日,夜率姬人并兩兒到真光看電影。”“2月17日,在真光西歺,并看電影,名《月宮盜寶》,奇幻之至。”“3月19日,夜赴總布胡同俱樂部談話并看電影。”[1](480-190)這一系列記載,可以讓我們感知以下幾點信息:第一,中國人創辦的電影院在當時北京已屬比較活躍的觀影場所;第二,當時的真光電影院同時經營西餐等,頗接近于今天以影院為中心的商業綜合體;第三,當時北京的觀影場所,除公開放映的電影院,還有類似于總布胡同俱樂部這樣的會所,以電影招待客人也是一種時尚的沙龍聚會方式……但總的來看,此時的余紹宋,看電影頻率并不算太高,大約每年四、五部的樣子,其間仍夾雜觀賞舊劇。如1933年4月16日記:“作譜至下午二時。忽發雅興,率姬人冒雨往大禮堂觀有聲電影,所映皆非洲風物鳥獸,有甚奇異者,觀畢復觀京劇,皆海上票友所演,末一劇為《霸王別姬》,飾項羽者為金少山,則伶人也,碩大聲弘,堅光切響,真黃鐘大呂矣。”[1](1089)
到30年代,余紹宋日記中看電影的記載增多,尤其1934年到1936年間,已逐漸占據其娛樂生活的主要時間。如1935年,居然一年看電影達20部之多,其中大多為左翼電影,如《桃李劫》《海葬》《大路》等。這種情況,一方面與此一時期國產電影產量尤其是左翼電影的大量涌現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余紹宋對電影的興趣日漸濃厚,且有逐漸超過舊劇之趨勢。而相應的變化則是:隨著看電影頻率的增多,日記中關于讀書、下棋、看戲等方面的記載越來越少,直到抗戰爆發離開杭州。整個抗戰期間,因困于鄉野,電影在余紹宋的生活中徹底消失。
初期,余紹宋看電影大多數情況下為“遣悶”,是對社交和家庭生活的一種調節:“夜同博生往看電影,近來精神似不若從前,入夜便不能用心,只好習字或看電影……”[1](1226)對影片的觀感也大多從聲色光電之類的新奇角度作評。如1924年12月5日所記:“真光劇場看《毋相忘》,末一幕演一女子善彈梵鈴,而以天仙魔影、山光月色波濤等真景,寓意正與樂天《琵琶行》以急雨細語、鶯聲泉響相喻同符,可知聲音之道無中外,古今一也。”[1](474)可見他對電影藝術有相當的認同。但比較微妙的是,在對電影興趣日增的同時,卻又不愿意承認對電影有更多的好感:“電影本非所喜,取其中所攝風景有非生平所能至者,亦足以少拓胸襟。”[1](1226)這反映了一個以傳統文化為正道的文人,多少有些視電影為末技的心態。等到左翼電影發展起來,他開始對電影的內容及其社會教化意義引起重視,尤其對左翼電影中的階級觀念反應強烈(此點容下文詳述)。相對應的,開始對符合傳統倫理觀念的電影有好評。如1935年9月3日記:“劇名《小天使》,所謂教育片也,頗有意義,國產影片中佳制也。”[1](1298)這是部家庭劇,講鄰里和睦、互助友愛,有強烈的道德教育意味,整體節奏緩慢,余紹宋對其作了較高的評價。
分析余紹宋日記中的觀影記錄可以看出,民國至抗戰爆發前的中國電影,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
第一是國外電影引進時期。《中國電影發展史》一書中認為:“中國的電影事業不是從自己攝制影片開始,而是從放映外國影片開始的。”[6]余紹宋在日記里充分印證了這一點:查對整個20年代所記片名,基本為國外引進,如《情海輪回》《俠犬蒙冤記》《太古遺跡》《黑海盜》《二孤女》《月宮盜寶》等。其中,1924年3月1日的日記中提到:“到劇場看《賴婚》影戲,此劇在西洋最有名。”[1](435-436)此劇為大導演格里菲斯的作品。
第二時期為國產片起步階段,從內容看,有新舊劇過渡的痕跡,主題以懲惡揚善為主,新瓶裝舊酒。“1932年之前的中國電影,無論改編還是新編,基本上源自言情小說以及武俠小說這樣的舊小說路數,基本沒有新文學作品思想的采納、加入。”[7]這一時期的舊倫理電影(有論者稱為舊市民電影)論藝術成就并不算高,面向的是中下層市民。“從1921年到1931年這一時期,中國各電影公司拍了約六百五十部故事長片,其中絕大部分是由鴛鴦蝴蝶派文人參加制作的。”[6](56)余紹宋作為藝術修養極高的文人,自然與此種低俗趣味格格不入。即使根據名著《紅樓夢》改編的,也因其改編趣味問題,讓其感到不堪忍受。1933年2月2日,他在日記中記:“偶觀電影演《紅樓夢》,丑惡不堪即離去。”[1](1073)查《紅樓夢》在1933年前的電影改編中,共有三個版本:1924年梅蘭芳的電影版《黛玉葬花》,1927年上海復旦影片公司的無聲時裝劇《紅樓夢》,1928年(或1929年)上海孔雀影片公司出品、程樹仁執導的古裝《紅樓夢》。至于1933年是否有新改編版本的《紅樓夢》上映,未見記載。余紹宋所看的很可能是27年版或28年版的老片重映。1927年版《紅樓夢》共四小時,放映后反響強烈,但因是時裝劇,頗有顛覆性,當時較具爭議。1929年版《紅樓夢》為突出情愛沖突主線,還加入現實人物曾友笛干涉女兒婚姻最終悔悟的情節。無論哪個版本,均以男女情感為主線,不脫“鴛鴦蝴蝶派”的審美風格。[8]
第三階段則是左翼電影的興起。“1930年代是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標志之一就是因為有了新電影——左翼電影。”[9]左翼電影以表現底層階級的貧困生活為主,表現窮人的苦悶和沒有出路,從而激發階級仇恨和革命觀念。而左翼電影對余紹宋的觀感沖擊最為強烈,電影主題思想和余紹宋固有的觀念不斷發生碰撞,終于讓他體驗到社會階層正在劇烈動蕩、分化的趨勢。
三、被撕裂的觀感
《余紹宋日記》中對電影的評價,針對左翼電影發表議論最多,反應也最激烈。概括起來,左翼電影大致包括三重主題:第一,謳歌勞工;第二,表現底層民眾的悲慘生活;第三,表現階級矛盾與暴力抗爭。對第一層主題,他頗有同感,對第二層主題不以為然,第三層主題則使其反應強烈。他最早接觸的左翼電影是《大路》。1935年2月4日記:“劇名《大路》,所謂時代作品也,劇情尚佳。”[1](213)該劇是典型的左翼電影,孫渝導演,表現筑路工人群體形象,片中的插曲《大路歌》《開路先鋒》由聶耳作曲,堪稱時代強音。對這樣一部進步電影,余紹宋似乎并不反感。從內容來看,該劇在突出勞工階層正面形象的同時,并未刻意強調階級矛盾,是重在熱情謳歌,而不是批判暴露。“《大路》意味著精英階層即知識分子在社會發展中的自我反省與主動退離。”[9](213)顯然,同為精英階層的余紹宋對這樣的反省還是能夠接受的。
但是,左翼電影的另兩重主題:表現底層的悲慘生活、揭露階級矛盾乃至激發斗爭覺悟,讓余紹宋頗受刺激。1935年6月17日記:“劇名《生之哀歌》,情節悲慘,近來風氣如是,固是社會實情,然實際無如是之酷……”[1](1278)《生之哀歌》的編劇是左翼劇作家陽翰笙,劇情如下:某公寓住著三個年輕人,大學助教林夢鷗、他的同學喬杰、幼稚園女教師梁素秋,三人親密如知己。夢鷗與校花趙曼娜相愛,后來夢鷗失業,曼娜卻于此時宣布與闊少柳榮結婚。夢鷗失望之余,與一直深愛他的素秋結成夫妻。婚后雖經濟拮據,夢鷗仍一直接濟失業的喬杰。喬杰不忍心拖累夢鷗,乃留書出走。幾年以后,夢鷗夫婦有了孩子,但無法擺脫貧困。迫于生計,素秋瞞著夢鷗當了柳榮兒子的家庭教師,卻在那里讓兒子傳染了百日咳。一次在送醫院治療之時,偶遇喬杰。原來喬杰出走后參加了“一·二八”抗戰,右腕傷殘,戰爭結束后被遣返,孑然一身,過著流浪生活。夢鷗夫婦因無錢繼續為兒子治病,兒子的病情加劇。影片結尾的時候,大雨滂沱,夢鷗欲哭無淚 ,抱著兒子尸體消失在雨簾中。對以上劇情所表現的貧寒青年生活現狀,余紹宋認為有夸大之嫌。劇中人物的生存讓人感到階層的差別和現實的壓抑,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更關鍵的是,他認為劇情“絕不涉因果報應,徒使惡人益無忌憚,善者一無希望,何以為勸懲耶?”[1](1278)這里體現出余紹宋對電影主題把握上的某種錯位,電影的目標是批判現實,而余紹宋則希望“勸懲”。這種錯位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左翼電影本身訴求的模糊性造成的。左翼電影反映了社會悲慘現狀,卻在進一步揭示社會根源方面顯得無力,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續著舊倫理電影的敘事框架:“從新舊電影形態的承接、發展的角度上說,左翼電影往往直接套用舊市民電影的架構和情節套路……”[9](210-211)在這樣的敘事框架下,社會不公平現象顯現為是由于富人、闊人當道造成的,由此形成“窮人/富人”、“好人/壞人”的二元對立敘事模式,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對余紹宋這樣歷經社會動蕩的士人階層而言,這樣一種表述讓他感到不安。在他看來,既然電影采用“好人/壞人”這樣的二元敘事模式,就必然需要給好人以出路,給壞人以懲罰,這樣才能起到勸懲作用。這反映了余紹宋的文藝觀:強調作品的教化和愉悅功能;舊戲劇、舊倫理電影的俗套情節、低俗趣味自然讓余紹宋不堪忍受,左翼電影拋棄舊電影的才子佳人大團圓模式固然有革新之效,但就此放棄其社會教化功能卻不可取。為此,他認為需要引起重視:“此皆由對舊劇矯枉過正之故,不足取也,此問題關系不細,余別有詳說。”[1](1278)表示將另行撰文詳細評論。
對《生之哀歌》問題的討論是否有機會發表尚不知道,但兩個月之后看電影《鐘聲響了》,他在日記里又說了一番話,似乎可以作為補充。1935年8月8日記:“夜同渭泉赴聯華看電影,劇名《鐘聲響了》,近來新出電影劇本……形容貧富相去情形過火,雖屬時會使然,而其影響卻甚大,負檢查之責者識不及此,可慨也。”[1](1292)這一次的看法更為明確,對于這類激發階級仇恨的電影,他認為其結果只會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社會動蕩。1935年11月3日記:“入聯華觀影劇,劇名《海葬》,仍是描寫漁人生活苦況,一味衰颯,閱之使人煩悶,大約現時流行戲劇皆做到萬分困厄終局,令人不歡而散。”[1](1315-1316)《海葬》的劇情是:漁民大毛、二毛、大山、虎子在海上和風浪搏斗,大山掉入海里死去。第二天,幸存者筋疲力盡地上岸,漁行老板不僅不借錢給他們修船,反而催逼他們再次下海。不幸的是他們的船遇到巨浪漂到了荒島上,大毛死了,奄奄一息的二毛掙扎著回到漁村,瞎爹抱著兒子漸漸冰涼的身體氣絕身亡。虎子得知姐姐被賬房先生霸占,打死賬房先生被送進了監獄。從《生之哀歌》里的走投無路,到《鐘聲響了》里的貧富對立,再到《海葬》的暴力抗爭,左翼電影完成了它的模式構建。“從左翼電影的‘三性’即階級性、暴力性和宣傳性上看,替弱勢群體即農民階級發聲,階級性和宣傳性是沒有問題的,唯一的問題是暴力性。”[9](212)電影是白日夢,但左翼電影恰是要喚醒白日夢。夢醒之后,接下來的路徑是兩條:要么改良,要么暴力。而暴力是對社會的破壞性改造,這是余紹宋這樣的士人階層所擔心的。當初,他告別仕途定居杭州,這樣的選擇本身就含有對國民政府以暴力方式獲取政權的不認同。1927年10月13日,他在離別京津之際的日記中記:“赴任公(梁啟超)處告別,談時事相對唏噓。”[1](633)當電影在余紹宋的生活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并希望在其中享受白日夢的時候,反映悲慘和暴力的左翼電影已成為電影的主流,對此他頗感無奈。
討論余紹宋對左翼電影的觀感,不能不對他當時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做一個分析。余紹宋擔任政府官員的時候,民國北京政府的財政極其困窘,政府常常借債度日,職員們幾個月領不到薪水是常有的事。雖居京為官多年,卻沒有多少積蓄。其所以敢放棄仕途,自食其力,一方面是因為老家尚有部分產業,如家族商業滋福堂藥店,每年能有一點分紅。最主要的還是因為自信其繪畫技能會被認可。實際情況也是如此,當時他的畫在上層社會頗受追捧,如1936年8月3日記:“寫竹四幅,段錫朋、羅家倫、楊振聲、雷震四人所求,寫松竹梅四尺中堂,王世杰、石瑛所求,皆為黃百新之母介壽者。”[1](1375)這些求畫者都是當時的名流顯貴,因而其畫作定價也高。筆者曾訪問余紹宋的長孫、《亭亭寒柯——余紹宋傳》作者余子安,據他介紹,余紹宋當年的畫每平尺的定價是10元。這是一個什么水準?當時的畫家中,除了吳湖帆,數馮超然、吳待秋、余紹宋等的價格高。吳湖帆為什么比他們高?余子安分析,吳湖帆是闊二代,對錢不在乎,一般情況下不肯畫,有人一定要,他便報一個高價。而且,吳湖帆畫工筆畫,費神費時,定價自然也高。余紹宋剛到杭州定居時的經濟狀況怎么樣?當時,他向當地名醫張星一租房子,按杭州慣例,要先交十個月的押金,大約一次性總計交六百元,余紹宋頗為窘迫:“一時安從得此巨款。”[1](770)還好房東慕其名望和為人,將這筆押金免了。僅僅三年后,余紹宋就憑賣畫收入,在杭州西湖邊蓋了房子。作為一個有恒產、自食其力的退隱士人,自然期望社會穩定,安居樂業。
于是,當電影反映的沖突出現在他的現實生活中,他有時表現出頗為中庸的態度。如1927年5月6日所記:“知衢州各店伙有罷工索加薪之舉,是兩敗之道也,可勝慨哉。”[1](603)顯然,他不贊成以激烈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但中庸并不代表他不希望改變現實,也不代表他在現實沖突面前的真實立場。余紹宋一方面在日記中對部分電影的左翼傾向表示反感,實際生活中,卻更多地站在弱勢者一方,尤其在勞資雙方沖突中,他總是支持勞工一方,對資方持批判態度,其立場竟和左翼電影相一致。如1935年9月中旬,因天氣轉冷,家鄉龍游的農民急需去典當行贖回棉衣過冬,“而龍游銀行因接辦問題未決不能復開,是將坐視鄉民之受寒矣,此皆上海銀行之罪惡……”[1](1300)他介入此事之后,招來銀行方面的嫉恨,但畢竟使問題得到了解決。1935年9月28日的日記里又提到,一位鄉民來向他反映,被民生銻業公司欺壓,而銀行又“助其肆虐”,余紹宋為此非常憤慨:“是又一受資本家之壓迫者。甚矣,今日資本家之可畏也。”[1](1302)更為典型的是,抗戰期間,余紹宋為免漢奸糾纏利用,蟄居家鄉浙江龍游溪口鄉間。此地傳統手工造紙業發達,紙業工人與紙商間利害沖突時有發生。余紹宋憑借其資歷與聲望,著力主張組建紙業合作社,以維護紙業工人利益。余紹宋此舉遭致諸多紙商抵制,1940年8月3日記:“有上海紙商蔣某者,求朱守梅(地方官員)向彼許其包營紙類,年可納捐十數萬。”余紹宋當即要求主管官員拒絕這一做法,認為“蓋此類奸商專以刻剝生產者以自肥者也,惡予提倡紙業合作,故有此舉,而主動者即溪口諸紙商,故不能不反對也。”[1](1595)現實生活中,作為鄉紳身份的余紹宋成為產業工人的代言者,站在了資本家的對立面上,其影院觀感和現實言行竟呈現相當大程度的背離。這非常典型地體現了當時士人階層在社會沖突面前的分裂心態和立場,同時,也折射出左翼電影對階級分析法的運用過于單一化。
作為社會轉型期的士人,“在余紹宋身上,交織了傳統士人‘天下己任’的抱負和近代知識分子的‘國民主體’意識。”[10]這體現了傳統士人一個非常可貴的現代性轉型。余紹宋雖然退隱后絕意仕途,但他有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這個理想就是鄉村自治。早在1917年初,他參與審議北洋政府《地方自治章程》時,在日記中提到這樣一件事:當時北京涿縣有一處插花地,在宛平城范圍內,兩縣都不管,“于是該處一切行政司法概由該處人民公舉之人處理,所舉之人名為山坡老人,每年納賦一次……謂為我國自治之模范。”對這樣“桃花源”式的社會治理,余紹宋稱:“殊令我想望不置也。”[1](5)這大約也是后來他在家鄉竭力主張組建產業合作社的初衷。
四、余論
余紹宋在左翼電影面前的分裂性觀感,或許也和他所代表的這個階層在電影中的形象缺席有關。舊上海電影是市民文化、好萊塢商業文化和左翼觀念的混雜體,獨缺中西方精英文化之影響。傳統士人階層在電影中的形象或缺席,或扭曲,像余紹宋這樣帶有現代改良主義色彩的士紳形象差不多完全被忽略。可以想象,在那個革命呼聲日益高漲的年代,這樣的社會理想是無法被人接受的。當年蔡楚生的優秀電影《漁光曲》播出后,也招致激進批評家的批評,因為其中的主角何子英是“改良主義的人物”,于是有人批評“作者正想搖身一變而如何子英,以他的立場解救大眾的倒懸。”[11]但蔡楚生隨即聲明這絕非他的本意。于是,作為觀眾的余紹宋,他的社會理想在電影銀幕上始終無從響應,因而難免為之失落和不滿足。倒是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在邵氏武俠電影中,士人氣質得以復活,但那已成為一種想象和追思,和歷史上真實的士人形象難以契合。
左翼電影一律以階級對立的觀念來解釋人物命運,構建了階級對立、階級壓迫這樣的電影語境,對觀影人群的身份、社會坐標起到提示、喚醒作用。這種二元對立的表述語態,無疑強化了電影的工具作用,在特定時代發揮著特殊功用。有論者指出:“民國電影具有強烈的人文意識與人文關懷,對底層民眾的悲歡離合有真切的體認與表達,但缺乏較為宏觀的文化視野與思維高度,在文化價值觀上失之于瑣碎。”[12]可惜任何創作都無法超越于它的時代。還有論者認為,左翼電影“替弱勢群體、尤其是弱勢中的弱勢——失去土地和家園的農民、淪為城市底層的農民工和進城賣身為生的女性性工作者張目、發聲。”[9](213)這一點甚至和當代第六代導演的電影特征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30年代中前期的高票房電影基本上是左翼電影,而今天的第六代賈樟柯、王小帥大多已趨于小眾化。這是時代特性所決定的:那是一個大眾喚醒、士人沒落的時代。中國的士人階層,向來有如《賣炭翁》《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作品所表達的濃重的底層關懷情結,但革命浪潮襲來,他們往往被自己的同情者視為革命的對象,找不到自己的歸屬,從而成為一個被撕裂的階層,并在這種撕裂中逐漸走向消亡,傳統士人的現代性轉型由此難以為繼。
參考文獻:
[1]余紹宋.余紹宋日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2:519.
[2]張濤.何處是吾鄉——梁各莊會葬圖中的文士與畫家[J].藝術史研究,2014(3).
[3]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M].北京:三聯書店,2008:3.
[4]張耀杰.北大教授與<新青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172.
[5]周子樂.<晨報>中的真光電影院與北京早期電影放映[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3(3).
[6]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55.
[7]袁慶豐.舊市民電影:1930年代初期行將沒落的中國主流電影特征[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5).
[8]何衛國.早期紅樓電影與海派文化[J].現代傳播,2014(4).
[9]袁慶豐.1930年代中國左翼電影及其當下意義[J].學術界,2015(6):210-211.
[10]毛建波.余紹宋:畫學及書畫實踐研究[M].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34.
[11]蔡楚生.給漁光曲的觀眾們[J].影迷周報.1934(1).
[12]李棟寧.民國電影的現實主義美學批判[J].藝術百家,2015(4).
〔責任編輯:高辛凡〕
作者簡介:徐洲赤,男,副教授,碩士。(浙江傳媒學院實驗電視臺,浙江杭州,310018)
中圖分類號:J9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552(2016)03-0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