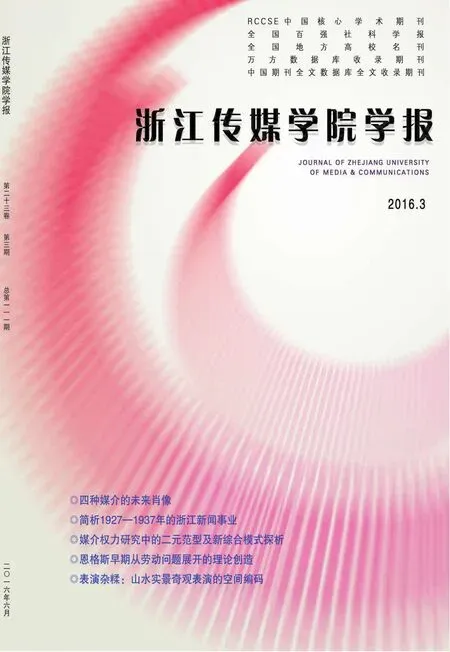《中國好聲音》:全球模式節目重構中的國家想象和本土現代性
戴穎潔 章 宏
?
《中國好聲音》:全球模式節目重構中的國家想象和本土現代性
戴穎潔章宏
摘要:文章以內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為主,深度訪談為輔,發現《中國好聲音》依賴靈活、多樣的敘事手法和置入策略對引進節目模式進行改編,在傳播流行文化的同時,契合政黨意識形態,建構國家共同體的想象,發展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本土現代性,實現了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雙贏。
關鍵詞:中國好聲音;模式節目重構;想象共同體;本土現代性
章宏,副教授,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一、引言
跨國電視節目模式交易始于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末,節目模式產業相對成熟,涌現出不少風靡全球的節目模式。和成品節目相比,節目模式允許填充開放性的文本,讓制片人可以根據當地受眾的文化口味、情感以及期待對節目作出本土化改編。[1]因此,有學者認為,引進模板不失為發展中國家節目本土化的一種形式。[2]正因為如此,近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積極引進成熟的節目模板來制作反映本土文化的節目。
《中國好聲音》是荷蘭著名廣播電視音樂節目《荷蘭好聲音》(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國版,由星空傳媒旗下的燦星制作公司以350萬三季的價格從版權代理公司IPCN手中購買,聯合浙江衛視所強力打造的大型勵志專業音樂評論節目,迄今已完成四季。《中國好聲音》可謂是引進模式本土改編的成功典范,自2012年7月13日第一季開播后,收視率節節攀升,就連一直對選秀節目進行管控的國家廣電總局,也公開對其進行表揚,認為該節目做到了關照現實和注重品質。[3]那么《中國好聲音》為何能實現市場和政治的雙贏呢?已有的研究多從模式創新、生產機制、品牌建構等方面探討中國版《好聲音》獲得市場成功的原因,[4][5][6][7]對《好聲音》等引進模式節目進行文化改編來迎合本土受眾需求少有涉及。[8]從電視文本呈現角度探討電視節目模板本土改編中如何將市場需求和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調和在一起的研究則更加有限。[9]
本文擬以《中國好聲音》這一模式本土化的成功典范為例,探討節目中如何運用“并置策略”,對外來節目模式進行本土重構,在內容呈現上既符合受眾娛樂的需求,又順應主流意識形態,從而建構國家共同體想象和本土現代性。
二、主要理論和研究方法
(一)理論闡釋
1.想象的共同體
安德森(Anderson)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想象共同體”的概念。他認為,國家經常是被想象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甚至聽說過他們,但是,在他們心中,都存在這么一個共同體的形象。[10]大眾傳播媒介在傳遞主流意識形態,建構“想象認同體”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安德森提到了書本和報刊等印刷傳播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10](15-16)其他研究者則進一步指出了電子媒介特別是電視的作用。[11][12]莫利 (Morley)認為,電視媒體通過聲音和圖像等聽覺和視覺符碼,連接家庭、國家和國際,維持國家家庭(National Family)等各種共同體的形象和現實。[13]貝爾(Bell)的研究指出,電視媒體塑造的國家認同弱化了國家內部民族間的差異,給人們帶來了國家內部同質化和平等的印象。[14]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了傳統意義上個體對國家故土一以貫之的穩定的依附性,也加速了由于社會斷裂、人際疏離,社會階層和利益分化所帶來的社會離心過程。因此,全球化時代下國家這一“想象共同體”的產生與維系,比以往任何時期呈現出更復雜的態勢。一些研究指出,當前媒介產業通過隱藏權力中心以及階級不平等的普遍性,強調注入年齡、性別、民族等其他形式的社會分類,對現實生活進行象征性模擬,并且依賴各種政治語言,創造各種國族神話和發明各種文化傳統,來凝聚人民的支持與情感。[8]15]有學者認為,在當今全球化和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一方面,民族主義敘事始終是中國大眾媒介的主旋律,另一方面,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跨國進程也是中國媒介構筑國家想象的重要方面。[12](16)馮應謙和張瀟瀟(2011)的研究發現,中國版《丑女貝蒂》(《丑女無敵》)的改編,既維護了傳統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又為受眾帶來了某些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和西方的價值觀,創造了雜糅化的國家想象。[9](265-276)
2.本土現代性
長期以來,伴隨著西方的崛起和殖民政策的實施,人們習慣于將“現代性”視為西方的產物,[16]將現代性等同于“西方現代性”或者“美國現代性” ,認為西方現代性具有現代性的典范地位,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改變貧困落后的生存狀態,實現從傳統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化國家的轉變。摩爾(Moore)認為,現代化就是對傳統的、現代化前的一個社會進行徹底的改造,將其改造成為一個西方世界所倡導的以技術和其相關社會組織為特征的社會形態。[17]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提出的“傳播與現代性”理論更是認為大眾媒介由于可以改變人們的態度和價值觀,對于西方現代性在發展中國家的擴散有促進作用。[18]但是,這種由西方定義的以理性、資本主義、工業化、世俗化和個人主義為特征的現代性及其傳播效果存在爭議。不少學者認為國際技術流的轉移以及伴隨著文化產品流動所帶來的媒介硬件的流動,實際上是加深了發展中國家的依賴性,阻止了其自我發展的道路。[18](95)許多批評家進一步指出,在“傳播與現代性” 理論提出的20年后,世界上的大多數地區似乎并沒有進入起飛階段,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日益加大。現代性的發展與發展中國家根本的社會結構有關,將西方現代性強加于發展中國家,無疑是忽略了全球化時代結構性不平等和當地民眾參與對促進后發國家之發展的意義。[17](42)
那么,是否存在一種可以讓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有關現代性的價值觀和信仰?羅杰斯1976年提出,現代化應當是一個多維的概念,并不能等同于歐洲化或西方化,不應當暗含某種價值判斷的成分。[19]因此,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模式并不是發展的唯一模式,每個國家都有選擇自己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事實上,在全球現代化的今日,世界各國,尤其是非西方國家自有尋求其現代性的必要性與責任,當今世界應當是“多元的現代性”。比如日本成功地從一個不發達的封閉國家轉化為一個舉世矚目的全球經濟巨人并保留了相當多的傳統方式。[17](49)因此,現代化的發展不僅僅是對西方框架的模仿,而是一種主動的,自我選擇的道路,根植于第三世界國家自有的文化傳統上。有學者將全球化浪潮中印度報業的興起定義為一種不同于西方的“本土現代性”,是長久以來印度報業對現代西方報業體系的批判性采納,以適應本土文化和受眾的需要。[20]對中國版的《丑女貝蒂》的文本研究,更是發現該劇在改編西方模板過程中,將中國的社會現實和文化與某些西方元素雜糅在一起,既相容于主流意識形態,又贏得民眾的合意,體現獨特的本土現代性。[9](274)可見,“本土現代性”不同于西方力量所主導的“西方現代性”,在推動原因和結局上都強調本土的作用,根植于本土社會結構和文化需要。
3.并置策略
“并置”是一種將社會主旋律和商業模式表現手法的精髓聯結在一起的方式。它已經被證實為可以讓商業節目制作人在達到政治要求的同時實現經濟效益的一種有效方式。[21]并置策略最早在電影、電視劇制作中運用,一系列塑造英雄、中共黨員、警察和軍人等正面形象的影視節目,就屬于運用商業模式反映主流意識形態的作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綜藝節目制作人也開始嘗試使用并置策略,順應主管部門對于綜藝節目領域的管控需要。并置策略的廣泛采納,跟中國電視產業的發展環境息息相關。李金銓指出,國家意識形態影響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呈現弱化趨勢:一方面,絕對的意識形態宣傳內容在減少,其他類型的文化節目變得更加豐富;另一方面,電視的政治工具意識在弱化,伴隨而來的是推動經濟現代化建設的意識在加強。[21](34)但是,全球化浪潮以及市場化的改革并不必然導致政府朝向自由主義模式的管理體制發展。實際上,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的媒介管理體制在政策目標、管理機構和管理手段上不斷變化,但政府依舊是媒介的所有人和主體。以模式產業在中國的發展為例,電視從業者一方面希望通過模式本土化進程來扶持和發展本土電視產業,另一方面也時刻警惕模式節目中所夾帶的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問題,強化對模式節目的管理,通過本土改編以及運用“并置策略”,將特殊的敘事策略巧妙地鑲嵌到商業化內容中去,以實現節目高收視率的同時保持政治導向的正確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本分析和內容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對三季《中國好聲音》的文本呈現進行分析,并對210名學員的性別、民族、年齡、來源地和職業等進行統計,探討節目中如何運用“并置策略”,對引進的節目模式進行本土重構,在滿足受眾收視需求的同時,傳播主流意識形態,從而構建出國家想象和中國的“本土現代性”。此外,本研究還對上海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節目模式研發部負責人徐帆進行深度訪問,了解《中國好聲音》生產、制作過程中的故事和策略性選擇。
三、研究發現
(一)從文本構成看 “想象共同體”
1.《中國好聲音》學員的性別比例情況
第一季“好聲音”共有學員66名,其中男性學員32名(占48.48%),女性學員34名(占51.52%);第二季共有學員60名,其中男性學員35名(占58.33%),女性學員25名(占41.67%);第三季共有學員84名,其中男性學員50名(占59.52%),女性學員34名(占40.68%),可見,《好聲音》節目中的男女比例符合我國男女大致均衡,男性稍多的總體人口現狀。
2. 《中國好聲音》學員的年齡分布情況
第一季學員中“90后”學員8名(占12.12%),“80后”學員48名(占72.73%),“70后”學員9名(占13.64%),“60后”學員1名(占1.52%);第二季中“90后”學員15名(占25%),“80后”學員36名(占60%),“70后”學員7名(占11.7%),“60后”學員1名(占1.7%);第三季學員中“90后”33名(占39.29%),“80后”37名(占44.48%),“70后”10名(占11.90%)。三季節目均兼顧了中國社會主要年齡段,并且“80后”學員比例不斷下降,“90后”學員比例大幅上升,60后和70后相對穩定。學員的年齡分布和變化符合中國社會當下“90后”成為社會新興的主力群體的整體趨勢。
正如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長江學者胡智鋒所說,年輕人是給予電視產業最多消費投入的一個群體,因此必須占領年輕人這個群體,才能夠引領時尚風潮,卷起娛樂旋風,撬動產業杠桿。[22]因此,對衛視頻道來說,年輕化、時尚化“已經成為做節目的一個法則”,得年輕人者得天下,儼然轉化為當下電視圈的一種共識。
3.《中國好聲音》學員的民族構成情況
第一季《中國好聲音》學員中除了漢族外,其他學員分別有阿美族、哈尼族、朝鮮族、回族、滿族、蒙古族、苗族和彝族等。第二季學員包括漢族、朝鮮族、哈薩克族、羌族、滿族和臺灣排灣族。第三季學員的民族構成為漢族、白族、佤族、維吾爾族、彝族和壯族。《好聲音》學員的民族構成比例符合我國以漢族為主體,少數民族為輔的現實情況,勾勒出一幅“民族大家庭”齊聚一堂的歡樂景象。
中國是擁有56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為了增進不同民族間的相互了解和聯結,節目置入了大量具有沖擊力的民族文化符號(服飾、語言、風俗等)。第一季《好聲音》學員,哈尼族的小伙子李維真身穿民族服飾參賽,介紹了該族人慶祝王子誕生普天同慶的民族儀式,并在流行唱法中加入了當地原生態的元素。來自四川大涼山的吉克雋逸非常鐘愛自己彝族女兒的身份,在舞臺上始終以民族服裝和首飾示人,民族性非常突出。第二季《好聲音》學員塔斯肯來自新疆的哈薩克族,是北漂多年的游子,他借哈薩克族的民歌表達自己的思鄉之情,表明新疆是自己的根,教育兒子從小學習哈薩克語,不忘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血液里流淌的故鄉情。第三季《好聲音》學員帕爾哈提是新疆的維吾爾族歌手,他將豐富的維吾爾民族元素融入到音樂創作中,將搖滾樂、民族樂、流行音樂融合在一起,展現出現代與本土相結合的音樂作品。美籍華裔秦宇子,老家是廣西南寧,身上流淌著壯族的血液,當她被問到為何不參加《美國好聲音》(The Voice of America) 時,她再次提到了根在這里,很自豪自己是壯族人。她用壯族語言歌頌家鄉美,希望家鄉人民能聽到她的歌聲。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節目模式研發部負責人徐帆提到,豐富節目的學員構成,納入更多少數民族學員,其實是一種共贏的策略。因為少數民族學員本身就能歌善舞,容易提升節目的專業水平和歌曲質量;與此同時,民族性的策略還有充分順應主流意識形態需要的考量。比如最新一季《中國好聲音》中加大了新疆學員的比重,這就跟習總書記2014年度在新疆工作會議上對新疆問題的重視有一定關系。*筆者對徐帆的訪談,上海,2015-4-22。另外,文本研究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發現,就是每一年的《好聲音》總決賽都安排在“國慶節”這一舉國同慶的日子進行,并且每一季《好聲音》最后的四強名單中,必定會有一名學員來自少數民族:第一季吉克雋逸(彝族),第二季金潤吉(朝鮮族),第三季帕爾哈提(維吾爾族)。由此可見,《好聲音》通過民族元素的成功置入,營造了華夏兒女共享的時間和空間體驗,不僅喚醒了共同的記憶,還喚醒了相遇的體驗及團結之情。這種個體對民族認同和歸屬感的情感體驗,最終全部被統攝到“中國”這一共同體的字眼下,終極目標是為了喚醒觀眾對“中華民族”這一共同體的想象和認同。
4.《中國好聲音》學員的地域分布情況
第一季學員涵蓋了臺灣地區和美籍華人,以及分布在祖國18個省級行政區的學員;第二季學員涵蓋了臺灣地區和加拿大籍華裔,以及分布在祖國22個省級行政區的學員;第三季學員涵蓋了臺灣地區和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以及分布在祖國26個省級行政區的學員。地域分布的廣泛性促使《好聲音》將個體的“你、我、他”都聚合到一個共同的“我們”概念下,正如其官方宣傳片所說,“這是一場關于信仰的聲音的戰役,這是每一年夏天和13億中國人心靈的約定”。與此同時,海外僑胞的參與,也讓《好聲音》成為了聯結全世界華人的情感紐帶,這種情感表達在港澳臺和華裔學員的身上更加凸顯。第一季學員張玉霞來自臺灣,在導師搶人環節,楊坤特地提到了會為她寫首穿越海峽的歌,點燃了海峽兩岸情結。第三季學員陳永馨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華裔,她說中國是自己的根,希望借《好聲音》這個舞臺,讓全家人得以在中國團聚,并找尋失聯多年的親戚。一句“踩著陌生而熟悉的土地,走一走爺爺當年走過的路”,散發著海外華人思鄉和渴望團圓之情,以血緣情感為紐帶,建構出天下華人同心的深厚情感和想象。
5.《中國好聲音》歌曲中的“集體性格”
《中國好聲音》總導演金磊認為,音樂是最有力量的文化表達和傳播的形式,[23]因此,弘揚本土音樂和傳統藝術形式應當成為《好聲音》節目模板本土化的立意之本。筆者對三季《好聲音》中的參賽歌曲進行了統計,發現每一季學員的參賽歌曲中,華語音樂比例都占多數:第一季177首曲目中,港臺和大陸歌曲占82.49%;第二季166首曲目中,港臺和大陸歌曲占78.92%;第三季195首曲目中,港臺和大陸歌曲所占比例高達88.21%。第三季《好聲音》曲目“回歸經典”的定位,正是金磊團隊的創意,他希望“用經典去尋找中國人的集體性格”。[24]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實現本土音樂的對外傳播,節目組也會鼓勵學員用改編經典、元素混搭的方式來演繹歌曲,將中華文化元素與現代技術手段相結合,將中國的民族音樂通過世界化的呈現手段傳播出去。在融合與碰撞中傳承民族精神命脈、回應時代精神訴求,從而在國際文化競爭中走出了一條立足本土的文化之路。
(二)“真實娛樂”折射“想象共同體”
“真實娛樂”是指綜藝節目在不影響真實性的基礎上,通過藝術化的表現手法,觸及社會熱點,觸及民生,觸及心靈;實質是用娛樂外衣傳遞人文內核,做好“人性的搬運工”以及“正能量的傳遞者”。這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5年出臺的“限真令”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限真令”要求真人秀節目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講好中國故事,展示中國形象,正確處理好“真”和“秀”之間的關系。因此,關注社會眾生態、關注普通人所思所想,成為綜藝節目制作尤其是真人秀節目創意的主要來源。韓國綜藝節目之所以大受歡迎,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節目內容兼具人文關懷與社會觀照。韓國MBC電視臺著名制作人金榮希將報紙作為綜藝模式創意靈感的重要來源之一,每天早上會仔細閱讀多份報紙,了解社會上發生了什么事,韓國人對哪些東西感興趣等等。正是這種對社會的敏銳觀察力和思考,讓韓國綜藝節目在娛樂性的同時充分彰顯著社會意義的文化內核。反觀國內綜藝節目,但凡成為現象級的,同樣也是成功做到了嫁接歷史記憶與人性關懷。電視生產者憑借著媒體人特有的職業敏感性,聚焦本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走向,讓外來節目模式更接地氣,更符合國內受眾的需求,體現了電視人應有的情懷與文化擔當。
作為第一梯隊的社會化制作公司,燦星一直將“真實娛樂”作為節目的制作理念。據公司節目研發總監徐帆介紹:“燦星實質是新聞系的魔方,公司核心層骨干大多來自復旦新聞系或者相關院系專業。這些受到傳統新聞學教育的新聞人,致力于將新聞夢想和綜藝夢想相結合,在節目制作中強調新聞文化,新聞理念,新聞人的社會擔當、人文情懷以及對社會的理解。他們始終認為,模式節目所需要的生產技術是很容易被復制的,無法復制的是節目所傳達的價值觀。”因此,為了讓節目內容觸及當下國計民生,自下而上、潤物細無聲地傳遞社會主流價值觀,導演團隊非常注重對社會熱點和話題的把握,將讀報讀新聞作為每日的必備任務,力求在有限的節目單元內盡可能地滿足觀眾的娛樂體驗、情感需求、人生投射等諸多訴求。
《中國好聲音》就是以這樣一種特殊的鏡像方式關照現實,提供了人們投射自身,閱讀夢想的空間。節目導演組專門設置了“故事導演”,負責對學員的故事進行梳理、篩選和呈現,從而提煉每個聲音背后生命個體的情感和情懷。《好聲音》總導演金磊認為,《好聲音》團隊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必須在短時間內塑造出一個鮮活的人,并且精確判定他的歌聲、夢想以及情感最終將引向什么方向,表達什么共鳴。[23]因此導演組需要不斷地與學員交流,了解其個人境遇的方方面面,然后在確保不編造、不篡改事實的前提下,將個人最閃光的部分進行放大。有時故事導演還會幫助學員確定歌單,結合他們的人生經歷,選擇那些能打動他們自己,同時也能感染別人的歌曲。比如參賽歌手平安的《我愛你中國》就是導演組考慮到其是知青子女而專門為他選的歌曲,不僅成功地幫助平安塑造了形象和個體辨識度,而且還引發了中國廣大知青群體的集體記憶。可見,“好聲音”舞臺通過強調學員的代表性和故事性來濃縮當今社會現實,使每位“好聲音”的觀眾幾乎都能在舞臺上找到屬于自己的影子。在聆聽他人的故事的同時,為觀眾提供了各種文化想象的空間:一方面,它生產了社會參與和公平公正的社會意象。無論是《好聲音》的官方宣傳片,還是各類媒體宣傳報道,都一再地強調“聲音是節目唯一的評判標準”,學員不論出身和樣貌都可以參與到節目中來,導師會竭盡所能幫助所有有夢想的音樂人,學員們便由此獲得了一種暫時擺脫經濟屈從地位的瞬間自由。另一方面,從欲望滿足來看,正如好聲音總導演金磊所言,它從社會階層的豐富性出發,放大了“底層奮斗”的故事,[25]提供了諸如成名和物質生活改變的想象。通過對底層群體真實處境的描繪以及他們通過追逐夢想等勵志方式實現逆襲,喚起了觀眾對美好生活的信念,寓意當今社會底層向上層的流動是可能的,機會是普遍存在的,從而給予了觀眾在要求獲得公平的社會資源分配方面的“象征性承諾”。[8](93)
(三)混雜:中國的“本土現代性”構建
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或轉化過程,從來就不是文化中立的,各個民族文化與西方啟蒙價值的碰撞是無可避免的。有的民族文化,會因宗教問題強烈地排斥西方價值;有的民族文化則自愿或不自愿地、自主或不自主地對西方文化和價值或多或少地接受并作出調試。[26]因此,現代性的構建過程是全球與本土互動的雜合過程,文化是無法缺位的,關鍵是本土文化在文化轉型中的自主性程度。印度報業的發展思路就是通過依賴西方技術和經驗,依附本土文化資源和價值觀,依據本土受眾需要來發展本地報紙,從而創造了混雜的現代性內容,使之在高度競爭的媒介環境中維持競爭優勢。[2O](915-916)由此可見,“本土現代性”的優勢在于,既對本土文化和價值觀非常敏感,同時又能將全球現代性以本土化形式進行生產,從而呈現出一種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本國文化不斷碰撞、協商的文化雜合(Hybridity)形態。
中國的本土現代性雖然深受西方模式影響,但不再是西方模式的簡單復制,它同時聯結了全球和本土的知識,期間往往經歷了多種文化不斷沖突、競爭、協調,最終形成雜糅的平衡狀態。《中國好聲音》作為全球模式的本土版,其成功的秘訣在節目制作方燦星公司總裁田明看來,莫過于在制作技術和傳播規律上學習西方,但是在精神內涵上卻強調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情感,實際上就是用國際一流的傳播手段去傳播當下社會的“中國夢”和“中國力量”。[5](44)這顯然是一種商業資本主義和國家權力機構、本土受眾需要相契合的產物,形塑了一種獨屬于中國的“本土現代性”。
一方面,生產技術和制作理念上的西方化。《中國好聲音》的成功建立在巨人肩膀上,而這巨人就是誕生于2010年的《荷蘭好聲音》。該節目在荷蘭RTL4電視臺播出后,就立即吸引了18.2%(300萬)的電視觀眾。隨后,該模式被迅速銷往世界各地,第一季《中國好聲音》開播時,《好聲音》就已經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取得了收視冠軍,成為全球熱銷的模式節目。因此,《中國好聲音》獲得的贊譽,是全球文化工業產品的勝利,它從多個版本Voice中汲取亮點(比如,舞美設計綜合英、美版本,地臺采用英國版,背景采用美國版等),[3](32-33)表明我國電視產業已經躋身于全球文化產業的浪潮中,并利用全球化優勢,結合自身需要為本土化服務。因此,在中國電視主管部門看來,全球模式節目不再是危險的、充滿爭議的,還有可能將其作為培育本土電視市場現代化發展的工具。[9](274)模式作為一整套生產標準,如同麥當勞的加盟指南一樣,往往有著非常詳細的關于節目樣式的規定和生產管理的方法。因此,外購版權節目不僅要學習節目模式與創意,更重要的是學習深層次的創作理念和制作方式。《好聲音》寶典中就詳細規定了節目宗旨,操作流程,錄制時間表,工作計劃,選手招募方式,樂隊、觀眾的位置,各種 LOGO的顏色、大小,現場的攝影機、燈位示意圖等諸多細節。版權方還提供了飛行制片人提供模式咨詢服務,并在前幾期的節目錄制中提供現場指導。《中國好聲音》制作團隊坦言,通過購買模式,他們一方面充分學習了西方模式中的專業分工和崗位職權意識;另一方面,與西方版權方、制作方、節目、模式的多年接觸,也反向激發起了團隊主創的本土意識和中國情懷。[7](23)
另一方面,價值觀和文化情懷的本土化。與成品節目相比,模式提供的是一個開放的文本,允許在框架中填入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具體人物情境乃至文化理念。相較于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現代性,《中國好聲音》在全球模式化的框架下,巧妙地嵌入了社會學家伯格所說的“非個人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現代性”,即一種崇尚集體團結和紀律的新形態的現代性。[27]美國的廣播電視體制是典型的私營體制,只接受法律監督,不受行政干預,因此美國版《好聲音》的制作理念和手法一切以獲取商業利益為目的。舞臺燈光冷艷,剪輯節奏較快,儀式感濃重,不斷設置懸念和興奮點,營造一種直逼人心的緊張效果;整個節目突出比賽的競技和輸贏,節目鏡頭更多地是集中展現獲勝一方的狂喜表現,失利者往往得不到導師與在場觀眾的安慰,個人主義價值觀頃刻畢現。《中國好聲音》則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不忘傳遞親情、友情、愛情等真善美的傳統道德觀念,這些不僅是主導文化的內核所在,也是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節目組在拍攝學員上場前的外景時,都基本要求學員帶家屬出鏡,也會有對家屬的單獨采訪。外場親友的陪伴和鼓勵,再加上“小二班”、“夢想班”、“阿妹′s Family”(阿妹的大家庭)、“楊家將”等充滿溫情的導師戰隊,充分展現了中國典型的“家”文化和集體主義價值觀。與此同時,《中國好聲音》還拋棄了原版節目中消費主義、娛樂至上等不符合我國主流文化的因素,以“勵志”為主題,走群眾路線,展示普通民眾的歌聲、夢想與情感,用普通人的經歷去感動普通人,傳遞出溫暖人心的正能量。
四、結語
模式節目的全球擴散不僅僅是文化全球化的過程,同時也是現代性全球化和混雜化的過程。在中國,全球電視節目模式本土化彰顯了想象與現實、全球文化形式和本土文化特性之間的雜糅。[9](265-276)這種混雜一方面是基于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同時也是基于中國文化傳統和受眾消費習慣所做的調試。《中國好聲音》作為全球模式《好聲音》的本土版,在節目生產技術和制作理念方面,深刻研習節目模式寶典,將西方的電視制作經驗以及商業主義模式框架服務于本土電視產業發展。同時,在內容呈現方面,又巧妙運用“并置策略”,在確保商業利益的前提下,服務于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
當今中國電視產業陷入政治與市場的境遇中,努力探索著在政治宣傳和娛樂功能之間取得平衡的方式方法。并置策略作為一個靈活和多樣的敘事策略,日益深受電視產業從業者的青睞。通過改變以往硬性的政治說教內容,電視產業從業者巧妙地將主流意識形態整合進娛樂節目中,實現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雙贏。《中國好聲音》就是成功的范例,它將娛樂、商業色彩與主流意識形態達成一種共謀,依靠“想象共同體”的構建來映射國家影像,并且依托個體對夢想的追逐喚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信念,創造了一種回應社會真實需要的神話。除此之外,《中國好聲音》還不忘在節目中植入血緣親情、故土鄉情、民族感情等主流價值觀,通過依托商業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建構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本土現代性”。可見,中國的“本土現代性”吸收了西方現代性的成分,同時又根植于本土文化和價值觀,將全球現代性以本土化形式進行生產。因此,“本土化”并非是個封閉的、停滯的概念,而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發展不斷發展,在變化中有傳承,傳承中又有變化的雜合化的過程,中國的“本土現代性”必然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掛鉤接榫的歷史運動。
參考文獻:
[1]章宏.全球化語境下的電視研究變遷[J]. 南京社會科學,2014(6):120-126.
[2]Straubhaar J.World Television[M].London: Sage,2007:154.
[3]馬中紅. 全球文化工業產品的復制與創新——評《中國好聲音》[J].中國廣告,2012(12):32-33.
[4]祝潔.《中國好聲音》帶給電視市場的若干啟示[J]. 聲屏世界,2013(4): 70-71.
[5]肖輝馨. 邏輯推理與經驗選擇:探析《中國好聲音》[J]. 現代視聽,2012(9):42-45.
[6]石拓. 中國好聲音節目創新研究[J].電視研究,2013(3):70-71.
[7]徐帆. 創意和聲音:復盤中國好生意[J]. 中國廣告,2012(12):22-24.
[8]佘文斌. 本土語境下電視節目模式的文化改編[J]. 現代傳播,2014(11):91-95.
[9]Fung A,Zhang ·X·X. The Chinese Ugly Betty: TV cloning and local modernity[J].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2011,14(3):265-276.
[10]Anderson ·B.Imaginedcommunities[M]. London:Verso,2013.
[11]Price ·M ·E. Televisi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National Identity[M].Oxford: Clarendon,1995.
[12]陸曄. 媒介使用、社會凝聚力和國家認同——理論關系的經驗檢視[J]. 新聞大學,2010(2):14-22.
[13]Morely ,David.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1992.
[14]Bell, Cludia. Inventing New Zealand: Everyday Myths of Pakha Identity[M]. Auckland: Penguin Books,1996.
[15]Bruin ,Joost D. NZ Idol: Nation Buiding through Format Adaptation, in Oren · T, Sharon· S. (eds),Globaltelevisionformats:Understandingtelevisionacrossborders[M]. London: Routledge, 2011.
[16]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Cambridge: Polity,1990.
[17]科林·斯巴克斯. 全球化、社會發展與大眾媒體[M]. 劉舸,常怡如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18]Sreberny-Mohammadi·A.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 Curran·J , Gurevitch·M (eds.).MassMediaandSociety[M]. New York: Rutledge,2001:93-119.
[19]Rogers· E.Communicationanddevelopment:thepassingofthedominantparadigm,inRogers·E,ed.CommunicationandDevelopmentCriticalPerspectives[M]. London: Sage, 1976:121-48.
[20]Neyazi·T·A. Cultural imperialism or vernacular modernity? Hindi newspapers in a globalizing India[J].Media,Culture&Society,2010,32(6): 907-924.
[21]徐明華. 全球化與中國電視文化安全[M]. 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
[22]林沛.“年輕化”成四大衛視2016年共同訴求[EB/OL].http://www.zongyijia.com/News/News_info?id=47409, 2015-12-22.
[23]騰訊娛樂.文藝圈的牛人之導演金磊:綜藝進入大片時代[EB/OL]. http://ent.qq.com/a/20121231/000350_1.htm,2012-12-31.
[24]李璇. 年度制作人金磊:對節目的每一秒負責[EB/OL].http://www.law-tv.cn/a/yantaoyupeixun/20150326/3928.html,2015-3-19.
[25]傳媒+公眾號. 金磊:《好聲音4》的兩個變化和一大堅持[EB/OL].http://www.vchale.com/ContentChina/207998496_1_1511d1df9860ab95 dd1f5808bc6b6a68.html,2015-6-14.
[26]沈洪. 尋求中國的“現代性”[EB/OL]. http://www.inBZm.com/content/82519,2012-11-2.
[27]菲斯克. 電視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責任編輯:詹小路〕
基金項目: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重點課題“沖突與共謀:全球模式節目本土化生產的權力博弈(2015Z012)”,浙江省文化廳2014—2015年度廳級文化科研項目“全球電視節目模式本土化路徑和策略研究(2015019)”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戴穎潔,講師,新聞傳播學博士。(浙江傳媒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中圖分類號:G2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552(2016)03-00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