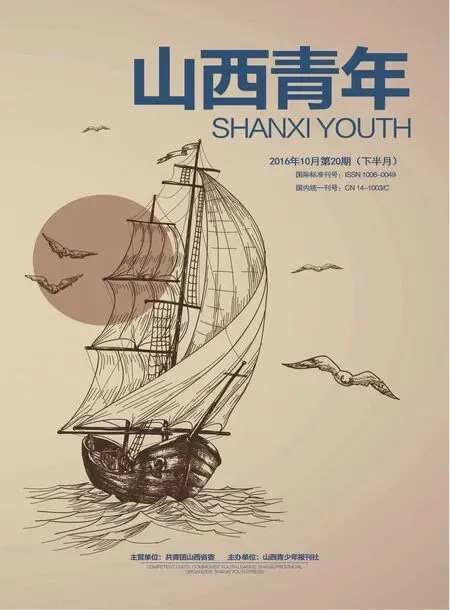寧波失地農民城市融合困境分析*
沈耿炎 殷 威
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
寧波失地農民城市融合困境分析*
沈耿炎**殷威*
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浙江寧波315211
失地農民城市融合的進程中,在教育、就業、社交等方面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依據失地農民的年齡層次差異,從教育學、社會學等角度深入分析原因。
失地農民;城市融合;原因
近年來,黨和政府越來越廣泛地關注失地農民城市融合問題。2007年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發布了“關于切實做好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勞社部發[2007]14號),浙江省人民政府發布了“關于調整完善征地補償安置政策的通知”(浙政發[2014]19號),寧波港是“一帶一路”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寧波是中國東部沿海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失地農民。因此,對寧波失地農民城市融合困境分析十分必要。
失地農民是指在城市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由于城市規模擴大失去土地的特殊人群。失地農民是一個重要的群體,在這個群體中分布著不同年齡層次的人群。失地農民依據年齡層次差異主要分為青少年人群(受教育階段)、中年人群(就業中或待就業)、老年人群(無業在家)這三類。不同年齡層的失地農民在城市融合的過程中面臨共性的問題,同時也產生了各自較為突出的問題。
一、青少年人群城市融合問題——教育
失地農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他們和城市里的孩子在同樣的環境和條件下學習,但是由于不一樣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習慣,使得他們在學校中也產生了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良好個人習慣的養成等方面的融合問題。
一方面,城市學生不愿意主動與失地農民孩子交朋友。首先,失地農民整天忙于賺錢養家,很少有像城市家長那樣關心孩子的學校生活情況。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失地農民的孩子存在個人衛生條件相對較差的情況。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城市孩子與其主動交朋友的積極性。其次,失地農民孩子的心理狀況很容易被忽視。家長缺乏和孩子的長時間的溝通交流,孩子容易形成孤僻或者偏激的性格。失地農民孩子人際交往能力的缺失,這也是城市孩子不愿意主動與失地農民孩子主動結交的另一個原因。失地農民的孩子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關愛的缺失,使得他們在學校與同學發生沖突時,有些孩子不知該如何處理,很可能會惡語相向,甚至沖動打架。
另一方面,部分教師不愿意接受失地農民孩子在自己所任教班級學習。有些失地農民孩子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去完成家務,這使得他們用在學習上的時間和精力遠遠低于城市的孩子。失地農民的孩子行為習慣的問題也比較多,例如:遲到、作業不及時完成、口語表達不規范等問題時常發生。以上這些行為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班級榮譽的評比。因此,部分教師不愿意接受失地農民的孩子來自己的班級里學習。
二、中年人群城市融合問題——就業和社交
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在短期內很難解決。首先,失地農民自身的能力水平和文化素質亟待提高。其次,城市愿意提供給失地農民提供多元化和長期性的工作崗位。最后,需要社會各界關注失地農民這一個群體。只有解決就業問題,失地農民才能真正地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真正的主人。
失地農民本來有自己耕作的土地,可以自給自足。自從他們失去了土地,進入城市以后,不得不找一份工作來養家。但是,由于失地農民知識水平和個人能力的限制,找到合適的工作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難題。現實生活中,他們找到的工作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工作強度大。失地農民在農村長大和生活,他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于城市人群。在城市,較好的工作崗位招聘中,很多需要文憑或是熟練的技能。這無疑從一開始就拒絕了失地農民的求職請求。于是,很多失地農民只能被迫選擇一些技術要求低、工作勞累、地位低的工作。只有這樣的工作崗位,失地農民才有機會獲得。第二,工作臨時性強。大部分失地農民進入城市后,水電費等各種開銷增多,急需一份工作來維持生計。這樣急迫的現狀導致失地農民選擇當臨時工,諸如小區保安、清潔工、建筑工人等工作。第三,工作保障低。失地農民工作的臨時性和低技術性,導致了失地農民工作提供的保障低,且隨時面臨被辭退的風險。此外,工作環境的安全保障也很低。失地農民中從事建筑工作的,不僅面臨著被拖欠工資的風險,還面臨著高空作業的危險。
失地農民雖然生活在城市,但是固有社交方式沒有改變。在農村人看來,只有在熟悉的圈子里交往才安心,這使得農民對陌生人一直抱有警戒的態度,不會去主動進入城市居民的交際圈。同時,城市的生活格局將原本可以互相走動的鄰里鄉親分隔了起來,導致失地農民工作之余僅剩下個人的空間。
(一)交往對象分類,對陌生人缺乏信任
這個城市融合問題是失地農民主觀因素造成的。幾十年的農村生活,使得他們彼此對村上的所有人都很熟悉,因此交往也充滿信任。但是,由農村進入城市生活后,失地農民不可避免地要與城市居民或者外來租住人口進行接觸。失地農民很自然地就將這些人歸類為“外人”。因為缺乏信任,失地農民不主動與“外人”接觸成了失地農民的習慣。也正是因為對“外人”信任的缺乏,使得失地農民的社交圈子一直沒有擴大。簡單地來說,失地農民只是客觀上住在城市里而已,主觀上還沒有把自己當做城市居民看待,城市融合問題依然存在。
(二)業余生活單一,看電視成為首要選擇
經調查,在工作之余,看電視成為很多失地農民最主要的娛樂消遣方式。究其深層原因是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失地農民賺的錢不多,又有農村人與生俱來的節儉意識。除了必要的生活開支外,失地農民不愿意將辛苦賺來的錢花在自身的消遣上。其次,失地農民不愿意主動結交“外人”的主觀意識,也使得他們的業余生活沒有新鮮的元素。因此,看電視成了他們不得不選擇的娛樂消遣方式。
三、老年人群城市融入問題——社會保障、心理認同和習慣
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是城市融入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他們在農村生活了大半輩子,安土重遷和小農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他們是最難融合的一群人。他們入住城市后,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社會保障金。但是作為失地農民,他們的社會保障的福利和城市老人相差巨大。對于失地的老年人來說,一個月的社會保障只有幾百塊錢,而城市退休老人一個月的社會保障可以達到四五千。同樣是老年人,對待城市居民和失地農民的方式卻差了那么多,這使得失地農民在心理上產生了巨大的落差,在心理上并不認同自己是城市居民的身份。老人心理上的融合沒有完成,那城市融合終究是個難題。
失地老人在城市融合的過程中,新舊生活方式也產生激烈地碰撞。失地老人還帶有許多農村生活的習慣。失地老年人在農村一直以農耕為主,在土地里勞動對于他們來說已經是一個無法改變的習慣了。失地老年人自從住進城市以后,再也沒有土地供他們勞動。雖然失地老人覺得自己依然還有勞動潛力,但是城市生活不存在田間勞動的可能。突然閑下來后,老人整天不知道干什么。況且在城市居住的房子不像農村房子那樣出入自由,逐漸消減了失地老人走家串戶交流的熱情。既沒有勞動的機會,也失去了走家串戶交流的條件,老人的生活變得異常乏味。日復一日,老人想起在農村生活的種種好處,將農村生活的豐富與城市生活的單調進行比較,愈發懷念農村生活。對農村的懷念,使得老人無法真正市民化。
失地農民擁有城市人的身份,卻沒有和城市人一樣展示自己的舞臺。既不能獲得良好的就業機會,又不能享受同樣的社保水平。他們就像是城市的邊緣人,失去了原本生活的地方,帶著原來的態度和習慣,來到了城市這樣一個新的環境。
[1]孫碧榮.失地農民城市融合問題淺析[J].現代經濟信息,2015(8).
[2]張建國.失地農民的社會適應研究[D].武漢大學,2011.
[3]廖小軍.中國失地農民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沈耿炎(1995-),女,浙江湖州人,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小學教育(中文)專業本科在讀,研究方向:小學教育,項目核心成員;殷威(1992-),男,江蘇宿遷人,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主要研究方向:學科教學(語文),項目負責人。
F323.89;F301
A
1006-0049-(2016)20-0030-02
寧波大學第七屆“挑戰杯”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選題“‘一帶一路’視域下失地農民城市融合困境與導引路徑研究——以寧波市為例”的階段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