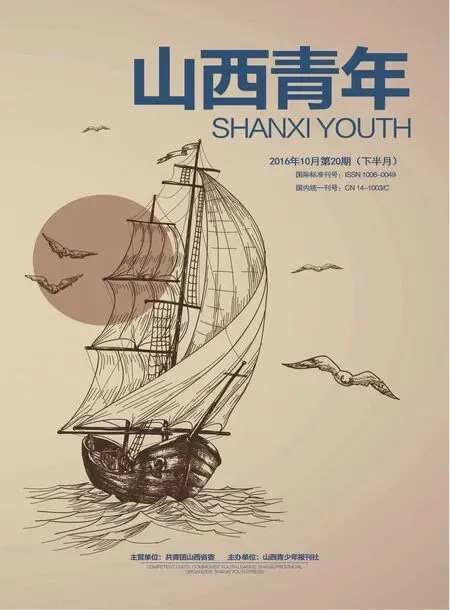蘇曼殊詩歌中的印度
石嘉欣
天津外國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天津 300204
?
蘇曼殊詩歌中的印度
石嘉欣
天津外國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天津300204
蘇曼殊一生不長,卻留下了不少名詩佳句。其中,印度文化對他的創作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順著詩歌中出現的印度俗文化詞匯、佛教用語探源,可以看出這種影響來自印度俗文學以及佛教禪宗的思想,這些使他詩歌多圍繞“愁苦”展開,徘徊于色空之間,又透著清靜的禪趣。
蘇曼殊;詩歌;印度文化
提起蘇曼殊,人們首先知道他是一個詩人,其次才知道他的小說、散文、翻譯多種成就。天然的才氣、敏感的神經、真情的流露讓這個多情的僧人詩名大躁。在研究蘇曼殊的熱潮中,有一點鮮有人注意,就是他的詩歌中涉及到了印度文化。本文旨在分析印度文化對蘇曼殊詩歌創作及譯詩產生的影響、影響的由來以及他如何看待這種影響。
一、印度純文學的影響
蘇曼殊與印度的姻緣要從他接觸梵文說起。從12歲出家對梵文產生濃厚興趣,到向喬悉磨長老學習梵文,再到寫下了彌補中國梵文研究空白的《梵文典》。蘇曼殊對梵文高度贊美,對印度文學的評價也極高,“衲謂文詞簡麗相俱者,莫若梵文,漢文次之,歐洲番書,瞠科后矣。”[1]
(一)印度古代文學的影響
蘇曼殊在詩歌《耶婆堤病中,未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士》中有對印度直接描寫。蘇曼殊曾兩次起意前往印度未果,從“梵土仍寥廓”、“恒河去不息”可以體會出蘇曼殊想象的印度地域遼闊、恒河水長流不息,該詩中還提及古印度神話中的“須彌”山。另在《本事詩(十首)》其六中,蘇曼殊將心上人百助比作印度傳說中的烏舍神女,表達了自己的濃濃愛意。《本事詩(十首)》其二,“生身阿母無情甚,為向摩耶問夙緣!”[2]使用了古印度傳說的摩訶摩耶夫人的意象,詠嘆自己的身世之苦。
印度古代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深得曼殊推崇,但要說蘇曼殊最喜愛的,還是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他在《燕子龕隨筆》里,稱譽迦梨陀娑為“梵土詩圣”,還將梵本《沙恭達羅》當做愛情信物送給了日本女友百助眉史(在他本事詩第七首中記錄了此事)。至于迦梨陀娑的另一部作品《云使》,蘇曼殊也是喜愛有加。《沙恭達羅》和《云使》正好契合了他的藝術審美觀,豐富的想象、優美流暢的語言、對細膩真摯的愛情的歌頌,這些都撥動著蘇曼殊富于浪漫的心弦。印度這種艷情味極濃的作品給了蘇曼殊創作靈感,大批深情綺艷的詩句從他筆下流出:“此后不知魂與夢,涉江同泛采蓮船。”“華嚴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愛我情!”鄭逸梅曾以“風華靡麗”四字概括曼殊的本詩(十首),高旭也稱贊他的詩是“其哀在心,其艷在骨”。
(二)印度近代文學的影響
隨著曼殊對梵語的掌握,蘇曼殊翻譯了一首印度近代女詩人陀露多的詩歌《樂苑》。曼殊在譯詩前嗟嘆陀露哆的才華,被陀露哆的愛國精神打動,于是譯此詩示世人。曼殊對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深為同情及感慨,對時局動蕩的中國也滿懷一腔熱血,在他的詩歌創作中更是感時憂懷,寫下了一首首愛國詩篇。如東居雜詩(十九首)其二,“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只淚流!”此時的曼殊雖然流寓日本,貧病交加,但對祖國的命運仍然牽掛。又如《為玉鸞女弟繪扇》,這首詩表面上寫佳人獨立江頭“似憐亡國苦”,實則抒發詩人因袁世凱竊國而引起的“亡國”之憂。
二、佛教禪宗的影響
(一)直接描寫僧侶生活
蘇曼殊在他的詩歌中大量運用了佛教名詞,描寫寺廟生活。如《住西湖白云禪院作此》,“齋罷垂垂渾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鐘。”描寫了曼殊在西湖旁白云禪寺打坐敲鐘的清凈生活。齋、入定、空、色、生天成佛、禪心、香火、劫灰、前身、破缽、袈裟、無生、孤僧、諸天花雨、妙跡、頭陀等,這些佛禪用語在他的詩歌中隨處可見,展現了一個具有佛心、佛理的詩境。
(二)以“愁苦”為主題
佛教認為人生即苦難,世事無常,所以人會陷入肉體、精神上的苦痛煩惱,曼殊自身的生活體驗也印證了這一點。曼殊在詩歌創作中高頻使用“愁”這個字眼,并多方面地展現人生之苦,有表現亡國之苦的“故國已隨春日盡,鷓鴣聲急使人愁”。有敘說命運之苦的“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諸天花雨隔紅塵,絕島漂流一病身”傳達出曼殊的貧病交加,身世飄零。還有寫詩人多情之苦的,“收將鳳紙寫相思,莫道人間總不知。盡日傷心人不見,莫愁還自有愁時。”寫出曼殊對已嫁作人婦的秦淮河歌妓金鳳的思念。“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無那正黃昏。”、“五里徘徊仍遠別”這些可以看出曼殊對百助的思念及不忍別離。
(三)“色”“空”之間的徘徊
曼殊一生真誠地愛過一些女子,但他的僧人身份使他不能與她們中的任何一個雙宿雙棲,因而曼殊在思想感情上產生了劇烈的矛盾和痛苦,這種矛盾痛苦正是這些纏綿悱惻詩篇的創作根源。“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禪心一任蛾眉妒,佛說原來怨是親。雨笠煙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懺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曾遣素娥非別意,是空是色本無殊。”正如柳亞子所斷言:“學佛與戀愛,正是曼殊一生胸中交戰的冰炭。”曼殊在我執與破除我執之間徘徊,寫出了一行行絕代傷心的愁句。
(四)具有閑適的禪趣
受隨緣自適的禪宗思想的影響,曼殊的詩自然閑適又帶有禪意,以《柬法忍》為例,曼殊可以將佛教的清規戒律丟到一邊,與友人開懷暢飲,到樂趣處提筆作畫。“落花深一尺,不用帶蒲團。”以心為本,隨處可安,不需要蒲團這種客觀實在的東西,只要心中有佛,隨處都可參禪。再有《題畫》一例,“海天空闊九皋深,飛下松間聽鼓琴。明日飄然又何處?白云與爾共無心。”寥廓天地間的孤鶴不會考慮明天要飛向何處,白云和鶴都是純任自然,無拘無束的,曼殊的心境也如這閑云野鶴,自由自在,一切隨緣,透出一股物我一境的禪趣。
三、總結
影響和接受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清末民初之際,出于對印度文學的贊賞、對從印度發軔的佛學的皈依,加上自身矛盾人生的作用,印度“微妙瑰奇”的文化深深吸引了蘇曼殊,蘇曼殊也主動地接受印度文化的影響,自覺地在詩歌創作包括譯作中融入了對印度的喜愛。
[1]朱少璋編.曼殊外集——蘇曼殊編譯集四種[M].學苑出版社,2009.
[2]邵盈午.蘇曼殊詩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
[3]柳無忌.蘇曼殊傳[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
I046;I206.6
A
1006-0049-(2016)20-02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