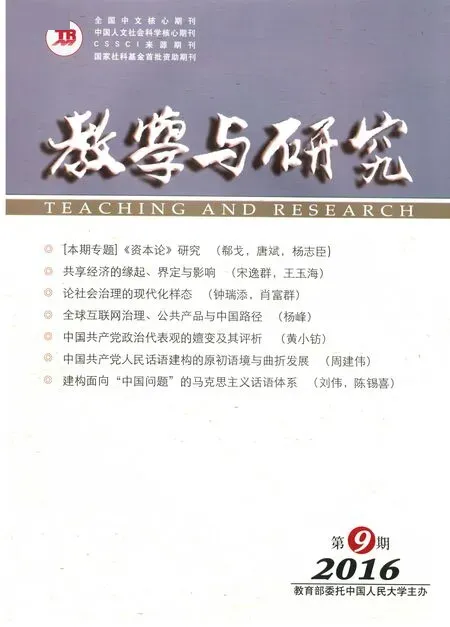啟蒙與“人的問(wèn)題”
——黑格爾的解釋路徑及其對(duì)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響*
田毅松
啟蒙與“人的問(wèn)題”
——黑格爾的解釋路徑及其對(duì)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響*
田毅松
啟蒙; 人; 共同體; 人的本質(zhì)(人性)
啟蒙運(yùn)動(dòng)對(duì)黑格爾和馬克思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在政治哲學(xué)中體現(xiàn)在處理人和共同體的關(guān)系上。在黑格爾的政治哲學(xué)中,共同體優(yōu)先于并影響著個(gè)體,然而,它不但沒(méi)有蔑視個(gè)體,而是認(rèn)為共同體應(yīng)該是個(gè)體實(shí)現(xiàn)自由的前提條件。馬克思早期一方面認(rèn)為共同體(類)優(yōu)先于個(gè)體,人的本質(zhì)體現(xiàn)為其類本質(zhì),另一方面認(rèn)為個(gè)體超越了共同體,人就是“現(xiàn)實(shí)的個(gè)體的人”,但他必須在真正的共同體即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才能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黑格爾關(guān)于人的雙重本質(zhì)理論對(duì)馬克思影響深刻并使其認(rèn)為人的本質(zhì)也具有雙重屬性——理性人和公民。
杜威曾引用英國(guó)詩(shī)人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詩(shī)句來(lái)描寫現(xiàn)代人,認(rèn)為他們“正徘徊于兩個(gè)世界之間,一個(gè)世界已經(jīng)死亡,而另一個(gè)世界尚無(wú)力誕生。”[1](P3)詩(shī)句揭示了現(xiàn)代人所面臨的困境,表現(xiàn)了在現(xiàn)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人們無(wú)所適從的窘境。盡管人們對(duì)這種窘境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像福柯等后現(xiàn)代主義者仍在繼續(xù)著對(duì)理性的批判,持續(xù)不斷地對(duì)啟蒙運(yùn)動(dòng)進(jìn)行反思和批判;像哈貝馬斯等現(xiàn)代性的呼吁者則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該繼續(xù)堅(jiān)持啟蒙的遺產(chǎn),發(fā)揚(yáng)理性的革命作用;而保守主義者則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該回歸古典,通過(guò)古希臘和中世紀(jì)的經(jīng)典文獻(xiàn)來(lái)恢復(fù)啟蒙運(yùn)動(dòng)帶來(lái)的不良后果。,但他們無(wú)疑都指向了一個(gè)共同的主題——啟蒙運(yùn)動(dòng)。哈貝馬斯就明確指出了現(xiàn)代性與啟蒙運(yùn)動(dòng)之間的關(guān)系——“哲學(xué),作為理性的守護(hù)者,則認(rèn)為現(xiàn)代性是啟蒙的產(chǎn)物”。[2](P180)但必須注意的是,近現(xiàn)代社會(huì)思想家對(duì)現(xiàn)代性問(wèn)題做出的杰出分析,卻是建立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家對(duì)啟蒙運(yùn)動(dòng)的考察之上的。
一、啟蒙與“我”的出現(xiàn)
啟蒙的內(nèi)涵是非常豐富的。人們既可以對(duì)它進(jìn)行歷史描述,也可以利用它對(duì)社會(huì)進(jìn)行批判,更能夠?qū)λM(jìn)行哲學(xué)分析。盡管啟蒙的世界歷史意義已經(jīng)得到認(rèn)可,但確實(shí)有很多歷史學(xué)家根據(jù)啟蒙運(yùn)動(dòng)發(fā)生的社會(huì)文化背景提出了蘇格蘭啟蒙運(yùn)動(dòng)和“德國(guó)的”啟蒙運(yùn)動(dòng)等*施密特就曾認(rèn)為“什么是啟蒙”是一個(gè)純粹的德國(guó)問(wèn)題。。盡管很多哲學(xué)家對(duì)它進(jìn)行了哲學(xué)分析,但現(xiàn)代社會(huì)思想家卻更多地借助對(duì)啟蒙的反思來(lái)批判社會(huì)事實(shí),主要指向經(jīng)濟(jì)權(quán)力對(duì)人的權(quán)利的擠壓、社會(huì)對(duì)自然的無(wú)節(jié)制索取以及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生活的高度背離。[3](P5)即使在黑格爾那里,啟蒙不但可以區(qū)分出古代的啟蒙(ancient enlightenment)和現(xiàn)代的啟蒙(modern enlightenment),而且現(xiàn)代的啟蒙本身也具有認(rèn)知(cognitive)維度和道德政治維度*黑齊曼認(rèn)為,黑格爾在《哲學(xué)史講演錄》中對(duì)啟蒙進(jìn)行過(guò)廣義的理解,即將啟蒙等同于教化(bildung)。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黑格爾那里,啟蒙的諸多維度之間是互證的,因?yàn)樗倪壿媽W(xué)、認(rèn)識(shí)論、道德—政治哲學(xué)等是融貫在一起的。Hinchman,L.P.Hegel’s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1984.P2,P5.。
當(dāng)我們將啟蒙的內(nèi)涵僅僅限定在“現(xiàn)代的啟蒙”上,那么就必須承認(rèn)啟蒙與現(xiàn)代性之間存在著密切關(guān)聯(lián)。然而正如黑齊曼所看到的那樣,現(xiàn)代性的典型現(xiàn)象學(xué)特征是心靈(mind,rescogitans)與世界(world,resextensa)的截然分離。[4](P4)正是這種分離,促使“我”的出現(xiàn),而從笛卡爾到康德直至黑格爾,“我”一直作為認(rèn)知主體貫穿整個(gè)哲學(xué)始終。
當(dāng)?shù)芽柎_立自己的哲學(xué)體系時(shí),首先提出了第一個(gè)命題,即“我思故我在”。在黑格爾看來(lái),這一命題的建設(shè)性意義遠(yuǎn)遠(yuǎn)大于其懷疑論意義,因?yàn)楫?dāng)?shù)芽柼岢觥拔宜肌钡臅r(shí)候,實(shí)際上他已經(jīng)完成了一個(gè)哲學(xué)上劃時(shí)代意義的變革,即通過(guò)一種“普遍性的形式把握它的高級(jí)精神原則”。這種普遍性的根源就是“絕對(duì)確定的‘我’”,因?yàn)椤拔摇笔恰皰仐壱磺屑僭O(shè)和規(guī)定”的“我”。換言之,正是由于“我”拋棄了一切假設(shè)和規(guī)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只具有抽象性,這種抽象性確定了它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在黑格爾看來(lái),笛卡爾的絕對(duì)的“我思”本身還客觀地包含著思維主體的“自由”,因?yàn)椤白杂墒歉荆矊儆诒徽J(rèn)為真實(shí)的東西,都應(yīng)當(dāng)以包含我們的自由為條件”*黑格爾:《哲學(xué)史講演錄》,第4卷,第73-77頁(yè),賀麟、王太慶譯,商務(wù)印書館,2009年。值得注意:如果將個(gè)體性(自我)作為現(xiàn)代性的重要特征,那么從現(xiàn)代性切入研究啟蒙,那么對(duì)它的解釋就可以像黑格爾那樣追溯至笛卡爾甚至更早。此外,如果注意到勒高夫的研究——他提出了“擴(kuò)展了的中世紀(jì)”(extended middle age)和“擴(kuò)展了的現(xiàn)代性”(extended modernity)概念,前者包括從公元3—19世紀(jì)中葉的漫長(zhǎng)時(shí)間,后者與之同時(shí)發(fā)生——那么將啟蒙和現(xiàn)代性問(wèn)題追溯至笛卡爾反而成了一種“保守的”做法。See Le Goff,J.The Medieval Imagin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黑格爾認(rèn)為,休謨?cè)诤艽蟪潭壬习l(fā)展了人的主體性,但同時(shí)也放棄了普遍性,因?yàn)椴还苁钦J(rèn)識(shí)論領(lǐng)域還是道德實(shí)踐領(lǐng)域,都是建立在一種基于個(gè)體主觀性的習(xí)慣之上。因此,不管是道德還是法律,都是建立在一種“主觀的……道德感上”,從心理角度強(qiáng)調(diào)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和道德觀念,無(wú)疑強(qiáng)調(diào)了人的主體性,但這種主體又是個(gè)別的,缺少一種普遍必然性。康德則不然,他通過(guò)對(duì)批判哲學(xué)的建構(gòu),確立了知識(shí)以及道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且將哲學(xué)范疇建立“在我的自我意識(shí)中的自我”這個(gè)主體之上。我們跨過(guò)康德復(fù)雜的哲學(xué)論證,僅僅從他對(duì)啟蒙的分析中就能夠看到他對(duì)作為自我意識(shí)的“我”的論述。在“答復(fù)這個(gè)問(wèn)題:什么是啟蒙運(yùn)動(dòng)”中,康德提出了一個(gè)關(guān)于啟蒙運(yùn)動(dòng)的經(jīng)典定義——“啟蒙運(yùn)動(dòng)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tài)……要有勇氣運(yùn)用你自己的理智”。[5](P22)在這里,康德的兩個(gè)概念需要我們注意,一是“不成熟狀態(tài)”,一是“理智”。對(duì)于前者,康德進(jìn)行了解釋,認(rèn)為所謂的“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人們沒(méi)有勇氣獨(dú)立地運(yùn)用自己的理智。這一概念蘊(yùn)含著一個(gè)重要的內(nèi)容,即沒(méi)有啟蒙的人往往籠罩在宗教之下而具有很強(qiáng)的依附性,人的獨(dú)立人格或自主性得不到完全的確立。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進(jìn)行“批判”考察。但要克服這種依附性,就需要求助于人自身的“理智”。在康德看來(lái),任何人都是有理性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理性僅僅是一種潛存,是一種有待人們自己對(duì)自身潛能進(jìn)行挖掘的東西。[5](P22)但是,在一個(gè)正在“啟蒙的”而非已經(jīng)“啟蒙了的”時(shí)代*在這里,何兆武先生將“啟蒙的”(enlightment)和“啟蒙了的”(enlighted)翻譯為“啟蒙運(yùn)動(dòng)的”和“啟蒙了的”。如果僅從字面意思上看,無(wú)疑何先生的翻譯更貼切,但根據(jù)文章的語(yǔ)境,徐向東的翻譯更為合理。施密特:《啟蒙運(yùn)動(dòng)與現(xiàn)代性——18世紀(jì)與20世紀(jì)的對(duì)話》,第65頁(yè),徐向東、盧華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宗教的巨大影響讓人缺乏運(yùn)用自己的理智的勇氣。[5](P28)我認(rèn)為,在一定意義上,啟蒙對(duì)宗教的反對(duì)更多的是為了鼓舞人們應(yīng)用自己的理性,推動(dòng)理性主體確立獨(dú)立人格。根據(jù)康德的分析,如果人按照自己的理性進(jìn)行判斷,那么人就能夠且必須為自然和自身的行為進(jìn)行立法,人的行為也就成了一種自我意識(shí)的(self-conscious)和自主的(autonomous)行為,也就是一種自由行為*關(guān)于自由、自主和自我意識(shí)之間的關(guān)系,可以參考麥克艾菲的進(jìn)一步論述。See McIvor.“Marx’s Philosophical Modernism: Post-Kantian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Karl Marx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edited by Andrew Chitt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9.P41.。換言之,當(dāng)人成熟運(yùn)用自己的理性進(jìn)行自我決定,即從他律走向自律時(shí),人的自由就具有了普遍性和必然性。
康德的“人是目的”命題在形式上強(qiáng)調(diào)了自我,但費(fèi)希特基于知識(shí)學(xué)的“主體性”學(xué)說(shuō)經(jīng)過(guò)對(duì)康德命題的改造而具有了很強(qiáng)的現(xiàn)實(shí)性。從笛卡爾到費(fèi)希特和黑格爾,自我變得日益現(xiàn)實(shí)和具體*黑格爾關(guān)于啟蒙與現(xiàn)代性和人的主體性之關(guān)系的論述,將在下文詳述之。。然而,青年黑格爾派在強(qiáng)調(diào)“自我意識(shí)”的同時(shí)忽略了它的現(xiàn)實(shí)性問(wèn)題。眾所周知,宗教批判幾乎是青年黑格爾派的共同主題,他們?cè)噲D以此來(lái)鞏固自我意識(shí)哲學(xué)和人的主體性地位。比如施特勞斯在《耶穌傳》中對(duì)基督教中的耶穌進(jìn)行了歷史還原,將之從神壇推倒,還原為一個(gè)常人。施特勞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目的無(wú)非是“協(xié)助人類精神從教條的壓迫奴役下進(jìn)行自我解放”。[6](P8)在施特勞斯的影響下,布魯諾·鮑威爾等人也對(duì)宗教進(jìn)行了批判,認(rèn)為它就是一種異化形式,顛倒了現(xiàn)實(shí)的理性世界之法則,把自我意識(shí)的普遍性遞交給異化了的神圣歷史。同時(shí),自我意識(shí)是真正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力量,它的本質(zhì)就是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目的(Zweck),也是歷史的唯一目的,而且歷史知識(shí)精神的自由意識(shí)的生成過(guò)程,或者說(shuō)是現(xiàn)實(shí)的、自由的、無(wú)限的自我意識(shí)的生成過(guò)程”。[7](PP36-37)通過(guò)對(duì)自我意識(shí)的強(qiáng)調(diào),人的個(gè)體性和主體性得到了確認(rèn),而且自我意識(shí)在青年黑格爾那里同樣具有普遍性。
不難發(fā)現(xiàn),啟蒙運(yùn)動(dòng)所開(kāi)啟的,實(shí)質(zhì)上是一條人不斷自我發(fā)現(xiàn)的路,是不斷張揚(yáng)人的理性和確立人的主體性的過(guò)程,更是人們賦予主體自由以普遍性的過(guò)程。啟蒙運(yùn)動(dòng)的這一特征不但對(duì)黑格爾,而且對(duì)馬克思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不管是其青年時(shí)期還是晚年時(shí)期,個(gè)體的自由及其普遍性追求一直是其終極價(jià)值目標(biāo)之一。
二、“拉摩的侄兒”與雙重啟蒙
當(dāng)近代哲學(xué)強(qiáng)調(diào)主體及其普遍性時(shí),他們卻不得不面對(duì)另外一種新的挑戰(zhàn),即如何解決因?yàn)槌前顕?guó)家瓦解之后留下的歸屬感的真空。此外,另一個(gè)現(xiàn)實(shí)的問(wèn)題是,當(dāng)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興趣并對(duì)近代倫理學(xué)和政治哲學(xué)提出挑戰(zhàn)時(shí),如何處理“原子式”個(gè)人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對(duì)人是狼”的自然狀態(tài)*盡管馬克思認(rèn)為“自然狀態(tài)”只是17、18世紀(jì)學(xué)者們的一種浪漫想象,但是這種浪漫想象的根源卻在近代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得到了印證,那就是當(dāng)每個(gè)人作為理性人進(jìn)入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時(shí),他們之間主要是一種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而這種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實(shí)質(zhì)上也就是一種霍布斯意義上的自然狀態(tà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0頁(yè),人民出版社,1995年。)實(shí)際上,資產(chǎn)階級(jí)學(xué)者(比如普芬多夫)對(duì)“自然狀態(tài)”也提出了質(zhì)疑,但是他們?nèi)匀辉噲D從家庭出現(xiàn)到國(guó)家形成這段時(shí)間中為“自然狀態(tài)”留下空間,進(jìn)而讓這一概念在經(jīng)驗(yàn)上得到證明,認(rèn)為它“既可以理解為‘概念上的虛構(gòu)’(per fictionem concipitur),也可以看作是‘真實(shí)存在’(revera existit)”。Pufendorf,De Statu Hominum Naturali,7;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I.i.7.轉(zhuǎn)引自李猛:《自然社會(huì):自然法與現(xiàn)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第207-209頁(yè),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盡管康德、費(fèi)希特等人完全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地位,但他們似乎并沒(méi)有解釋,在社會(huì)中呈現(xiàn)出來(lái)的作為自我意識(shí)之體現(xiàn)的“我”或個(gè)體,如何在嚴(yán)重沖突中構(gòu)建起一個(gè)現(xiàn)代意義上國(guó)家——它既能讓個(gè)體的自主性得到彰顯,同時(shí)又能讓個(gè)體不能因?yàn)槠鋬?nèi)在的“普遍性”而相互敵對(duì)和消滅。這就涉及到了雙重啟蒙問(wèn)題。
所謂“雙重啟蒙”,在我看來(lái),是指人的啟蒙和公民的啟蒙。在德國(guó)18世紀(jì)關(guān)于“什么是啟蒙”這個(gè)問(wèn)題的爭(zhēng)論中,門德?tīng)査蓪?duì)“什么是啟蒙”這個(gè)問(wèn)題的理解并不遜于康德。因?yàn)樵谒磥?lái),這個(gè)問(wèn)題不但可以從認(rèn)識(shí)論和政治哲學(xué)意義上分別進(jìn)行討論,而且必須在政治哲學(xué)意義上對(duì)其進(jìn)行進(jìn)一步區(qū)分。因此,門德?tīng)査蓪⒚蛇^(guò)程中人的命運(yùn)(或身份)分裂為“人作為人的命運(yùn)”以及“人作為公民的命運(yùn)”,這就是啟蒙的雙重性。[8](P57)
雖非嚴(yán)格意義上的政治哲學(xué)著作,但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試圖繼續(xù)論證門德?tīng)査商岢霾⒆隽顺醪浇忉尩膯?wèn)題。黑格爾首先認(rèn)識(shí)到了啟蒙的雙重性,而這是通過(guò)借助狄德羅的著作《拉摩的侄兒》闡發(fā)出來(lái)的。
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中,黑格爾并沒(méi)有像一般人那樣譏諷“拉摩的侄兒”是一個(gè)小丑,而是視其為追逐財(cái)富的代表。在黑格爾看來(lái),盡管這位“小丑”公開(kāi)承認(rèn)自己就是富人手中的玩物,但是他取悅那些富人的目的只是為了獲得利益。因而,黑齊曼認(rèn)為,黑格爾在討論“財(cái)富”(reichtum)這一主題時(shí)引用這一典故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如果人們不為自己謀取一份利益,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那么他就是一個(gè)十足的傻瓜”這樣一種價(jià)值觀。同樣,科耶夫也認(rèn)為“拉摩的侄兒”實(shí)際上是功利主義的典型代表——他“不關(guān)心別人”,因而處在了“個(gè)人主義的極點(diǎn)”上*Hinchman,Hegel’s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P117. 科耶夫:《黑格爾導(dǎo)讀》,第160頁(yè),譯林出版社,2005年。。“拉摩的侄兒”表明,在市民社會(huì)中,這正是一種普遍的特殊性,而它可能會(huì)使整個(gè)社會(huì)推向了崩潰的邊緣*正像科耶夫所言,當(dāng)每個(gè)人都像拉摩的侄兒那樣高談闊論、追逐利益時(shí),“世界將因此而改變”。賀麟先生等人也指出,拉摩的侄兒的精神狀況實(shí)際上指的是法國(guó)大革命前的人們的普遍狀況,即蠅營(yíng)狗茍但又毫無(wú)信仰。參見(jiàn)科耶夫:《黑格爾導(dǎo)讀》,第160頁(yè);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下卷,第62頁(yè)下注,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當(dāng)然,如果我們將黑格爾的這一論述與其晚期的《法哲學(xué)原理》結(jié)合起來(lái)進(jìn)行解讀,不難發(fā)現(xiàn),作為“倫理階段”最重要內(nèi)容之一的“市民社會(huì)”之所以被視為“需要的體系”,就在于它揭示的是個(gè)體的一種普遍的特殊性追求。
那么,“拉摩的侄兒”所體現(xiàn)的這種普遍的特殊性是不是人的本質(zhì)或自然(nature)?是,但又不是。認(rèn)為是,因?yàn)樗_實(shí)反映了任何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利益訴求;認(rèn)為不是,因?yàn)樗鼪](méi)有完全體現(xiàn)出人的共同本質(zhì)(gemeinwesen)。因而,人的或自我意識(shí)的本質(zhì)應(yīng)該是雙重的,其一是人之為人的本質(zhì),是人的純粹自然屬性;其二是人作為共同體成員的身份特征,是人的共同本質(zhì),或共同體屬性。
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中認(rèn)為,自我意識(shí)具有雙重本質(zhì)(doppelwesen),它能夠通過(guò)在兩種精神力量直觀到。第一種精神力量是一種自在存在(an-sich-sein),它經(jīng)過(guò)異化之后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shí)的國(guó)家權(quán)力(staatsmacht);第二種精神力量則是一種自為存在(für-sich-sein),也就是財(cái)富。[9](P46-47)既然是雙重本質(zhì),那么它們直觀后的國(guó)家權(quán)力和財(cái)富的善惡如何確證?黑格爾給出了多種可能。他指出,從直接規(guī)定來(lái)看,國(guó)家由于是自在存在,因而是善的;財(cái)富則因?yàn)槠涫亲詾榇嬖冢识菒旱摹8鶕?jù)精神性的判斷*關(guān)于精神性的判斷的討論,還需要引入新的補(bǔ)充性標(biāo)準(zhǔn)——“同一性”(gleichheit)。關(guān)于精神性判斷與同一性之間關(guān)系的討論,參見(jiàn)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下卷,第48-49頁(yè);See Hegel,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S.388-390.,國(guó)家也是善的,因?yàn)閭€(gè)體在國(guó)家權(quán)力中發(fā)現(xiàn)“自己的根源和本質(zhì)得到了表達(dá)、組織和證明”;財(cái)富則相反,因?yàn)閭€(gè)體在其中體會(huì)不到他的普遍本質(zhì),因而是惡的。[9](P49-50)但是,財(cái)富的惡并不是絕對(duì)的,它在市民社會(huì)的需要體系中由于能夠?qū)ⅰ爸饔^的利己心轉(zhuǎn)化為對(duì)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滿足是具有幫助的東西”。因而也具有善的一面,可以看作是人的一種本質(zhì)。[10](P210)作為社會(huì)實(shí)體的人,是具有自我意識(shí)的主體,它所具有的雙重本質(zhì)就是,它既能認(rèn)識(shí)到自己是“自在存在”,又能意識(shí)到自己是“犧牲了普遍而又變成自為存在”。作為自在存在,個(gè)體在同樣是自在存在著的國(guó)家權(quán)力中表現(xiàn)為公民身份,而作為自為存在,個(gè)體在追求財(cái)富的市民社會(huì)中表現(xiàn)為一種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理性人。但是從黑格爾的邏輯發(fā)展上來(lái)看,作為自為存在的理性人是人的“第一自然”,而體現(xiàn)了普遍性或社會(huì)性的公民則是人的“第二自然”。[11](P515)
正是通過(guò)對(duì)“我”的個(gè)體性與普遍性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非常詳細(xì)的論述,黑格爾指出了“我”的雙重本質(zhì)的辯證特征,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二者之間相互依存。因?yàn)椤白晕壹仁沁@個(gè)特殊的我,但同時(shí)又是普遍的我;它的顯現(xiàn),既直接是特殊的我的外化和消逝,同時(shí)又是普遍的我的保持和持存”*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下卷,第55頁(yè),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但需要注意,這里的“特殊的我”,原文是“dieses Ich”和“diese Ichs”,我們排除德語(yǔ)中形容詞格和名詞數(shù)的的變化,它們都可以還原為“die Ich”,那么這個(gè)“die”作為定冠詞翻譯為“個(gè)體的”似乎更合適。Hegel,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erlin: Akademie Verlag,1998,S.390.。如同科耶夫所言,“啟蒙運(yùn)動(dòng)的批判任務(wù)主要在于清除了這樣的觀念:人是一種自然的、給定的、‘世代相傳的’定在。”[12](P158)自我意識(shí)因而具有了雙重啟蒙的內(nèi)涵,而這種內(nèi)涵的深層含義,則是試圖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個(gè)人自主和古代社會(huì)的公共本質(zhì)加以超越和融合*See Horstmann,Rolf-Peter,“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in Hegel on Ethics and Politics,edited by Robert B.Pippin and Otfried H?ffe;translated by Nicholas Walker,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11-212. 另參見(jiàn)朱學(xué)平:《古典與現(xiàn)代的沖突與融合——青年黑格爾思想的形成》,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黑格爾的這一結(jié)論,直接影響到了馬克思的早期政治哲學(xué)。
三、政治獅皮與人的解放
黑格爾自我意識(shí)的雙重內(nèi)涵,往往被演化為市民社會(huì)與國(guó)家之間的對(duì)立關(guān)系。但我們業(yè)已指出,在黑格爾那里,二者與其說(shuō)是對(duì)立的,不如說(shuō)是統(tǒng)一的。當(dāng)然,由于國(guó)家作為倫理的最高階段,必然會(huì)去規(guī)約市民社會(huì)這個(gè)需要的體系所帶來(lái)的混亂,因而,可以說(shuō)是它們統(tǒng)一于國(guó)家,但理性國(guó)家作為行走在地上的神,應(yīng)該能夠同時(shí)維持人的雙重屬性,使之統(tǒng)一起來(lái)。
應(yīng)然不等于實(shí)然。應(yīng)然與實(shí)然之間現(xiàn)實(shí)存在的鴻溝,實(shí)際上讓黑格爾的理論設(shè)計(jì)幾乎變成了“無(wú)”,而將這種黑格爾的“無(wú)”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shí)的,是馬克思的政治哲學(xué)。換言之,黑格爾關(guān)于人的雙重本質(zhì)理論,直接影響到了馬克思早期的政治思想,但是,人的雙重本質(zhì)理論與市民社會(huì)和國(guó)家之間的對(duì)立理論被馬克思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我們?cè)谶@里僅僅試圖指出而非論證黑格爾對(duì)馬克思《德法年鑒》時(shí)期思想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但是,通過(guò)文獻(xiàn)考察不難看出,馬克思在寫作《論猶太人問(wèn)題》的前后都在關(guān)注黑格爾的著作,在之前是《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之后則寫過(guò)《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導(dǎo)言》和《關(guān)于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筆記》等內(nèi)容。MEGA-2,I-2,1982,Dietz Verlag Berlin;MEGA-2,VI-2,1981,Dietz Verlag Berlin,S.493.。
馬克思早期的政治理論仍像大多數(shù)青年黑格爾分子一樣,是把宗教批判作為起點(diǎn)的,認(rèn)為“對(duì)宗教的批判”盡管已經(jīng)基本結(jié)束,但這“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頁(yè),人民出版社,2009年。盡管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基本上沒(méi)有把宗教批判作為主要內(nèi)容,但每一論題又無(wú)不與宗教問(wèn)題絞合在一起。。然而,青年黑格爾派所完成的宗教批判,只是顛倒了主詞和謂詞之間的關(guān)系,不再?gòu)钠毡樾酝茖?dǎo)出特殊性,但他們大多僅僅停滯于此。馬克思與之不同的是,他認(rèn)識(shí)到了黑格爾關(guān)于宗教分析的合理性,認(rèn)為是宗教(基督教)把適用于市民社會(huì)的個(gè)人主義的道德合法化了。換言之,經(jīng)由啟蒙之后,宗教由于退縮到私人領(lǐng)域,與經(jīng)濟(jì)人聯(lián)系在了一起。宗教與政治之間的關(guān)系實(shí)質(zhì)上也就轉(zhuǎn)化成了經(jīng)濟(jì)與政治之間的關(guān)系。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wèn)題》中就明確指出,“宗教信徒和政治人之間的矛盾,是bourgeois和citoyen之間、是市民社會(huì)的成員和他的政治獅皮之間的同樣的矛盾”。[13](P31)
不難看出,宗教信徒和政治人、資產(chǎn)階級(jí)(bourgeois)和公民(citoyen)以及市民社會(huì)的成員和公民這三對(duì)概念實(shí)質(zhì)上是同一的,它們同樣都是在反映人的雙重本質(zhì)。對(duì)于前一組概念(宗教成員、bourgeois和市民社會(huì)的成員),它們就是指人的第一種本質(zhì),即追逐私利最大化、以利己主義作為道德原則的自然人或理性人(homme)。馬克思在討論人權(quán)的時(shí)候指出,人權(quán)(droits du l’homme)中的“人”就是指“利己的人”,是“同其他人并同共同體分離開(kāi)來(lái)的人”。[13](P40)馬克思繼續(xù)解釋說(shuō),這種人具有“非政治”(性),因而“必然表現(xiàn)為自然人”,表現(xiàn)為“具有感性的、單個(gè)的、直接存在的人”。而另一組概念(政治人、citoyen和政治獅皮)指稱的是人的第二種本質(zhì),它的特點(diǎn)是“抽象的、人為的、寓意的和道德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6頁(yè)。其原文是:“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人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但根據(jù)德文原文,這里的法人實(shí)為“moralische”,似乎翻譯為“道德人”更為合理,不過(guò)根據(jù)一般理解,翻譯為“法人”更能體現(xiàn)人的本質(zhì)的二重性。MEGA-2,I-2,1982,Dietz Verlag Berlin,S.162.。馬克思關(guān)于人的雙重本質(zhì)理論要求,當(dāng)尋求人的解放的時(shí)候,不可能僅僅恢復(fù)人的某一種本質(zhì),而是力圖實(shí)現(xiàn)人的全面回歸。因此他認(rèn)為,解放的目的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種關(guān)系回歸于人自身”。它“一方面把人歸結(jié)為市民社會(huì)的成員,歸結(jié)為利己的、獨(dú)立的個(gè)體,另一方面把人歸結(jié)為公民,歸結(jié)為法人”。[13](P46)
然而,馬克思“政治獅皮”的隱喻說(shuō)明,人的第二本質(zhì)往往會(huì)阻礙人的全面解放。因?yàn)樵谒磥?lái),政治形式已然不能完全實(shí)現(xiàn)人的解放,真正解放應(yīng)該以市民社會(huì)的成員(自然人)為基礎(chǔ),同時(shí)將人的共同本質(zhì)補(bǔ)充進(jìn)去。“只有當(dāng)現(xiàn)實(shí)的個(gè)人把抽象的公民復(fù)歸于自身,并且作為個(gè)人,在自己的經(jīng)驗(yàn)生活、自己的個(gè)體勞動(dòng)、自己的個(gè)體關(guān)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shí)候,只有當(dāng)人認(rèn)識(shí)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huì)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lái)因而不再把社會(huì)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shí)候,只有到了那個(gè)時(shí)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3](P46)
黑格爾關(guān)于人的雙重本質(zhì)雖然極大地影響著馬克思,但他已然注意到,黑格爾所謂的個(gè)體的共同本質(zhì)——國(guó)家,實(shí)質(zhì)上不過(guò)是一張保護(hù)有產(chǎn)者階級(jí)利益的“政治獅皮”,但要?jiǎng)兊暨@張“獅皮”,最終必須從另外一個(gè)與之對(duì)立的范疇——市民社會(huì)中尋找資源。正是在這種張力下,馬克思逐漸開(kāi)始向唯物史觀發(fā)展;而且,馬克思早期大體上認(rèn)同了人的雙重本質(zhì)理論,這種理論是否延續(xù)到了馬克思成熟時(shí)期,則仍是需要考察的問(wèn)題。
[1] 杜威.人的問(wèn)題[M].傅統(tǒng)先,邱椿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2] 哈貝馬斯.后民族結(jié)構(gòu)[M].曹衛(wèi)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 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哲學(xué)斷片[M].渠敬東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 Hinchman.Hegel’s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M].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1984.
[5] 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0.
[6] 施特勞斯.耶穌傳[M].第1冊(cè).吳永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1.
[7] Moggach,Douglas.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Bruno Bauer[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8] 施密特.啟蒙運(yùn)動(dòng)與現(xiàn)代性——18世紀(jì)與20世紀(jì)的對(duì)話[M].徐向東,盧華萍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 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M].下卷.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
[10] 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5.
[11] Hegel,G.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M].Translated by J.B.Baillie.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 Row,1967.
[12] 科耶夫.黑格爾導(dǎo)讀[M].姜志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責(zé)任編輯 孔 偉]
Enlightenment and “the Question of Man”
——Hegel’s Explanation Path and Its Influence on Marx’s Early Thought
Tian Yiso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enlightenment; human; community; the natur of man (human nature)
The Enlightenmen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Hegel and Marx. It is embodi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community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community is a priority and affects the individual. However, it does not despise the individual, but holds that the community should be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individual to achieve freedom. Marx, in his early years, holds on the one hand that community is a priority to the individual and the essence of man is embodied in its community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individual is beyond the community. Hegel’s theory on the dual nature of man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Marx, and makes him think that the essence of man has a dual attributes, which are the rational people and citizens.
* 本文系教育部哲社重大課題攻關(guān)項(xiàng)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新MEGA)研究”(項(xiàng)目號(hào):10JZD0003)和教育部清華大學(xué)自主科研項(xiàng)目“以新MEGA為基礎(chǔ)的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項(xiàng)目號(hào):2010THZ0)的階段性成果。
田毅松,北京師范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講師(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