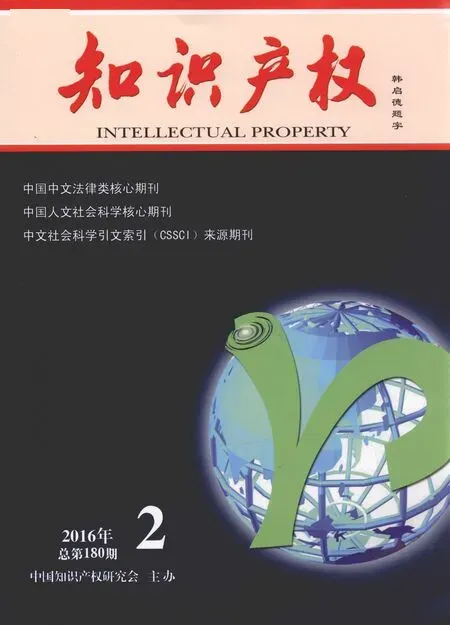論公權對商標權性質(zhì)的影響
孫淑濤
?
論公權對商標權性質(zhì)的影響
孫淑濤
內(nèi)容提要:商標權的權利性質(zhì)問題是商標權法律制度的基本問題,也是知識產(chǎn)權法律制度的重要問題。盡管?與貿(mào)易有關的知識產(chǎn)權協(xié)議?(簡稱?TRIPS協(xié)定?)開宗明義提出“知識產(chǎn)權是私權”,但是受近些年來興起的“私法公法化”等學說的影響,有的學者提出了“私權公權化”的觀點,認為商標權已經(jīng)不是純粹的私權,公權性質(zhì)成為商標權的重要屬性。在全面分析商標權產(chǎn)生、行使、保護等各個環(huán)節(jié)中公權的作用,及其對商標權性質(zhì)的影響后認為,不管公權與商標權法律制度的關系如何密切,商標權的權利內(nèi)核都沒有變化,商標權仍然是一項純粹的私權。
關 鍵 詞:商標權 公權 民事權利 私權公權化
《TRIPS協(xié)定》將“承認知識產(chǎn)權為私權”寫入其前言,商標權作為知識產(chǎn)權的一個類別,在性質(zhì)上也應當是私權。但是,時下流行的私法公法化趨勢為商標權的定性問題掀起多重波瀾。實際上,多數(shù)主張商標權公權化的學者并不否認商標權的私權性質(zhì),而是在承認商標權為私權的同時認為商標權具有公權屬性。其中,行政公權對商標權產(chǎn)生、行使、保護的干預是相關學者主張商標權公權化的主要依據(jù)。本文擬通過全面探討公權與商標權的產(chǎn)生、行使、保護的關系,對商標權的性質(zhì)予以進一步澄清。
一、商標權的取得與公權的關系
有學者認為,“與一般的有形財產(chǎn)所有權的產(chǎn)生不同,知識產(chǎn)權中商標權的設立需經(jīng)過國家行政管理機關的審查,通過審查方予以授權”a鄒波:《知識產(chǎn)權公權屬性簡探》,載《河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第78頁。。“世界各國對知識產(chǎn)權的確認,都采取行政確權的程序,由國家主管知識產(chǎn)權的行政管理機關,根據(jù)法律的規(guī)定,對有關知識產(chǎn)權的申請進行審查,決定是否授予知識產(chǎn)權專有權”b馮曉青、劉淑華:《試論知識產(chǎn)權的私權屬性及其公權化趨向》,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1期,第64頁。。所以,“國家授予性正是知識產(chǎn)權的公權性質(zhì)的直接體現(xiàn)”c李永明、呂益林:《論知識產(chǎn)權之公權性質(zhì)——對“知識產(chǎn)權屬于私權”的補充》,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65頁。。
商標權的“國家授予性”直接體現(xiàn)在商標立法中。我國《商標法》規(guī)定,全國商標的注冊和管理工作由商標局負責,經(jīng)商標局核準注冊的商標才能成為注冊商標并受法律保護。可見,注冊商標權至少在形式上是由國家行政機關商標局核準授予的。或者說,沒有商標局的核準,商標不能獲得注冊,申請人不能對其持有的商標行使注冊商標權。顯然,國家授權成為注冊商標權產(chǎn)生的必要手續(xù)和必經(jīng)環(huán)節(jié)。
那么,與物權、債權相比,為什么注冊商標權的產(chǎn)生離不開國家行政機關的審查核準呢?主張國家授予性體現(xiàn)商標權公權性質(zhì)的學者對此進行了相關探討,并指出,國家授予性是由商標自身的特點決定的。因為商標本身是無體的、易復制的,而且商標持有人不能像占有實體物一樣實際控制商標,所以人們無法僅僅依靠商標的使用人來判斷商標的實際權利人(如在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情形下),也無法僅僅依靠權利人自身對商標的使用而自然制止他人對商標的再利用(但物權可以,因為物權人在占有、使用某物的同時也在事實上排除了他人對該物的占有和使用)。然而,上述問題在行政公權的參與下迎刃而解。通過向商標局申請商標注冊并由商標局予以核準公告,商標持有人成為注冊商標所有權人,并借助國家機器實現(xiàn)對注冊商標的專有使用。不可否認,行政公權對商標權的產(chǎn)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商標權本身也是公權呢?本文將從以下兩方面進行說明。
(一)與不動產(chǎn)登記制度的類比:私權不因行政權力的介入而具有公權屬性
前述觀點存在明顯的邏輯錯誤。其核心內(nèi)容,即因為在商標權產(chǎn)生的過程中伴隨著行政公權的介入,所以商標權自身也具有公權的屬性。在這里,即使暫且不考慮公權可否與私權共存于商標權一身,僅從邏輯上講,行政公權的介入與商標權自身的性質(zhì)應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商標權不應當因行政公權的介入而必然具有公權的性質(zhì)。不動產(chǎn)登記制度便是很好的例證。
所謂不動產(chǎn)登記是指“專門的登記機構根據(jù)登記申請人的申請,依據(jù)法定的程序,對其不動產(chǎn)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的情況在不動產(chǎn)登記簿上進行記載并供不特定的第三人查閱的行為。”d王利明主編:《民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頁。我國《物權法》明確規(guī)定,“不動產(chǎn)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應當依照法律規(guī)定登記。”如在買賣房屋時,購買人應當及時向相關行政機關申請產(chǎn)權登記,并辦理、領取產(chǎn)權登記證。本文認為,行政登記機關將不動產(chǎn)物權的設立、變更公之于眾,與商標局將注冊商標予以公告并無實質(zhì)區(qū)別。理由如下:
第一,負責辦理不動產(chǎn)登記的當為行政機關無疑,并且登記是行政機關的一項行政管理職權,在登記過程中行政機關行使的是行政公權。這與作為行政機關的商標局在商標審查核準時行使行政公權的情形無異。
第二,或許有人會說,商標局可以駁回商標注冊申請,從而直接影響注冊商標權的產(chǎn)生,此與不動產(chǎn)登記是否有別?實際上,二者沒有任何區(qū)別。《商標法》第30條規(guī)定:“申請注冊的商標,凡不符合本法有關規(guī)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已經(jīng)注冊的或者初步審定的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標局駁回申請,不予公告。”該條明確告訴我們,商標局駁回商標注冊申請不是恣意妄為,而是必須存在不符合商標核準注冊的法定情形。不動產(chǎn)登記應當與此無異,試想,如果登記申請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行政登記機關是否有必須予以登記的義務?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僅如此,《商標法》第28條還規(guī)定,“對申請注冊的商標,商標局應當自收到商標注冊申請文件之日起九個月內(nèi)審查完畢,符合本法有關規(guī)定的,予以初步審定公告。”該條明確要求商標局,只要商標注冊申請符合法定條件,商標局都必須予以公告。此外,《商標法》第33條規(guī)定,“公告期滿無異議的,予以核準注冊,發(fā)給商標注冊證,并予公告。”該條又明確要求商標局,只要公告期滿無異議,那么商標就必須核準注冊,向商標注冊申請人頒發(fā)注冊證,并且公之于眾。所以,行政登記機關與商標局在登記事項與商標核準事項上都必須依法辦事,而沒有自由裁量空間。
第三,《物權法》規(guī)定,“不動產(chǎn)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jīng)依法登記,發(fā)生效力;未經(jīng)登記,不發(fā)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所以不動產(chǎn)登記直接影響物權設立和變更的效力,這亦與商標局的審核直接影響商標注冊申請無異。
綜上所述,行政登記機關將不動產(chǎn)物權的設立、變更公示于眾,與商標局將注冊商標予以公告并無實質(zhì)區(qū)別。不動產(chǎn)物權不會因為行政公權的介入而由私權轉變?yōu)楣珯啵虡藱嗤瑯硬粫蛐姓珯嗟慕槿攵厝痪哂泄珯鄬傩浴?/p>
(二)審視公權在商標制度的作用:輔助確權無法改變商標權的私權性質(zhì)
1.商標審查的依據(jù)
我國《商標法》規(guī)定,“對申請注冊的商標,商標局應當自收到商標注冊申請文件之日起九個月內(nèi)審查完畢,符合本法有關規(guī)定的,予以初步審定公告。”是否符合《商標法》關于商標注冊的規(guī)定,是商標能否通過商標局初步審定的唯一標準。《商標法實施條例》的規(guī)定更為明確,“商標局對受理的商標注冊申請,依照商標法及本條例的有關規(guī)定進行審查”,并對符合規(guī)定的予以初步審定、公告,而對不符合規(guī)定的予以駁回。條例的規(guī)定明確指出商標局進行商標審查的依據(jù)是商標法及其實施條例。
審查標準的法定性,決定了商標局不能依其主觀意愿而任意決定審查結果。商標局在審查商標注冊申請時,其主要任務是判斷某既存可視性標志是否符合商標注冊的要求。或者說,商標局在審查商標注冊申請的過程中,只是扮演了一個中立的判斷者的角色,作為參考系的判斷標準是法定的,待判斷的標識是由申請人提出的,商標局需要做的只是居中裁斷。這種居中裁斷行為對商標權產(chǎn)生及定性的影響,在商標局的行政機關角色的掩飾下,顯得朦朧模糊。
2.商標審查并非必然由商標局進行
從以上分析可知,商標局在商標審查過程扮演的是居中裁斷者的角色。為什么是由商標局充當這個角色?或者說,這個角色能否由其他主體擔當?
在這里,我們作一個假設。既存的已知事實是商標審查過程中審查主體僅承擔居中裁斷者的角色,假設的前提是商標審查的標準客觀、明確因而具有足夠強的實際操作性,或者說,將商標申請與審查標準作一對比,可以輕易判斷出商標申請是否符合審查標準的要求。那么,商標審查工作是否必須由商標局承擔?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審查標準的明確性使得不同主體進行商標審查時所得出的結論應當是一致的,那么審查工作由商標局承擔與由其他社會組織承擔并無實質(zhì)區(qū)別,甚至每個正常的個體都可以擔當起裁斷者的角色。
回到現(xiàn)實中來,實際上商標審查的標準無法達到足夠的確定性。所以,對同一商標申請,不同主體對其適用同一審查標準時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而對于特定的商標申請來說,要么其符合要求而獲得注冊,要么因不符標準而被駁回。所以,結論的非一致性必將導致商標使用秩序的混亂。要結束這一局面,就必須出現(xiàn)一個具有壓倒性權威的主體,商標審查的結果僅以該主體的判斷結論為依據(jù)。“對知識作為一種權利對象進行確認必須有超越于個人的第三方加以肯定,否則知識產(chǎn)權無法行使,因此作為極具公信力的國家行政機關就擔當起重任”e彭禮堂、武芳:《知識產(chǎn)權屬性的法理探析》,載《知識產(chǎn)權研究》2005年第3期,第37頁。。于是,政府成立了名為商標局的行政機關,并以政府的公信力和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商標局的審查結論可以得到社會成員的認可。在這里,“公權所起的作用只是宣示權利的產(chǎn)生并對權利擁有起到公示公信作用”f衣慶云:《知識產(chǎn)權公權化理論之批判》,載《電子知識產(chǎn)權》2007年第7期,第36頁。。此外,商標審查工作的專業(yè)性以及國家財政的支持都是商標局承擔商標審查重任的重要因素。
但是,我們應當看到,由商標局進行商標審查只是解決方案中的一種。或許這是可行性相對較高并且相對經(jīng)濟合理的方案,但它決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因為從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的力量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還有其他解決方法的存在。所以,商標審查由商標局負責有其客觀需要,但并非必然如此。
3.商標核準是確權行為
很多學者將商標局核準商標注冊并發(fā)給商標注冊證的行為定性為權利的授予行為,尤以主張知識產(chǎn)權具有國家授予性的學者為代表。其典型觀點如“知識產(chǎn)權只有在獲得專利局和商標局等行政機關的授權后才能受到法律的保護。”g同注釋c。“政府行政管理機關對于專利、商標,一般都要經(jīng)過實質(zhì)審查或形式審查后才授予權利人專有權并予以登記和公告。”h同注釋b。即便是主張商標權為私權的學者,持上述觀點的也不在少數(shù),如吳漢東教授認為,知識產(chǎn)權產(chǎn)生的法律事實包括創(chuàng)造者的創(chuàng)造性行為和國家機關的授權性行為,并認為授權性行為是創(chuàng)造者的權利主體資格得以確認的程序。i吳漢東:《關于知識產(chǎn)權私權屬性的再認識——兼評“知識產(chǎn)權公權化”理論》,載《社會科學》2005年第10期,第59頁。當然,并非所有學者皆持上述觀點,有的學者認為,商標確權是指商標注冊機構就注冊商標的申請、異議和無效做出決定的行為,以及法院就上述決定進行司法審查的行為j李明德:《專利權與商標權確權機制的改革思路》,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第12頁。,從而將商標核準行為定性為商標確權行為。要弄清此問題,應當從確權與授權的含義入手,只要總結出二者的主要特征或區(qū)別,問題將迎刃而解。
確權,簡而言之,即確定權利的歸屬。確權的前提是權利主體尚未得到有拘束力的確認,這種拘束力既可以是法律意義上的,也可以是行政意義上的,確權的目的就是結束權利主體懸而未決的狀態(tài)。商標確權亦如此,其主要目的在于裁斷商標的歸屬和商標權的主體,它既包括對商標注冊申請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做出裁斷,也包括在發(fā)生商標爭議等情形后決定商標權的主體;前者直接影響申請注冊的商標是否歸屬申請人(申請人是否適格),后者則是在兩個或多個主體間進行判斷選擇。
“授”即授予、給予,授權是指將自己所擁有的權力/利委托給他人行使,常見的如法律實踐中的授權委托書等。授權的條件之一當為受權人所獲權利/力是授權人自身所合法擁有的,倘若授權人自身無此權利/力,則授權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根本無從談起。
由此,我們來分析商標局的核準行為是授權行為還是確權行為。首先,作為行政機關的商標局在進行商標核準時其自身是否擁有商標權?對于這一事實問題,答案不言自明,商標局并非商標權的主體。那么,商標局的核準行為不符合授權行為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所以核準行為并非授權行為。其次,商標核準行為是否為確權行為?對此問題,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第一,商標局在做出商標核準注冊決定前,申請注冊的商標的歸屬是否確定?對此問題,我們可以從商標異議制度中找到答案。《商標法》規(guī)定,“對初步審定公告的商標提出異議的,商標局應當聽取異議人和被異議人陳述事實和理由,經(jīng)調(diào)查核實后,自公告期滿之日起十二個月內(nèi)做出是否準予注冊的決定,并書面通知異議人和被異議人”,這意味著在商標異議階段,商標的歸屬尚未形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結論,其他主體可以通過異議程序使被異議商標無法獲得注冊,從而使被異議人不能取得對被異議商標的注冊商標權。第二,商標局核準注冊后,商標歸屬是否確定?對此,無論是主張商標局授權還是確權的學者,都一致認為,在商標局核準注冊、發(fā)給商標申請人商標注冊證并予以公告后,注冊商標即歸商標申請人所有,商標及商標權的歸屬問題即告解決。縱使之后可能會出現(xiàn)商標爭議等法律問題,都不過是對注冊商標權法定效力的例外、糾正和補充。第三,商標局的角色。商標局作為中立裁斷者,是判斷商標申請是否符合法定條件;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商標申請人就獲得該商標權。所以,商標局所決定的,不是符合條件時申請人能否獲權,而是是否符合法定條件。因為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商標局有義務予以核準,或者說,如果申請符合法定條件,那么商標局拒絕核準的行為是違法的。
由上述三點觀之,商標核準的主要作用即在于依據(jù)法定標準確定注冊商標權的歸屬。此外,《商標法》第31條的規(guī)定也對此有所印證,該條規(guī)定:“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商標注冊申請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申請注冊的,初步審定并公告申請在先的商標;同一天申請的,初步審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商標,駁回其他人的申請,不予公告。”該條實際上為多人對同一標識主張注冊商標權時商標歸屬問題提供了明確的解決之道。
正如劉春田教授所言,“商標核準本是由一個職能部門對一個確立私權的請求進行合法性審查并向社會公示的行為,卻在潛意識里給企業(yè)造成某種國家授權的誤解,以為商標能否注冊,取決于政府”k劉春田:《商標法代表了我國民事立法的方向》,載《中華商標》2002年第8期,第8頁。,實際上,政府部門以國家名義對商標予以注冊、核準,其本質(zhì)并非將本屬于政府的權利授予申請人,而只是為了保障公平合理、有效充分地維護民事主體的利益,對可能發(fā)生的利益沖突,對正當合理的權利要求和主張進行審查、甄別、確認和公示的必要的行政行為。l劉春田:《知識財產(chǎn)權解析》,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4期,第118頁。商標核準行為當為確權行為,而非授權行為。
4.公權對商標注冊的意義
商標局是進行商標審查工作的可能機關之一,商標局進行商標審查所必須遵循的標準是由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而且商標核準行為只是確認注冊申請人對特定標識享有合法權益。將這些結論綜合起來不難發(fā)現(xiàn),商標局對商標權的產(chǎn)生起的是一種形式意義上的客觀的確認作用,或者說從商標審查到商標核準,都可以由其它主體依據(jù)法定審查標準和程序完成,而不需要行政權力的干預。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即商標局的行政機關身份及其掌握的行政權力對商標權的產(chǎn)生有無影響?具有何種影響?
如前所述,商標局的公信力和權威是其承擔商標審查、核準工作的基礎,而“政府權威需要適當權力”m劉尚哲:《論政府權威與權力制約》,載《法制與社會》2008年第3期,第153頁。,所以適當?shù)男姓嗔κ巧虡司中惺蛊渖虡俗詫彶楹秃藴事毮艿谋U希股虡司謱ψ陨虡藱鄽w屬的裁斷成為可為公眾普遍接受的唯一結論。商標核準注冊后公告的公示效力亦與此相關。所以,公權對商標審查和核準,基本上起后臺支持和后勤保障作用,具體而言,即協(xié)助、保障商標確權程序的完成,與商標權的產(chǎn)生并不存在直接關系。所以,公權在商標權產(chǎn)生過程中的角色就是輔助商標確權,對商標權的產(chǎn)生、內(nèi)容與定性影響甚微。對于這種公權為私權所用的情形,自然不必妄自菲薄,將公權作為商標權的屬性。
二、商標權的行使與公權的關系
我國《商標法》第42條規(guī)定:“轉讓注冊商標的,轉讓人和受讓人應當簽訂轉讓協(xié)議,并共同向商標局提出申請。轉讓注冊商標經(jīng)核準后,予以公告。受讓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標專用權。”由此可知,在我國,轉讓注冊商標應當由商標局予以審查、核準。
關于注冊商標的使用許可,我國《商標法》也有特殊要求。《商標法》第43條規(guī)定:“商標注冊人可以通過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許可他人使用其注冊商標。……許可他人使用其注冊商標的,許可人應當將其商標使用許可報商標局備案。”與轉讓注冊商標不同的是,注冊商標的使用許可只須報請商標局備案,并不需要申請商標局核準。不過,由上述法律法規(guī)的措辭來看,履行備案手續(xù)是注冊商標使用許可當事人的義務。
那么,如何看待核準、備案、公告與商標權性質(zhì)的關系?是否如學者所言,《商標法》自身設置的商標的轉讓核準和使用許可備案,是國家干預的體現(xiàn),使商標權具有公權性質(zhì)?本文認為,并非公權所至皆為公權,同為公權,在不同的情境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其功能、作用、地位亦不相同。倘若認為凡為國家機關干預者皆為公權,恐怕普天之下,私權再無立足之地。由此,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理解公權在商標權轉讓、許可使用中的角色定位。
(一)商標局審核的內(nèi)容與目的
注冊商標的轉讓須經(jīng)商標局的審核批準,但是商標局所審為何?為此,經(jīng)查閱商標局關于商標轉讓的相關規(guī)定,并向商標局作過電話咨詢,始終沒有找到商標局所欲審核內(nèi)容的明確規(guī)定。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其他方面對其作一大致推測。在商標局的官方網(wǎng)站“中國商標網(wǎng)”上,其商標申請指南曾對申請商標轉讓的程序做出詳細說明nhttp://sbj.saic.gov.cn/sbsq/sqzn/200901/t20090110_68045.html.。首先,“將注冊商標轉讓給他人的,應當?shù)缴虡司洲k理注冊商標的轉讓手續(xù)”。其次,申請人需提交的申請文件包括《轉讓申請/注冊商標申請書》、轉讓人和受讓人的經(jīng)蓋章或者簽字確認的主體資格證明文件復印件、委托代理的提交受讓人出具的《代理委托書》(直接在商標注冊大廳辦理的提交受讓方經(jīng)辦人的身份證原件和復印件)。此外,申請移轉的,還應當提交有關證明文件;申請文件為外文的,還應提供經(jīng)申請人或代理組織簽章確認的中文譯本。商標局在其官方網(wǎng)站上提供了《轉讓申請/注冊商標申請書》的格式,申請人應當按照要求如實填寫,并不得擅自修改格式。《轉讓申請/注冊商標申請書》的內(nèi)容包括申請人的基本信息,如轉讓人和受讓人的名稱、地址、郵政編碼、聯(lián)系人、電話、傳真、代理組織等,以及被轉讓商標的相關信息,如商標申請?zhí)?注冊號、類別以及是否共有等。此外,還有轉讓人、受讓人和代理組織的章戳或簽字,以及商標轉讓前后共有人的名稱或姓名。
除上述申請書、主體資格證明文件復印件、代理委托書等文件外,申請人無需提交其他文件或證明。那么,商標局審查的也不外乎上述文件。這些文件又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待轉讓商標的基本信息,主要體現(xiàn)在《轉讓申請/注冊商標申請書》中;一類是申請人與代理機構的基本情況。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商標局的審查內(nèi)容主要包括兩項:一是申請人的信息是否真實;二是待轉讓商標是否真實存在、是否有效、是否存在禁止轉讓的情形等。此外,《商標法實施條例》第31條規(guī)定,“轉讓注冊商標的,轉讓人和受讓人應當向商標局提交轉讓注冊商標申請書。轉讓注冊商標申請手續(xù)應當由轉讓人和受讓人共同辦理。商標局核準轉讓注冊商標申請的,發(fā)給受讓人相應證明,并予以公告”;“轉讓注冊商標,商標注冊人對其在同一種或者類似商品上注冊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未一并轉讓的,由商標局通知其限期改正;期滿未改正的,視為放棄轉讓該注冊商標的申請,商標局應當書面通知申請人”。所以,商標局的審查內(nèi)容還包括商標是否一并轉讓、是否存在其他禁止轉讓的情形。不論審查內(nèi)容如何繁多,商標局審查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即通過審查轉讓主體與對象的真實性,保證交易安全,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二)商標局審核行為的定性
設定商標局審核程序的必要性。《商標法》第42條規(guī)定,轉讓注冊商標的,轉讓人和受讓人應當簽訂轉讓協(xié)議。訂立協(xié)議的雙方是自然人、法人等“理性人”,雙方出于自愿而達成轉讓協(xié)議,并依照協(xié)議的約定享受權利、履行義務、承擔責任。如果一方的合法權益受到另一方不法行為的侵害,一方可以依據(jù)協(xié)議或法律規(guī)定要求另一方賠償損失或承擔其他責任。所以,借助轉讓協(xié)議、法律規(guī)定及司法系統(tǒng)等,轉讓協(xié)議雙方即可實現(xiàn)維護自身權益的目的。這實際上與一般民事行為無異。那么,商標局的審查究竟有無存在必要?前面已述,商標局的審查主要包括兩項內(nèi)容,即轉讓協(xié)議雙方和商標自身的真實性。這兩項內(nèi)容實際上完全可以由協(xié)議雙方自行完成,正如在房屋買賣合同中,買賣雙方的姓名、住址等信息以及賣方房地產(chǎn)權證的真實、合法性的確認,這些都是作為“理性人”的買賣雙方自身即可完成的。倘若所有的物權變動皆由登記機關逐一審查,勞民傷財不必多言,其可行性都值得懷疑。而且,轉讓協(xié)議雙方在訂立協(xié)議前應當已經(jīng)對彼此基本情況有所了解,待轉讓商標的信息亦可以通過“中國商標網(wǎng)”的商標查詢系統(tǒng)予以檢索,爾后,商標局還要將上述信息逐一重新審查,不但降低了商標流轉的效率、可能導致受讓人喪失商機,而且對于商標局自身而言,亦有徒增負擔、增加不必要成本之累。所以,商標局打著保護協(xié)議雙方權益的旗號,對所有的商標轉讓詳細審查,無論對于轉讓雙方,還是對于商標局自身,似乎都是出力不討好的事情。此外,有學者研究指出,《歐洲共同體商標條例》、《丹麥商標法》、《美國法典》、《英國商標法》等皆實行商標轉讓登記制度,即商標主管機關應當事人的請求對商標轉讓情況予以登記,商標主管機關并不負責商標轉讓信息真實性的審查o左浪、李兆強:《從“達娃紛爭”探析我國的注冊商標轉讓制度》,載《金卡工程(經(jīng)濟與法)》2010年第7期,第61頁。。由此觀之,商標局對商標轉讓予以審查,其弊遠大于利,而且也不為主要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所采用。
即使不考慮商標局審查程序存在的必要性,單純觀察審查行為與商標權的關系,商標權公權化的主張也難以成立。商標局的審查行為只是干預商標權權利行使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而且也只是進行信息真實性的審查,其離商標權權利內(nèi)核尚有十萬八千里之遙,僅以該審查行為由商標局而為,就斷定商標權具有公權性質(zhì),實是風馬牛不相及。
(三)商標局公告行為的定性
《商標法》規(guī)定,轉讓注冊商標經(jīng)核準后,商標局應當予以公告。商標轉讓公告的內(nèi)容包括五項:被轉讓商標的注冊號或申請?zhí)枴⑸虡吮旧怼⑥D讓人姓名或名稱、受讓人姓名或名稱、商標轉讓的生效日期等。此公告的作用與物權公示制度的功能無異,即公示權利現(xiàn)狀,保護第三方的信賴利益。物權不因公示而公權化,商標權亦如此。
(四)商標局備案行為的定性
《商標法》規(guī)定,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應當報商標局備案,此備案程序如同公告,與商標權及其性質(zhì)并不相干。
三、商標權的保護與公權的關系
我國《商標法》第7章專門規(guī)定“注冊商標專用權的保護”。第61條規(guī)定,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有權依法查處;涉嫌犯罪的,應當及時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此外,《商標法》第62條還直接規(guī)定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查處侵權行為可以行使的職權。這些條款將商標權的保護納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職權和職責范圍,足見行政保護對商標權的重要意義。于是,有學者指出,“我國對知識產(chǎn)權保護實行‘雙軌制’,即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雙管齊下,在有中國特色的國情下,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是兩個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兩者各司其職,不能相互替代;現(xiàn)階段對知識產(chǎn)權的行政保護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具有強化的趨勢,行政管理機關運用行政手段處理知識產(chǎn)權糾紛、制裁侵權行為,是運用得最頻繁、效果最直接的保護方式”p李永明、呂益林:《論知識產(chǎn)權之公權性質(zhì)——對“知識產(chǎn)權屬于私權”的補充》,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63頁。。本文認為,對此問題應全面看待。
首先,行政公權是保護商標權的重要手段。商標的使用與市場主體的經(jīng)濟活動密切相關,侵犯商標權的行為多數(shù)發(fā)生于市場經(jīng)濟活動過程中。這些侵權行為,不僅侵犯了商標權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損害了消費者和其他經(jīng)營者的利益,并且可能對市場經(jīng)濟秩序等產(chǎn)生負面影響,所以商標權的保護問題涉及諸多市場主體的經(jīng)濟利益。快速發(fā)現(xiàn)、打擊侵犯商標權的行為,維持良好的市場秩序,是市場經(jīng)濟的正常運行提出的內(nèi)在要求。而由于司法機關的“不告不理”,導致司法保護具有被動性,同時訴訟程序的漫長又使得權利的保護遙遙無期,所以司法保護無法完全滿足市場主體保護商標權的內(nèi)在需求。因此,“將高度專業(yè)化且具靈活性的行政執(zhí)法機關納入到知識產(chǎn)權的執(zhí)法隊伍中來,并以終局的司法復審程序作為保障,既可以解決法院之圍,又有利于保護知識產(chǎn)權人的利益進而化解或者避免利益沖突”q孫海龍、董倚銘:《知識產(chǎn)權公權化理論的解讀和反思》,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第84頁。。所以,行政保護對商標權的意義不言而喻。
其次,行政保護對當前我國商標權保護的重要性不可否認,但是這仍然沒有改變商標權的私權性質(zhì)。這主要是因為行政保護針對的是侵犯商標權的行為,而非商標權本身。行政保護是通過打擊侵權行為來保護商標權,這些侵權行為與商標權的行使沒有直接關聯(lián),比如商標行政管理機關依法打擊假冒“耐克”商標的經(jīng)營者,而“耐克”商標的所有人及其合法使用者仍然在權利范圍內(nèi)行使商標權,而絲毫沒有受到行政管理機關公權的影響。所以,行政機關的公權性質(zhì)與商標權的性質(zhì)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商標權的性質(zhì)不會因為公權的保護而有所改變。
結 語
總之,商標權法律制度中難免有公權的身影,但是公權的干預卻不可能使商標權由私權變成公權。簡單地由公權的干預而推測商標權性質(zhì)改變的觀點,高估了公權對私權的影響,并且不符合社會現(xiàn)實。對此,劉春田教授特別指出,“知識產(chǎn)權從屬性上來說是財產(chǎn)權,是民事權利,因而是私權。法律無論用什么手段來調(diào)整這一權利,無論將它歸入哪一類,無論由誰來管,也無論司法機關設置什么機構來保證權利的實現(xiàn),都不能改變其私權的本質(zhì)屬性。在民事權利領域,權利百分之百屬于主體,而沒有什么機關可以干預。因此,我們在立法時,必須凸顯知識產(chǎn)權的本質(zhì),并圍繞這一點來調(diào)整利益關系”r周文斌:《凸現(xiàn)知識產(chǎn)權的私權權利——中國人民大學劉春田教授訪談》,載《光明日報》2000年7月17日,轉引自馮曉青著:《知識產(chǎn)權法利益平衡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頁。。
Abstract:The nature of the trademark right is basic for the legal system of trademark right, as well as important for the legal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though the TRIPs agreement states that “recognizing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private rights”, some scholars put forward that the private rights have partly been turned into public powers. After analysing the infl uence of public power to the trademark right, we can fi nd that the cont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trademark right are not changed, and the trademark right is still a kind of private right.
Key Words:trademark right; public powers; civil rights; the tendency of public right of private right
作者簡介:孫淑濤,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chǎn)權專業(y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