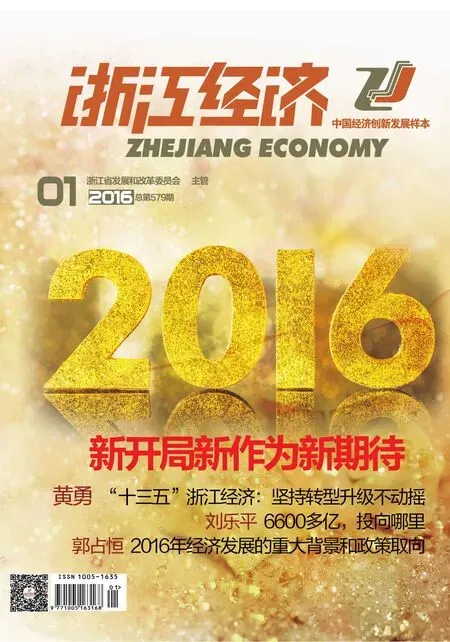有效投資:供給側改革的開山斧
王國翔
有效投資:供給側改革的開山斧
王國翔
供給側改革已是當下的熱頻詞。需求側理論我們大多耳熟能詳。推動經濟發展的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之和,被喻為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宏觀調控的“三大手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計劃手段,也是直接在需求端發力,通常短期即可收獲“立竿見影”之效。因此,當經濟出現過冷或過熱現象時,我們就習慣性地開出“傳統藥方”,采用積極的、或緊縮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計劃手段來“刺激提振”或“去火降燥”。但是,凡藥都有三分毒,久服必有副作用。日積月累,不但刺激效果日漸式微,而且經濟結構失衡加劇、經濟運行難求平穩。自2010年首季開始,到最近的2015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已連續23個季度處于下降通道,降幅高達43%,這便是明證。每一輪“強刺激”之后,都難免留下“一地雞毛”,加劇一批過剩產能、銀行不良資產和地方政府債務,這也是明證。
供給側改革另辟蹊徑,著眼于供給端來尋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自然呼之欲出,成為必然選擇。正是目前存在的供給側質量、效率不高,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令宏觀調控“投鼠忌器”、“左右為難”。廣義貨幣(M2)已突破130萬億元,卻難以支撐60多萬億元的GDP,實體經濟對資金需求還普遍“喊渴”、“喊貴”。從1990年至2014年,中國M2總量增長80倍;同期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從1990年的1516.21元增加到2014年的28844元,增長了19倍。“錢都去哪兒了?Mckinnon研究提出的M2/GDP金融深度指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給側存在的效率不高、結構失衡等問題。空轉導致效率低下,錯配造成沉淀浪費,供給側出了問題。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就是通過改革創新、簡政放權、制度供給、激發活力等手段,破除“供給約束”、優化供給結構,促進生產要素的供給水平和有效利用,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勇于實踐、勇于改革、勇于創新的浙江,可以在哪些方面重拳出擊,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呢?
“騰籠換鳥”就是供給側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就提出,要破解浙江發展瓶頸,必須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騰籠換鳥”。浙江省500多個年產值超億元的塊狀經濟,涉及175個行業、24萬多家企業,但“鋪天蓋地”的多,“頂天立地”的少,多數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產品附加值不高,排放污染卻不少。“低小散”、“僵尸企業”、產能過剩企業擠占大量資源,卻使得全社會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造成“供給約束”。消費受到制約,社會資源配置失衡。“騰籠換鳥”必須針針見血、刀刀見骨!必須堅定不移地淘汰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落后生產技術、工藝和產品,給吃得少、產蛋多、飛得遠的好“鳥”騰地兒,騰出供給新空間。
“五水共治”就是供給側改革。“五水共治”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和制度供給,實現五水聯動共治,產業聯動治水、科技聯動治水、區域聯動治水。通過治水實現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發展方式的轉變和轉型,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2015年以來,全省電鍍、印染、制革等六大重污染高耗能行業已關停2219家,整治提升3465家;22個特色污染行業整治關閉3108家,整治提升6403家。2015年前三季度,全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分別比上年同期提高0.7個、1.3個百分點。在關停的同時,此間爆發的新供給更不可小覷。舉一個最小的例子。“五水共治”需要鋪設大量管子,以前的管子都是“沉默”的管子,破損、泄漏、壓爆無人知曉,直到發生大面積噴管、坍陷、爆炸等重大災難。如果能供給“會說話的管子”,在管內流向發生變化、管壓達到臨界、管道發生裂隙泄漏之初能及時預警,災難是可以避免或大大減輕的。供給側改革就是這樣具體和簡單。
“兩化融合”就是供給側改革。通過信息化與工業化在技術、產品、業務、產業等多個方面進行融合,衍生創造出新的供給,迎來燦爛“艷陽天”。以“五水共治”為例,在污水防治、節水供水、防洪排澇等眾多領域的設備、材料,與信息化深度融合、智能化全面對接后,在研發新設備、新材料、新工藝方面將迸發出無限商機。利用物聯網技術實現節水和減排,利用傳感器產品加強水資源監測、排污監控、洪澇預警、清潔生產、水環境治理等等,都具有良好的現實需求和應用前景。
應當看到,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并沒有天然的鴻溝、天生的標簽。投資,能夠直接拉動需求,在凱恩斯理論中是最有力的需求刺激“強心針”,是“三駕馬車”中最能“揚鞭奮蹄”的快馬;但有效投資,直接形成有效供給,恰恰是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開山斧”,今天的投資就是明天的產出,就是后天的供給。因此,有效投資,一頭連著需求端,一頭連著供給端,是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同時發力的最佳利器。擴大有效投資,就是最有效的供給側改革!
作者單位: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