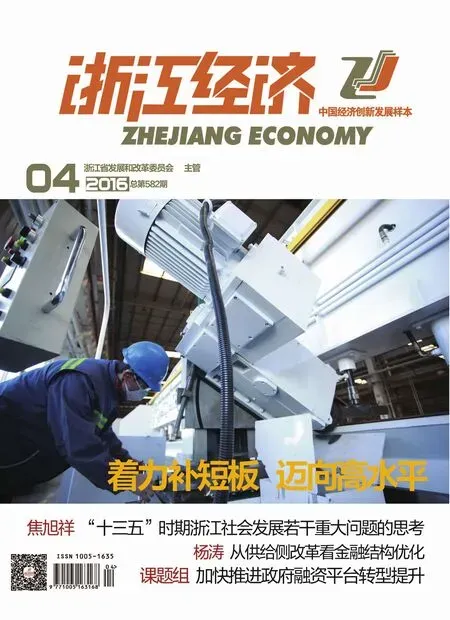大數(shù)據(jù)智庫
王寧江
·首席論衡·
大數(shù)據(jù)智庫
王寧江
回顧一年前啟動“首席論衡”欄目的約稿,很是誠惶誠恐,怕辜負刊物和讀者的期待。首篇寫的是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算是有感而發(fā),對智庫建設泛泛地談談,寥寥幾句個人的觀點。一年后,在大數(shù)據(jù)的風口之上,對于原先隱隱約約定位于大數(shù)據(jù)建新型智庫,又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
未來新型智庫的發(fā)展,大數(shù)據(jù)至少可以有兩方面定位,發(fā)揮兩方面作用。一個層面,大數(shù)據(jù)作為新型智庫的支撐。兩辦《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文件中有明確表述,評判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基本標準之一就是,要具備有功能完備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統(tǒng)。如果大數(shù)據(jù)在智庫中是輔助支撐的定位,那么大數(shù)據(jù)和大數(shù)據(jù)技術更多地是發(fā)揮工具的作用。另一個層面,圍繞大數(shù)據(jù)建設新型智庫。大數(shù)據(jù)則是智庫的核心與基礎,大數(shù)據(jù)產品就是智庫的主營,以此,大數(shù)據(jù)和大數(shù)據(jù)技術在智庫中的作用將是不可替代的。我們姑且把這一類智庫稱為大數(shù)據(jù)智庫。
既然稱為大數(shù)據(jù)智庫,那還是需要一些特征條件的。一是大數(shù)據(jù)智庫要有數(shù)據(jù)庫。傳統(tǒng)的文獻庫,想必任何一個智庫都不會忽視的。大數(shù)據(jù)智庫掌握的數(shù)據(jù)資源不能僅局限于傳統(tǒng)的文獻庫,還應涉及政務數(shù)據(jù)庫、商務數(shù)據(jù)庫、民調數(shù)據(jù)庫、輿情數(shù)據(jù)庫、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庫等。這些大數(shù)據(jù)可能源自互聯(lián)網,也可能源自局域網或相關信息化系統(tǒng)。二是大數(shù)據(jù)智庫要有大數(shù)據(jù)分析方法。數(shù)據(jù)分析挖掘有數(shù)據(jù)理解、數(shù)據(jù)準備、建模、評估以及部署等幾個階段,在建模和評估階段離不開分析工具、算法研發(fā)和使用等。三是大數(shù)據(jù)智庫要有大數(shù)據(jù)產品。無論是政務主體還是商務主體,大數(shù)據(jù)產品主要是要圍繞咨詢對象和咨詢需求來設計,可以是純大數(shù)據(jù)產品,也可以是為智庫的決策咨詢報告提供量化的結論支撐。
大數(shù)據(jù)庫智庫要聚集一批大數(shù)據(jù)復合型人才,人才是大數(shù)據(jù)智庫生存和發(fā)展的關鍵和基礎。數(shù)據(jù)可以交易,工具也可以購置,而人才是最緊缺的,而且大數(shù)據(jù)智庫對復合型人才的要求更高。
一是思維方式要復合,即實現(xiàn)傳統(tǒng)思維方式和互聯(lián)網思維方式的復合。傳統(tǒng)思維方式有幾個特點,如系統(tǒng)性和整體性、感性和悟性等。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孺子百家的各學術思想成果,無不寥寥幾筆,靠悟、理解和發(fā)展,影響著中華民族幾千年。而互聯(lián)網思維典型的特征便是共享和開放、平臺和協(xié)同、生態(tài)和融合。傳統(tǒng)思維和互聯(lián)網思維之間有些是共通的,有些確實是顛覆性的。
二是數(shù)據(jù)理解要復合。既要有專業(yè)需求的視角,也不能太超越目前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實現(xiàn)條件,這一點,有點類似于IT序列的系統(tǒng)分析員角色,這里姑且稱為數(shù)據(jù)理解。所謂復合就是要把兩個不同語言體系打通,翻譯成“普通話”,然后實現(xiàn)交流。從大量的信息化系統(tǒng)建設實踐看,業(yè)務需求和技術設計之間確實存在“語言不通”的情形,業(yè)務需求不知道如何釋義他所要的功能,IT人員聽不懂業(yè)務需求究竟想要實現(xiàn)什么功能,于是兩者之間,總是存在隔閡。大數(shù)據(jù)時代,需要復合型人才在源頭上突破這個瓶頸。
三是專業(yè)要復合。復合型人才最好有與業(yè)務需求對應的專業(yè)和大數(shù)據(jù)技術專業(yè)的學科背景。智庫團隊可以通過不同層次、專業(yè)、年齡等人才結構實現(xiàn)團隊復合化,但如此,還是會在內部造成不同層次之間脫節(jié),打造復合型人才是破解復合化的最好方式。以前總是在講,高校要打破“近親繁殖”,其實,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獨立的學術體系,也有自己的邏輯表達習慣,需要復合型人才在學科之間“穿針引線”。
四是分析方法要復合。主要是定性和定量要結合。人工智能可以實現(xiàn)無人駕駛汽車,卻無法取勝圍棋,這就是人腦的勝利。只要有模糊性存在,定量替代不了定性;憑借感覺、經驗來衡量判斷,是人腦定性之所長。同樣,定性分析會受分析員的情緒和情感、有限的記憶存儲量、有限的分析維度、有限的勞動強度等方面制約。大數(shù)據(jù)技術發(fā)展之后,定量技術可以在無限量的大數(shù)據(jù)之中通過無限的維度、不間斷地進行定量分析,挖掘隱藏在數(shù)據(jù)中的秘密,這是定量的優(yōu)勢。只有實現(xiàn)定量和定性結合、優(yōu)勢互補,才能發(fā)揮最大價值。當然,在現(xiàn)階段的經濟管理和社會治理領域,定量和大數(shù)據(jù)技術更多地是為定性和決策咨詢服務。
作者為浙江省經濟信息中心副主任、浙江省信用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