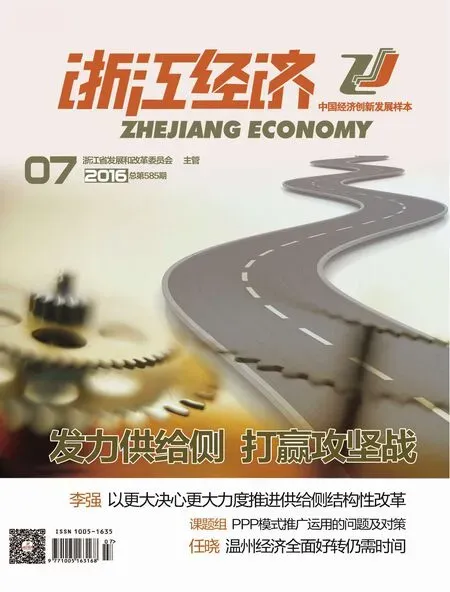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綠色低碳發展
鮑健強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綠色低碳發展
鮑健強
堅持綠色低碳發展導向,以科技創新創業為載體,破解生態環境約束,實現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認識、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客觀要求,也是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必然選擇,更是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有效途徑。眾所周知,供需關系是傳統市場經濟中的核心問題,但是如何駕馭供需關系,把握市場經濟規律對于帶有計劃經濟印跡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而言始終是一個時代命題,浙江也不例外。尤其是面對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全球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的挑戰,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模式和機制也悄然變化。科技創新正在顛覆傳統市場經濟的供給側管理模式,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的供給創造新需求、新市場、新消費,傳統的“需求(市場)決定供給”轉向“創新供給激活消費(市場)”的新階段。而隨著資源環境對傳統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約束力的不斷增強,對市場供給側提出了綠色低碳發展的強烈要求,它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盡管本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期望清除制度性障礙、釋放改革紅利、提供有效供給、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增長率,但有一個大目標是明確的,即要實現中國經濟健康、有序、協調、綠色發展。
供需錯位和資源錯配引發生態環境的憂慮
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供需關系也由“供不應求”向“供過于求”轉變,尤其是眾多傳統產業出現產能嚴重過剩。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鋼鐵產能約12億噸、煤炭產能約57億噸、水泥產能約27億噸,而市場需求鋼鐵為8.03億噸、煤炭為41.4億噸、水泥為23.5億噸。這種“供需錯位”和“資源錯配”,不僅反映出中國經濟的“供需關系”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脆弱和“失靈”,而且也引發人們擔憂傳統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過度發展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損害。大面積的區域和城市霧霾、大范圍的水環境質量下滑,加深了對供給側粗放型產業結構、高碳化能源結構的反思和重視。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及時而精準的,改革將更多地注重市場供給體系的結構、質量和效率的協調發展,矯正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供需失衡,并把綠色發展提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方向。
中國經濟體量大、市場規模大、消費需求大,“供需錯位”是結構性和階段性的,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供需市場的整體均衡與協調。按照國際經驗,人均GDP在8000-10000美元時,消費需求將從低端消費向高品質消費、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從物質類消費向精神類消費轉變,如創意文化、旅游休閑、健身養生、生活服務、醫療服務、健康服務等消費需求和市場不斷擴展,對生態環境質量的期望和要求不斷提高,而供給側顯然跟不上經濟社會和消費市場的變化。提出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應該有加有減、有乘有除,“加法”是通過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補齊老百姓生活和生態環境上的“短板”;“減法”是通過政府簡政放權,為企業降低成本,給市場微觀主體松綁減負,激發企業活力和創造力;“乘法”是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培育創新動能,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帶來的“乘數效應”;“除法”是以生態優先、綠色引領為導向,分業施策、多管齊下去除落后產能和過剩庫存,實現經濟結構的綠色化轉型、產業結構的低碳化升級。
創新供給與創新驅動優化資源配置,轉換發展動能
創新供給與創新驅動是中國經濟新舊動力轉換的核心問題,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問題。創新供給包含了“三大創新領域”,即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動能創新。
制度創新是通過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確保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充分發揮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的有效作用,處理好市場“無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之間的復雜關系,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破解“供需錯位”和“資源錯配”的關鍵環節。通過調整落后產能、壓縮低端產品,補齊環境短板,實現綠色發展。
科技創新是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要素效率提高的根本途徑,對推動產業升級、發展新興產業、培育新供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國硅谷科技創新成功的經驗表明:現代科技產業化的“顛覆性”增長和“爆發性”發展的邏輯是“始于技術,源于市場,成于資本”。即美國資本市場云集著眾多風險投資人,他們用敏銳的市場眼光,捕捉下一個帶來科技變革的新技術和新產業,如微軟(Microsoft)、蘋果(Apple)、谷歌(Google)、亞馬遜(Amazon)、特斯拉(Tesla)、優步(Uber)等高科技企業在創業期都受資本市場的青睞而得以飛速發展。科技與金融的深度交互和融合,培育和提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是激活消費、創造需求、引導市場的最重要的路徑。
動能創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要求。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中,加快培育新動能、大力發展新經濟,把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轉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要素效率提高上來。中央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了創新、創業、創造潛力,催生了顛覆性新技術,推動了新產業、新業態的快速發展。因此,應通過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推進“中國制造2025”與“互聯網+”融合發展,一方面改造提升傳統動能,運用信息網絡等現代技術,推動生產、管理和營銷模式變革,有序化解過剩產能,減輕生態環境壓力;另一方面,打造培育創新動能,做大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新興產業集群,重塑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打造動力強勁的發展新引擎。
綠色低碳發展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堅定取向
綠色低碳發展是未來中國社會和百姓的最大需求和期許,資源環境的強約束也直接影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價值取向。遵循綠色發展理念,通過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強化對低端供給側發展的約束,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綠色發展導向,形成低碳循環和減量化的經濟發展方式,形成綠色、低碳、環保的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滿足人類需求無限性與資源、環境、生態供給可持續性中尋求最優最佳配置。以生態文明建設為指導,以綠色發展為理念,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最小的能源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取得最大的產出效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綠色低碳產業上有作為、有發展:
加快新能源汽車發展。尤其是純電動汽車的發展,實現了傳統汽車工業的低碳革命和綠色轉型,以減輕城市霧霾和生態環境的壓力。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發展早、起點高,與發達國家處在同一技術水平和發展水平,應該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視關注的領域。
發揮中國高鐵的技術優勢,實現互聯互通。今年春運期間,僅高鐵承擔的出行人數就達3.03億人次。高鐵是容量大、速度快、安全高效、綠色低碳的交通方式和低碳交通、綠色出行的有效載體,它能壓縮傳統汽車的使用規模,減少汽車尾氣排放,與之相應的地鐵也是大眾化的低碳交通工具,但這方面的供給仍滿足不了現實需求。
發展低碳能源技術和產業。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發揮中國核電技術優勢,積極發展核電,用清潔、低碳、綠色能源替代傳統化石能源。加大新能源供給側的改革力度,消除太陽能、風能、地熱能、潮汐能、生物質能開發的技術障礙和制度障礙,積極推行分布式能源、智能電網、能源互聯網建設,實現2020年非化石能源(新能源)占比15%的目標。
發展綠色制造業。以“中國制造2025”為指導,重視傳統制造向綠色制造轉型,形成綜合考慮環境影響和資源效益的現代化制造模式,實現產品從設計、制造、包裝、運輸、使用到報廢處理的整個產品生命周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資源利用率最高的目標。
發展信息經濟產業。以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滲透、融合、提升和轉型,具有“四兩撥千斤”的功能。“互聯網+”行動計劃能大幅提高市場要素的配置效率,信息經濟、智慧應用給各行各業帶來深刻變化,尤其是在智慧低碳城市建設中大有可為。
發展綠色生態農業。眾所周知,“民以食為天”,過去是“吃飽”,現在是“吃好”,供給側已發生許多新變化,要求綠色生態農產品的供給呼聲更強烈。生態環境好、重視綠色生態農業成為一種優勢、一種品牌、一種價值,這也體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增強預見性,找準出擊點,把握平衡度。盡管改革千頭萬緒、路徑千變萬化、目標千差萬別,但是必須堅持以綠色低碳發展為導向,以科技創新創業為載體,破解生態環境約束,實現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作者為浙江工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