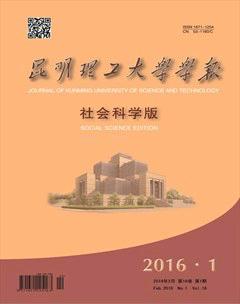生命的自在意蘊與倫理本位
摘要:生命既是本體的又是形成的。在本體世界,生命原發存在,其自在性和他者性內在地統一,并表征為感性的倫理意蘊。在形成世界,生命繼發存在,其潛在倫理意蘊必彰顯為現實倫理要求,并因為遭遇利害而敞開三種可能性朝向。但是,這些體現不同可能性朝向的倫理要求只能在生命創造之“生命的產物”這個層面展開,根本無助于消解生命自由與生命平等之間的矛盾和生命的產物控制與反抗控制之間的沖突。生命倫理學誕生于這一雙重拉鋸戰中,并必然肩負以下使命:一是在人的形成世界中如何引導生命和呵護生命;二是在人的本體世界中如何實現生命的自在與自由。由此,生命倫理學必然開辟出生命本體的倫理學、生命形成的倫理學以及能夠整合二者的生命倫理方法學。
關鍵詞:生命倫理;自由的平等限度;生命本體的倫理學;生命形成的倫理學;生命倫理方法學
中圖分類號:B82-0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1254(2016)01-0001-12
Lifeinitself Implication and Ethical Ontology of Life:
A TriDimensional Bioethics Research
TANG Daixing
(Polit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Sichuan, China)
Abstract:Life is both ontological and becoming. In the ontological world, life is the origin being, so its lifeinitself and otherness are internally unified and characterized as sensible ethical implication; in the becoming world, life is a secondary being, so its potential ethical implication will ?emerge as real ethical requirements, and open up three possible orientations because of the interests encountered. However, these ethical requirements reflecting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can only develop on the level that life creates “lifes product”, and they cannot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reedom of life and equality of life, and conflict between lifes product controlling life and lifes rebellion against the control. Bioethics came into being in this "double seesaw" battle, and it is apt to bear two tasks as follows: (1) how to guide and protect life in the world of human becoming; (2) how to realize lifeinitself and freedom of life. Thus, bioethics will give birth to ethics of life ontology, ethics of life becoming, and the methodology studies with these two integrated.
Keywords:bioethics; limit of freedom; ethics on life ontology; ethics on the life becoming ; methodology studies of bioethics
在對生命倫理學有限智識中,我認為何倫教授對生命倫理學的基本判斷頗有道理。他認為“生命倫理學是理解道德哲學的一個小小的窗口,抑或可以說是反觀理論倫理學的一條路徑。起碼,我從生命倫理學領域可以窺視到當代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理論與實踐正在發生的轉變,感受到生命倫理學作為這種轉向的先驅。”[1]我對生命倫理學歷來心懷虔敬,最終理由可能亦在于此。因為有了生命倫理學,默默消長不息的生命才獲得凸顯,并由此使生命問題本身成為當代文明探索中的重要內容。雖然如此,生命卻并沒有在生命倫理學喧嘩的世界被照亮:生命倫理學在銳意張揚生命的過程,在無形中遮蔽或消解著生命。這是因為生命倫理學雖然脫胎于醫學倫理學,但它所關注的決不僅僅是生命的活力狀態(即健康或疾病)問題,生命的權利(比如墮胎、安樂死、自殺),生殖技術或生命的保障性生存等問題,這些問題雖然重要,卻僅是生命的形成問題,而不是生命的本質問題、本體問題。有機論哲學家懷特海認為:“歐洲哲學傳統最可靠的特征是,它是由關于柏拉圖的一系列注釋所組成的。”[2]柏拉圖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原創地位,是在于他區分了本體的世界(world of being)和形成的世界(world of becoming):本體的世界是世界的恒常狀態、不變狀態,表現為普遍、永恒、真理;形成的世界是世界的流動狀態、變化狀態,表現為具體、短暫、易逝。生命是構成世界的最精彩的部分,它構筑起本體的世界和形成的世界,并分領這兩個世界。對生命予以倫理審查,當然要關注生命的形成問題,但更要注目生命的本體問題,只有生命的形成獲得生命本體的照亮、生命的本體實現著生命的形成,生命倫理學才可實現對生命本身的解蔽而成就自己。
一、生命的自在意蘊
何倫曾在《生命的倫理困惑:臨床生命倫理學導論》中指出:“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不能只是因于應用規范倫理學的理論框架,僅著力于應當的謀劃,急于規范的建構。因為對生命的思考和對生命現象所呈現出來的道德問題的反觀,離不開元倫理學探究一般問題的努力。特別是在價值多元化的社會里,人們對什么是善并不是自明的,在許多時候,善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對善的理解不僅因時因事而異,而且因人而異。生命倫理學如果不去努力尋求關于善的共識,則有關應當行為的謀劃很可能是脆弱的。所以,生命倫理學的實質是兼有規范倫理學和非規范倫理學的性質。”[3]此論極對,但客觀審視,“善”亦不是生命倫理學的根本問題。因為“善”可以構成生命倫理學的尺度構建問題,卻不構成生命倫理學得以構建的邏輯起點,更不能以此而解決生命倫理學得以建立的最終依據等問題。所以,在生命倫理學中,比“善”更重要、更根本、更具有決定性和指導性作用的恰恰是“生命”及其與倫理的本原關聯問題。
簡要地講,生命是一種充滿自“活性力”的有機體[4]。以此審視“生命倫理”概念,首先意指生命體現其倫理訴求,其次意指從倫理角度審視生命。致思“生命倫理”的必要前提,是重新理解“倫理”。在西語中,“倫理”概念源于希臘語ethos,其辭典意義是指品性與氣稟、習慣及風俗。在漢語中,“倫者,輩也”,意指血緣關系,并有“等級”之蘊含。血緣不僅把人與人之間的生存關系明確地確定在各自應居的位置上,使之獲得了等級性,而且也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成獲得了“類”的分明的界線性,即有血緣關系的人不僅構成了“輩份”,也構成了“一類”——血緣之內是一類,血緣之外是另一類。由“倫”概念產生的原初涵義可以看出,在人間,作為以血緣為本質規定的輩份關系和類聚關系的形成,卻并非人力,而是自然使之:“倫”作為人際關系的原初倫理涵義恰恰是由自然生成的,所以“倫”一詞的原初語義里面蘊含“理”,即自然之理。這個自然之理就是血緣輩份和類聚,即按照血緣輩份這一自然之理締結成血緣人際關系,并遵循“物以類聚”這一自然之理締結成非血緣的社會人際關系,前者是初民時代的主要人際關系形態,后者是國家社會的基本人際關系形態。后來“倫”字走向與“理”的合成而生成“倫理”概念,其內在的語義聚合力就在于此。《說文》和《辭海》都認為“理”之原初語義是“治玉”,意即運用特定的模式和方式將天然之璞打造成人意化的美玉、玉石,后來才以此而賦予“理”這個概念以整治、治平、條理、道理、規律等引伸語義。因而,當“倫”與“理”合成為“倫理”概念時,意指人與人之間的人倫關系締結應該遵循自然之理。遵循自然之理而締結的人際關系,就是倫理(道德或美德)的人際關系[5]。
概括上述內容,所謂倫理,就是蘊含利害取向的人際關系。過去,我們一直把“人際關系”定位為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我們的倫理學從古到今都是建立在這一基本的認知基礎上的。其實,這種認知理念很狹隘,它遮蔽了對人際關系的本質的認知。認真說來,倫理因人的緣故才獲得產生:倫理乃人之社會的造物。這是因為:第一,倫理乃是人組構社會的展現,人是倫理構建的主體,沒有人,不可能有倫理,即使產生出倫理,也無用武之地;第二,社會是倫理產生的真正土壤,只有當人組建起社會時,倫理才產生,沒有社會,倫理亦無從產生。所以,組構社會才構成倫理生成的前提。然而,社會的組構者當然是人,但人組構社會需要兩個條件,即人和物:人和物才使社會成為真實的社會,只有物,或者只有活的工具而沒有人的社會,往往缺乏真實性。因為,人的生存的最大需要是對人和物的需要。進一步看,人對物和人的需要,并不構成人的社會,只有當人對所需要的物和人予以合意的安排時,才構成人的社會。相應地,人對物和人的需要也并不構成倫理,只構成倫理產生的可能性條件;只有當人對所需要的物和人予以某種價值訴求的安排時,才產生出倫理。所以,倫理既是人安排物和人的獨特方式的展現,又是人對物和人進行安排所生成的實際關系。由此,體現倫理訴求的人際關系,不僅僅是人與人的關系,它還指人與群、人與社會、人與物、人與地球生命、人與自然的關系[6]。這是我們理解生命倫理的必要倫理認知。
在獲得正確的倫理認知基礎上,致思“生命倫理”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到底是人賦予給生命以倫理?還是生命本身蘊含倫理?如果屬于前者,那倫理就外在于生命,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給生命附加上任何內容;反之,如果倫理乃生命的內在呈現,那么人就須得尊重生命本身的倫理訴求。倫理到底是外在于生命的還是生命的內在訴求,表面看來好像并不重要,實質上卻是根本,因為它體現兩種根本不同的生命倫理來源,并由此形成看待和理解生命倫理的不同出發點、不同視角、不同視野、不同方法。比如,假定生命的倫理是外在于生命的,是人的覺醒和需要賦予給生命的,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據將生命裝進倫理之框中,完全按照人的意愿來處置生命。人類文明前進的腳步從遠古邁向當代的歷史進程中,我們不僅可以任意處置人的生命,比如開動國家機器的戰爭、個體性殺人、死刑罪以及對安樂死的鼓吹等,都是任意處置人的生命的方式;不僅如此,我們更可能任意地處置地球上的任何生物,比如各種形式的生物實驗、動物實驗、捕殺野生動物。為了物質幸福和生活快樂,我們可以不顧一切地改造自然、掠奪資源、蹂躪地球環境,由此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許多物種快速滅絕,這就是我們任意處置地球生命的基本方式。我們何以這樣既快樂地任意處置地球生命,又如此輕松地任意處置人的生命?是因為我們有人類中心論的價值評價體系和判斷尺度,這套價值評價體系和判斷尺度卻有人本主義的倫理理念、道德原理為支撐。人本中心的倫理理念和道德原理引導了我們現行的生活倫理,形成了我們普遍遵從的道德規范甚至美德訴求。人本中心論的倫理理念,就是“人是萬物的尺度”(普羅泰戈拉),就是人的“理性為自己立法”,人的“知性為自然立法”。由此,相對自然和地球生命論,倫理、道德是人類按照自己的愿意、并以自己為尺度而創制的,它只適用于人類,更具體地講,只有人類才有權向地球生命和自然世界要權利、要利益,根本不可能存在地球生命和自然世界向人類要權利、要利益的可能。這就是生態學和環境哲學領域圍繞動物有無權利而爭論不休并最終不了了之的認知根源。相對人類社會內部論,倫理、道德最終淪為強權的道德,柏拉圖曾認為公正就是強權、亞里士多德主張不平等的公正和公正的平等,以及現代社會中許多國家由政治倫理來統攝普通倫理、用意識形態的道德來取消公民道德,其根源亦在“生命的倫理來源于外部”,而不是來源生命本身。反之,假如承認倫理是生命的本性要求,那么,我們只能尊重生命的本性來確定倫理準則。比如,面對安樂死的問題,如果要去倡導、鼓吹或普及安樂死,那就是違背生命之自身本性,也是有違倫理的。因為每個生命都不是從他自身得來,任何個體生命都是得之于天、受之于地、承之于(家族、種族、物種的)血緣,最終才形之于父母:每個生命都是天地神人共創的杰作,亦是眾生合樂的存在形式,所以每個人都有呵護自我生命的責任、經營自我生命的權利,卻沒有處置自我生命的權利——其他人更是如此,哪怕是政府、法律,也沒有處置生命的權利,這或許是許多國家取消死刑的最終理由。個體生命當然要接受社會的規訓,但更要接受自然律的引導——要經歷現實,也要趨向于未來,更要擔當起過去。在現實的聚光燈下,個體生命與個體生命之間各自所承受的苦樂可能完全不同,但以生命之歷史本身為鏡,每個生命所經歷的苦樂都是相等的:付出與獲得、索取與享用……永遠對等,這是自然的取予法則,也是生命的倫理律令。安樂死將尊重生命、減輕其痛苦為根本理由,其實質卻是既以逃避生命必擔之責務的借口,也是違背生命本身的倫理律令,更是對自然法則的漠視。
生命的倫理到底來源于生命自身,還是來源于人的賦予,要對此做出清晰的判斷和正確的選擇,需要回到生命本身。西美爾講道:“只有生命才可能理解生命。”[7]37只有在通過生命來理解生命的基礎上,才可能通過生命來理解倫理——生命本身是理解生命和理解倫理的必需橋梁。
從生命理解生命,所涉及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生命的來源問題,即生命從何處來?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有宗教的和科學的兩種想象方式。在宗教的想象方式中,生命來源于上帝:上帝是生命的生命,但其前提是上帝是自然的自然。在《舊約全書·創世紀》中,上帝是原自然、原生命、原創力。上帝原創的首要成果是天地山水,然后是生命萬物;最后是人。在科學的想象方式中,生命來源于進化,即生命對生命的進化,其前提卻是自然對自然的進化——只有在自然對自然的進化之旅全面展開的進程中,才能逐步實現生命對生命的進化。這其中仍然存在著原自然、原生命、原創力的問題。
在過去,宗教與科學始終在殊死搏斗,但客觀地看,這種殊死搏斗不過是人的無知觀念所為。撇開人的無知的偏執觀念,宗教與科學在其形成意義上雖各不相同,但在本體意義上卻是同構的。這種同構不僅表現在如上方面,更表現在對生命的等級性設定上:在宗教那里,上帝的創化由整體到具體、由低階向高階方向展開,其創化的最高成就是人這個生物的誕生,其后就是人的墮落和自救。在科學那里,世界的進化由一般到具體、由低階向高階方向展開,進化的最高成就仍然是人這個生物的誕生,其后繼續進化而上升為智力人、現代人、文明人。這一進程在形成性層面,是人的上升,但在本質層面,卻仍然是墮落和由此引來的自救,這就是當代人類的境遇。
宗教和科學,對生命來源的不同想象方式,無意間達成本質上的同構,表明人的想象在最終意義上不能脫離存在本身:在形成世界中,生命來源于他者;但在本質世界中,生命來源于自己。在宗教那里,上帝創造生命的前提是上帝創造自我:上帝本身就是生命,是本原的生命。在科學那里,自然進化生命的前提是自然進化自我,這不僅在生物學那里如此,在現代天體物理學那里也是如此:宇宙大爆炸的前提是極小體積、極高密度、極高溫度的“奇點”,這個“奇點”卻是自生成的。
生命來源于自己,意味著生命必以自己為要求,即生命必以自己為出發點,并以自己為目的。生命以自己為出發點和目的的根本前提,是生命的存在本質是生命本身,具體地講,是生命的本性。所以,生命以自己為出發點和目的,講的是生命必須按照自己的本性來確立自己的出發點和目的。這在宗教的想象性表述中,生命本性乃上帝意愿,在上帝的意愿中,生命的起點也是生命的歸宿、生命的動機亦是生命的目的,二者原本為“一”。人這個生命在無意中違背上帝意愿而墮落成為“人”,其永劫的自救不過是對生命本性的艱難回歸。在科學的想象方式中,生命本性乃自然本性,生命的起點和歸宿、動機與目的同樣是一個東西,人類按照科學的引導踏上文明發展的道路,必然迫使生命沉淪于科技化生存的死境之中,其所背負的永劫的自救仍然是對生命本性的艱難回歸。
宗教和科學對生命來源的不同想象方式,均來自于生命存在及其敞開存在的歷史:生命誕生于偶然,偶然誕生的生命卻使因生而活并為活而生且生生不息的本性成為必然。這種必然性敞開的形成世界及其本質命運,卻為宗教和科學所分別直觀并進行不同的描繪:在生命向人的世界的形成過程中,必然牽動其無機體(自然)一同沉淪——沉淪本身意味著生命自救的啟航,這是生命倫理學得以誕生的內在契機和最終原動力。
生命以自己為要求和目的敞開自身的軌跡,之所以構成宗教和科學的想象方式,最終還是源于生命本身。因為生命既來源于自己,更來源于他者。生命來源于自己,這是生命的發生學,并形成生命的原發存在;生命來源于他者,這是生命的存在論,并形成生命的繼發存在。從存在論或者說繼發存在的角度觀之,生命的他者性之實質表述,就是生命始終得之于天、受之于地、承之于(物種、種族、家族、家庭)血緣,并形之于父母。概括地講,生命誕生于天地神人的合樂,這就是以自身之內在規定性為本體的生命的他者性。
生命的他者性,表明生命的生存本質是他者性存在。生命的他者性,仍然來源于生命的自身性。
首先,生命的自身性的首要含義,就是生命的自在性,即生命按自己的本性要求而存在并敞開其存在。這對每個生命物種、每個物種生命個體來講,都沒有例外。這種無一例外的本質同構和同等要求,構成了生命存在的絕對平等。因而,生命的自在性,必以他生命的自在性為本來要求。
其次,生命的自身性亦是生命的個體性,這是所有生命都無法改變的存在事實,這一存在事實要求生命與生命之間必須平等。生命的個體性存在表明生命是有邊界的。這種邊界蘊含著一種內在規定,即生命與生命之間必存在著空間距離。這種空間距離的大小,并不具有絕對的規定性,卻有最低的限度要求,即任何一個生命得以自在的最低空間距離是不容縮小的,更是不能取消的,否則,生命就難以獲得自在性存在,生命的自身本性就將遭受侵犯。生命的個體性存在還表明生命是自我限度的。生命的自我限度表現在他自在的限度性,生命的自在始終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自在生命。所以,生命之于自由亦是相對的。從本質論,生命自在的相對性和由此形成的生命自由的相對性,均源于生命之自身力量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體現為每個生命都不能憑一己之力而存在,更不能憑一己之力而自在存在和自由存在,他必須走向他種生命、走向他物和他種存在,并憑借他者之力而實現自身存在。所以,作為個體生命,其存在和生存最需要的是其他生命、其他物、其他存在。簡言之,生命最需要的是他者。
再次,生命的自身性就是生命對于他者的需要。生命對他者的需要,構成每一個生命存在的最低條件。生命對他者的需要的首要前提,是生命的他者性本身,即生命得之于天、受之于地、承之于血緣、形之于父母的事實本身,這也構成了“生命最需要的是他者”的絕對前提。
二、生命的倫理本位
從起源講,生命既來源于自己,也來源于他者;從原發存在論,生命既是自在的,也是他在的。生命的雙重來源和雙重存在方式,均張揚出生命的內在倫理意蘊。生命的自生性和自在性,體現了生命的為己——為己,這是生命誕生和存在的最終依據、最終理由,也是生命蘊含倫理意趣的內在方式;生命的他生性和他在性,體現了生命的為他——為他,這是生命誕生和存在的絕對前提,也是生命彰顯其內生倫理意蘊的外在方式。
生命的原發存在必然朝向繼發存在方向敞開,這就是生命的生存。生命在原發存在境域中,其全部的倫理意趣均蘊含于生命之中而待發;生命從原發存在境域中迸發出來向繼發存在領域敞開,其蘊含在生命之中待發的倫理意蘊必然因為生存利害的激勵而獲得其現實性——在生命敞開自身的生存境域中,其潛在倫理意蘊變成了現實的倫理要求,并且這種現實的倫理要求構成了生命敞開自身存在實施生存的本體規范。由此,倫理獲得了生命本位。
在生存境域中,倫理對生命的本位確立,實際上源于如下因素的激勵:
首先,原發存在境域中的潛在倫理意蘊上升為生存境域中的現實倫理要求,其主體性前提是生命世界中人這一物種從一般生命形態變異為人質化的生命形態,即從物的生命變成人的生命,其實質性標志就是他獲得人質意識并不斷自我強化其人質意識。人從動物狀態獲得人質意識并不斷強化其人質意識,這是一個形成人的世界的過程。這一形成過程實現了三個方面:首先是產生對象性意識和分離觀念,然后是在此基礎上生成目的性意識并產生自我設計意愿以及其將此意愿轉化為實際生存力量的努力。
其次,以人質化意識為武裝的生命,一旦實施其目的性意識和自我設計意愿,則必然要遭遇利害,由此利害逼促生命緊急應對。這種基于生命本性的啟動而敞開的緊急應對,既可采取趨利避害的方式,也可采取趨害避利的方式。在實際生存利害面前,生命本性朝向趨害避利方向敞開,無論有無其度,都合倫理。這是因為趨害避利的方式敞開生命本性,是生命實現生殖生命的基本方式,也是生命實現生殖所敞開的基本狀態。與此不同,生命本性朝向趨利避害方向敞開,則有度的要求性:趨利避害有其度,則合倫理,因為有限度地趨利避害,既是生命實現對自己生殖的方式,也是生命實現對生命生殖的方式,更是生命實現了對自己生殖的同時實現了對生命生殖的共贏狀態。
再次,在生存之域,生命遭遇利害并被逼促而選擇,其被逼促選擇趨害避利、有限度的趨利避害或無限度的趨利避害這三種方式,呈現生命本性敞開應對生存的三種可能性。而形成生命本性敞開應對生存的三種可能性的根本原因,卻是生命的自為性。如前所述,生命的自為性是從自在性和他者性兩個方面得到規定的。
生命的自在性要求生命必須追求自由,并且這種追求是絕對的,否則,生命的自在性將遭遇瓦解。與此不同,生命的他者性要求生命必須持有平等,并且這種持有亦是絕對的,否則,生命的他者性將遭遇消解。生命自在性所形成的絕對自由取向和生命他者性所形成的絕對平等取向,必然形成對立、矛盾和沖突。這種對立、矛盾和沖突的具體情景定義,就是實在的利害。對利害的權衡與選擇,就是其絕對自由與絕對平等之對立、矛盾、沖突的消解。它有下列三種基本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以趨害避利的方式消解生命自由與生命平等之對立、矛盾、沖突,其實質是以犧牲生命自由而實現生命平等,即“我運用自由美化你的鼻尖”。“我運用自由美化你的鼻尖”,是指放棄本屬于我的生命自由來實現你的生命平等。這種以趨害避利的方式來消解生命自由與生命平等之對立、矛盾、沖突的方式,就是美德方式,它的實質是付出自我生命自由的代價來實現他者生命平等,但其前提必須是:付出自我生命自由的代價本身是自由的,即我要放棄生命之自由來幫助他者(比如他人、他物)生命的平等之全過程,從動機生成、行為手段或方式選擇以及行為展開所努力達到的最終結果:其一,必須是自主、自為的;其二,這種自主、自為的付出自由的行為結果,不僅實現了他者的生命平等,同時也實現了自我之自由;其三,這種以犧牲生命自由而得來的新自由,必須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自由,是生命內在化充盈的自由。
第二種方式,是以有限度的趨利避害的方式消解生命自由與生命平等之對立、矛盾、沖突,實質就是生命自由與生命平等之相互妥協,即在某個雙方可接受的空間之“點”上實現互利和共贏,這就是“我的自由止于你的鼻尖”。“我的自由止于你的鼻尖”,首先是指人的生命自由是有限度的,或可說是有邊界的。這種限度和邊界形成于:其一,每個人都是個體生命;其二,每個個體生命都有自由的本性;其三,人的自由本性都可在自然狀態下得到無限度的發揮;其四,任何個體生命一旦以其本性的方式無限度地釋放生命的自由時,必然要遭受阻礙,這種阻礙恰恰來自于另外的生命及其自由。如果無視這種阻礙,將可能遭遇比自由更大的傷害。其次,“我的自由止于你的鼻尖”是指人的生命自由的限度不是由自己來界定,而是由自己之外的他者來界定。因而,我的生命自由的空間必須以“他人的鼻尖”為界,反之,他的生命自由的空間亦必以“我的鼻尖”為界。任何一個人的生命自由,一旦跨過了這個界限,即當你的生命自由觸及到了“他人的鼻尖”時,不僅僅意味著你侵犯了他人的生命自由,更意味著你的生命自由也面臨喪失。一個人敞開其自為的生命自由的方式多種多樣,比如吃飯的自由、睡覺的自由、說話的自由、跳舞的自由、談情說愛的自由,以及揮動拳頭的自由或者說謊的自由等,其最后的空間邊界或界標就是“他人的鼻尖”。比如,中國大陸跳廣場舞的自由曾經為媒體所追捧,而且這種自由行為也為生活大眾所容忍。但是,這種自由卻折射出了國民的最低生活素質問題,而且也不同程度地體現了一種群體性的不道德或反道德,因為跳廣場舞的自由不同程度地逾越了他人的“鼻尖”。“我的生命自由止于你的鼻尖”揭示了生命倫理之本質:生命倫理的存在本質是生命利益,生命倫理的生存本質是生命權利,生命倫理的行為本質是生命責任,生命倫理的行為本質是生命對生命的權責對等。它具體表述為:你要獲得一份生命的自由,你必須為此而向與你的生命自由相關的他人、他種生命擔負維護其生命自由的責任,這就是生命平等。所以,“我的生命自由止于你的鼻尖”還揭示了生命平等的實質是“不損”,它的表現形態是生命與生命之間分享自由的共贏,這種生命與生命的共贏,就是生命道德。
第三種方式,是以無限度的趨利避害的方式消解生命自由與生命平等之對立、矛盾、沖突,實質就是生命自由以絕對方式實現了對生命平等的取消,這即是“我的自由削平你的鼻尖”。“我的自由削平你的鼻尖”,這是一種反生命道德的自由。這種反生命道德的自由,體現極端的自我主義,也是絕對的自私主義。它的基本理念是:世界是“我”的,“我”才是世界的主人,因而一切都必須服從于“我”,一切都應該為“我”讓路。它的行為表現是:只要“我”高興,干什么都是對的,做什么都是好的。因而,任性而為,本身就是自由之目的。為了實現任性而為的自由,只講目的,不講手段,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我的自由削平你的鼻尖”的行為準則[8]。
在生存之域,生命本性因為利害激勵敞開三種可能性朝向,最終使生命本身獲得兩種形成狀態,即生命固守其倫理本位的活力狀態和生命脫嵌倫理本位的非活力狀態。生命固守其倫理本位,就是其原發存在的倫理意蘊自我形成為繼發存在的倫理要求,其具體表征為在生命的形成世界中實現生命自由與生命平等的內在協調和外在統一。在生命的形成世界中,生命自由與生命平等的內在協調,就是生命自在性與他者性的自為化。在生命的形成世界中,生命自由與生命平等的外在統一,則表征為“己他兩利”或“舍利執愛”:前者乃生命敞開生存的道德本位;后者乃生命敞開生存的美德本位。所以,生命在形成世界中固守倫理本位的實質,就是固守道德本位或美德本位。生命固守道德本位,就是在充滿利害取向的情景定義中其生存選擇行為必須接受“己他兩利”之倫理準則的導向;生命固守美德本位,是指在充滿利害取向的情景定義中其生存選擇行為必須接受“舍利執愛”之倫理準則的導向。
從根本上講,生命既存在于本質世界,也存在于形成世界,或可說,生命既是一個本質世界,也是一種形成世界。本質的生命世界是自足的,是自在性與他者性的真正同一。與此相反,形成的生命世界是非自足性的,因為在形成世界中生命始終處于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斷完成的進程之中,它通常表現為自在性與他者性的分離,這種分離抽象為生命的絕對自由與絕對平等的沖突與矛盾,這種分離具體敞開為利與害的博弈,而利與害博弈則具體化為權與權的博弈和權與責的博弈,前者意即民權與公權的博弈,后者即是權利與責任的博弈,但無論是公權還是民權,都必須以責任為根本要求和規范。以此觀之,這種以利害為實質取向、以權權對博和權責對弈為兩維方式的博弈之實質規定,就是倫理,既是倫理的一般規范,又是倫理的具體生成——倫理構成了一切生存境遇中利害博弈、權權博弈、權責博弈的認知框架和價值訴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生命是嵌含在倫理之中的。這就是在生命從原發存在向繼發存在敞開的形成世界中倫理始終具有本位功能的根本理由。在由具體的利害為牽引力的權權對博和權責對弈的形成世界中,生命一旦脫嵌于倫理,就必然要遭遇墮落,這種墮落的本質呈現,就是生命本性的淪喪或弱化;這種墮落的形成性敞開,就是反倫理,具體地講就是道德淪喪或美德消隱。
在形成世界中,生命中以實際生存境遇的利害為取向、以權權對博和權責對弈對為展開方式的博弈,本質上是生命自由與生命平等的博弈。當在這種博弈中生命自由徹底戰勝或取消生命平等、或者生命平等徹底戰勝或取消生命自由時,就是生命脫嵌倫理。生命脫嵌倫理的實質,是生命脫嵌其自為本性。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就意味著生命之自為本性被其他因素或力量所操控,即被低于生命本性的因素所控制,生命就因此而停止自我生殖并趨于自我消解。
三、生命的倫理關注
在原發存在中,生命自為地和諧。在繼發存在中,生命的自由與平等分離,這是人的生命敞開自身存在所不可避免的命運,因為生命從原發存在向繼發存在敞開的生命前提,是其生命獲得人質意識:
無論什么時候,只要生命超出動物水平向著精神水平進步,以及精神水平向著文化水平進步,一個內在的矛盾便出現了。全部文化史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的歷史。一旦生命產生出它用以表現和認識自己的某種形式時,這便是文化,亦即藝術作品、宗教作品、科學作品、技術作品、法律作品,以及無數其他的作品。這些形式蘊含生命之流并供給它以內容和形式、自由和秩序。盡管這些形式是從生命過程中產生的,但由于它們的獨特關系,它們并不具有生命的永不停歇的節奏、升與沉、永恒的新生、不斷分化和重新統一。這些形式是最富有創造力的生命的框架,盡管生命很快就會高于這些框架。框架也應該給富有模仿性的生命以安身之所,因為歸根結底生命沒有任何余地可留。框架一旦獲得了自己的固定的同一性、邏輯性和合法性,這個新的嚴密組織就不可避免地使它們同創造它們并使之獲得獨立的精神動力保持一定的距離。文化之所以有歷史,其終極原因就在這里。只要生命成為精神的東西,并不停地創造著自我封閉,并要求永恒的形式,這些形式同生命就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形式,生命便不成其為生命。[7]23
在原發存在中,生命的形式就是肉體,它自為地存在。所謂自為地存在,就是生命內容與形式內在統一,或者說生命與形式內在統一,并在這種內在統一中自為創造著這種內在的統一,這就是生命生殖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與形式的內在統一。在繼發存在中,生命創造出兩個形式:一個是與生命內在統一并真正實現生命自為存在的肉體;另一個是生命以意識的方式創造對象化的存在形式,即文化。僅從形式論,生命創造肉體,這是生命的情感生殖;生命創造文化,這是生命的精神生殖。生命創造肉體之所以獲得內在統一的自為存在,是因為情感的勃發與張揚最終要內斂地回歸于生命本身;生命創造文化之所以出現矛盾從而形成分離性存在,是因為意識的勃發與張揚最終外向地擴張而脫離生命。所以,在原發存在中,沒有形式,生命就不成其為生命;但在繼發存在中,因為有了意識對象化的形式,生命才出現異化。
意識對象化的生命形式何以會導致生命本身的異化呢?生命哲學家們對此做了最好的解答:
使生命高揚的哲學家堅決地堅持兩件事情。一方面它拒絕作為普遍原則的機械學:它充其量是把機械學看成是生命之中的技術。另一方面它拒絕把形而上學奉為獨立的東西和首要的觀念。生命不愿被低于它的東西所控制;它確實是一點也不愿意被控制,甚至不愿意被那些要求列于它之上的觀念所控制,并不更高的生命形式,盡管沒有觀念的引導也能了解它自己,但現在,這卻似乎只有觀念從生命派生出來時才有可能。生命的本質就是產生引導、拯救、對抗、勝利和犧牲。它似乎是通過間接的路線,通過它自己的產物來維持和提高它自己的。生命的產物獨立地和生命相對抗,代表了生命的成就,表現了生命的獨特風格。這種內在的對抗是生命作為精神的悲劇性的沖突。生命越是成為自我意識,這一點便越是顯著。[7]37-38
生命在本性上是自為的:生命是生命的動因,也是生命的目的。生命只為生命本身而存在。不僅在生命世界里,而且在整個世界里,生命是惟一的、最高的存在,也是最高的成就。所以,惟有生命可以指令生命,惟有生命才能控制生命,也惟有生命才能張揚生命。然而,自人的生命獲得了人質化意識,其不斷強化的意識便達向新的生命形式即文化的創造。文化一旦被意識地創造出來,它就脫離生命而成為一種高于生命的存在:文化高于生命而存在的方式就是控制生命,但生命的自為本性恰恰是不受控制的。由此,生命的意識化成果(生命的產物)對生命的控制取向與生命自為存在的反控制之間便形成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和斗爭。
在生命被人質化意識所“綁架”的歷史進程中,生命不僅以其自為本性敞開自我生殖、創造生命,更熱衷于為意識激發起來的欲望所鼓動而超越其自為本性地去創造文化(包括物質財富、科學技術、思想觀念……)及其各種扼制、異化生命本性的機械原則和制度裝置。人質化的生命之所以熱衷于創造出這些生命之外的東西,是因為這些“生命的產物”能夠給生命的自為存在帶來如下幾方面的好處:
首先,生命的產物能夠為個體生命解決其存在之“生”的問題提供各種可能性條件。個體化的生命要獲得生的資格、生的條件,必須解決力量與物質兩個方面的問題:對前一個問題的解決,必須走向他者、走進人群,這就是生命的求群、適群、合群的實現,但其前提卻是生命與生命的交通,包括約定、協作、遵守、踐諾等,觀念、思想、規則、制度裝置等成為生命所需要的東西;對后一個問題的解決,必須走向獲取,這不僅需要體力,更需要技藝,由此科學、技術、經驗等成為生命所喜愛的東西。
其次,生命的產物能夠為個體生命的自由存在提供各種便利。在人的存在世界中,所有的物質、器物、技術、工具……都是為生命存在提供便利而制造,并實實在在地為生命存在提供了便利。
再次,在形成世界中,生命必然喜悅于享樂,這就是生命享樂生命。生命享樂生命的原動力是生命的親生命性。生命的親生命性表現為生命的自親性和生命的親他性。生命的自親性就是生命以自己為親;生命的親他性是指生命親近生命。生命的親生命性成為生命享樂生命的原發動力。在原發存在中,生命享樂生命的直接方式,是生命擁有生命且生命進入生命,從而實現生命的生殖。在原發存在中,生命以親生命性為原動力來享樂生命,源于生命的內在要求,即生命享樂生命乃是生命實現生命的本性,所以生命享樂生命既符合生命本性,也是生命所必為的——從宗教視角看這就是上帝耶和華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亞當之后,還要從亞當身上取材創造一個陪伴他的夏娃的理由;從耶和華創造亞當和夏娃的行為看,生命享樂生命實質上是生命享樂自己。
生命享樂自己,這是生命享樂生命的原發方式,也是生命享樂生命的最高方式。但是,在繼發存在中,人這一生命創造了享樂生命的繼發方式,這就是生命享樂生命的產物,即生命享樂物質、生命享樂財富、生命享樂技術、生命享樂觀念和思想及想象和歷史……生命享樂生命的產物,是生命享樂的擴張方式,也是生命享樂的普遍方式,更是生命享樂的墮落方式。相對地講,生命享樂生命,是生命的自為存在方式,也是生命的生殖方式,它象征完美、壯麗,是生命對生命的實現,也是生命對自己的實現。因而,生命享樂生命是生命的升華。反之,生命享樂生命的產物,恰恰是生命的異己存在方式,也是生命的內在萎縮方式和外在衰落方式。并且,生命越是熱衷于享樂生命的產物,生命就越走向于自我萎縮,生命的內在本性也越發枯萎。比如,在沒有圖像技術和圖像文化的生存時代,節假婚慶,親人團聚,面對面地悠雅清閑地漫談、交流,甚至不分天南海北的閑聊,迸發出來的是熱騰騰的心緒和熱騰騰的情感,張揚出生命對生命的親近。但是,自進入圖像文化時代,哪怕是一年一度的團年聚會,現代人也往往窮于應付,家人之間除了必要的實務性交待,幾乎沒有了超越實利的交流,因為電視比親情“更重要”了。再比如,在農耕時代,人最大程度地實現著生命享樂生命的日常生活,親人之間有說不完的話,道不完的親愛、親近、親熱,所謂“老婆孩子熱炕頭”便是對此的一種寫照。這種生活應該是生命存在敞開的正常狀態。但是,自從有了網絡、有了手機,生命幾乎被人遺忘,并且生命幾乎被生命本身遺忘。如果略加留意便可發現,今日生活中,人們走路看手機、吃飯看手機……手機才是至愛,是須臾不離的現代“鴉片”。在網絡和手機時代,生命被技術全面異化,生命被物全面異化。正是這種異化,將生命完全解蔽的同時也將生命徹底地遮蔽。
關于解蔽,海德格爾談得最深刻。他說:“解蔽貫通并統治著現代技術。但這里,解蔽并不把自身展開于ποησιS意義上的產出。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是一種促逼(Herausfordern),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9]生命被生命的產物徹底解蔽,是通過技術和器物而實現的。解蔽,就是解除遮蔽,使之敞開、敞顯,使之凸顯、暴露,使之赤裸化。生命的產物(科技和器物)對生命的解蔽,就是將生命赤裸化。這種赤裸化,首先是消解了生命的生意和神性,使生命成為一個純粹的物,使由生命創造的世界成為一個徹底的物的世界,原本是生意和神性的自然亦淪為純粹的物質的自然,人的生命就在這種物化的自然中被物化的欲望和貪婪所劫持,在這種無窮地滋生物的欲望和貪婪中,生命被徹底地遮蔽。
從根本上講,生命的意識對象化形式越發展,生命越異化;生命越異化,生命的產物對生命的控制與生命反控制的自為本性之間持續展開的沖突就越普遍;矛盾和斗爭越朝向深度化方向敞開,生命的倫理問題就越發引來意識的關注,最后促成生命倫理學的誕生。
四、生命倫理學的基本維度
概括前面的內容:生命是自為和他為的。生命的自為性和他為性形成了生命的自在性與他者性。在原發存在中,生命的自在性和他者性因生命本性而獲得內在統一:生命本性將生命的自在性與他者性予以內在統一的感性方式,就是生命的倫理意蘊。在繼發存在中,其潛在的倫理意蘊必然顯揚為現實的倫理要求。這種倫理要求具體敞開為有限度地趨利避害、無限度地趨利避害和無限度地趨害避利這樣三種可能性朝向,由此形成道德對生命的引導和美德對生命的激勵。然而,所有這些“引導”或“激勵”都只能在生命創造“生命的產物”這個層面展開,并且也只能在這個層面上發揮其功能,卻根本無助于真正消解生命產物對生命的控制和生命對生命產物的反控制之間的矛盾。生命倫理學就誕生于生命遭受控制與反控制的拉鋸戰中,并必然肩負起雙重的責任與使命:一是在人的形成世界中如何引導生命和怎樣呵護生命;二是在人的本體世界中如何實現生命的自在和自由。以此觀之,生命倫理學實質包括了生命本體的倫理學、生命形成的倫理學和生命獲得內在統一的倫理方法學。
在一般人看來,生命倫理學就是應用倫理學。生命倫理學作為應用倫理學,自有其充足的理由。首先,它有一個將自己定位為應用倫理學的來源,這就是現代臨床醫學。但是,現代臨床醫學中各種突出的生命現象、生命問題及其生命所引發出來的許多技術難題、認知困境、倫理難題,是臨床醫學倫理學所不能涵蓋和解決的,由此生命倫理學從臨床醫學倫理學中突破出來而專門解決現代臨床醫學中日益復雜的生命難題。其次,由于生命倫理學出身于臨床醫學,它也必須為此而努力,所以生命倫理學成為臨床醫學中求解生命問題的非技術的方法學,雖然后來它從臨床醫學領域擴展到社會生命領域,但它也往往在社會“生命健康”的層面上得到運用。
其實,“生命健康”問題僅僅是生命倫理學的一部分,即它只屬于生命形成的倫理學的范疇。當我們用“生命形成的倫理學”來表述生命倫理學的應用部分,首先須明確“生命形成的倫理學”中的“生命”,是專指人的生命。所以,“生命形成的倫理學”,是人的生命形成的倫理學的簡稱。其次需要定位“生命形成的倫理學”中的“形成”概念,它是柏拉圖哲學意義的、與“本質”相對應的概念。如前所述,“本質”所指涉的是普遍、不變、永恒、真理;“形成”則意指個體、變化、易逝、現象。生命形成的倫理學,實質上是指生命個體、變化、易逝、現象的倫理學。生命形成的倫理學的根本來源、根本動因,不是臨床醫學中所遭遇的各種生命問題、困境、難題,而是生命本身的未完成性、待完成性和需要不斷完成的吁求性。正是因為生命的未完成性、待完成性和期望不斷完成的吁求性,才推動人的敞開、人的變化。人的動態不息的敞開、人的從不自足的變化,才生成出人的健康問題;人的健康問題,才導致臨床醫學中的生命難題、生命困境及其生命技術的道德問題;并且,也正是因為人的健康問題,才形成了家庭、社會的生命關注意識、生命關懷取向,由此才引發出工作、學習甚至娛樂等方面的自由、平等、人道、公正問題。
簡要地講,應用意義上的生命倫理學,是圍繞生命形成而展開的。生命形成的所有問題,都與生命形成的倫理學相關,都屬于生命形成的倫理學探討、研究的范疇。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可以將生命形成的倫理學所關注的主要內容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臨床醫學中的所有生命問題、困境、沖突、矛盾,當然也包括生命技術問題,比如試管嬰兒、無性生殖、體外受孕、人體實驗等所蘊含或表現出來的倫理問題,都屬于這一類;二是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問題;三是社會對生命的定位所產生出來的各種倫理問題,但這類問題要成為生命形成的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其前提是它必須涉及到生命的健康——即社會對生命的定位涉及到生命的健康時,它就是生命形成的倫理學研究的問題;如果沒有涉及到生命的健康問題,就屬于其他領域的倫理學所研究的內容。比如,勞動分配制度、社會福利等問題一旦涉及到公民的生命健康時,生命形成的倫理學就有權研究它;反之,勞動分配、社會福利等領域的問題,就屬于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內容。
客觀地看,生命形成的倫理學所指涉的范圍,是人的生命的形成世界,是人在生命的形成世界中如何經營生命的倫理學。人在形成世界中經營生命必以生命本性為本質規定,更要以生命的自為存在方式為根本依據。因而,生命形成的倫理學要探討、研究和解決任何現實生存中的生命問題、生命困境、生命難題、生命技術的道德困境,都必須尋求最終尺度的確立和最終依據的明確。所以,生命形成的倫理學研究一旦展開、并謀求健康的發展,就必須觸及到生命的最終根源和依據問題,就必須涉及到生命存在的本質問題、本體問題。以此觀之,生命倫理學必然要開辟生命本體的倫理學。在生命形成的倫理學中,其“生命”是專指人這一物種的生命,所以它是文化學意義的生命;但在生命本體的倫理學中,其“生命”是指包括人在內的世界生命,所以它是自然學和生物學意義的生命。
生命本體的倫理學關注生命的起源、生命的依據、生命的歸宿和生命的本質、生命的本性等問題。所以,生命本體的倫理學更多地注目于人的原發存在境域,以及人從其原發存在境域向繼發存在境域敞開進程中,其生命的朝向、生命的裂變、生命的異化以及異化進程中的生命的回歸等問題。這些問題關聯起如下三維世界:
首先是自然世界,其所關涉的是生命與自然的關系。在一般人看來,生命與自然之間僅具其外在關聯性,但這只是從形成(現象)角度看,從實質觀之,生命與自然之間是一種內在生成關系,這種內在生成關系由兩個方面規定:其一,生命原本是自然,并且生命源于自然并表征自然,所以生命與自然之間形成本原性的原始關聯性,在這種本原性的原始關聯性中蘊含一種存在真理和一個存在法則,這就是自然為生命立法、生命為自然彰法;其二,由于生命既源于生命而且生命更源于自然這一雙重性,從而形成生命的親生命性。親生命性,這是生命本性的自為釋放方式,它同樣既蘊含一個存在法則,更體現一種存在真理:這個存在法則就是生命既是生命的動因,也是生命的目的,這就是動機—目的一體論。動機—目的一體論法則,構成了生命形成的倫理學的行為準則。這個存在的真理就是生命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即生命的內容與生命的形式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生命的本質與生命的形成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生命與自然的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這既是生命自在存在的事實,更是生命他者性存在的事實。對這一雙重存在法則、存在真理和這一雙重存在事實的形上拷問與檢討,則構成生命本體的倫理學研究的奠基問題,亦是生命本體的倫理學的真正起步,因為這些問題蘊含著生命倫理學的最終邏輯起點。
其次是原發存在世界,其所關涉的是生命的自為存在問題。生命的自為存在實際上呈現一體兩面,即生命自在性與他者性。在原發存在中,生命的自在性與生命的他者性是內在地統一,這種內在統一的自身依據就是生命完形的本性,簡稱為生命本性。在這個維度上,生命本體的倫理學必須探查和檢討生命的自在存在和生命的他者性存在的內在統一何以可能,以及生成其內在統一的內隱機制。這些構成了生命本體的倫理學研究的基本問題。
再次是繼發存在世界,其所關注的是生命的生存問題。生命的生存問題具體表述為生命對生命的需要和生命對物的需要所牽涉出來的所有問題,這些問題均可用“利害”來概括之。生命遭遇“利害”的選擇的各種可能性,以及這些可能性最終變成現實性所形成的倫理要求與倫理規范問題,構成了生命本體的倫理學所研究的重心問題。
對形成的倫理學和本體的倫理學予以整合所構建起來的生命倫理方法論,構成了生命倫理學的第三個維度,它所集中關注并謀求解決的基本問題是生命本體的倫理學和生命形成的倫理學如何獲得內在的一致性和統一性的問題,或者說生命本體的倫理學和生命形成的倫理學達成內在一致的統一性何以可能,構成了生命倫理方法論的基本主題。
如前所述,當生命突破原發存在的散漫而向繼發存在世界敞開,因為遭遇利害糾纏而將自由與平等之間的沖突凸顯了出來;并且,當生命進入形成的生存進程,因生命享樂生命的本原性得到無限度釋放所形成的生命產物控制生命與生命反抗其控制的矛盾也凸顯了出來。這種雙重凸顯既要求生命本體的倫理學必須為對一切形式的生命形成的倫理問題的探討提供認知依據、理論基礎和思想原理,更要求生命形成的倫理問題的探討必須達向生命本體的倫理學高度并獲得其真正的解決,包括認知解決和實踐解決。基于這一雙重要求,生命倫理方法論在其實際上應該是生命倫理原則學。整體觀之,生命倫理方法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具體的研究方法,即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方法,“我們通常講‘研究方法,也無非是收集資料的方法與分析資料的方法。不同學科、不同研究領域、不同研究主題的性質決定了應采用的研究策略與方法”[10];二是指導和規范研究方法選擇和運用的原則,這就是研究的原則方法。從根本上講,倫理原則構成倫理問題探討的根本方法。在生命世界里,對生命的倫理問題的目的性關注和探討,必須有其明確而共守的原則,否則其探討和研究就會各自為政、互難交通。對生命問題予以倫理探討和研究所必須遵循的共守原則,就是生命倫理方法論研究的基本構成內容。
客觀地看,生命從原發存在向繼發存在進發所產生出來的自由和平等之間的沖突問題,實質上所涉及的是一個限度問題,即自由的限度和平等的限度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民主主義者更強調平等的絕對性,自由主義者更強調自由的絕對性。“自由就是生命,對自己,對別人,對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而言,都是如此。”[11]43自由才是生命,沒有自由就喪失了生命,這對所有人都是如此——首先是對所有生命必須如此。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貝爾有一個回憶,講述自己12歲時的一天黃昏,他將捕捉到的一只美洲小畫眉關在籠子里,目的是要讓它為自己唱歌。這只小畫眉的母親來給它喂食物,但讓他感到不幸的是這只小畫眉第二天死了。貝爾對此大惑不解,于是向當天來拜望他父親的著名鳥類學家阿瑟·威利求解疑惑。威利告訴他:當一只美洲畫眉發現她的孩子被關進了籠子后,就一定要喂小畫眉足以致死的毒莓,她似乎堅信孩子死了比活著做囚徒好些。鳥類學家的話使貝爾覺悟:“從此以后,我再也不捕捉任何活物來關在籠子里,因為任何生物都有對自己自由生活的追求,而這種追求無疑是值得肯定的。”[11]44自由才有生命,但生命自由之內在規定,卻是平等:從靜態看,每個生命的自由都是絕對的;但從對動態觀,任何生命的自由都只能是相對的。因而,自由與平等之獲得內在統一所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就是自由對自由的平等限度。因為自由而遵守平等限度之準則,這是生命倫理研究的根本方法。以此自由的平等限度為根本準則,如下的道德規律才可成立:“在道德規律面前,一切人的生命都有同樣的價值,一旦某人遇到了危險,所有其他的人,不管他們是誰,在那個人得到援救以前,都不再安然無恙地享有生存權利。”[11]295
自由與平等的問題,是生命與生命的問題。而生命產物對生命的控制和生命對其控制的反抗之間的沖突與斗爭,恰恰是人與物的問題。人與物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生命與欲望之間的沖突。更進一步講,這是生命本性遭遇利害時所表現出來的異化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所必須遵循的根本準則仍然是限度原則,即生命本性的限度規定了生命的限度,也規定了生命對欲望的限度,更規定了生命對責任的限度以及生命對痛苦、不幸、失敗甚至絕望的承受與忍耐的限度。這種限度在由生命自身本性所規定的質和量上是絕對平等的,但個體生命對其總量的消費與節度各有差別,因為不同的生命在其本性的限度內消費生命和役使生命的量與質各不相同,這種不同必須以生命本性的同構以及其本性所煥發出來的自由的平等為基數,減去其所消費的量,就是每個生命實際得到或必須付出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來看健康問題、疾病問題、生育問題,以及疾病治療過程中所引發出來的技術問題、失誤問題等,都沒有純粹的意外,有的只是基于生命本性的限度對個體生命的補償或擔當要求而已。比如,一個人昨天還活蹦亂跳,今早卻傳來其死亡的消息;一個病人經歷10年的痛苦和折磨,但至今還活著。前者是因為其有限生命在付出與獲得方面達到本性的限度,因而其生命可以圓滿謝幕;后者是因為其有限生命的長度沒有消失,具體表現為其享樂生命的量在事實上超過了本性的限度,而其生命付出卻遠遠沒有達到其本性的限度。
由此不難看出,對生命倫理學的定位和探討,并不接受觀念的支配,而是必須遵循生命的法則。生命的法則就是生命成為生命的法則,這個法則的內在規定就是生命本性,這個法則外化要求的基本準則就是自由的平等限度,包括生命與生命的互為限度,生命自為存在的限度。尤其是生命的自在存在中其質量的互為限度、付出與獲得的互為限度、快樂與痛苦的互為限度,這種互為限度所達及的動態平衡狀態,才是生命的倫理。這種互為限度所敞開的動態平衡進程,才是生命的倫理生成。
參考文獻:
[1]何倫.生命的困惑:臨床生命倫理學導論[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1.
[2]范明生.古希臘羅馬美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1.
[3]萬慧進.生命倫理學與生命法學[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6.
[4]埃爾溫·薛定諤.生命是什么[M].羅來歐,羅遼復,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68.
[5]唐代興.生境倫理的知識論構建[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183-185.
[6]唐代興.生境倫理的人性基石[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22-26.
[7]西美爾.現代人與宗教[M].曹衛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8]唐代興.生境倫理的規范原理[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19-128.
[9]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M].孫周興,選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932-933.
[10]勞倫斯·馬奇,布倫達·麥克伊沃.怎樣做文獻綜述:六步走向成功[M].陳靜,肖思漢,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4.
[11]湯姆·睿根,彼得·辛格,約翰·羅賓斯,等.地球也是它們的[M].祖述憲,馬天杰,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