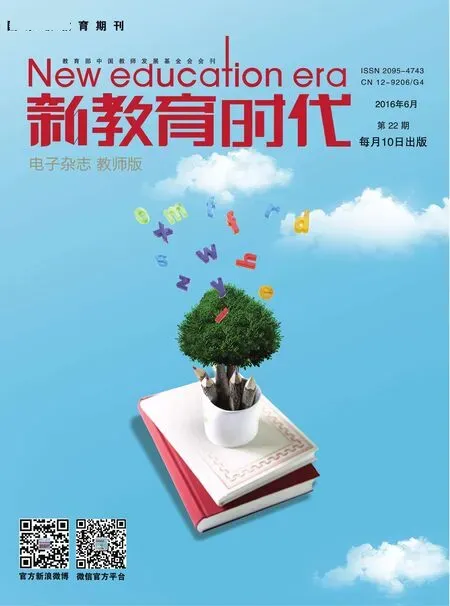論《紅樓夢》中石頭神話的功能
葛俏俏
(天津師范大學 天津 300387)
?
論《紅樓夢》中石頭神話的功能
葛俏俏
(天津師范大學 天津 300387)
摘 要:《紅樓夢》既是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名著,但其中的神話故事也讓這部作品具有了神秘的浪漫色彩。本文以《紅樓夢》中的石頭神話為研究對象,在明確闡釋其概念的基礎上,深入分析了石頭神話在作品結構、人物性格塑造和作品主題表達三個方面的功能。力圖對《紅樓夢》中的石頭神話的內在價值作進一步的挖掘,對石頭神話和小說《紅樓夢》有更深層次的本體性認識。
關鍵詞:《紅樓夢》 石頭神話 圓形結構 賈寶玉
《紅樓夢》是我國古典文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美麗而迷人,充滿了神秘感。這種神秘感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其中包含的神話故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本文的研究對象——“石頭神話”。《紅樓夢》中的石頭神話指的是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的頑石幻化成賈寶玉,賈寶玉在人世間徹底看透了人生的本質后感到無限悲涼,最后寶玉重又幻化為石頭回到大荒山青埂峰的神話故事。雖然我們把石頭神話如此定義,但《紅樓夢》中的石頭神話絕不僅僅是一個石頭幻化成人的簡單神話故事。石頭神話貫穿于整部小說,是一個復雜而嚴密的神話系統,其它的神話都是在石頭神話的框架結構下存在的。所以我們應該把石頭神話稱為“石頭神話系統”。雖然石頭神話系統在《紅樓夢》中并不是主體故事,遠不如賈寶玉以及其家族的經歷那樣重要,但是無論是從內容還是形式上來說, 石頭神話系統對于整部作品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和作用。[1]
一、結構功能——圓形的故事框架
石頭神話在整部《紅樓夢》中,只在第一回、第五回、一百一十六回和一百二十回有過詳細描寫,其余在六十九回和一百一十一回零星提及,跟其主體敘事相比篇幅較小,其超越內容功能之上的形式功能顯現出來。故事從青埂峰下補天被棄的一顆頑石幻形入世開始,又以頑石復歸原處作結,中間的部分講述了現實世界中一個完整的故事,這樣就用這顆石頭的入世歷劫之經歷給作品畫了一個大圓,形成了作品的圓形結構。[2]
我們說石頭神話是一個復雜的神話系統,嚴格地講,這一系統包括三個部分:入世神話、歷劫神話和返歸神話,也就是石頭的入世、歷劫和返歸。這三部分又分別包括一些更小的神話故事。其中,入世部分包括女蝸補天、頑石通靈和僧道點化;歷劫部分包括太虛幻境、靈力丟失、和僧道幫助;返歸部分包括神瑛神話、木石前盟和返歸大荒。那么作品的圓形結構就不止是頑石幻形入世,歷劫后重回青埂峰下這一個籠罩全書的抽象化的大圓。其次還有,寶玉在秦可卿房中小睡時訪至太虛幻境,夢醒又回到現實生活這一個小的圓圈所。再次,絳珠仙草幻形為女身以淚酬報神瑛侍者灌溉之恩,淚進而亡,完成報恩又是一個圓環組成。
石頭神話系統構成的圓形結構,以一種不著痕跡的筆法,自然地構建了一個從茫茫大荒的虛幻世界到熙熙攘攘的現實世界,最后又回到原來空幻世界的情節體系。作者的這種構思,給故事主體內容罩上了一層奇幻而美麗的外衣,也給予高度寫實的生活內容以一種空靈的詩意和美感。“這種空靈,是偏于陰柔之美的范疇,它淡雅而不鄙俗、清遠而不纖媚、含蘊而不劍拔弩張,總是在不知不覺中給人以‘情韻連綿,風趣巧撥’的感發”[1]這種圓融的整體架構,蘊含著虛實相生的美學風格,也正契合了東方傳統的審美觀念,暗含著微妙的美感。正是由于《紅樓夢》中石頭神話系統的存在,才使虛幻的浪漫主義彌散在濃重的現實主義之中,構建出了真實感人而又飄忽悠遠的藝術境界。
二、性格塑造功能——賈寶玉的石性玉質
頑石經一僧一道點化通靈后,幻形入世成為通靈寶玉,附著在了賈寶玉身上,成為寶玉出生時口中含著的那塊玉。這塊玉的存在,使得賈寶玉的身份變得特殊起來,他的身世、性格乃至整個生命都與通靈寶玉息息相關著。作者在這里其實是運用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美學技巧——幻形原理。“‘幻形’原指由魔幻而產生的形變,在文學創作及審美欣賞中,是一個普遍遵循的美學原則。”[2]在“頑石——賈寶玉——頑石”的圓形結構中,不同層次間就是靠幻形進行溝通和轉化的。[3]
通靈寶玉是由頑石幻形而來的,其本質屬性是石頭,所以“石性”是賈寶玉的本質屬性,是他性格特征的主要方面,對應著賈寶玉天性中遠離仕途經濟、追求個性自由、個性自然率真的成分。石頭幻形成通靈寶玉,通靈寶玉又被視作主人公賈寶玉的“命根子”。通靈寶玉意外遺失后,賈寶玉便生了重病,性格逐漸變得與往常截然不同。可以說,通靈寶玉是主人公賈寶玉生命存在的象征,是其一切生命活力的根源,失去了它,賈寶玉的現實人生也就快要結束了。在世俗社會中,賈寶玉又擁有著“玉性”,他養尊處優,被整個家族視為掌上明珠,被嬌生慣養,地位高貴無比。
石頭對應賈寶玉未經雕琢的自然特性,通靈寶玉對應賈寶玉對富貴、溫柔的世俗欲望。石是玉的本相,玉是石的幻相,二者構成了一體二名、連類并稱的審美關系。書中時而說石是頑石,時而又說石是美玉,表面上看“石”和“玉”相互對立,其實不然,它們巧妙地結合在賈寶玉身上,因此賈寶玉形象擁有了兩種特性:在世俗眾人眼里他是“不肖種”、“混世魔王”,這是其玉質表象,是他人的認定;而在超越世俗標準的警幻仙姑口中,他是值得贊賞的“古今第一淫人”、“情癡情種”、“千古情人”,這是其石性表現,是內心的原始情愫。石頭神話的存在,使得主人公賈寶玉擁有了“石性玉質”的雙重復雜性格。[4]
三、主題表達功能——空幻世界中的執著情感
石頭神話作為小說中的一個象征性寓言,隱指著更為深刻的哲理寓意。在石頭動了凡心,想要跟隨一僧一道進入俗世享受溫柔富貴時,一僧一道的回答是“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作品的第一章就用這層神秘的外衣預示了故事的結局,“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后面所有的繁華、美好都只是大夢一場,最終一切都會消失不見。那么既然終會成空,為什么還要經歷這一切呢?作者用這個“空”想表達的是什么呢?
作者通過石頭“無材補天、幻形入世”到歷盡塵緣、“復還本質”的故事,寄寓了自己對人生之情感的執著追求。在這個空幻的世界中,石頭明知一切會成空,仍愿下凡歷劫。作者用石頭的經歷,表達出了《紅樓夢》的核心價值追求——情。石頭下世為人、塵世歷劫、返歸大荒的生命歷程,不是對人生與生命價值的根本否定,反而正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歌頌。“空幻”指向的是人生的歸宿、生命的盡頭,石頭明知自己“劫終之日,復還本質”的歸宿,還是
心慕“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執意要求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他“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里受享幾年”。作者從人生無常、生命短暫中流露出感傷的情調、虛無的體驗,但在內心深處又充滿了對人生的眷戀、對情感的執著。
在石頭生命軌跡的圓圈之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其塵世歷劫的部分,也就是賈寶玉在紅塵俗世中的生活。而賈寶玉的生活中,最動人而占據核心地位的是其情感生活。賈寶玉從小就顯示出行為上對“情”的“怪僻”,并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地加強,這里的“情”既包括他與林黛玉的愛情,也包括他對紅樓眾女兒乃至世間一切美好生命的深情。在大觀園的眾女兒中,他不但發現了所有女性所共有的真、善、美,還發現了不同女性身上的個性美,對這些女性保有著長久的眷戀與關懷,確信“為這些人死了也甘心”。明知“劫終之日,復還本質”的人生結局,卻仍然保有著對萬物深情相待的執著,可見這份情深刻到何種地步。由此我們可以說,石頭神話所隱含的人生哲理的最高價值,在于其對于“情”的命題的引入。
小解:
①唐富齡,論<紅樓夢>的空靈美,紅樓夢學刊,1995 年第2期,第 139 頁。
② 彭兆榮,幻形——一個鮮為人知的美學原理,文藝理論研究,1985年04期,第62頁。
參考文獻:
[1](清)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M].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8.
[2](清)曹雪芹著;(清)脂硯齋評.脂硯齋評石頭記[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3]彭兆榮.幻形——一個鮮為人知的美學原理[J].文藝理論研究,1985,04:62-63.
[4]楊紹固. 《紅樓夢》中的“石生人”神話系統研究[D].新疆師范大學,2008.
[5]武建雄,張運磊. “情”本位的哲理建構與人世演繹——論《紅樓夢》神話敘事結構對主題的揭示[J]. 東方論壇,2007,02:27-32.
葛俏俏,女,1991——,天津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在讀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