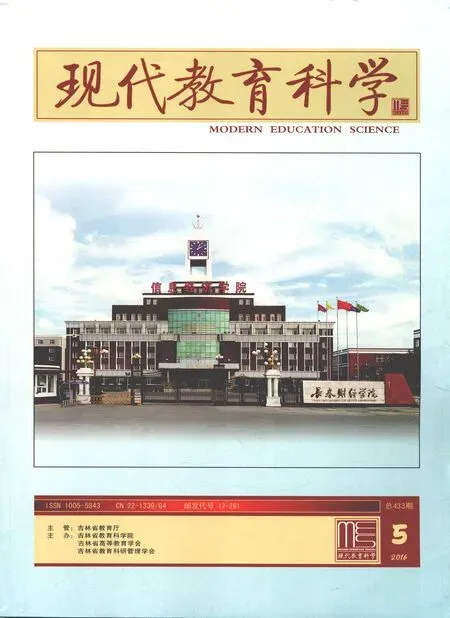心智與美德分野的再探討
——兼評《文化溯源:東方與西方的學習理念》
侯海榮,唐楠
(吉林師范大學博達學院,吉林 四平136000)
?
心智與美德分野的再探討
——兼評《文化溯源:東方與西方的學習理念》
侯海榮,唐楠
(吉林師范大學博達學院,吉林 四平136000)
[摘要]《文化溯源:東方與西方的學習理念》為廓清東西方學習理念的差異找到了文化歸因:歐裔/西方人的學習模式偏重心智取向,中華/東亞人的學習模式偏重美德取向,這是由東西方悠遠而迥異的文化傳統決定的。一方面,它們各本其宗,各有所倚;另一方面,文化涵化等因素促使二者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伴隨全球化的推進,教育改革者既需“深造自得”,亦需“左右逢源”,洞悉兩種學習理念各自的長存價值,將中西不同學習類型的功能加以耦合,建構“心智+美德”模式應該成為理想的育人愿景。
[關鍵詞]心智導向美德導向學習理念文化尋根教育省思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5.002
華人教育學家、哈佛大學人類發展暨心理學博士李瑾所著《文化溯源:東方與西方的學習理念》于2015年在國內譯介出版。作者探究儒家與歐美兩種文化傳統對人類學習的持續影響,揭秘東西方兩種教養文化與學習表現之關聯。通過追溯兩種學習模式的文化淵源,作者得出的結論是:歐裔/西方人為心智導向學習模式(Western mind model),聚焦于開發心智以理解世界;中華/東亞人為美德導向模式(East Asian virtue model),追求個人道德日臻完善并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多元智能理論創建人霍華德·加德納贊譽該書為探討東西方學習文化的扛鼎之作,并斷言:“此后對東西方學習文化的探討,均需從這部論著開始。”[1]如果我們靜思這些不同學習模式的特點及其對學習者產生的形塑效應,東西方的教育發展和教育改革都將從中得到理論啟發和實踐思路。那么,這兩種文化傳統是否仍然制約著當代的學習者?這些追問為本文的緣起提供了再探討的空間。
一、歐裔/西方人的學習理念:心智導向——為掌控宇宙而學
任何文化皆有其獨具傾向的自性,藉此作為主根與動源,最終形成自家的文化面貌,“文化自性乃相對獨立的文化基因與價值規導”[2]。李瑾正是把東西方兩種文化經由各自關于學習的基本命題作為分析架構。她指出,在西方知識傳統的哲學討論中,大部分思想家都以心智為重心。何為心智(mind)?它是人類實體負責“知”的部分即我們的思維能力,這是人類的一種官能,心理學視閾將其視作一種潛能,神經科學將其解釋為人腦的一種電路系統。迄今當代心理學、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仍致力于探索人類心智各層面不同功能的精確圖像。把握東西方不同知識傳統的思想內核,可以為兩種文化背景下學習觀念的差異奠定檢驗與詮釋的根基。李瑾提煉出西方知識傳統的四個主題:知曉客觀世界、準確無誤的知識、心智的奇跡、省視過的人生[3]。歐裔/西方人學習特點表現為具備并善用良好的心智、天生的好奇以及發自內心的喜悅、對未知世界的癡迷,把了解和掌握世界作為學習的終極目標。此種心智導向從學習概念、學習模式、學習過程、學習情緒四個維度加以展開得以確證。
學習概念。該著的作者通過問卷調查,得出美籍學習者評選出的與學習最具相關性的語匯包括study(研讀)、thinking(思考)、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information(信息)、discovery(發現)等。美國學童、家長、老師對孩子的成就以“能力”為準繩作以衡量,對照的亞洲組則將學生的成績歸結為是否“努力”。這個差距被稱為“學習鴻溝”(Larning gap)。從學習概念可以得知,西方人擅于“用腦”,東方人長于“用心”。
學習模式。李瑾將學習模式從學習目的、學習的原動過程、成就的種類三個層面加以考察。歐裔人的學習目的集中于發展心智能力/理解世界、培養才能/技術、達成自身目標。三種目的本質上互相關聯,其中心智居于主控的位置。學習的原動過程體現為主動投入、剖析推理、發明新物、交流互動。成就種類分為擁有專門知識、具備個人見解、盡力做到極致。整個歐裔/西方人的學習模式印證了久遠的西方認識論(epistemology)傳統,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再到笛卡爾,對心智的敬畏在西方知識史上一再復蘇。
學習過程。西方人的學習過程包括四個重點,即積極投入、探賾本質、思考批判、自我表達。在自然科學領域,達爾文等人的研究方法,一向受到推崇,就連人文社會學科,學生們的訓練也不以記憶為主。相較之下,“東亞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體系在國際上早已不是秘密,規定學生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扼殺學生的創造力等,與美好的西方教育制度相比簡直是萬惡淵藪,引得伊許沙達(Ishisada)直呼為‘考試地獄’”[4]。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博物館珍藏歷屆得主的自傳,所有的科學巨擘都陳述了自己從童年起就熱衷考究事理、動手造物以及享受發現的樂趣[5]。在學習過程中,批判性思考引發極度追捧,它通常被定義為:對于何者可信及何者當為所作的理性思考和反省[6],包括尋求真相、開放心靈、事實分析、探求答案[7]。批判性思考在西方是一種充滿價值觀而非價值中立的行為,它鮮明地昭示出西方相信每個個體都擁有對任何事情質疑并進行調查研究的權利。從學習過程的這些特質來看,東方人所謂的“標準答案”等等,著實為學生的心智開發帶來致命的禁錮。
學習情緒。普通心理學認為,情緒是以個體愿望和需要為中介的一種心理活動,是客觀事物和主體需求之間關系的反應,包含情緒體驗、情緒行為、情緒喚醒等復雜成分。學習情緒指的是針對學習和自行投入學習過程時所有的情緒反應以及長期的感受[8]。歐裔/西方人的正向學習情緒體現為興致的高昂、內在的愉悅、挑戰的豪情、成功的快慰;負面情緒體現為冷漠與倦惰、失敗而絕望等等。
二、中華/東亞人的學習理念:美德導向——為完善自我而學
儒學是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的主流和正統,它創建了中華民族的集體人格,并積淀為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其中蘊化的價值觀念,形成了儒家知識傳統的四個主題:完善自我、以天下為己任、學習美德、行勝于言。可見,為達成個人盡善盡美所作的種種努力構成了“儒家文化圈”即中華/東亞人學習的核心要旨,因此也鑄就了其人生目標與西方人的差異:一個人心智上所關注、思考、實踐和生活的對象是他的自我,而非外在世界[9]。并且,個人的自我完善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社會性。誠然,儒家的學習之路與其說是為了個人的成就感,不如說它把學習的意義從個體的層面漸次擴大到人類生命的格局。正是這樣一種將道德修為、社會層級、經濟獲益一舉空前地加以合并,才導致學習在中國文化里占據無與倫比的至尊地位,而且逐步強化其無可非議也不容商榷的剛性價值。
學習概念。與歐裔/西方人不同,華人評選出與學習最具相關性的語匯包括學無止境、勤能補拙、知書明禮、鍥而不舍等等。由此可見,如果說心智中一項最偉大的能力是思考的話,則中華/東亞人在這方面的認知明顯缺失。之所以產生東西方關于學習概念如此大的語匯差異,這是由群體共識推衍出來的實證結果,其所體現出來關于文化層面的學習概念,描繪出通過語言媒介而呈現出的一種文化學習模式的樣貌。
學習模式。從學習目的、原動過程、成就種類三個層面觀之,學習目的包括為道德完善、獲取知識、施予社會,這些學習目的顯然是儒家價值觀的外化;原動過程表現為認真誠意、勤奮刻苦、秉燭達旦、砥礪不懈等等;成就種類體現為對知識的精通程度、對知識的運用程度、知識與道德的結合程度。從學習模式可以看出中華/東亞人承繼的儒家淵源根深蒂固,學習美德乃華人學習傳統中保留最完整且生命力最強的部分。
學習過程。中華/東亞人學習過程表現為誠意、勤奮、刻苦、專心、恒心等等。這些詞匯內涵具有極大的交叉性,在華人文化框架內一直得到高度贊同,其中練習成為學習的主要行為表現,因此出現“熟能生巧”“水滴石穿”“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拳不離手,曲不離口”等成語或警句。但類似如此某個概念范疇在一種文化里呈現出繁復的狀貌,被羅伯·利瓦伊稱為“高度認知與其相對立的低度認知(hypercognition vs. hypocognition)”[10]。有數據顯示,歐裔美國受訪者僅38%描寫與美德有關的學習過程,涉及心智導向則高達96%[11]。
學習情緒。華人學習的正向情緒表現為承諾與抱負、熱情與摯愛、尊敬和接受、謙虛和完善等;負向情緒表現為缺乏求知欲、傲慢、學業不佳而產生羞恥心和愧疚感。華人學習情緒的起點是所謂的“立志”,其學習動機并非系于對某學習活動的好奇,換言之,不以自我為基準,不依學習任務而決定,不以樂趣為學習的主要條件,似乎更植根于一生的胸襟與信念。此外,對老師的尊敬之情在東西方的受教者人群中呈現出不同的情緒體驗。倘若將尊敬分為道義式尊敬(ought-respect)和愛慕式尊敬(affect-respect)的話,則亞裔學生強調向古圣先賢學習所產生的愛慕式尊敬更為普遍。從師生關系的獨特視角切入,其闡發的重要意義在于,前者基于政治、道德、法律的考慮,不是特定社會情境下或人際關系的產物,緣于其緊扣以權力為基礎的道德原則,因此成為原型情感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這是一種具有理性態度的思維產物。后者是尋找與效仿行為榜樣的關鍵,并力圖實現“自我畢馬龍過程”(self-pygmalion process)[12]。該論點得到其他西方學者的呼應。譬如,金立賢等發現英國學生描述的好老師形象是能夠激發學生興致,有效運用教學方法并解釋透徹,華人學生欽敬的好老師務必學養厚重,同時是一個道德楷模[13]。
上述西方和東亞沿著不同的路徑形成了差異頗大的學習風格,一為向外無限拓展認知邊界,一為向內日益強化自我精進,不同文化在每一位學習者的學習概念、學習模式、學習過程、學習情緒方面皆有跡可循。值得肯定的是,李瑾以實證和質性方法漂亮地揭開了東西方學習結果背后的文化力量。
三、“心智+美德”模式:全球化語境下彼此互鑒的育人理想
從前述可以看出,西方知識傳統賦予心智莫大的膜拜,東亞知識傳統賦予美德極度的仰望,從而出現了兩種學習導向的分野。我們需要深思的是,這兩種文化傳統是否依然影響當代的學習者。筆者認為,李瑾對東西學習文化的闡論非常可貴,我們看到知識與美德在華人文化里有機融匯,而在西方,卻是截然分離的兩種驅策力,它將幫助我們理解在采借和吸納其他文化元素時頗為復雜的過程。任何一種知識傳統在歷史的賡續都有自身邏輯,但它絕非只屬于過去時的靜態結構,隨著教育階段的歷史演進,兩種學習理念均暴露出各自的短板并發生了新的動向,這也正是《文化溯源:東方與西方的學習理念》作者李瑾的良苦用心:人類知識在持續擴張的同時變得更加抽象,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傳承下建立最好的教導和學習方式成為重要的教育議題,西方和華人/東亞的學習傳統就是應這個考慮發展出來的[14]。那么,如何審視當下東西方學習文化的博弈并解開作者的迷津?
(一)心智導向的優長與評價
第一,心智導向的不容輕覷。“當下是文化反思的起點,而我們置身的當下,適值多層級變革相互疊加”[15]。信息社會與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最大的區別,就是智能代替了體能和機械能。當科技成為第一生產力,心智作為人類操控世界的至高動能,新技術革命條件下心智開發與心智水平的優先地位更加凸顯。現在全球有知識趨同(convergence)現象,大多由西方世界所促成,這類知識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產,譬如,所有的課程系統都把數學和科學納入其中。可見,在知識經濟時代,依托人力資源、智力資源和思想資源推動的社會飛躍,務必著力汲取西方邏輯辯證思維的神髓,而這一引領使命需要心智教育擔荷。
第二,心智導向的過猶不及。心智模式重在淬煉學生智力,尋究萬物的本質,最大化改造世界。浸潤于西方文化血脈的單純的絕對的心智導向猶如孤翼而飛,缺失美德的教育某種程度蛻變為異化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可能是有智力沒情懷的“怪物”(朱永新語)。令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的第28任院長亞瑟·克里斯托弗·本森憂心忡忡的是,“現在許多公立學校及大學教育既不功利,也不注重學生的智力發展。因為他們的首要目標是發展智力,接著才是功利,結果,哪一個目標都沒有達成。”“當前擺在教育者更為艱巨的任務是,當我們具備了把學生培養成有用之才的觀念后,還要盡可能地喚醒學生的靈魂。在這方面,我敢肯定,我們失敗得一塌糊涂……這才是我們教育的真正弊端所在,我們在長期‘智力饑餓’系統之下培養了許多代人,但我們沒能填飽學生的心靈”[16]。因此,一方面,當西方陷入德行共識的危機,教育學領域的道德訴求始終沒有間歇,以德性倫理學為基礎的道德教育模式于20世紀末期應運而生。另一方面,當“征服自然”的口號在生態環境惡化之后才逐漸沉寂,然而人類一味開掘自身無限心智潛能的同時早已付出慘重代價。
第三,心智導向與美德導向并行不悖。西方的心智訓練,對東方教育倡揚的堅韌不拔、持之以恒等學習美德一向頗有微詞。目前,整個美國教育學界被一種全新的教育理念席卷:Grit(堅毅)。它是一種包涵自我激勵、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的性格特征,是對長期目標的持續激情以及不忘初衷的執著不怠。2013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Angela Duckworth的演講引起教育界對“堅毅”的空前矚目。Angela Duckworth教授和她的團隊甚至制定了測量“堅毅指數”的工具,使得堅毅成為最可靠的預示成功的指標,這一舉措被譽為 Grit開啟了“性格教育時代”[17]。不難發現,這一導向與儒家知識傳統如出一轍,是東方的“自家寶藏”在西方“被拿來主義”后“舊曲新彈”。由此可見,啟迪心智仍然需要一定的美德品質作為支撐,二者完全可以兼容,殊途同歸。那種認為“中華/東亞教育體系與好的教育制度所具備的一切已知優點都相互抵觸”[18]的偏執論調既無需辯護,亦無需妥協。
第四,心智導向與美德導向日趨靠攏。目前,尚無跡象顯示出西方國家把諸如儒家的求知方法納入西方教育的課程。相反地,中國和東亞的其他國家從教育制度到實際的教學內容,無一不全盤西化[19]。以高等教育觀之,當代大學生的學習特點被總結為知識的專業性、外延的開放性、運作的自主性、求解的探索性、運用的實踐性、個體的差異性[20]。加之泛在學習環境、網絡平臺以及后喻時代的來臨,教師、家長、學生三重主體發生了變化,訓導式、灌輸式、獨裁式教育招致有識之士的口誅筆伐,知識的“絕對真理性”遭遇顛覆,“生成性”與“不確定性”被揭示出來,東亞的教育理念逐漸在向心智模式靠攏。
(二)美德導向的新變與守護
第一,美德導向的漸行式微。當中國教育告別了私塾時代、書院時代與科舉時代,當代教育大多以知識教育代替人格教育,以政治教育代替品行教育。易中天教授曾痛斥“今天的大學簡直是飼養場”,由于被培養的學生多數變成了“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錢理群語)與“高學歷的野蠻人”(鮑鵬山語),教育中“美德缺席”的呼聲越來越高。關注受教群體精神價值的失落,是教育系統中人學視野的積極轉向。對于本土的傳統,理性的姿態是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教書育人始終保守德行精神,占據應有的人類精神之文化制高點,將鍛鑄人格視作永恒的教育真諦。學校教育回歸到“人的教育”,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美德導向的固有精華作為中華歷史共同體在文化上的恰切表達,其正當性得以挺立并持續強勁,茍日新又日新,方能實現與時俱進的文化意義。
第二,美德導向的時代變遷。當代高等教育的頂層設計是讓職業教育中學歷教育和職業培訓“兩個輪子一起轉”,同時鼓勵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從中小學基礎教育開始,創新教育成為素質教育的又一增長點,所有這些教育戰略的調整其實質都是更加張揚人的主體精神。有學者總結出創新人才應該具備內在動機、問題發現、多元文化經驗、說服傳播、專門領域知識、專門領域判斷標準共六種心智[21]。看來,中國學習文化的心智導向先天匱乏,但所謂文化,也“決不是鐵板一塊,釘插不進,水潑不進的東西”[22],教育的新階段新特征呼喚新思想新思路。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我們進一步領悟“以學習為中心的質量內涵觀”的真正意蘊,得西方的心智教育導向之風骨,而非掠其皮毛,因為學習模式是決定學習效果的內在微觀機制。
第二,美德導向的復雜情勢。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皆為整個人類文明的“子集”,全球化時代使得多種異質文化之間的聯系由此前的松散、斷裂、間接變得立體、緊密、復合,又緣于文化生成過程絕非單因子的直線推進,因而中華/東亞人學習的美德模式在多元教育環境里變得復雜,主要體現為移民、留學因素帶來的文化涵化。譬如,目前中國仍然是留美學生最多且增長最快的國家,現在也出現了流動的“跨國家庭”(transnational familie),還有來自亞洲的班機往西方投下一個又一個“降落傘兒童”(parachute children)。尤其是幾代移民的后裔,受“兒童發展生態龕”(ecological niches) 的改變更大。這樣同一個文化個體兼受兩種學習模式的熏陶,“一個人可以同時與自己文化中已濡化的部分以及在其他文化中涵化的部分一同成長”[23]。誠然,每一種學習方式緣于歷史悠久,其秉承的文化傳統作為自身獨特的精神標識與身份認同,不太可能由于吸收了其他文化的知識體系和教學法而消失殆盡。由于現代社會的文化彈性增大,排他性減弱,傳統約束力降低,因此在文化涵化的雙向運動中,文化共性日益增多。
第四,美德導向的當代揚棄。在李瑾看來,君子更接近儒家的最高境界。然而少說為佳成為智慧的象征,“君子敏于行而訥于言”“巧言令色鮮矣仁”等儒家教誨成了東方學生課堂互動的文化障壁,東亞學習者在課堂屬于緘默的“傾聽式學習”(listening-oriented learning),即使發言也往往是“猶豫的說話人”,而歐美學生受西方雄辯術與修辭學傳統的影響,十分健談甚至成為“魔鬼的辯護者”(devil’s advocates)[24]。玉成君子,實乃孔圣人念茲在茲的人格理想。事實上,“君子”胚胎于政治等級結構之中,其背后依附的是一整套的政治價值系統[25]。《論語》中某些命題與標準,已不再是當下界定君子形象的基本參照與完整指涉。膠柱鼓瑟,必貽害后學。這就警示我們:現代教育對傳統教育的繼承與突圍,需要現代文明因素與現代價值觀的攝入。儒家傳統需要當代的創造性轉換與轉換性創造,路途漫漫。
綜上,文化作為一種包含精神價值與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不同文化基質孕生出不同的學習模式。教育活動作為人類實踐的高級形式,“它應該而且只能是一種創造性實踐”[26]。“民族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唯在人類整體的文明進程中才能澄明”[27]。日前,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美國著名的亞裔教育聯盟主席趙宇空撰著的《華人成功的秘訣》,分享了華人父母如何薈萃中美教育理念之長,及其子女取得傲人成績并大比例進入常春藤等美國名校的成功經驗[28]。因此,未來教育必須致力于優化整合,不宜株守一隅,在理論與實踐雙重向度游刃于心智導向與美德導向之間,“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讓東方傳統以一種順暢的方式納入新的體系,在全球化語境中找到“浴火重生”的契機,進而獲得現代化前提下世界性的互補、互鑒、創新、創生。誠如2016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就記者“怎樣看待中西方教育的異同”問題的回答:我們的教育與西方相比,確有不盡人意之處,正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29]“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教育理念的生生之道,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人類。
參考文獻:
[1][3] [8] [9] [11] [12] [14] [18] [19][23] [24] [美]李瑾.文化溯源:東方與西方的學習理念[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前言,17,80,33,132,153,97,65,57,295,283.
[2]周瑾.自性與共生:儒學現代轉化的路向[J].北京大學學報,2015(6):97-107.
[4]Ishisada,M.(1974).The civi service examination:China s examination hell.chinese Education,7,1-74.
[5]Nobel Museum(n.d).Retrieved October 5,2010 from [EB/OL].http://nobelprize.org/nobel-prizes/physics/laureates.
[6]Ennis,R.(1987).A taxonomy of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and abilities.In J.Baron&R.Sternberg(Eds).Teaching thinking skills:Theory and practice (pp.9-26).New York:Freeman,p.10.
[7]Facione.p.(1990).Critical thinking: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nd instruction.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Delphi Report”Mibrae ,CA:Th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0]Levy,R.I.(1973).Tahitia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Jin,L,Cortazzi ,M(1998).Dimensions of dialogue:Large classes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rch,29(8),739-761.
[15]馮天瑜.中國文化生成史[M].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1.
[16][英]亞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論教育之道[A].大學之窗[C].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121-135.
[17] 解讀美國最時髦的教育理念:Grit [EB/OL].http://www.3lian.com/zl/2015/07-04/339121.html.
[20]暢肇沁.大學生學習特點探究[J].山西師范大學學報,2010(5):131-133.
[21]衣新發.創新人才所需的六種心智[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1(4):31-40.
[22]周谷城.中西文化的交融[J].復旦學報,1986(2):61-63.
[25]向欣.當代大學生新君子教育摭談[J].現代教育科學,2015(6):61-66.
[26]安富海.教育實踐是一種創造性實踐[J].高等教育研究,2014(3):73.
[27]鄒廣文.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綻放[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3):40.
[28]劉平.《華人成功的秘訣》解讀美華裔成功秘訣.中國青年報[N].2016-02-05(08).
[29]袁貴仁談中西方教育異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EB/OL].http://edu.newssc.org/system/20160311/001866647. htm.
(責任編輯:劉宇)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inds and Virtues——Comments on the “Cultural Origins: the Learning Idea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HOU Hairong, TANG Nan
(BodaCollege,JilinNormalUniversity,Siping,Jilin136000,China)
Abstract:The book of “cultural origins: the learning idea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shows the cultural attribution which can clarify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learning ideas that the European or western learning model lays stress on mind orientation while Chinese or Asian learning model focuses on virtue orientation,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ir distant and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y have their own origins and affili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because of acculturation and some other factors. With the advance of globalization, the education reformers should not only study further by themselves, but also gain advantages from both sides. They should know the enduring values of two learning concepts and merge the two learning models together to establish the ideal education vision of learning model with both minds and virtues.
Key words:mind orientation; virtue orientation; learning concept; cultural-root exploration; education introspection
[收稿日期]2016-03-11
[基金項目]吉林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項目編號:GH15777)。
[作者簡介]侯海榮(1971-),女,吉林長春人,博士,吉林師范大學博達學院科研處處長;研究方向:中國傳統文化、高等教育。唐楠(1986-),女,吉林通化人,碩士,吉林師范大學博達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教育學。
[中圖分類號]G4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16)05-0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