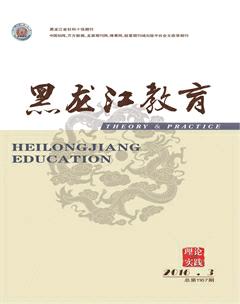關于“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教學實踐的幾點思考
王昊寧(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黑龍江哈爾濱150080)
?
關于“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教學實踐的幾點思考
王昊寧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黑龍江哈爾濱150080)
摘要:“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是黑龍江大學哲學專業本科生選修課程。現象學是現代西方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這門選修課程相應地也就成了哲學專業本科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在幾年的教學實踐基礎上,對這門課程在教材選取、講授過程、討論過程等幾個方面作出了反思。通過反思,發現了講授過程和討論過程存在著的一些問題,并作出了相應的調整。對講授過程的調整在于采取“開宗明義”的方式,使學生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認識到胡塞爾現象學的理論目的是什么以及所需要的方法又是什么。這樣一來,學生便會對胡塞爾的思想有一種整體把握,避免以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后果。對講授過程的調整,還在于采用不同的理論“視角”進行講解,這有益于在具體的教學實踐當中引導學生養成與時俱進的學術習慣。對討論過程的調整在于把現象學方法與學生自己感興趣的哲學問題結合起來,引導學生自覺使用現象學方法去探討、解決自己感興趣的哲學問題,從而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關鍵詞:現象學;思維習慣;本科教學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于2009年秋修改本科教學計劃,增設了“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這門課程,并于2010年秋季學期實施,迄今已歷5年。從本科2008級到2012級,除2011級以外,目前筆者共為4屆本科學生講授過這門課程。從課程的授后效果、督導評價、學生反饋等各方面意見綜合來看,本門課程對本科學生在學習現代西方哲學的過程中包括在考研、讀研過程中有較為重要的影響,故筆者對此進行了一些總結,也對不足之處作了反思。
一、在教材選取方面的思考
自2010年秋季學期開始為2008級本科學生講授“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這門課程起,筆者一直選用胡塞爾晚期代表作《笛卡爾式的沉思》作為教材。之所以選取《笛卡爾式的沉思》作為教材,有以下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笛卡爾式的沉思》是胡塞爾晚期的代表作。作為晚期的代表作,它兼具了胡塞爾思想的代表性與思想的成熟性,其對后來的哲學家(比如利科)影響也較大,因此,如果不對之有所了解,恐怕對后來的哲學家的思想難以把握。
第二,《笛卡爾式的沉思》思想覆蓋面較廣,幾乎涵蓋了胡塞爾思想的全部要點。早期的《邏輯研究》等著作論述較為集中,側重性和傾向性很大,相應地有些思想就沒有被涵蓋到或者被一筆帶過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笛卡爾式的沉思》更適合于本科學生全面了解胡塞爾思想。
第三,《笛卡爾式的沉思》本身就是一本講演錄集成,因此每一節的觀點都很鮮明,甚至可以說醒目,這便于學生掌握胡塞爾思想的要點。
出于以上原因,筆者選取《笛卡爾式的沉思》一書作為“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這門課程的主講教材。
當然,多年來一直選取一本著作作為主講教材,也有其弊端,例如,可能造成學生對胡塞爾早期思想或者更晚期的一些思想了解得不夠充分,所以筆者在實際講授過程中,結合具體的知識點,有針對性地將相關的早期思想或者更晚期的思想適量地引入進來,避免造成上述可能產生的弊端。
二、對講授過程的思考
在為2008級本科學生講授“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這門課程后,有學生反映,在上完這門課程之后,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也就是說,對胡塞爾現象學的思想無法整體性的把握。筆者對此作了反思。
在為2008級本科學生講授“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這門課程,筆者是按照《笛卡爾式的沉思》逐章逐節地進行講解。《笛卡爾式的沉思》思想覆蓋面較廣,知識點較多,這是它的優勢。但同時,由于思想覆蓋面較廣,知識點較多,對于初學者來說,便有一種無處下手的感覺,也就是學生所說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這是它的不利之處。
筆者針對這種情況,對講授過程作了調整,不再按照逐章逐節的方式進行講授,而是首先選取胡塞爾現象學中的一些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來進行講解。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學生能夠對胡塞爾現象學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形成清晰的認識。只有“概念清晰”了,下一步的講授才能順利展開。
在選取重點概念時,筆者是根據兩個原則來進行選取的,第一個原則是:選取胡塞爾本人最重視的概念,這一原則的目的是要尊重胡塞爾的本意;第二個原則是:選取與以前哲學史關聯性較大以及對后來哲學影響較大的概念。之所以根據這一原則進行選取,是因為選修“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這門課程的學生在此前都已經系統地學習過“西方哲學史”這門課程以及其他選修課。因此,選取與以前哲學史關聯性較大以及對后來哲學影響較大的概念,便于學生從以往已經學習過的知識或其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出發來接受胡塞爾的思想,這樣既可以把胡塞爾的思想納入到哲學史的宏大背景中或自己的興趣點上來加以消化吸收,又可以使學生把胡塞爾思想與其他的哲學思想聯系起來、結合起來。
但是,僅做到“概念清晰”是不夠的。為了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還要做到“思路清晰”。也就是使學生對胡塞爾現象學的思路有一個清晰的了解,知道它要做的是什么。為此,筆者進一步調整了講授方式,把原書中第40節和第41節放在開頭講。這是因為這兩節的內容表達了《笛卡爾式的沉思》一書的核心觀點,放在開頭講授,可以起到一種“開宗明義”的作用,使學生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認識到胡塞爾現象學關心的是什么問題、它的理論目的是什么以及相應的所需要的方法又是什么。這樣一來,在接下來的講授過程中,學生便會對胡塞爾的思想有一個清晰的思路、一種整體性的把握,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后果。
對講授過程的調整,還在于筆者在逐年講授過程中,采用了不同的理論“視角”。具體說來,筆者在2010年給黑龍江大學2008級本科生、2011年給黑龍江大學2009級本科生、2012年給黑龍江大學2010級本科生講授“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這門課時,采取或者說側重的是從“存在論”這一角度去解讀胡塞爾的《笛卡爾式的沉思》。而自2014年開始,特別是2015年,在分別為黑龍江大學2012級省外班和2013級省外班講授《笛卡爾式的沉思》時,則開始轉向側重從“倫理學”角度進行解讀。
筆者認為,這種理論視角的轉換,在講授過程中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首先,理論視角的轉換,意味著講授者本人思考層面的切換。而這種切換在具體的教學實踐當中顯然具有積極的意義。其次,理論視角的轉換,有益于與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相結合,這樣更有利于在具體的教學實踐當中引導學生養成與時俱進的學術習慣。
隨著這種理論視角的轉換,在學生的論文里,從現象學的角度去關注、探討倫理問題的論文數量明顯增多,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對學生能夠將現象學“學以致用”這一環節的訓練初見成效。
三、對討論過程的思考
在講授“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這門課程時,筆者通常會安排一次討論。討論一般安排在這門課程的最后一次課。討論的形式是:首先由選修這門課程的每位學生簡要地講述其關于這門課程的結課論文的內容;其次,在每位學生講述完畢之后,由其他學生和任課教師針對其論文內容進行提問,該生須對提問作出回答,以此形成一種答辯式的互動。筆者認為,這種互動,有利于激發學生之間以及師生之間的深度對話與思考,有利于推動學生對其已完成的結課論文作進一步的思考或補充。
在經過幾屆的討論之后,筆者發現了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較多學生不能很好地掌握現象學方法,也不會使用現象學方法。
我們知道,現象學方法對現代西方哲學影響很大,甚至對其他一些相關學科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因此,如果學生不能掌握和使用現象學方法,那么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象學與解釋學著作導讀”這門課程在筆者這里是失敗的。
因此,筆者對此進行了長時間的反思,并在原有的討論模式的基礎上進行了調整。調整的重心是:把現象學方法與學生自己感興趣的哲學問題結合起來,引導學生使用現象學方法去探討、解決自己感興趣的哲學問題。這是一項比較艱苦而具體的工作。首先需要任課教師對學生的興趣點有所了解,比如有的學生對形而上學感興趣,有的學生對道德哲學感興趣,有的學生對政治哲學感興趣。那么,任課教師就要對學生的這些興趣點有所了解和掌握,并在平時的講授過程中有針對性引導學生將現象學方法與他們的這些興趣點結合起來。作為引導的過程,這是一個需要多次、反復提示的過程,提示學生有意識地、自覺地將現象學方法與自己的興趣點結合起來,并需要適當地做出一些例示,比如把現象學的懸擱方法與政治哲學的一些理論觀點結合起來,提示性地講授一下,以此來啟發對政治哲學感興趣的學生對此作出思考。
隨著這種提示與例示在講授過程中的滲透,有利于學生培養起自覺地使用現象學方法的意識,形成這方面的“思維習慣”,最后再在討論過程中,將學生的論文內容與現象學方法之間的關系作為重點提示對象以問題的形式向學生提出,使其更加明確地意識到如何使用現象學方法去探討自己所感興趣的哲學問題,從而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作者簡介:王昊寧(1978-),男,黑龍江雞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現象學、形而上學、倫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