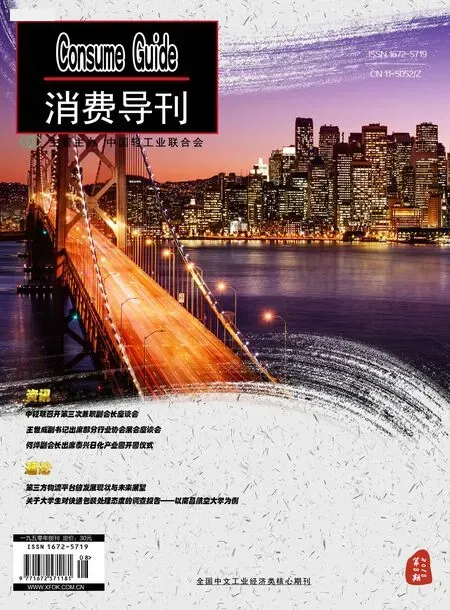我國醫療救助制度現狀、問題及對策分析
周雅倩 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
我國醫療救助制度現狀、問題及對策分析
周雅倩 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
重大疾病現今已經成為了導致眾多家庭致貧、返貧的重要原因,而醫療救助制度無疑是切斷因病致貧這一惡性傳導通路的有力武器以及保障居民基本健康權的“最后一道安全網”。然而我國現有醫療救助制度還存在很多問題,從救助病種及用藥范圍界定不清、救助對象覆蓋不全面,到救助標準不統一、醫療救助制度的法律保障不健全等,都大大降低了醫療救助的可及性。因此,醫療救助制度應該從按費用明確就醫用藥范圍,拓寬救助對象,提高救助額度、統一救助標準,理順醫療救助管理體制和加強立法保障幾個方面加以改善。
因病致貧 醫療救助 問題
一、我國醫療救助制度的發展現狀
醫療救助是政府通過提供財務、政策和技術上的支持以及社會通過各種慈善行為,對貧困人群中因病而無經濟能力進行治療的人群,或者因支付數額龐大的醫療費用而陷入困境的人群,實施專項幫助和經濟支持,使他們獲得必要的衛生服務,以維持其基本生存能力,從而改善目標人群健康狀況的一種醫療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司,2007)。在我國,城鄉醫療救助制度不僅是構建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一環,同時也是保障貧困人群基本生存權和健康權的最后一道安全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自2005年城鄉醫療救助開始運行以來,我國的醫療救助水平在不斷提高,直接救助人次、救助資金財政支出與自主參保參合人次等都在不斷攀升,醫療救助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盡管我國社會醫療條件水平相比之前已經得到了較大提高,但是現行醫療救助制度仍舊不健全。2011年我國災難性衛生支出家庭占比仍高達12.9%,近十倍于同期的歐洲國家(向國春等,2014),這表明仍有相當一部分受困群眾沒有被納入救助體系之內,其正常的醫療衛生需求得不到基本保障,極其容易陷入“因病致貧”的困境。因此,針對當前醫療救助制度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應盡快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醫療救助體系,真正實現“全民保障”、“全面救助”的終極目標。
二、我國醫療救助制度在救助界定方面主要存在的問題
(一)救助病種、用藥目錄限制過嚴且界定不統一,影響保障的可及性
救助病種目錄決定了醫療救助直接救助的范圍,而目前醫療救助制度的病種目錄基本沿襲了城鄉基本醫療保險和大病保險的界定病種,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報不了的病落到醫療救助上還是報不了,這樣一來就意味著那些罹患某種重大疾病但該病種又不在救助病種目錄范圍內的城鄉困難居民被排除在了救助體系之外(賴志杰,2014)。同時,救助病種目錄也決定了用藥目錄。用藥目錄范圍窄,則自費藥的領域就大,而對于自費藥,醫保、新農合都不報銷,當然也就沒有被納入醫療救助的范圍。即對于自費藥來說,整個醫療保障體系都形同虛設,極大程度上影響了醫療救助制度對受困群眾的可及性。
此外,盡管目前醫療救助主要是實施大病、重病救助,但是很多地區對重大疾病內涵界定仍不統一。以江蘇省為例,雖省內無錫、泰州等6個地區的重大疾病的起始費用標準均為當地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封頂線,但當前不同地區實行的基本醫療保險封頂線差異較大,因此即使名義上以同一標準作為起點,但是事實上因為地區情況上的差異性,界定范圍從一開始就失去了可比性。(詹長春等,2013)而對重大疾病內涵界定的不統一,必然會引起救助水平的差異,從而導致全省各地就醫和待遇保障的不公平性。
(二)救助對象覆蓋不全面,導致保障的不公平性
我國醫療救助對象包括城市救助對象和農村救助對象兩大方面。城市救助對象為城市居民低保對象中未參加城鎮職工醫保人員、已參加城鎮職工醫保但個人負擔仍較重的人員和其他特殊困難群眾。農村救助對象是農村五保戶、貧困戶家庭成員以及地方政府規定的其他符合條件的貧困農民。(任等,2015)而兩者均未將戶籍不在當地的外來務工人員納入體系范圍內。這些務工人員在外地工作,大多數人員收入較低。而按照醫療救助制度規定,他們無法得到工作所在地的醫療救助。此外,低保邊緣的困難民眾也未被明確納入醫療救助體系中,對他們來說,醫療費用的個人自費部分依然是較重負擔。同時由于這部分人群生活條件差,對自身的健康狀況重視度不高,小病拖、大病扛的現象非常普遍,事實上疾病發生率遠高于普通人群。因此他們也是醫療救助體系需要重點關注的人群。
(三)醫療救助標準較低,與適宜的保障水平標準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
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研究結論指出“當個人自付費用占醫療總費用的比例低于15%時,很少會有家庭受到災難性衛生支出的影響。”換言之,若醫療保障支付的醫療費用能沖抵醫療總費用的85%以上時,很少有家庭會受到受到災難性衛生支出的影響(詹長春等,2013),即“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家庭數量將大幅減少。在緩解災難性衛生支出對家庭影響的眾多因素中,重特大疾病的醫療救助理應擔任著主力軍的角色,而事實上我國醫療救助體系為家庭支付的比例還不能完全實現對災難性衛生支出的大幅沖抵效果,緩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有其局限性。
另外,《關于進一步完善醫療救助制度全面開展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工作的意見》中明確規定需設立起付標準及報銷比例。參保人要享受到醫療救助,則必須自付一定金額,并自行承擔一定比例費用。此項規定將有可能出現患者因無力跨過起付標準這道門檻或無力承擔報銷后自付部分而根本無法觸及醫療救助的情況。除起付線以外,較低的封頂線同樣也是拉低救助標準的一環。由于地方政府救助資金的短缺,各地都相應設置了較低的封頂線,這一舉措易導致救助效果的削減,從而使得人均救助水平整體偏低。設置起付線和封頂線本意是為了保證資金的使用效率,防止醫療服務的濫用,但是在整個救助體系中普遍較高的起付線和較低的封頂線同樣也讓醫療救助服務的可及性打了折扣。
三、完善我國醫療救助制度的
對策分析
第一,在病種界定方面,醫療救助的病種目錄可按費用進行界定,作相應增添。按照2005年WHO提出的家庭災難性衛生支出的概念來看的話,如果一個家庭發生的衛生費用達到或者超過其可支配收入的40%,則可認為該家庭發生了災難性衛生支出。換言之,即可將某地區重大疾病的起始費用標準定義為該地區災難性衛生支出的起始點(即該地區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40%)。也就是說在一定時期內(通常指一年),當參保人發生的住院費用達到或超過當地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40%時,即可將其所患疾病視為住院重大疾病,并且參保人可以享受醫療救助服務(詹長春等,2013)。與此同時,病種目錄決定用藥目錄,增添之后的病種目錄所對應的醫療救助可報銷的藥物范圍也將自行擴充。
第二,在救助對象界定方面,需要以其個人或家庭收入為基礎參照,同時參考其經濟、社會等多項特征,通過多維甄別機制來合理界定醫療救助對象(楊立雄,2012)。另外,在合理界定救助對象的同時也適當擴大醫療救助人群,給予城市中的外來務工人員充足的醫療救助保障,同時兼顧低保邊緣困難群體的醫療需求,讓患有重大疾病的困難群體都能夠被醫療救助這張“安全網”網住。
第三,適當提高重特大疾病的救助比例和封頂線,降低起付線。救助額度的提高對提高救助標準,拉升人均救助水平有很大的幫助。不僅能為極端貧困群眾救急,又可以使陷入重特大疾病困境的家庭獲得合理的救助,不至于半途而廢或者被醫療救助拒之門外。此外還需要簡化準入程序,采取事前事中和事后相結合的救助,事前措施主要指資助參保,主要面向身體健康但未參加新農合的貧困群體。事中服務則包括門診減免、藥品床位減收及總醫療費用優惠等,事后是指對經過幫助后仍困難的人員提供二次補助,對于已資助參保的人員,幫助其繳納新農合方案中規定的起付線部分比例,或承擔共付線超過封頂線的部分比例,對自主參加新農合且因病報銷后負擔仍然較重的人員提供二次救助。
[1]葉芳,王燕.重大疾病對家庭經濟影響的研究綜述.中國衛生經濟.2013(03)
[2]Xu K.Designing health financing systems to reduce 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R].WHO EIP/HSF/PB, 2005.
[3]向國春,顧雪非,李婷婷,張振忠,毛正中.我國醫療救助的發展及面臨的挑戰.衛生經濟研究.2014(03)
[4]最低生活保障司.城市醫療救助試點工作評價研究(摘要)[EB/OL].2007(12)
[5]賴志杰,城鄉醫療救助制度的現狀、主要問題與建設重點.當代經濟管理.2014(07)
[6]詹長春,周綠林,蔣欣.重大疾病醫療保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重慶醫學.2013 (24)
[7]任玙,曾理斌,楊曉勝.城鄉醫療救助制度之現狀、問題與對策.南京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1)
[8]楊立雄.我國醫療救助管理制度改革探析.學術研究.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