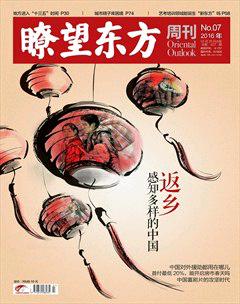馮英:芭蕾人才沒(méi)有形成良性循環(huán)
陳莉莉

2015年5月30日,中央芭蕾舞團(tuán)演員赴黑龍江齊齊哈爾扎龍國(guó)家級(jí)自然保護(hù)區(qū)采風(fēng)創(chuàng)作《鶴魂》
羞澀、緊張以及向往,中央芭蕾舞團(tuán)原創(chuàng)舞劇《鶴魂》的排練現(xiàn)場(chǎng),年輕演員努力將諸多情緒表現(xiàn)得恰如其分,但對(duì)于糾結(jié)與困惑的表達(dá),似乎顯得有些生硬。
位于中央芭蕾舞團(tuán)二樓的排練廳里,一直坐在旁邊指導(dǎo)的馮英站起來(lái),用舞蹈語(yǔ)匯將她自己理解的“掙扎”示范給年輕演員。
她對(duì)演員說(shuō),“你要讓觀眾看到你的自如,而不是你的努力。”
十多歲起遠(yuǎn)離父母、身赴異鄉(xiāng),開啟芭蕾舞生涯,沒(méi)想到一輩子就扎在了北京。幾十年的歲月里,演員、老師,中央芭蕾舞團(tuán)副團(tuán)長(zhǎng)、團(tuán)長(zhǎng)的角色變更,讓中國(guó)芭蕾舞的歷史上,有了一段屬于馮英的印跡。
如何用舞蹈語(yǔ)匯來(lái)體現(xiàn)更高的藝術(shù)性、表達(dá)更加深厚的情感,對(duì)馮英來(lái)說(shuō)已熟稔于心。
作為代表國(guó)家藝術(shù)形象和藝術(shù)水準(zhǔn)的院團(tuán),其責(zé)任與使命,不僅體現(xiàn)為對(duì)藝術(shù)性的要求。如何管理、經(jīng)營(yíng)院團(tuán),如何在變化紛繁的國(guó)內(nèi)以及國(guó)際舞臺(tái)呈現(xiàn)“國(guó)家級(jí)院團(tuán)”形象,這樣的問(wèn)題同樣拋給了馮英。
“雖然國(guó)際上說(shuō)21世紀(jì)芭蕾在中國(guó),但是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國(guó)芭蕾。這是我們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馮英說(shu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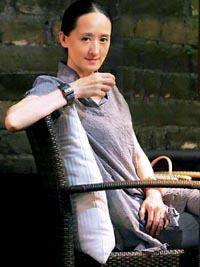
馮英中央芭蕾舞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藝術(shù)總監(jiān)。她于1979年畢業(yè)于北京舞蹈學(xué)院,1980年進(jìn)入中央芭蕾舞團(tuán)任主要演員,曾主演《天鵝湖》《吉塞爾》《堂·吉訶德》《紅色娘子軍》《林黛玉》等作品。1997年起,她先后任中央芭蕾舞團(tuán)教員、總排練者、芭蕾大師,副團(tuán)長(zhǎng),2009年2月被任命為團(tuán)長(zhǎng)。
用舞蹈語(yǔ)匯反映現(xiàn)當(dāng)代社會(huì)
《瞭望東方周刊》:作為中國(guó)芭蕾舞界的代表,中央芭蕾舞團(tuán)近年來(lái)的創(chuàng)作情況有什么趨勢(shì)?
馮英:我2009年起接任中央芭蕾舞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這時(shí)候的中央芭蕾舞團(tuán)經(jīng)過(guò)50年的摸索,已經(jīng)形成了一套科學(xué)的創(chuàng)作、創(chuàng)編、創(chuàng)排規(guī)律。從我接班以來(lái),我們就堅(jiān)定地傳承中芭精益求精、不斷追求的藝術(shù)信念。現(xiàn)在,中央芭蕾舞團(tuán)的發(fā)展思路從原來(lái)兩條腿走路變成了三足鼎立。站在國(guó)家級(jí)院團(tuán)的方陣?yán)铮醒氚爬傥鑸F(tuán)承載著“中國(guó)芭蕾將引領(lǐng)世界”的夢(mèng)想或者說(shuō)追求。
傳承、引進(jìn)經(jīng)典上,我們每年必須保持復(fù)排、引進(jìn)一到兩部經(jīng)典作品。因?yàn)橹醒氚爬傥鑸F(tuán)是古典芭蕾舞團(tuán),必須讓中國(guó)觀眾看到和了解到世界古典芭蕾里面最經(jīng)典、最精彩的傳世之作,我們把這當(dāng)作自己的責(zé)任。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講好中國(guó)故事。比如《紅色娘子軍》這樣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讓所有中芭人更有信心,因?yàn)檫@部作品在創(chuàng)新、走出自己特色的芭蕾風(fēng)格上,稱得上是一面旗幟。后來(lái)我們也有《沂蒙頌》《草原兒女》《林黛玉》《祝福》《楊貴妃》《雁南飛》等作品。
除此以外,我們也不乏探索性的嘗試,比如《覓光三部曲》。上世紀(jì)80年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大潮涌進(jìn)中國(guó),大家都在困惑、尋覓。但是到底在尋覓什么?我們用舞蹈語(yǔ)匯反映年輕人在沉淪中如何覺(jué)醒。我們也嘗試過(guò)讓國(guó)際友人來(lái)編中國(guó)的故事,比如說(shuō)《梁祝》。我們?nèi)ヌ剿鲊?guó)際友人眼里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
《瞭望東方周刊》:看起來(lái)這些作品大多是反映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和革命時(shí)代的故事?
馮英:我要說(shuō)的第三方面,就是彰顯時(shí)代精神,做好現(xiàn)當(dāng)代作品的創(chuàng)排。只有做好這三方面,劇團(tuán)才能“穩(wěn)、準(zhǔn)、狠”地發(fā)展。也是在這樣的理念下,我們2010年創(chuàng)辦了“芭蕾創(chuàng)意工作坊”,一年一屆、到2016年已經(jīng)是第七屆了。其實(shí)工作坊的模式在國(guó)外非常普遍。我們通過(guò)這種實(shí)驗(yàn)性的項(xiàng)目,為年輕編導(dǎo),或者有志于在轉(zhuǎn)業(yè)后向編創(chuàng)方向發(fā)展的演員提供了很好的平臺(tái)。我們的理想是引領(lǐng)世界,用現(xiàn)當(dāng)代作品反映當(dāng)下的中國(guó)。如果現(xiàn)當(dāng)代作品不發(fā)達(dá),談何引領(lǐng)?
知名度得一場(chǎng)一場(chǎng)演出來(lái)
《瞭望東方周刊》:從中央芭蕾舞團(tuán)的情況來(lái)看,芭蕾舞的市場(chǎng)反應(yīng)如何?
馮英:從中央芭蕾舞團(tuán)50多年的藝術(shù)實(shí)踐來(lái)看,一個(gè)規(guī)律是,真正能反映人們所關(guān)心、跟人們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作品票房好,觀眾也喜歡。
從傳承經(jīng)典上來(lái)看,不管是中國(guó)觀眾還是國(guó)外觀眾,仍然最愿意看《天鵝湖》。隨著閱歷的不斷豐富,看芭蕾或者看藝術(shù)作品的中國(guó)觀眾的素養(yǎng)和水平不斷提升,他們也開始看《吉塞爾》《堂·吉訶德》這種風(fēng)格性強(qiáng)的作品了,還有法國(guó)的浪漫作品,比如《蝙蝠》等。
關(guān)于中國(guó)的作品,比如《紅色娘子軍》,還是老百姓最愛(ài)看的,可以說(shuō)是百看不厭。《紅色娘子軍》自1964年首演起到現(xiàn)在50多年,演出了4000多場(chǎng)。這個(gè)過(guò)程中,我們一直在觀察和調(diào)研,也曾考慮過(guò)年輕人會(huì)不會(huì)不接受這樣的題材。但是現(xiàn)在看來(lái),我們的擔(dān)心有點(diǎn)多余。
后來(lái)我們推出的《過(guò)年》,是根據(jù)《胡桃?jiàn)A子》改編的、反映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舞劇。舞劇中表達(dá)了很多關(guān)于家庭團(tuán)圓概念,還有存錢罐、陀螺、糖葫蘆、絲綢、青花瓷、仙鶴等個(gè)性鮮明的中國(guó)文化元素。在舞蹈語(yǔ)匯上我們也是想定為中國(guó)語(yǔ)匯和芭蕾語(yǔ)匯相結(jié)合。這部舞劇非常有意思,觀眾們很喜歡,也得到了國(guó)際上的普遍贊揚(yáng)。
《瞭望東方周刊》:現(xiàn)在芭蕾舞在大眾的認(rèn)知度上還沒(méi)有那么普及,這其中的原因或者困惑是什么?
馮英:我們的困惑,或者說(shuō)我們做得不夠的地方,就是宣傳力度和廣泛性的欠缺。
這個(gè)與我們的經(jīng)費(fèi)有關(guān)系。一直以來(lái),國(guó)家院團(tuán)創(chuàng)作經(jīng)費(fèi)雖然在逐漸改善,但是還沒(méi)有到宣傳、推廣領(lǐng)域。經(jīng)費(fèi)不足,肯定就有所限制。像我們自己做的《過(guò)年》,宣傳的幅度和廣泛性就差一些,這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芭蕾藝術(shù)的傳播和普及。這不像《紅色娘子軍》,因?yàn)楫吘菇?jīng)過(guò)50多年的時(shí)間,大家對(duì)這個(gè)故事已非常熟悉。
《過(guò)年》就靠我們一場(chǎng)一場(chǎng)地演,現(xiàn)在口碑也不錯(cuò),觀眾給的評(píng)價(jià)都說(shuō)老少皆宜。前后經(jīng)歷了五六年的沉淀,現(xiàn)在很多觀眾覺(jué)得過(guò)年就要看這個(gè)。每年春節(jié),我們也借此帶給大家喜氣祥和的氛圍。

中央芭蕾舞團(tuán)演員在彩排芭蕾舞劇《堂·吉訶德》
這些年來(lái),中央芭蕾舞團(tuán)其實(shí)就是要做文化大餐,各種各樣菜肴。因?yàn)橐喜煌瑢用嬗^眾不同的需求。比如《堂·吉訶德》等西方經(jīng)典的作品,完全就是欣賞。但是《過(guò)年》這樣的作品不一樣,能產(chǎn)生共鳴,現(xiàn)場(chǎng)有互動(dòng),有共同呼吸的氣場(chǎng)。所以我們對(duì)中央提的創(chuàng)作“人民需要的作品”也是有深深感觸的,這也是我們的創(chuàng)作宗旨。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guó)芭蕾舞在國(guó)際、國(guó)內(nèi)的傳播情況符合你的預(yù)期嗎?
馮英:中央芭蕾舞團(tuán)的性質(zhì)決定了它是一個(gè)國(guó)際化平臺(tái)。但是另一方面,中國(guó)有很多觀眾還沒(méi)有看過(guò)芭蕾,我們要做各種普及,讓觀眾知道、接受這種形式。在這點(diǎn)上中芭還是有強(qiáng)烈的使命感和主動(dòng)性的。
在這樣的國(guó)際背景和國(guó)內(nèi)情形之下,我們要把中國(guó)故事講好,帶著它們走世界。
2015年7月,《紅色娘子軍》在美國(guó)林肯藝術(shù)中心上演。雖然美國(guó)人講個(gè)人英雄主義,《紅色娘子軍》是表現(xiàn)集體英雄主義精神,但是演出效果仍然非常好,觀眾們都起立鼓掌。它的音樂(lè)真的給人以鼓舞和力量。那種激情、奮進(jìn)、熱血沸騰,美國(guó)的觀眾也可以感受到。
走向世界,主要是進(jìn)入主流社會(huì)、主流媒體、主流劇場(chǎng)。在這樣的定位下,還要把芭蕾普及到百姓中去,比如進(jìn)入學(xué)校、社區(qū)以及養(yǎng)老院、艾滋病等公益活動(dòng)中去普及。國(guó)外一些地方也會(huì)邀請(qǐng)我們給低收入家庭去做公益性演出,在演出過(guò)后我們就會(huì)介紹中國(guó)作品。我們也希望世界有更多地方、更多人認(rèn)識(shí)到中國(guó)芭蕾。而這個(gè)狀態(tài)的呈現(xiàn),我們希望是自如的、協(xié)調(diào)的。
人才培養(yǎng)需要良性循環(huán)
《瞭望東方周刊》:你如何看中國(guó)芭蕾舞的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
馮英:現(xiàn)在芭蕾舞的世界格局,從古典芭蕾上來(lái)看,還是俄羅斯、法國(guó)排在前面。這是有歷史淵源的,芭蕾舞藝術(shù)興起于法國(guó),路易十四建立了一所專業(yè)舞蹈學(xué)校。400多年來(lái),這所學(xué)校一直專門為巴黎歌劇院輸送人才。蘇聯(lián)時(shí)期也延續(xù)了對(duì)于文化的傳承和對(duì)于藝術(shù)的重視,馬林斯基劇院、莫斯科大劇院也有舞蹈學(xué)校,去對(duì)口輸送人才。
學(xué)校是他們最重要、最堅(jiān)強(qiáng)的后盾。我們?cè)瓉?lái)的老團(tuán)長(zhǎng)就愛(ài)講,一個(gè)良性的循環(huán)應(yīng)該是,一代一代地傳承、培育。我們今天發(fā)展的困惑是劇團(tuán)沒(méi)有自己的學(xué)校,應(yīng)該迅速建立起來(lái)。一個(gè)人才從學(xué)校培養(yǎng)出來(lái),進(jìn)了劇團(tuán),在劇團(tuán)做了多年演員后,再回學(xué)校培養(yǎng)人才。一個(gè)良性循環(huán)應(yīng)該是這樣的,這點(diǎn)從上百年的案例中很容易看到。現(xiàn)在我們的卻一直沒(méi)法實(shí)現(xiàn),制約了發(fā)展。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現(xiàn)在仍然有一些著名演員出國(guó),怎么辦?
馮英:現(xiàn)當(dāng)代芭蕾舞領(lǐng)域,德國(guó)、荷蘭比較發(fā)達(dá),美國(guó)的商業(yè)性比較濃厚。這些年,陸陸續(xù)續(xù)有中國(guó)芭蕾舞演員流向這些國(guó)家。中央芭蕾舞團(tuán)的演員收入不是很高,宿舍條件也不好。這些年我總在呼吁,希望能在這方面有所改善,因?yàn)榘爬傥柩輪T的培養(yǎng)不容易。曾經(jīng)有過(guò)調(diào)研,培養(yǎng)1個(gè)芭蕾舞演員相當(dāng)于6個(gè)飛行師的投入。要珍惜他們,他們的舞臺(tái)生命很短,我們要盡可能地留住他們。我們最無(wú)奈的就是人才外流,國(guó)家培養(yǎng)了這么久,但因?yàn)榇龅葐?wèn)題導(dǎo)致優(yōu)秀人才流到了別的國(guó)家,非常可惜。
我們比較普遍的困惑,就是我們的人才培養(yǎng)與劇團(tuán)無(wú)法保持一致。如果能有自己的學(xué)校,就可以針對(duì)劇團(tuán)的需求去培養(yǎng)人才,輸送到劇團(tuán),然后再回到學(xué)校去培養(yǎng)人才,成為一個(gè)良性的循環(h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