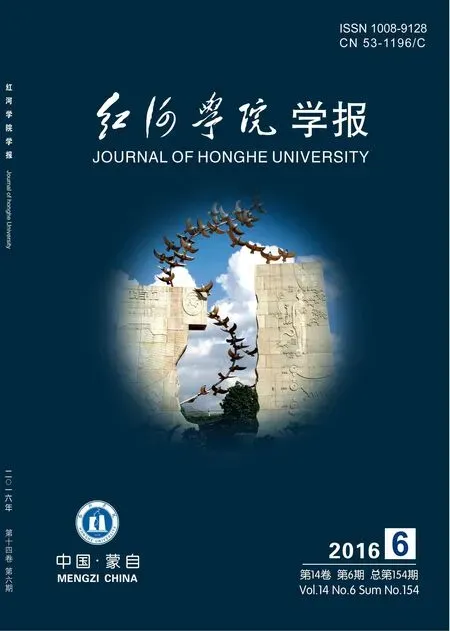從《聲無哀樂論》到《文心雕龍·知音》
——前進中的文學接受論
徐東哲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長沙 410012)
從《聲無哀樂論》到《文心雕龍·知音》
——前進中的文學接受論
徐東哲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長沙 410012)
《文心雕龍·知音》(以下簡稱《知音》)篇著力探討了文學作品的接受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學作品評價與接受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并從創作論的角度對文學批評與鑒賞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與方法,《知音》篇可謂是我國文學接受理論的濫觴與典范。《知音》篇中諸多文藝批評觀點繼承了魏晉時期嵇康《聲無哀樂論》中的理念,并對嵇康的文藝觀念進行了修正與完善,將嵇康玄學與儒學的文藝理論有機融合,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文學接受理論體系。
文學接受論;禮樂文化;道家;玄學
《知音》篇不同于書中其它篇目,沒有以文學創作為研究對象,而是主要論述讀者對于文學作品的接受與評價,在談及鑒賞原則時將創作觀點穿插其間,相為照應,體現了《文心雕龍》文學觀念的完整統一。《知音》篇開篇即點題: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7]
此處指出文學作品接受與鑒賞之難,紀昀即曾對《知音》篇評價為:“難字一篇之骨”。在文學作品鑒賞中,就作品本身而言,讀者往往因其形式復雜,感情曲折而難窺其文意;而對讀者自身來講,閱歷的不足及知識積累的匱乏,導致其無法對作品做出正確評價。正是由于主客觀多方面的問題,使得文學作品的接受成為一大難題。故而劉勰專作《知音》一篇論述文學接受問題。
“知音”一詞最早指善于理解音樂的能力,《禮記·樂記》云:
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 ,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1]
故而在后世會有“伯牙鼓琴,子其知音”的佳話。但劉勰《知音》篇中所謂的“音”,不簡單只有音樂這一層含義,而是一個泛藝術概念,包含著音樂、文學、書畫等多重美學觀念,尤其常出現于音樂及文學藝術中。這與中國古代文藝觀有著重要關聯。在中國文學產生自覺之前,詩樂舞結合是文學藝術的重要特點,《尚書·堯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2]《詩經》正是通過采集民謠樂歌而形成,詩都是合樂的,“詩”主要為“樂”來服務。中國早期的文學批評來自于音樂批評,正是自《詩經》開始,“季札觀樂”是先秦音樂批評的最好例證,在對風,雅,頌諸篇的評論中,從音樂的特點而聯系到政治的清明與否和倫理教化的優劣,他所觀之樂都是與詩結合的,可以說對音樂的批評同時也是對詩的批評,即文學批評。孔子全盤吸收了“季札觀樂”的批評理論,并將其作為儒家人格修養理論的基礎,《論語》中便有大量記述,如: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3]
文與樂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樂不僅與文相屬,同樣又有著教化民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政治功用,縱觀《詩經》305詩篇,祭祀,兵戎,儀禮題材的詩占據了很大篇幅,“國之大事,在祭與戎”,詩樂與政治生活息息相關。文王制禮做樂,通過音樂調節社會秩序,禮樂制度成為周朝統治的支柱。伯禽分封魯地,面對殷商遺民及奄國守舊勢力,三年時間“變其俗,革其禮”,通過灌輸禮樂文化使社會達到了高度和諧,至今尤有魯頌存世,所謂“頌”,便是周王室的正統雅樂。孔子高度贊揚了音樂“移風易俗”之功用,而儒家“克己復禮”之“禮”,便是以周代“禮樂文化”為內核的。可以說中國古代音樂及文學批評,便是以儒家“禮樂”思想為主流,與政治高度結合,以尚實、尚用為主要特點。但西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后,儒家經學在思想界占得統治地位,經學繁縟復雜,動輒“一字可注萬言”,內容也多為“倫理綱常”“陰陽災異”之事,與雅正的禮樂文化已愈走愈遠。文學淪為注經的工具,音樂也成為了禮儀道德的附庸,都已僵化呆板,其藝術性大不如前,儒家文藝觀已走進了一條死胡同。文學家與音樂家急于尋找新的出路,反復探尋著革新之法,就在這種環境下,嵇康的《聲無哀樂論》橫空出世,打破了儒家“禮樂”理論的禁錮,對之后新文藝理論的探索起到了開拓性作用。可以說,《聲無哀樂論》開《知音》篇之先聲。
一 “聲無哀樂”與“音實難知”
張少康曾對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做出極高的評價:
《聲無哀樂論》也是玄學道家文藝美學思想方面的綱領性文件,魏晉南北朝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正是按照它所啟示的方向發展的。[4]
之所以此篇文章對后世文藝理論可以產生巨大影響,主要在于其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儒家的“禮樂制度”。“哀樂”是儒家評判音樂的重要標準,在儒家音樂批評集大成之作《禮記·樂記》中有這樣的標準: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
儒家認為音樂是承載感情的工具,而音樂的感情基調則為評判音樂優劣的重要方面。孔子對《關雎》評價“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成為儒家對音樂藝術的最高追求,荀子作《樂論》,將孔子的思想發展成為了儒家“中和”的審美標準。所謂“中和”之美,強調的是感情與倫理的高度和諧統一,優秀的作品應是感情平和,不激不厲,無傷無哀的,情感的抒發合乎理性規范,最終以達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至高境界。“中和”之美在文學中則表現為“盡善盡美”與“文質彬彬”,都在強調文采與內容,美感與道德的和諧統一,這與儒家“中庸”的人生觀相輔相成。
重視藝術作品的情感表達并沒有錯,但忽略作品本身藝術價值,按照儒家道德追求將作品與情感內涵簡單和比,則使得藝術過于類型化而失去個性。嵇康正是抓住儒家以“哀樂”評價音樂的不合理性,立論展開批判,破天荒的提出:
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于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系于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5]
嵇康首先否定儒家對音樂的評判標準,從而在根本上動搖了儒家“禮樂”制度。嵇康認為對音樂的批評應從音樂本身形式入手,拋開道德倫理與政治功用,去探尋純粹的藝術之美。嵇康嗟嘆世人不解音律,只是迷信經書,人云亦云,以至于對音樂做出十分荒謬的評價。他舉出“季子聽聲”“師襄奏操”“師涓進曲”等所謂“知音斷事”的例子,以反證法一一反駁,指出若音樂與情感真的有明確對應關系,那么“三皇五帝可不絕于今日。”[5]顯然與現實不符,“聲有哀樂”說不攻自破,極附有邏輯思辨力。嵇康對儒家這種藝術理論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指出過去對音樂“哀樂”的評判為:
(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為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以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于當時,慕古人而自嘆。[5]
嵇康認為儒家并沒有客觀的對作品進行藝術分析,而是唯心的對作品做出詮釋,以神化其倫理道德觀念;同時對當世鑒賞家提出批評,認為鑒賞者并沒有真正的對藝術“得之于心”,只懂倚仗前言,唱著陳詞濫調,思想呆板僵化,不知變通。
《知音》篇秉持了嵇康的藝術欣賞觀點,主張文學鑒賞應當從作品本身入手,作品形式是不可或缺的評價要素。《知音》開篇就點出“知音”之難,與嵇康對音樂欣賞謬誤的批評極為相似,但劉勰具體分析了藝術鑒賞中的問題,并對其進行了抽象的概括,將前人文學批評中的錯誤總結為三類,即“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嵇康只注意到儒家文藝批評“重情輕質”的弊端,而未對鑒賞者個人修養及鑒賞水平有足夠重視。劉勰則認為個體的知識修養及文學觀念亦對作品的批評產生重要影響,以往批評中的種種錯誤不只是指導理論存在不合理性,更與鑒賞者自身的觀點態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縱然是秦皇漢武“鑒照洞明”,班曹“才實鴻懿”,如果不能破除一隅之見,做出再高的評判也走不出“貴古賤今”“ 崇己抑人”的誤區。劉勰與嵇康都肯定作品的藝術價值存在于作品本身,而不是所謂的“哀樂”。嵇康借魏晉時代新興的玄學思想對儒家禮樂文藝觀展開猛烈批評,使得藝術在死水般沉寂的社會風氣中逐漸蘇醒,而劉勰則將這種追求藝術本質之美的批評觀帶入文學,并以理論的形式加以確立。從“聲無哀樂”到“音實難知”,是一個從藝術覺醒至藝術探尋的發展過程。
二 “情隨曲變”與“披文入情”
很多人對《聲無哀樂論》的一個理解誤區在于,既然嵇康否定音樂中包含情感,那么嵇康一定割裂了音樂與情感的關系。事實上,嵇康正因為想要喚醒人們對于音樂的情感,才會將“哀樂”排除于音樂之外。首先,嵇康所論之“哀樂”,并不是后世所認為的一般意義上的情感,在其所處時代,所謂“哀樂”應該代表著儒家“禮樂”文化中的“哀樂說”。嵇康在《聲無哀樂論》開篇便提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5]引《論語》闡述“哀樂”實質,實際上就是在駁斥后世儒家傳統“哀樂”觀念,儒家對“哀樂”的看法已不單純是人的情感,而是與政治功用與倫理教化息息相關,如《左傳·莊公二十年》提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6]個人哀樂甚至可以決定國家命運,社會個體的哀樂成為了政治穩定的保障因素,因而統治者加強了對民眾的感情控制,任何過激與過哀的情感都是違背倫理而不被允許的,而音樂自然成為鉗制人民情感的主要武器。在這種背景之下,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正”之樂大盛,而其他音樂也被人為貼上了“樂”與“哀”的標簽,喪失了真正的藝術價值。嵇康否定的與其說是音樂情感,倒不如說是儒家音樂評判中的“哀樂觀”。嵇康或許知道自己作“聲無哀樂”論的片面性,但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只有這種理論才能起到“不破不立”的效果。只有打碎早已失去生命力的“哀樂觀”,才能誕生真正意義上的音樂,之后再來探討音樂與情感之關系才會有意義。
嵇康盡管提出“和聲無象,哀樂有主”,但其并沒有割裂二者的關系,恰恰相反,在《聲無哀樂論》中,嵇康論述到:
夫哀心藏于內,遇和聲而后發。
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
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5]
以上觀點中,嵇康認為音樂是激發人們情感的觸媒,情感通過音樂去表達,音樂的創作過程同時也是情感的抒發過程。而音樂亦不是“一致之聲”,面對作品,不同的人會產生不同的情感體驗,所獲得的藝術領悟也千差萬別,并不會與創作者的感受完全重合。嵇康從接受論的角度探討藝術批評問題,看到了欣賞者的情感體驗在批評當中的重要作用。盡管最后嵇康還是將批評觀念拉回到道家“大同于和”的理想,但他對“人情不同,各師所解。則發其所懷”[5]的發現無疑具有進步意義,就如同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中“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指出讀者個體情感與體驗影響著對作品的解讀,而這點決定了對作品的評判絕不是簡單的標準所能解決的。
《知音》篇對文學作品藝術性與情感的分析則更進一步,嵇康只發現了藝術表現情感,個體情感影響著藝術批評,而劉勰則在肯定嵇康觀點的基礎上,將探索文情作為文學批評的重中之重,并指出探索文情的困難與解決方法: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7]
“披文以入情”并不是簡單地事情。在探索文情時主要有兩方面的困難,即“篇章雜沓,質文交加”[7]與“知多偏好,人莫圓該”[7]。在客觀上,文學作品本身的復雜性使得批評難度極高;而在讀者主觀層面上講,自身知識積累的不足,鑒賞水平的低下,觀點態度的偏激往往導致對文章的理解難以全面貫通。
針對鑒賞文情中的問題,一方面,劉勰主張讀者自身需要加強文化修養,增加閱讀實踐經驗。這要求鑒賞者要能“博觀”,即擴寬閱讀的廣度,豐富自己的情感體驗,即為“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7]。只有博見廣聞,進行大量的藝術實踐工作,才能在鑒賞中拋棄自己的愛憎偏私,真正洞察到理辭中的文情。另一方面,劉勰制定“六觀”法去解決作品復雜多變的問題。任何復雜隱晦的文章都是由篇章辭句組成,必定有形式,“六觀”法正是從微觀入手,對文章的辭句、體裁、用典、音韻、風格等方面分解研究,各個擊破,對文章形成多方面的立體認識之后,便可將文情從抽象的藝術形式中抽離出來。“六觀”在《知音》篇中并沒有展開論述,但這一方法來自于《文心雕龍》中的創作論,“六觀”正是基于劉勰的文學創作理論,對批評鑒賞所形成的系統觀念,與《文心雕龍》全書是相互照應的。創作與批評是雙向活動,批評者只有充分理解創作原則,才能“沿波討源”,更好的去鑒閱文情。
三 “太和”與“圓照”
儒家在進行音樂批評時關注的是道德人倫,并將“哀而不淫,樂而不傷”的中和之美作為音樂藝術的至高境界。但嵇康則認為音樂產生于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即為“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5],這是嵇康繼承了道家美學思想的結果。道家思想起源于老子,老子對于音樂的評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大音希聲”。道家推崇“道”,道便是萬物的起源與歸宿,因為自然體現了“道”的本質與規律,所以自然之中承載著“道”,即為“道法自然”。在自然之中,“無”是最高級的存在形式,“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道家認為藝術應該師法自然,不應受到人為的約束與限制,應該追求一種絕對自由,而“無”正是沒有任何約束,絕棄人工,渾然天成的藝術境界。當音樂拋棄音律、音色、規制等等限制的時候,便將進入“大音希聲”的絕妙境界。莊子在繼承老子美學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天籟”的藝術觀點。《莊子.齊物論》曰:
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8]
莊子認為真正美妙的音樂是萬物各遂其情而悠然自鳴,與自然和諧,與萬物統一所達到的“逍遙”境界。嵇康所處時代,統治者實行的高壓政策使士人壓抑苦悶,而《莊子》逍遙自在,追求自由的思想成為了人們普遍的理想追求,《莊子》也成為玄學的重要經典。嵇康正是在《聲無哀樂論》中發揚了莊子“天籟”的美學思想,提出:
五味萬殊,而大同于美;曲變雖眾,亦大同于和。[5]
而音樂的至高境界便是與自然相和諧,不受人為樂律規制與喜憎哀樂的影響,自由平和,陰陽圓融。而在鑒賞中,人們之所以對相同的音樂產生不同的感情,是“吹萬不同,使其自己”[8]的結果,人們若能物我兩忘,丟開自我,天人合一,便能體味到音樂中的自然平和之美,而這才是嵇康音樂鑒賞中的最高境界—“太和”,即為天人之間的絕對和諧。“太和”已擺脫了一己之情,而在鑒賞中充分領悟到藝術的美感,若想達到“太和”境界,就必須拋開人情,倫理,政治等世俗牽絆,使自身進入“虛靜”,充分感受音樂的平和之美,《聲無哀樂論》對此評價到:
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途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于歡戚,綴虛名于哀樂哉?[5]
而這一點正詮釋了鑒賞中平和心境對追尋“太和”之美的影響。
而在《知音》篇中,對鑒賞的最高境界定義為“圓照”之象,“圓照”一詞來源于佛教,《圓覺經》有言:
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凈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9]
“圓照”是指內心圓滿無礙,明澈空明的狀態。“圓”,即為圓滿,無缺憾;“照”,指擁有無上智慧(般若)后洞悉世間萬物的察驗能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云: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10]
劉勰將“圓照”的佛學思想引入文學,并不代表劉勰吸收了佛家藝術思想,而是“圓照”的圓融明澈的狀態正與劉勰所構想的文學鑒賞最高境界相契合。佛教與道家推崇自然的態度不同,佛教將世界看作虛無的存在,由地水火風構成,在成住壞空中不斷輪回,沒有歇止。《金剛經》曰: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11]
因此,佛教將心性看作是第一位的,修行就是修心,明心見性,即可頓悟成佛。劉勰認為完美的心性是鑒賞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只有鑒賞者內心圓通明凈,才能在鑒賞文學作品時做到周遍全面,洞若觀火,清晰透徹。相較于嵇康提出的“至和”之境,“圓照”之象更為關注人內心的感受與體驗,嵇康更為重視作品的形式美,認為最好的作品是沒有人為矯飾,發乎自然,渾然天成的,而最好的鑒賞也是追求達到天人合一,無染哀樂的境界,強調的是欣賞者與自然之道的契合。劉勰在肯定藝術形式美的基礎上,對鑒賞做出了更全面的分析。劉勰認為,人畢竟是藝術的創造者,藝術的鑒賞中不能拋棄人的作用,人被外物激發,產生了不同的情感體驗,并據此進行創作,因此每部作品的內涵意蘊都是不同的,藝術風格也是千差萬別,所以對作品的分析也一定要實際具體。為能做到客觀公允,清晰周全的把握每部作品的藝術特征,心性的圓融明澈便成了鑒賞的至高追求。相較于抽象的“至和”理念,由人的心性出發而產生的“圓照”更易為人所理解,但“圓照”對鑒賞者提出的要求也更為苛刻,“至和”只要求鑒賞者契合自然,而“圓照”則要求鑒賞者能夠充分把握每一篇作品的方方面面的特點。想要理無不達,必須先要心敏,而要達到“圓照”之象,必須要博觀,這與“披文入情”是一種道理,只有進行大量的實踐,積累廣博的藝術知識與經驗,才能達到“圓照”之象,內心才能明晰如鏡,對作品的批評才能做到周詳全面。
《聲無哀樂論》不僅是玄學音樂理論確立的標志,同時也為魏晉以后的文藝復興打開了一扇大門,而劉勰則將文學理論在這次復興中推到了一個巔峰。《聲無哀樂論》沖擊了儒家的“禮樂”制度,讓音樂擺脫了倫理與政治的桎梏,得以朝著真正的藝術化前進,在客觀上也給文學帶來了新的生命氣息,《知音》篇的創作正是在《聲無哀樂論》所帶來的勁風中產生與發展,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添加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李慧玲,呂友仁.禮記[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2]慕平.尚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9.
[3]張燕嬰.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5]嵇康.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4.
[6]左丘明.左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2
[7]劉勰.文心雕龍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7.
[8]莊周.莊子[M].北京:中華書局,2007.
[9]徐敏.圓覺經[M].北京:中華書局,2010.
[10]弘一法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錄[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3.
[11]江味農.金剛經講義[M].山東:齊魯書社,2013.
[責任編輯 自正發]
From The theory of Sound not Sorrow and Joy to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t Understanding Friend—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cceptance in Progress
XU Dong-zh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China)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t understanding friend has the main research problems of the literature acceptance.It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to point out that the problems of literature evaluation and acceptance,and it also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s on Writing theory.Therefore it is the source and the model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cceptance of China.Some viewpoint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have inherited corrected the concept of The theory of sound not sorrow and joy writing by Ji Kang,Wei jin dynasty.It organically melted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The metaphysics and Confucianism,developed it become to be a complete set of literature acceptance theory system.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cceptance;the culture of rites and music;The Taoist;The metaphysics
I206
A
1008-9128(2016)06-0049-04
10.13963/j.cnki.hhuxb.2016.06.015
2016-03-21
徐東哲(1990-),男,山東濟寧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學。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