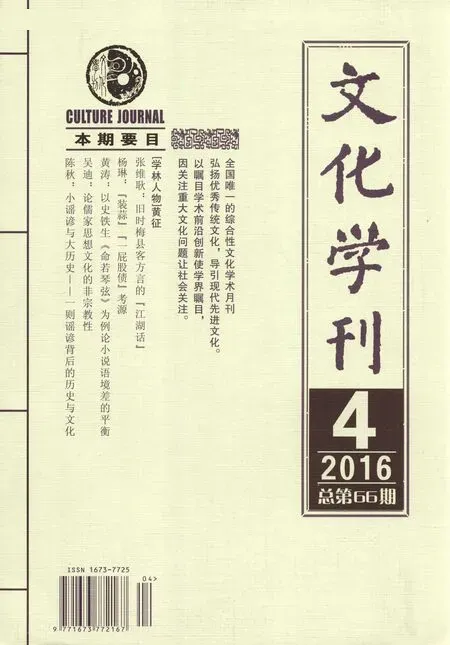論康德的批判理性
聶文文
(上海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上海 200093)
?
【文化哲學】
論康德的批判理性
聶文文
(上海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上海 200093)
在西方哲學史中,理性主義有悠久的發(fā)展歷程,然而歷經(jīng)古希臘和中世紀的發(fā)展,傳統(tǒng)理性主義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局。康德通過對理性的剖析,運用批判思維,創(chuàng)造性地對經(jīng)驗論和唯理論進行批判繼承,重構傳統(tǒng)理性主義,創(chuàng)立了批判理性主義,對近代西方的科技和社會發(fā)展以及現(xiàn)代西方理性哲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康德;困境;重構;批判理性
在近代西方哲學史上,理性主義的發(fā)展一直備受哲學家的廣泛關注,然而,長期以來,理性主義卻無法得其歸宿,直到康德摒棄對“理性”的盲目崇拜,對經(jīng)驗論與唯理論進行調(diào)和總結,才結束了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困境,開辟了“批判理性”時代,對近代西方科學及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也為現(xiàn)代西方理性哲學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流變及其困境
(一)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流變
哲學在本質(zhì)上是理性的事業(yè)。作為西方哲學史上公認的第一位哲學家,泰利斯首先提出了“什么是世界的本源”這個有意義的哲學問題,而他的回答“水是萬物的本源”則揚起了希臘理性的第一面旗幟,然而,與泰利斯所屬的伊奧尼亞派不同,畢達哥拉斯學派堅持數(shù)是萬物的本源,具有不變的特性。該觀點在古希臘哲學史上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將某種抽象的概念下降到可被感知的事物,而非通過從感覺經(jīng)驗上升到普遍理性的道路,認為理性主義是通過科學來理解和解釋自然的。
以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為起源,嚴格意義上的理性認為萬物在永無停息地運動著,且這種變化發(fā)展是按照某種規(guī)律進行的。此后,阿那克薩戈拉又明確提出努斯才是萬物的本源,是理性的精神實體;作為愛利亞學派祖師的巴門尼德則指出了真理之路和意見之路的不同:意見之路是按大眾的習慣去認識感覺對象,真理之路則是用理智來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學;智者學派的普羅泰格拉堅持“人是萬物的尺度”,把感覺經(jīng)驗的可靠性絕對化;蘇格拉底則認為要真正地理解人,就要從思維的角度入手,到其心靈世界中去探求真理;柏拉圖通過對現(xiàn)實世界進行重新建構,提出了理念論和靈魂學說,認為“普遍的東西(即共相)只能為思想所產(chǎn)生,它只有通過思維的活動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圖把這種有普遍性內(nèi)容規(guī)定為理念”[1]。到了亞里斯多德哲學,古希臘理性主義已發(fā)展到頂峰,它注重確定性,通過探尋事物的確定性來追問哲學本體論的根源,認為關于精神和自然的特質(zhì)可以通過一種簡單的方式來概括,進而形成一系列理性主義的原理。
到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席卷歐洲,人的理性被上帝的理性所取代,哲學開始為神學服務,上帝成為解釋真理和宇宙本體論的根據(jù)。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chǎn)力的快速發(fā)展,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和自然哲學思潮又重返歐洲大陸,人的理性開始對上帝的理性發(fā)出挑戰(zhàn)。
(二)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困境
歷經(jīng)古希臘時期的自然理性、中世紀時期神的理性和文藝復興時期人的理性三大階段的洗禮,近代西方哲學家以人的認識為出發(fā)點,將理性定義為人的一種能力,賦予理性更加完備的意義,探索出近代以來理性的意蘊。然而,隨著啟蒙理性主義的形成,理性主義內(nèi)部也正在發(fā)生一場裂變,即經(jīng)驗論與唯理論之爭,“唯理論者企圖以人的理性認識作為統(tǒng)一思維與存在的橋梁;經(jīng)驗論者企圖以人的感性認識作為統(tǒng)一二者的橋梁”[2]。但嚴格來講,經(jīng)驗論和唯理論都秉承了理性主義的衣缽,但在關于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普遍必然性的來源問題上,雙方各執(zhí)一詞,在相互競爭與否定中陷入了自我否定的困境。
在有著唯名論傳統(tǒng)的英國,經(jīng)驗論的代表人物培根、霍布斯、洛克和休謨試圖在經(jīng)驗的范圍內(nèi)定義理性;認為經(jīng)驗論本質(zhì)上是一種經(jīng)驗理性,其主要觀點為經(jīng)驗是知識和觀念的源泉,強調(diào)觀察、實驗,推崇經(jīng)驗歸納法,強調(diào)感性認識的重要性。然而,與經(jīng)驗論不同,理性論的主要代表人物笛卡爾、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認為認識源于理性,重視理性主義演繹法,強調(diào)可以通過數(shù)學方法的客觀性和普遍性,來得到確切的理性認識。
在唯理論者看來,來自于感覺經(jīng)驗的知識是偶然的、個別的、片面的,不具有確定性,知識的邏輯確定性也無法被保證,因此感性知識必然會被排除在科學知識的系統(tǒng)之外。唯理論者拒絕將經(jīng)驗作為理性認識的基礎,天賦觀念也必然無法為知識的普遍性與必然性提供充足的保障,這樣理論者的理性認識就自然成為無根之木。簡言之,近代哲學認識論由此進退維谷,陷入危機,經(jīng)驗論陷入懷疑論,至此沉默無聲;唯理論則陷入獨斷論,理性大廈坍塌無疑。
二、康德對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繼承和重構
(一)對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繼承
西方傳統(tǒng)理性主義內(nèi)部的經(jīng)驗理性論與天賦理性論的爭斗曠日持久,使得雙方都瀕于絕境,因而到了18世紀末,康德開始致力于調(diào)和二者之間的矛盾。由于受萊布尼茨—沃爾夫哲學體系的影響,因此在他的前批判時期,康德認為應將“天賦理性”置于經(jīng)驗的歸納綜合之上。與此同時,在不斷的思考與探索過程中,他有機會接觸到牛頓物理學,并由此注意到了經(jīng)驗的重要性,認為經(jīng)驗論在傳統(tǒng)形而上學和唯理論的批判中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對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重構
在康德看來,對理性主義的不斷追求是人的本質(zhì)體現(xiàn),也飽含了人對自身價值的肯定。傳統(tǒng)理性主義陷入自我發(fā)展的困境,主要原因就在于人們對理性認識的片面性,因此只有對理性進行批判,實現(xiàn)對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重構,人們才能確保知識的確定性。
在休謨那里,基于感官的經(jīng)驗論被推向了極致。雖然他承認基于感官世界所接觸的事物獲得的印象,但卻不承認所獲得的印象就來自于其所看到的事物,認為一切離開我們的印象和知覺的知識都是不可信的,這種唯理論的先驗直觀性都只是后天的經(jīng)驗而已。基于此,康德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開始反思人的認識能力問題,以期重建科學的基礎。而笛卡爾所堅持的唯理論則企圖用數(shù)學精神解釋世界,一切基于數(shù)學精神推出的自然規(guī)律和知識就是科學,否認一切形式的感官主義。康德綜合二者,指出數(shù)學本身就來源于先天綜合判斷,解決了休謨對因果律的懷疑。“康德關于先天綜合判斷的學說是對唯理論和經(jīng)驗論兩種知識論的綜合”[3]。數(shù)學通過先天綜合判斷,將感覺經(jīng)驗嵌入先驗的經(jīng)驗模式,實現(xiàn)了對自然界規(guī)律的認識。知識離開了經(jīng)驗,就成為無源之水;知識離開了先天的認知形式,就難以保證其有效性。
可見,康德對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構建不但強調(diào)經(jīng)驗的重要性,將其作為一切知識的來源;而且還強調(diào)先天綜合判斷的重要性,主體的能動性被認為是實現(xiàn)對事物全面性認識的重要因素。通過對理性的批判重構,康德既崇尚理性,又指出了理性發(fā)揮作用的局限性。一方面,理性并非萬能的,受到個體差異及環(huán)境的影響,它只能在一定條件下發(fā)揮作用,以獲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另一方面,為實踐理性提供廣闊的空間,限制認知理性,為人的自由發(fā)展提供依據(jù)。
三、康德批判理性主義產(chǎn)生的重要影響
(一)對西方近代科學及社會產(chǎn)生的影響
如果說古希臘的理性重在探討宇宙的本體,中世紀的理性強調(diào)崇尚神學與信仰,那么近代的理性主義則被認為是照亮新時代的曙光,即自然科學的精神。而作為對傳統(tǒng)理性主義的集大成者,康德的批判理性無疑對近代西方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它是決定現(xiàn)代社會基本構架和現(xiàn)代人生存狀態(tài)的重大力量,直接塑造了當代世界的基本面貌”[4]。一方面,康德的批判理性主義不但重視經(jīng)驗的重要作用,同樣也重視理性邏輯思維的重要性。在近代科學發(fā)展的過程中,西方文化中固有的批判理性主義使得科學家能正確把握知識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用先天的理性思維,將眾多的經(jīng)驗材料從感性認識層面抽象到理想層面,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科學研究體系,進而對新科學技術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由于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fā)展,西方社會的生產(chǎn)力更加發(fā)達,由此萌發(fā)更加先進的生產(chǎn)關系,人們的社會觀念也更加理性化。社會的開化為新技術、新文化的產(chǎn)生培育了優(yōu)質(zhì)的土壤,二者的發(fā)展也相得益彰。
(二)對西方現(xiàn)代理性哲學產(chǎn)生的影響
從黑格爾哲學開始,西方現(xiàn)代理性主義哲學主要沿著兩條道路不斷發(fā)展: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在社會主義國家大放異彩,以叔本華唯意論為首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則在歐洲國家掀起高潮。非理性主義以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為背景,力圖利用自然科學的成果對事實進行歪曲利用,將非理性因素,如個體的感受、意念等,充當人與世界的本質(zhì),主張用認識論來推翻理性主義的統(tǒng)治地位。顯然,基于西方古典理性主義的科學精神及理性觀,遭到了非理性主義的強烈反對,因為非理性主義否認把握世界萬物規(guī)律性的可能性。因此,只有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才能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理性主義,以進一步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
[1]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288.
[2]張世英.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
[3]趙敦華.西方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301.
[4]高文武,潘少云.康德對理性主義的重建及其重要影響[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1,(2):26-29.
【責任編輯:董麗娟】
B565.59
A
1673-7725(2016)04-0193-03
2016-02-15
聶文文(1992-),女,河南焦作人,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