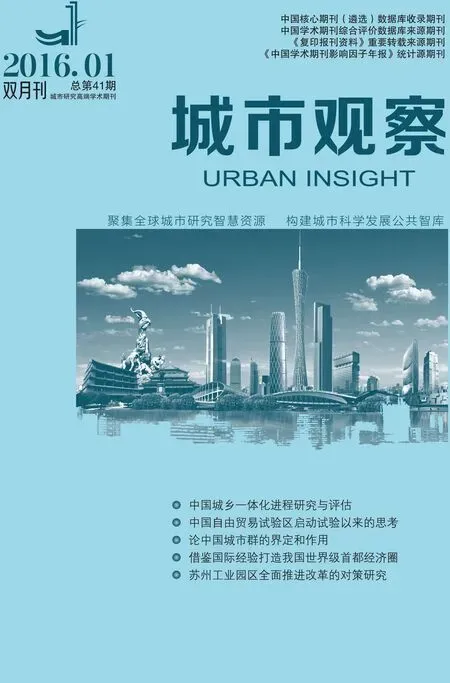論中國城市群的界定和作用
◎ 寧越敏
?
論中國城市群的界定和作用
◎ 寧越敏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群空間組織模式,并成為國家空間發(fā)展的重心。本文首先回顧了城市群研究進展,認為城市群界定必須建立在都市區(qū)基礎之上,并提出了六項界定指標;而后利用“五普”數(shù)據(jù)界定了13個城市群,并采用“五普”和“六普”數(shù)據(jù)分析了城市群的人口增長動態(tài)和城市化趨勢。對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城市群在國家中的經(jīng)濟地位進行分析,并以珠三角為例,分析了其人口和經(jīng)濟集聚過程,認為由于珠三角極化發(fā)展態(tài)勢未發(fā)生根本改變,廣東省內(nèi)核心-邊緣格局仍將持續(xù)。
關(guān)鍵詞:城市群 界定 集聚與擴散
一、引言
城市群的概念最初來自宋家泰、崔功豪等人于1985年編著的《城市總體規(guī)劃》,該書對城市群下的定義是:多經(jīng)濟中心的(指同一級,或稱“城市群”)城市區(qū)域,如蘇錫常、長株潭、沈鞍撫本遼,甚至擴而大之,象京津唐地區(qū)都是。大城市及其周圍小城鎮(zhèn)或衛(wèi)星鎮(zhèn)的結(jié)合,可視為城市群類型的變型[1]。換言之,城市群是在一定區(qū)域范圍內(nèi),由若干個具有一定經(jīng)濟規(guī)模,且差異不大,彼此存在內(nèi)在聯(lián)系的城市集合體。
從“十一五”規(guī)劃起,我國歷次規(guī)劃都提出要發(fā)揮城市群對區(qū)域發(fā)展的輻射作用,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zhèn)化工作會議公報里進一步明確城市群要成為帶動區(qū)域發(fā)展的增長極。作為國家戰(zhàn)略的城市群,其概念源自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的大都市帶研究。戈特曼在研究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化現(xiàn)象時發(fā)現(xiàn),這一地區(qū)形成了由若干大都市區(qū)首尾連成一體,彼此在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存在著密切的交互作用的巨大的城市地域復合體,其人口規(guī)模超過了3000萬人。戈特曼采用megalopolis命名這一超級大都市區(qū)[2]。無獨有偶,增長極戰(zhàn)略也是由法國學者提出的。法國經(jīng)濟學家佩魯于1950年首先提出增長極理論,當時它被定義為對其他經(jīng)濟部門施加推進效應的一個快速成長的經(jīng)濟部門,通過投入產(chǎn)出原理,這種效應將帶動整個國民經(jīng)濟的發(fā)展。其后,增長極的理論被引入?yún)^(qū)域科學中,認為在特定的城市或區(qū)域中密集投資,可以激發(fā)周圍區(qū)域的成長。從1960年代開始,一些國家采用增長極理論編制區(qū)域發(fā)展規(guī)劃,以應用于落后地區(qū)的開發(fā)[3]。
大都市帶和增長極兩個概念及應用有顯著區(qū)別。戈特曼認為大都市帶是國家的核心區(qū)域,它集外貿(mào)門戶職能、現(xiàn)代化工業(yè)職能、商業(yè)金融職能、文化先導職能于一體,成為國家社會經(jīng)濟最發(fā)達、經(jīng)濟效益最高的地區(qū),具有國際交往樞紐的作用。而增長極戰(zhàn)略通常用于經(jīng)濟落后地區(qū)的開發(fā),通過對增長極的密集投資進而對周邊地區(qū)形成涓滴效應來促進區(qū)域的均衡發(fā)展。
2014年,國務院頒布的《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2014-2020)》及2015年中共中央關(guān)于“十三五”規(guī)劃編制的建議均提出要建設沿海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三個世界級的城市群,還要在中西部地區(qū)建設若干個區(qū)域性城市群及一批省內(nèi)的城市群以促進區(qū)域的均衡發(fā)展[2]。從目前城市群建設情況看,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一是迄今規(guī)劃所談的城市群皆缺乏一定的界定標準,造成城市群規(guī)模差異過大。如發(fā)展水平最高的珠三角城市群面積僅5.47萬平方千米,而長江中游城市群面積廣達31.7萬平方千米,超過除黑龍江外所有東部和中部各省的面積,也大大超過世界上兩個最發(fā)達的大都市帶——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帶18萬平方千米的面積和日本東京-北九州大都市帶10余萬平方千米的面積。顯而易見,如此龐大的城市群與定位于城市這一空間尺度的增長極相差甚遠。二是國外通常把空間增長極布局在經(jīng)濟落后地區(qū)以推動區(qū)域經(jīng)濟的均衡發(fā)展,而我國城市群往往已是區(qū)域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地區(qū)。從全國角度看,中西部地區(qū)城市群的發(fā)展固然有助于全國的均衡發(fā)展,但就城市群戰(zhàn)略而言,應該首先帶動本地區(qū)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首先探討中國城市群的界定問題,在此基礎上,分析城市群在區(qū)域發(fā)展中的作用,最后分析珠三角城市群崛起與廣東省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之間的關(guān)系。
二、中國城市群的界定
2000年以來,國內(nèi)外學者對大都市帶或城市群展開持續(xù)研究,而這一研究的前提就是相關(guān)概念的界定。
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學院大都市研究所的Lang和Dhavale于2005年發(fā)表了“Beyond Megalopolis: Exploring America’s New ‘Megapolitan’ Geography”一文,他們在戈特曼大都市帶概念基礎上提出巨型都市區(qū)“Megapolitan Areas”概念,認為這是人口超過1000萬人由都市區(qū)組成的集群網(wǎng)絡。巨型都市區(qū)要滿足以下標準:一是至少由兩個或更多的都市區(qū)組合而成,都市區(qū)和小都市區(qū)成連綿分布;二是預計到2040年人口規(guī)模達1000萬以上;三是具有獨特的歷史和認知的“有機的”文化區(qū)域;四是具有大致相似的自然環(huán)境;五是由重要交通走廊連接主要的城市;六是由物流和服務流形成城市網(wǎng)絡;七是以縣作為基本單位。通過這上述標準,他們界定出美國有10個巨型都市區(qū),其中6個位于美國東部,4個位于美國西部。這些巨型都市區(qū)除1個城市化水平為67.3%外,其余城市化水平均超過80%,顯示巨型都市區(qū)的重要特征是城市化高度發(fā)達的地區(qū),并在美國經(jīng)濟中起著重要的作用[4]。
我國學者姚士謀等首次使用“城市群”命名我國大尺度的城市密集地域[5],其后周一星在基于都市區(qū)界定的基礎上提出都市連綿區(qū)的概念[6],一批學者據(jù)此研究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及遼中南四個都市連綿區(qū)[7-9]。近年來,方創(chuàng)琳在其城市群研究中提出了“15+8”的概念,15指15個發(fā)育比較成熟的城市群,8指8個發(fā)展中的城市群,缺點是前者和后者規(guī)模相差太大[10]。
筆者認為,目前一些城市群的研究由于缺乏界定,空間尺度差異過大,由此或?qū)е乱?guī)模小的城市群經(jīng)濟總量過低,難以起到帶動區(qū)域經(jīng)濟增長的作用;或由于城市群圈定的范圍過大,致使城市群整體發(fā)展水平較低,內(nèi)部的區(qū)域差異較大。如姚士謀、方創(chuàng)琳等提出的成渝城市群的面積約為20萬平方千米,是我國最大的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面積的一倍,而成渝城市群在2000年五普時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僅28.8%。因此,城市群概念的確定和范圍的界定并不僅僅是學術(shù)問題,而是直接影響到城市群能否發(fā)揮對區(qū)域經(jīng)濟的帶動和輻射作用[11]。
鑒于城市群具有引領(lǐng)區(qū)域經(jīng)濟增長的作用,而這種作用的發(fā)揮需要城市群具有一定的規(guī)模和經(jīng)濟實力,筆者在過去提出的城市群界定標準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為以下6條標準:一是以都市區(qū)作為城市群的核心。由于中國城市的行政區(qū)劃不能反映城市實體地域的大小,有必要引入城市功能地域即都市區(qū)的概念。一個城市群至少有兩個人口百萬以上大都市區(qū)作為發(fā)展極,或至少擁有一個人口在200萬以上的大都市區(qū)。二是大城市群的總?cè)丝谝?guī)模達1000萬人以上。三是應高于全國平均的城市化水平。四是沿著一條或多條快速交通走廊,連同周邊有著密切社會、經(jīng)濟聯(lián)系的城市和區(qū)域,相互連接形成的巨型城市化區(qū)域。五是城市群的內(nèi)部區(qū)域在歷史上要有較緊密的聯(lián)系,區(qū)域內(nèi)部要有共同的地域認同感。六是作為功能地域組織的都市區(qū)缺少相應的經(jīng)濟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而地級市能夠提供較為齊全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因此城市群的組成單元以地級市及以上城市型行政區(qū)為主,包括副省級市、直轄市(重慶的市域規(guī)模相當于省,只計算核心地區(qū)),個別情況下包括省轄市,如中原城市群的濟源市,武漢城市群的仙桃、天門、潛江三市。
以2000年“五普”和2010年“六普”數(shù)據(jù)首先對中國大都市區(qū)進行界定,并辨認出若干個大都市區(qū)集聚區(qū)域[12-13]。由于2000年時中國整體的城市化水平還比較低,城市群的范圍不宜圈的過大,除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個別早已明確范圍的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的空間界定都以兩大都市區(qū)為端點,沿鐵路干線所形成的城市帶。如遼中南城市群主要以沈大線之間的城市組成,山東半島城市群主要由濟南-青島-威海之間的城市組成,成渝城市群主要以成都和重慶之間的城市組成,中原城市群主要以隴海線開封-洛陽之間的城市組成,等等。這樣,中國大陸合計有13個規(guī)模較大的城市群。其中,長江三角洲、珠三角、京津唐、山東半島、遼中半島、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吉林、中原地區(qū)、閩南地區(qū)、成渝地區(qū)等10個地區(qū)均有兩個人口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qū)以及一批人口在50~100萬的都市區(qū),這些都市區(qū)沿交通干線相互連接,形成了彼此間有著密切的社會經(jīng)濟聯(lián)系的城市群。此外,武漢、長株潭、關(guān)中等三個地區(qū)雖無兩個人口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qū),但核心都市區(qū)的人口超過200萬人[14]。
表1是根據(j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結(jié)果計算出的13個城市群的人口規(guī)模和城市化率。它們的總?cè)丝诰^了1000萬,按照城市群人口規(guī)模的大小,可將13個城市群分為三個等級:一級城市群的人口總規(guī)模達到5000萬人以上,包括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三大城市群。其中長三角城市群2010年的人口超過1億人,遠遠超過其他城市群的人口規(guī)模,是中國最大的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若包括區(qū)域中心城市香港、澳門,其人口規(guī)模也超過6000萬人,是中國第二大城市群。京津唐人口超過4700萬人,是第三大城市群。二級城市群的人口規(guī)模介于2000萬~4000萬之間,包括成渝、山東半島、遼中南、中原、武漢、閩東南等6個大城市群。三級城市群的人口規(guī)模介于1000萬~2000萬之間,包括關(guān)中、哈大齊、長吉、長株潭等4個城市群。
城市群是城市的集聚區(qū),一般具有較高的城市化水平。200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為36.09%,除中原城市群外,其他12個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其中,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和東北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均超過50%,山東半島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接近50%;而閩東南、成渝、武漢、關(guān)中、長株潭、中原等6個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均不到50%;成渝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僅為44.1%,但比四川盆地城市群28.8%的城市化水平已高出15.3個百分點。顯而易見,本文界定的成渝城市群比四川盆地城市群更好地反映它作為巴蜀地區(qū)增長極的地位。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mào)易組織后,全球資本加快向中國轉(zhuǎn)移,由于全球資本轉(zhuǎn)移主要發(fā)生在沿海地區(qū),所產(chǎn)生的就業(yè)機會導致中西部地區(qū)人口加速向沿海地區(qū)流動,這種雙向流動造成沿海城市群人口激增。2000年至2010年間,長三角人口增加了2020萬人,珠三角、京津唐兩個城市群人口也增加了1000萬人以上,三大城市群合計人口增加4347萬人。其他10個城市群除武漢城市群人口略微有所減少外,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別是同處沿海的山東半島、閩東南以及成渝、中原四個城市群的人口也增加了300萬以上。13個城市群人口合計增加6459萬人,而同期全國人口(不包括港澳臺)增加7400萬人。這表明歷經(jīng)30多年的改革開放,人口流動已突破省、市行政區(qū)劃的束縛,城市群這一空間單元已成為我國人口的主要集聚區(qū)。
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城市化率提升較快的時期,2010年我國人口城市化率為49.68%,而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和遼中南的城市化率接近或超過了70%,珠三角的城市化率甚至達到82.73%,成為一個超級都會區(qū)。其他城市群中,除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率略低于50%外,均在50%~60%之間,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表1 2000年,2010年中國城市群的人口和城市化水平
城市群的分布具有沿海、沿軸、沿江的特點,東部沿海地區(qū)有6個城市群,其余城市群則沿東北的哈大線、中部的京廣線、隴海線以及長江沿線分布(圖1),這和中國的人口分布格局和經(jīng)濟梯度空間格局是一致的。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構(gòu)成了我國的高鐵網(wǎng)絡。圖1還顯示了《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2014-2020)》提出的建設三大世界級城市群和建設中西部哈長、中原、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范圍。其中,京津冀城市群的范圍和二市一省行政區(qū)劃完全吻合,而其他城市群則仍以直轄市或地級市作為城市群的基本單元。

圖1 中國城市群分布
三、城市群的集聚和擴散效應分析
戈特曼認為大都市帶是國家的核心地區(qū),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地方。同樣,中國的城市群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也應該領(lǐng)先于其他地區(qū),這樣才能在國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中起到引領(lǐng)作用。2000年,13個城市群的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為52074億元,占全國GDP的58.25%。2012年,各城市群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達到了203053億元,占全國的比重上升到61.44%,經(jīng)濟集聚度有所上升。其中,長三角因其規(guī)模較大,占全國GDP的比重高達17.37%, 珠三角所占份額為9.21%,京津唐所占份額為7.62%。不過,長三角和珠三角占全國GDP的比重較早期已有所下降。三大城市群貨物進出口總額占全國的比重達74.5%, 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合計占全國進出口額的60%以上。三大城市群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為90%左右,其中長三角實際利用外資幾乎占全國的一半。在機場旅客吞吐量方面,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機場合計占全國的35.2%(表2)。另根據(jù)北京和上海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shù)據(jù),2012年,北京擁有跨國公司地區(qū)總部248個,跨國公司研發(fā)中心466個,上海則分別擁有445個和366個。綜上所述,三大城市群不僅已成為我國經(jīng)濟的核心地域,而且也是我國與世界經(jīng)濟聯(lián)系的樞紐。英國拉夫堡大學“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組2012年公布的世界城市網(wǎng)絡研究結(jié)果顯示,在世界城市的排名中,上海僅次于倫敦、紐約、巴黎、東京、香港,列第六位,而北京列第八位[15]。這證實了筆者在1998年的判斷,即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出現(xiàn)管理與生產(chǎn)分離的等級結(jié)構(gòu)對于中國城市等級體系的重構(gòu)有重要意義[16]。
一般認為,增長極的培育時間需要20年至30年。此后,由于增長極集聚了大量的經(jīng)濟能量,對區(qū)域發(fā)展的擴散和帶動效應將逐步顯現(xiàn),核心和邊緣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珠三角是我國最早實施改革開放戰(zhàn)略的地區(qū),從深圳被開辟為經(jīng)濟特區(qū)起,迄今發(fā)展已經(jīng)歷35年。從時間上說,珠三角已完成增長極的發(fā)展階段,其能量開始向邊緣地區(qū)擴散。表3顯示,1990年,珠三角人口和GDP占全省的比例分別為35.2%和65.5%,人均GDP是外圍地區(qū)人均GDP的3.49倍。1990年代是珠三角經(jīng)濟起飛的時期,人口和經(jīng)濟迅速向珠三角集聚。2000年,珠三角人口占了全省的一半,GDP更是占到了78.4%,而珠三角和外圍地區(qū)人均GDP的比值擴大到3.68,經(jīng)濟的極化現(xiàn)象十分顯著。為促進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廣東省很早就提出振興兩翼,促進北部山區(qū)發(fā)展的規(guī)劃,并出臺不少政策措施。進入21世紀,人口繼續(xù)快速向珠三角集聚,但經(jīng)濟的集聚勢頭大大減緩,一方面珠三角進入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時期,另一方面,珠三角向周邊擴散的“涓滴效應”有所加強。2010年,珠三角占全省的經(jīng)濟份額僅比2000年增加0.9個百分點,表明邊緣地區(qū)的經(jīng)濟增速已開始趕上珠三角,所以珠三角和外圍地區(qū)人均GDP的比值快速下降到3.19。

表2 三大城市群主要經(jīng)濟指標占全國的比例2012
近幾年,珠三角特別是深圳、廣州、東莞等城市為適應經(jīng)濟新常態(tài)出現(xiàn)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大幅度調(diào)整,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大量外遷,人口增長的速度也因此大大減緩,其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0.1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外圍地區(qū)很多市的經(jīng)濟增長速度超過了珠三角,使2014年珠三角GDP占全省的比重較2010年下降了0.4個百分點,但仍達到78.9%。這說明近年來珠三角一極發(fā)展的態(tài)勢雖有所減緩,但還沒有出現(xiàn)根本性的轉(zhuǎn)折。顯然,區(qū)域經(jīng)濟的發(fā)展有慣性的傳導機制,破除“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并不容易。而且,從珠三角的案例看,增長極的能量即使向外擴散,也未必遵循距離衰減的原則使毗鄰的邊緣地區(qū)首先得益。珠三角產(chǎn)業(yè)外遷并不總是發(fā)生在廣東省的兩翼或北部山區(qū),而是以“蛙跳”形式或遷往中西部地區(qū),或直接遷往東南亞國家。進一步看,由于深圳、廣州等地經(jīng)濟轉(zhuǎn)型較早,正在孕育下一輪發(fā)展的機會,而外圍地區(qū)的競爭力遠遠落后于珠三角,兩者之間的發(fā)展差異從長期看能否縮小目前尚難判斷。
四、結(jié)論
城市群是城市化空間組織的重要形態(tài),且多次寫入國家的發(fā)展規(guī)劃。根據(jù)本文提出的城市群界定6條標準,目前中國有13個大城市群,它們在國家經(jīng)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正在向世界級城市群發(fā)展。
但是,城市群在歷經(jīng)長期發(fā)展后,能否產(chǎn)生帶動和輻射作用,促進區(qū)域的均衡發(fā)展仍然有待觀察。特別是當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從勞動密集型轉(zhuǎn)向更多依賴人力資本、科技創(chuàng)新后,城市群特別是其中的核心城市因集聚了高級生產(chǎn)要素而擁有更強的競爭力,使缺乏高級生產(chǎn)要素的邊緣地區(qū)在競爭中仍然處于劣勢。因此,以增長級為理念的發(fā)展模式的利弊需要學術(shù)界長期觀察和更深入的探討。

表3 珠三角人口與經(jīng)濟的集聚和擴散
參考文獻:
[1]宋家泰,崔功豪,張同海. 城市總體規(guī)劃[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2]Gottmann, J. Ma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 [J]. Economic Geography, 1957(33): 189-200.
[3]于洪俊,寧越敏. 城市地理概論[M]. 合肥:安徽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1983.
[4]Lang, R. E. & Dhavale. D. (2005) Beyond Megalopolis: Exploring America’s New “Megapolitan” Geography. Metropolitan Institute Census Report Series, Census Report 05:01, May.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Alexandria.
[5]姚士謀,陳振光,朱英明等. 中國城市群[M]. 合肥:中國科學技術(shù)大學出版社,1992.
[6]周一星,史育龍. 建立中國城市的實體地域概念[J]. 地理學報,1995,50 (4):289-301.
[7]趙永革,周一星. 遼寧都市區(qū)和都市連綿區(qū)的現(xiàn)狀與發(fā)展研究[J]. 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7,(13)1:36-43.
[8]寧越敏,施倩,查志強. 長江三角洲都市連綿區(qū)形成機制與跨區(qū)域規(guī)劃研究[J].城市規(guī)劃,1998,1:16-20.
[9]徐永健,許學強,閻小培. 中國典型都市連綿區(qū)形成機制初探—以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為例[J]. 人文地理,2000,(15)2:19-23.
[10]方創(chuàng)琳. 中國城市群形成發(fā)育的新格局及新趨向[J]. 地理科學,2011. 31(9),1025-1033.
[11]寧越敏,張凡. 關(guān)于城市群研究的幾個問題[J]. 城市規(guī)劃學刊. (1) 48-53.
[12]寧越敏. 中國大城市群的界定和作用——兼論長三角城市群的發(fā)展[C]//寧越敏主編:中國城市研究(第三輯)[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3]張欣煒,寧越敏. 中國大都市區(qū)的界定和發(fā)展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的研究[J].地理科學, 2015,(35)6:665-673.
[14]寧越敏. 中國都市區(qū)和大城市群的界定——兼論大城市群在區(qū)域發(fā)展中的作用[J]. 地理科學. Vol.31, No.3, pp257-263,2011.
[15]http://www.lboro.ac.uk/gawc/world2012t.html.
[16]寧越敏. 新城市化進程—90年代中國城市化動力機制和特點探討[J]. 地理學報,1998,53(5): 470-477.
(責任編輯:李鈞)
On the Definition and Roles of City Clusters in China
Ning Yuemin
Abstract:The rapid urbanization of China has formed a new spatial form of city clusters, which has been the core of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city cluster,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definition of city cluster must be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 According to six indicators, the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a fifth census to definite 13 city clusters with a population of at least 10 millions in 2000, and analyzes the growth trend of population of 13 city clusters using the data of fifth census and sixth census. Then, the paper measures the economic concentration index of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Tangshan in national economy, and taking Pearl River Delta as a case to analyze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the city clusters as growth poles can play a role of trickling down to the peripheral areas so as to reduce regional disparity.
Keywords:city cluster; definition;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作者簡介:寧越敏,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主任,研究方向為城市地理、城市規(guī)劃。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1JJDZH00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171145。
【中圖分類號】F29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6.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