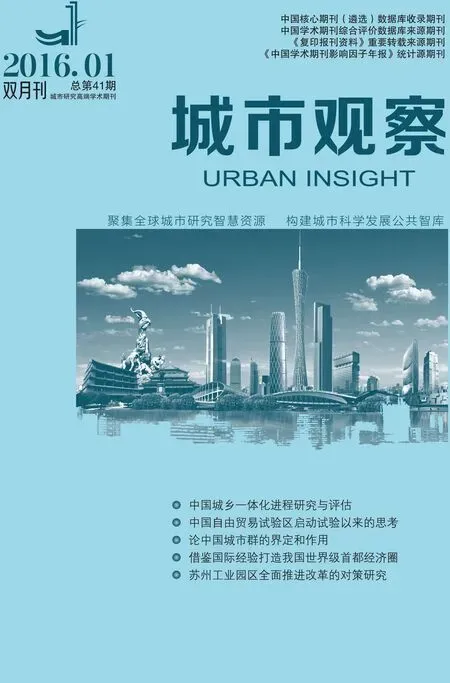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研究
◎ 段雪輝
?
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研究
◎ 段雪輝
摘要:運用2014年上海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生活調查數據,文章采用多類別對數比率回歸模型探討影響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研究發現,職住距離、居住時間、受教育程度與居民社區滿意度存在負相關關系;年齡、住房產權、住房類型對社區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社區滿意度 大型居住社區 居民
一、引言
建設大型居住社區是保障性住房體系建設的重要基礎,是一項惠及民生、造福百姓的民心工程,更是推進中國城鎮化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建設大型居住社區對改善城市中心區環境,緩解中心城區的人口與交通壓力,促進周邊郊區社會經濟發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大規模人口的迅速導入與集聚,使得大型居住社區公共服務配套建設需求增長,也使得基層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迅速重組。一直沿用至今的“鎮管社區”模式已經無法有效應對大型居住社區人口大量快速導入的現實挑戰。“產城脫節”的發展模式使得大量導入來的居民不能就近就業,大型居住社區淪為僅僅具備居住功能的“臥城”,大型居住社區“人戶分離”現象嚴重。
社區滿意度是判斷居民居住地選擇是否成功的一個天然標準[1]。社區滿意度不僅可以直接反映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的生活質量和主觀幸福感,而且還是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會沖突的晴雨表。研究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促進居民更好地融入大型居住社區生活,對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以及中國城鎮化進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社區滿意度研究
既有社區滿意度研究基本上有兩種取向:結構性研究和功能性研究[2]。結構性研究主要關注社區滿意度的概念以及結構要素的界定,功能性研究集中探討影響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在社區滿意度的影響因素研究中,西方大量的研究成果聚焦從需求層面探討影響居民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大量經驗研究證實社區服務或社區環境與社區滿意度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3-12]。國內不少學者的研究也證實社區需求關系對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影響[2,13-14]。還有學者從社區意識角度探討影響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因素[15]。耿金花的研究指出,社區管理與社區建設對于社區居民滿意度的影響最大[16]。
既有大型居住社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探討大型居住社區的戰略規劃、空間布局、開發設計以及公共資源配置、鎮管社區模式等方面。關于影響大型居住社區居民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研究中,Berkoz等人的研究指出,影響大型居住社區居民滿意度的因素在于社區不同功能區域的可涉取性、住房的環境特性、社區內各種設施的滿意度、環境安全、鄰里關系、住房環境的外觀等因素[17]。北京大型居住社區研究發現,影響居民生活滿意度的因素主要有教育資源、公共交通、文娛設施等因素[18]。南京拆遷安置社區的研究發現,居住時間、拆遷安置模式、職住空間關系、文化程度以及工作穩定性狀況是社區滿意度的主要影響因素[19]。天津村改社區的研究發現,居住適應性、生活便利性、多元需求滿意度是影響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因素[20]。
梳理既有大型居住社區滿意度的研究發現,不同學者運用不同維度來測量社區滿意度,社區滿意度的多元維度測量為文章留下了較大的研究空間。職業與居住空間不匹配是大型居住社區滿意度研究的重要維度,國內研究較少探討職住分離對居民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影響。本研究嘗試運用2014年上海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生活調查數據,探討影響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希望可以拓展學者關于社區滿意度的理解,豐富有關社區滿意度的定量研究成果。
三、數據與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主要按照地域劃分,兼顧考慮調研實施的簡便性和社區管理方式的代表性,按照判斷抽樣的方法,選擇閔行浦江、寶山顧村、嘉定江橋、浦東三林、松江泗涇五個大型居住社區進行研究。其中,顧村社區300份問卷,其他社區各200份問卷,共計1100份(實際完成1108份)。在每個大型居住社區,根據街坊類型(經濟適用房、動遷安置房等)和入住戶數(首選入住戶數更多的街坊),按照判斷抽樣的方法,選擇4個街坊/居委會,最終選擇了19個居委會。在每個街坊/居民區,根據居委會的入住家庭名冊,以機械抽樣的方式選擇50戶家庭進行調查,按照生日法選擇生日最小的一位年齡在18歲以上的常住居民作為調查對象。
樣本的基本情況參見表1。除表1描述的基本信息外,樣本的平均年齡51.35歲(標準差為0.47歲);平均年收入38043.66 元(標準差為1581元)。
(二)主要指標的操作化測量
因變量:社區滿意度是指居民通過自身對所生活社區的事前期望同事后實際獲得的人文關懷、生活服務感受相比較而得出的一種對社區能否滿足自身需求的主觀評價[13]。本研究使用“總體上,您對大型居住社區的管理狀況是否滿意?”、“總體上,您對大型居住社區的服務狀況是否滿意?”這兩個問題來測量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的社區滿意度,分為非常滿意、滿意、不太滿意 、一點不滿意、說不清,分別賦值為1、2、3、4、5。調查數據顯示,對大型居住社區管理狀況滿意的比例為59.71%,對大型居住社區服務狀況滿意的比例為60.46%(見表2)。為了研究需要,本研究對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情況進行轉換處理,如果對大型居住社區管理與服務狀況都不滿意,生成“不滿意”變量,賦值為“1”。對大型居住社區管理或服務其中一種狀況滿意,生成“弱滿意”變量,賦值為“2”。對大型居住社區管理與服務狀況都滿意,生成“強滿意”變量,賦值為“3”。調查數據顯示,66.51%居民對大型居住社區的管理與服務狀況表示滿意(見表3)。

表1 樣本基本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表2 居民社區滿意度基本情況

表3 轉化后的居民社區滿意度情況
自變量:職住分離是指由于制度約束和市場缺陷所導致的居住空間與就業空間的分離[21]。本研究使用“您的主要就職單位距離本小區大概有多遠?”這一問題來測量,分為:1公里以內、2~5公里、6~10公里、11~20公里、大于20公里、不固定。為了研究方便,本研究進行了重新編碼,分為5公里以內、6~20公里、20公里以上,分別賦值為1、2、3。
居住時間:分為“不到1年”、“1年”、“2年”、“3年”、“3年以上”五類。
住房類型:分為“經濟適用房”、“租用房”、“動拆遷安置房”、“普通商品房”四類。
控制變量:本研究將性別、年齡、年齡的平方、收入的平方、婚姻、受教育程度、戶口是否落在本社區、住房產權、職業類別等變量作為控制變項引入多類別對數比率回歸方程,以考察影響居民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三)研究假設
職業與居住的空間不匹配對居民日常通勤行為有重要影響,不僅會導致居民通勤距離以及通勤時間的增加,提高了居民私家車使用率,加劇了能源與環境的負擔,還可能造成其日常生活成本的增加,也容易導致居民主觀幸福感與社區滿意度的降低[21-32]。鑒于此,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設一:職住距離越長的居民,其社區滿意度會越低。
一般人們認為,居住在不同住房類型的居民,由于其生活環境不同,其對社區的認知水平也存在差異,對社區的滿意度也存在差異。鑒于此,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設二:居住在不同住房類型的居民,其社區滿意度存在差異。
居住時間對居民社區滿意度有較大影響,居民完全融入新社區需要較長的時間過程,居民在社區內居住的時間越長,就可能產生對新社區環境的習慣性適應,會提升社區歸屬感和認同感,社區滿意度就越強[2,3,15,19]。鑒于此,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設三:居住時間越長的居民,其社區滿意度會更高。
一般人們認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居民,其社會認知水平就越高,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就越高,社區滿意感就會越強。鑒于此,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設四: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其社區滿意度也會越高。
(四)分析方法與統計模型
多類別對數比率回歸(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是簡單對數比率回歸的擴展,由一組對數比率方程構成。如果把多類別變項中的一類作為基準類( baseline category) ,那么就形成了基準比較模型( baseline category contrast)。具體做法是先選擇基準類,然后將它的機率與其他各類的機率對比。在社區滿意度的回歸分析中,文章將社區不滿意作為基準類,研究一組自變項X 如何影響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的機率,用P1、P2表示將社區滿意度定位為弱滿意和強滿意的機率,那么由此形成的多項對數比率回歸方程就是:

四、統計結果與分析
文章通過對社區滿意度為不滿意、弱滿意和強滿意三個子樣本分別建模來考察影響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的影響。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表5)是關于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情況的多類別對數比率回歸分析。除了基本的控制變量外,模型一加入職住分離變量,模型二加入住房類型變量,模型三增加了居住時間變量。
(一)職住分離與社區滿意度分析
模型一中,與居民社區不滿意相比,6~20公里職住距離居民的社區強滿意度比職住距離不到5公里居民的社區強滿意度下降了62%。這種影響在0.05的水平達到顯著。模型三在模型一的基礎上納入了居住類型,居住時間兩個變量后,考察職住分離對社區滿意度的影響依然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作用,并且在0.05的水平顯著。與居民社區不滿意相比,20公里以上職住距離居民的社區強滿意度是職住距離不到5公里居民的社區滿意度的33.6%。職住距離與社區滿意度的統計結果顯示,職住距離越長,社區滿意度可能會越低。職住距離與居民社區滿意度一定程度上存在負相關關系,統計分析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研究假設一。
(二)住房類型與社區滿意度分析
模型二中,與居民社區不滿意相比,動拆遷安置房居民的社區強滿意度是經濟適用房居民社區強滿意度的43.6%。這種影響在0.05的水平達到顯著。在增加了居住時間變量后,這種影響依然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影響,這種影響在0.01的水平顯著。模型三中,與居民社區不滿意相比,動拆遷安置房居民的社區強滿意度是經濟適用房居民社區強滿意度的30%。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動拆遷安置房居民的社區滿意度最低。住房類型對社區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研究假設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驗證。
(三)居住時間與社區滿意度分析
模型三中,與社區不滿意相比,居住時間為1年、2年、3年、3年以上的大型居住社區居民,其社區強滿意度分別是居住不到1年居民社區強滿意度的10.1%、7.8%、9.4%、16.3%,并且影響分別在0.01、0.01、0.01、0.05的水平達到顯著。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居住時間不到1年居民的社區滿意度最高,其次是居住3年以上的居民、居住1年的居民、居民3年的居民,居住時間為2年的居民社區滿意度最低。居住時間一定程度上與社區滿意度負相關,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證偽了研究假設三。

表4 社區滿意度的多類別對數比率回歸分析

注: 因變量為社區滿意度,參考類別為社區不滿意 雙尾檢驗統計顯著度:p*< 0.05,p**< 0.01,p***<0.0011,參考類別為女性 2,參考類別為無配偶 3,參考類別為小學及以下 4,參考類別為戶口不在新社區 5,參考類別為無住房產權 6,參考類別為農民 7,參考類別為不到5公里 8, 參考類別為經濟適用房 9,參考類別為不到1年
(四)影響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分析
模型一中,年齡對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的社區滿意度有十分明顯的作用,這種影響在增加了居住類型和居住時間變量之后依然存在,并且都在0.01的水平達到顯著。模型三中,與社區不滿意相比,年齡每增長一歲,居民的社區弱滿意度下降40.5%,居民的社區強滿意度下降32.9%。模型一中,年齡的平方對社區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在增加了居住類型和居住時間變量之后依然存在。模型三中,年齡的平方的回歸系數為1,回歸系數顯示這種影響近似于U型,一定程度上表明年齡的增長不一定會帶來更高的社區滿意感。
模型一中,受教育程度對社區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與社區不滿意相比,高中文化程度居民的社區弱滿意度僅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居民社區弱滿意度的2.2%,這種影響在0.01的水平顯著,在增加了居住類型和居住時間變量后,依然在0.01的水平顯著。模型三中,與社區不滿意相比,高中文化程度居民的社區弱滿意度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居民社區弱滿意度的1.4%。模型一中,與社區不滿意相比,專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的社區弱滿意度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居民的弱滿意度的3.1%,這種影響在0.05的水平顯著,在增加了居住類型和居住時間變量后,這種影響在0.01的水平達到顯著。模型三中,與社區不滿意相比,專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的社區弱滿意度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居民社區弱滿意度的1.3%。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其社區滿意度可能越低。受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與社區滿意度負相關,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證偽了研究假設四。
模型三中,住房產權對社區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與社區不滿意相比,擁有住房產權的居民社區強滿意度是沒有住房產權居民社區強滿意度的7.7倍。統計結果顯示,住房產權與社區滿意度一定程度上存在正相關關系。
五、結論
關于社區滿意度研究,不僅是社會學領域的研究問題,還涉及經濟學、心理學、管理學、人口學等多個學科,需要學者運用不同的理論視角進行研究。基于2014年上海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生活調查數據,文章運用社會學實證的定量分析方法,探討影響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因素,重點關注了職住分離、住房類型、居住時間以及受教育程度對居民社區滿意度的影響,對既有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數據支持。通過第四部分的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上海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屬于中等水平。居民對社區服務狀況的滿意度要好于社區管理狀況。這說明,近年來上海大型居住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取得一定成效,社區管理水平也在逐步提高。然而社區服務與社區管理水平仍未能滿足居民不斷增長的社會需求。因此,為了保障大型居住社區有序運轉,必須提升大型居住社區服務與管理水平。
第二,職住分離對社區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職住距離越長,社區滿意度可能會越低。中國職住空間分離現象實際反映了城市居住郊區化、住房政策等宏觀結構性因素與城市居民對職住空間分離反應之間的關系[28],社會非自愿流動不一定會把人們重新分配到更好的社區[33],中國經濟適用房的發展可能導致新的社會隔離[34-35]。職住距離與社區滿意度負相關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大型居住社區居民社區滿意度具有較強的工具理性傾向,是需求滿足而致的社區滿意。公共配套設施的嚴重滯后可能是導致居民社區滿意度降低的直接原因,大型居住社區相當一部分居民是從城市中心地區搬遷而來,由于大型居住社區公共配套滯后和地處近遠郊區,與原來中心城區居住地反差較大,部分居民不可避免會產生“鄉下人”的感覺。由于不能就近就業,不少居民的工作單位仍在中心城區,日常通勤距離的拉長,必然增加這部分居民的通勤時間與生活成本,必然會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勢必降低居民的社區滿意度。
第三,住房因素對社區滿意度具有重要影響。研究發現,住房類型對社區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居住時間與社區滿意度負相關,住房產權與社區滿意度正相關。動拆遷安置房居民社區滿意度較低的事實,就可能與補償等歷史遺留問題有關。部分居民認為自身是利益受損者,被剝奪感強烈,自然對新居住地缺乏社區認同感和社區滿意度。住房建筑質量問題可能是造成居民社區滿意度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隨著居住時間的增加,房屋建筑質量問題會進一步暴露出來,低質量住房可能會導致居民社區滿意度的降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住房作為個人經濟實力的象征,可以直觀反映居民的社會經濟地位,明顯地影響了居民對社區的主觀認知與感受。在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利益關系及價值認同“碎片化”的格局下,經濟因素對社區滿意度的重要影響得到強化。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資源配置與資源滿足是衡量居民社區滿意度高低的核心要素。然而研究發現,是否擁有上海本地戶籍,以及戶籍是否落在新社區對社區滿意度并沒有顯著影響,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戶籍制度對社區滿意度的影響隨著中國住房體制的改革而逐漸減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
第四,受教育程度與社區滿意度負相關。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其社區滿意度最低。研究還發現,與教育程度密切關系的收入、職業變量對社區滿意度的影響并不顯著,這是否意味著社會經濟地位對社區滿意度的影響隨著中國住房體制的改革而逐漸減弱,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重要問題。
注釋:
①大型居住社區一般是指用地規模約為 5平方公里,人口規模約10萬人,以居住功能為主體,生活與就業適當平衡,功能基本完善的城市社區。
②鎮管社區是1993年浦東原嚴橋鎮(現屬于花木街道)最早提出的,指的是在現有的行政架構下,以黨的領導為核心,以社區共治為方向,以基層自治為基礎,在鎮與居委之間搭建覆蓋各居住區的綜合性管理平臺、網絡化服務平臺和協商式共治平臺,從而形成公共管理服務有效下沉、社區自治共治逐步發育的一種社區管理模式。
參考文獻:
[1]Garling, T, Friman, M.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esidential choice and satisfaction,in: J. I. Aragone’s, G. Francescato & T. Garling (Eds)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Choice,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2002, pp. 55-80.
[2]張晨,陳嘉俐.新型都市商住小區社區居民滿意度影響因素分析——基于蘇州工業園區若干社區的調查,中國名城,2013,24-30.
[3]Kasarda,John and Janowitz, Morris.,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4 (39): 328 -329
[4]Rojek, Dean C., G lemente, Frank, and Summers Gene F.,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 Study of Contentment with Local Services. Rural Sociology, 1975 (40): 177 - 200.
[5]Christenson, James A., Urban ism and Community Sentiment: Extending Wirth’s Model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79(60): 387 - 400.
[6]Stinner, William F. and Loon, Mollie Van., Community Size, Individual Social Position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Rural Sociology, 1990( 55 ): 494- 521
[7]Sirgy J, Rahtz D, Cicic M, Underwood R. A Method for Assessing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Based Services: A Quality of Life Perspective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0, (49):279-316.
[8]Theodori G L.,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nd attachment on individual w ell-being [J] .Rural Sociology, 2001.
[9]Sirgy J, Cornwell T. Further Validation of Sirgyetal’s Measure of Community Quality of Life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1, (12):5- 43.
[10]Sirgy J, Gao T, Young R, How Does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 Services Influences Quality of Life (QOL) Outcome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8, (3):81- 105.
[11]Epley D, Menon M.A Method of Assembling Cross- Sectional Indicators into A Community Quality of Life[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8, (2):281- 296.
[12]Seongyeon Auh, Christine C.Cook, Quality of Community Life Among Rural Residents: An Integrated Model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9, (94):377- 389.
[13]趙東霞,盧小君,柳中權.影響城市居民社區滿意度因素的實證研究[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65-71.
[14]仰和芝,李陽.老年失地農民社區滿意度影響因素調查與對策[J].安徽農業科學,2015,(1):334-336.
[15]桑志芹,夏少昂.社區意識: 人際關系、社會嵌入與社區滿意度——城市居民的社區認同調查[J].南京社會科學,2013(2):63-69.
[16]耿金花,高圣齊.基于聯立方程的社區滿意度模型[J].系統工程,2007,(3).
[17]Lale Berkoz. S,sence Turk. Omer L.Kellekci.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User Satisfaction in Mass Housing Areas: The Case of Istanbul, European[J]. Planning Studies.2009, 17(1):161-174.
[18]王淳.城市外圍大型居住區的公共服務配置與居民生活滿意度——以北京市為例[J].城市觀察, 2012,(1):109-114.
[19]夏永久,朱喜鋼.城市被動式動遷居民社區滿意度評價研究——以南京為例[J].地理科學,2013,(8): 918-925.
[20]王瀟,焦愛英.城鎮化發展中“村改社區”居民認同感實證研究——以天津市為例[J].經濟論壇,2014,(7):103-106.
[21]鄭思齊,曹洋.居住與就業空間關系的決定機理和影響因素——對北京市通勤時間和通勤流量的實證研究[J].城市發展,2009,(6):29-35.
[22]周素紅,閆小培.廣州城市居住-就業空間及對居民出行的影響[J].城市規劃,2006(5):13-18.
[23]鄭思齊,張文忠.住房成本與通勤成本的空間互動關系:來自北京市場的微觀證據及其宏觀含義[J].地理科學進展,2007,(2):35-43.
[24]李強,李曉林.北京市近郊區大型居住區居民上班出行特征分析[J].城市問題,2007,(7):55-59.
[25]李雪銘.基于居民通勤行為的私家車對居住空間影響研究—以大連市為例[J].地理研究,2007,(5): 1033-1042.
[26]孫斌棟,潘鑫,寧越敏.上海市就業與居住空間均衡對交通出行的影響分析[J].城市規劃學刊, 2008,(1):77-82.
[27]張艷,柴彥威.基于居住區比較的北京城市通勤研究,地理研究[J].2009,28(5):1327-1340.
[28]劉志林,王茂軍.北京市職住空間錯位對居民通勤行為的影響分析——基于就業可達性與通勤時間的討論[J].地理學報,2011,(4):457-467.
[29]鐘喆,孫斌棟.居住-就業平衡與城市通勤——以上海普陀區為例[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2,(3): 88-92。
[30]張萍,李素艷,黃國洋,閆倩倩.上海郊區大型社區居民使用公共設施的出行行為及規劃對策[J].規劃師,2013,(5):91-95.
[31]黨云曉,張文忠,余建輝,諶麗,湛東升.北京居民主觀幸福感評價及影響因素研究[J].地理科學進展, 2014,(10):1312-1321.
[32]劉望保,侯長營.轉型期廣州市城市居民職住空間與通勤行為研究[J].地理科學,2014,(3):272-279.
[33]Goetz, E. Desegregation in 3D: displacement, dispersal and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public housing[J]. Housing Studies, 2010, 25(2): 137-158.
[34]Wang, Y. P. & Murie, A.Social and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housing reform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0, 2(2):97-417.
[35]Stephens,M. locating Chinese urban housing polic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J].Urban Studies, 2010,7(14):2965-2982.
(責任編輯:李鈞)
Research on Community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s In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Duan Xuehui
Abstract:Based on residents’ survey data of Shanghai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2014, the article employs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ommunity satisfaction in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job-housing separation, the length of residence time, education level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ge, house type and house property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community satisfaction in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Keywords:community satisfaction;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residents
作者簡介:段雪輝,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會學、組織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D669.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6.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