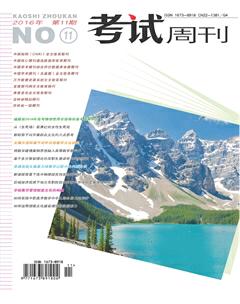高效課堂里的“小先生”
舒華榮
“陶博士并不僅僅屬于中國,而是屬于世界的……在美國,大家都知道陶博士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 這是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在《紀念陶行知博士》中對陶行知先生的評價。宋慶齡更說陶行知先生是“萬世師表”。陶行知先生雖然主要生活在民國,但他的許多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有寶貴的指導借鑒意義。他的“教育救國”在當時雖然沒有實現,但“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在當下的中國是不易之真理。在陶行知先生的眾多創造性教育思想和實踐活動中,“小先生制”就是其中極富特色的部分。
陶行知先生非常重視當時中國的鄉村教育,并為此專門在中華教育改進社起草發表了《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提出了要改變一百萬個鄉村,而且身體力行,先后創辦了曉莊試驗鄉村師范、山海工學團等學校,創立了生活教育理論,開展了平民教育,等等,創造性發明并推行了藝友制、小先生制等極富中國特色的教育思想和形式。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論是他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的精華,他創造的“小先生制”就是其重要體現和實現形式。“小先生制”不僅是他“生活教育”理論的繼承和創新,而且在實踐上推動了“生活教育”理論在全國的傳播和發展。因此,我們應當充分肯定陶行知“小先生制”教育思想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并結合時代特點加以發展,以指導今天中國的教育改革實踐。
1932年,陶行知于上海創辦上海工學團,開展普及教育運動,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他主張“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并在教育實踐中總結了“即知即傳”的方法,初步創立了“小先生制”。先生即教師,“小先生制”意為以學生、小孩為師,讓小孩教小孩,小孩教成人,這既是一種教師教育方式,又是一種學生學習方式。陶行知認為,小孩子有很大的力量,小孩子能做先生,做先生的不局限于師范畢業。“即知即傳”是小先生制的一個重要原則,即用自己所學的知識教人,一面溫習,一面把學問傳給他人。后來,陶行知在創辦其他學校時,進一步發展了“小先生制”,并為此編寫了適用于當時農村的識字課本,而且實驗效果良好。何謂“小先生”,用陶行知先生自己的話就是:“生是生活。先過那一種生活的便是那一種生活的先生,后過那一種生活的便是那一種生活的后生,學生便是學過生活的人,先生的職務是教人過生活。小孩子先過了這種生活,又肯教導前輩和同輩的人去過同樣的生活,是一名名副其實的小先生了。”他又說:“小孩子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小孩子隊伍里最進步的小孩子!”從中可看出他濃重的“生活教育”思想,他認為學生并不只是知識的接受者,也可以做“小先生”,也可以向別人傳授知識,每個學生都可以并有義務進行文化知識的交流和傳承。陶行知先生曾說:“普及生活教育所要樹立的第一個信念,便是小孩能做先生。自古以來,小孩是在教人。但正式承認小孩為小先生是一件最摩登的事。這正式的承認,到現在,還只是限于少數的實驗學校。我們必須使大家承認小孩能做教師,然后教育才能普及,小孩的本領是無可懷疑。我們有鐵打證據保舉他們做先生……”所以,“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先生對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一個重大創新與發展,其中蘊涵了“即知即傳”、“教育民主”等基本價值和理念,這些思想為今天的教育改革和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啟迪,更是現今構建高效課堂的寶貴思想資源。
提高教學的有效性,使教學事半功倍,是自從有教學活動以來人們的追求目標之一。孔子有“因材施教”;張載認為教學要注意學生的可接受性,即“教之而不受,雖強告而無益”;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教育家蔡元培要求教師的教學不要“像注水入瓶一樣,注滿了就算完事”,而必須“引起學生讀書的興味”,“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都講給學生聽”,只有當學生有困難而自己又沒有能力解決的時候,教師才給以幫助。從中都可看出這些教育家對學生在教學中地位和作用的充分重視。陶行知先生雖然沒有對有效教學、高效課堂進行過專章論述和闡釋,但是他豐富的教學思想和實踐都體現了教學的有效性。在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中,“小先生制”正契合了當今的教育改革和實踐。
首先,即知即傳。“天下為公,文化為公”,“即知即傳,自覺覺人”,這是陶行知“小先生制”所蘊涵的一個重要思想理念。他說:“干民眾教育,便是要把教育知識變成空氣一般,彌漫于宇宙,洗蕩于乾坤,普及眾生,人人都得呼吸,空氣是不要錢買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呼吸,教育也就不能以金錢做買賣,人人可以自由享受。”他認為知識是天下之公器,屬于大家的,是公有的,他曾教育學生有擔任“小先生”的義務,識字的人有教不識字的人的義務。現今,當然不可能機械模仿當時的做法,但這種調動學生主動性和積極性,有天下為公,熱心于公益和公共事務的理念和情懷卻是當今社會急需的。在高效課堂中,正好可以發揮學生的這種主動性和積極性,先進輔后進,先知喻后知,先覺幫后覺,在合作和競爭中共同進步和提高。因為學生的進步與教師的教育教學雖然有很大關系,然而與班級學習氛圍,同齡人的相互影響,同學的感染有莫大關系。這種影響既有知識上的,更有價值觀、語言、心理上的部分。因為同齡人在這些部分很相似,更容易相互影響。
其次,教育民主。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都是受教者。陶行知說:“少爺小姐有的是錢,大可以為讀書而讀書,這叫做‘小眾教育,而人民需要的是‘大眾教育,為生活的教育。”陶行知先生這種人人爭當“小先生”在全社會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的思想已經超越了課堂教學的范疇,但仍可以在教師課堂教學中加以運用。這在當今教育改革中強調大力發揮學生主體作用,是有廣泛的用武之地的。在教學中要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陶行知先生認為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是平等的、民主的,他說:“教師要跟小孩子學習,不愿向小孩子學習的人,不配做小孩的先生。”“師生本無一定的高下,教學也無十分界限;人們只知教師教授,學生學習;不曉得有的時候,教師倒從學生那里得好多的教訓。”他又指出:“教師對學生,學生對教師,學生對學生,精神都要融洽,都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校之中,人與人的隔閡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師生在情感、精神上的溝通是實施有效教學的重要條件。
第三,能者為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是先師孔子的遠見和覺悟,我們也在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中重溫到這種思想和遠見。在談到兒童教育時他曾指出:“應該‘承認小孩子有力量,‘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創造力;所以教育者必須向兒童學習,‘不拜兒童做先生,就做不好先生。”陶行知先生還在他的“創造的兒童教育”一文中指出:“我們加入兒童生活中,便發現了小孩子有力量,而且有創造力。”陶行知曾經寫詩祝賀一學校:“有個學校真奇怪,小孩自動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學如在。”陶行知先生認為:小孩身上蘊涵著極大的創造力。因此,陶先生創造了著名的“即知即傳人”的“小先生制”,畢生倡導施行推廣。這在遍地文盲的當時具有積極意義,就是在文盲率大大減少的今天,在努力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的大環境中,仍具有借鑒和指導意義。一個最新的教學嘗試就是“翻轉課堂”,這是從英語“Flipped Class Model”翻譯過來的術語,一般被稱為“翻轉課堂式教學模式”。互聯網的普及和計算機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應用,使“翻轉課堂式”教學模式變得可行和現實。學生可以通過互聯網使用優質的教育資源,不再單純地依賴授課老師教授知識。而課堂和老師的角色則發生了變化。老師更多的責任是理解學生的問題和引導學生運用知識。借助互聯網和計算機在教學中的普及,使得知識獲得過程得以重構。“小先生制”借助互聯網和計算機技術在翻轉課堂中則有更加有效的運用,是新教改的有益嘗試。這當然需要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評價體系和標準,考試考核制度的配套改革,這些已經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人人爭當小學生,讓學生主動參與課堂教學活動,發揮學生主體作用和主觀能動性,從而使學生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搭建“小先生”施展才能的平臺,充分了解各類學生的特點特長和學習程度;結成幫扶共學的形式實現新時代的“小先生制”,培養互相幫助的團隊精神和合作意識;如可在班級中定期設立最佳資料收集獎,最佳合作獎,最佳口才獎,最佳組織獎,等等,這樣可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和培養他們的主體性。這些都是在新一輪教育教學改革背景下,對陶行知“小先生制”的豐富和發展。
參考文獻:
[1]怎樣做小先生.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
[2]怎樣知道小先生.陶行知全集(第四卷)[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
[3]小先生與民眾教育.陶行知文集[M].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
[4]劉金玉.高效課堂八講[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5]黃發國,張福濤,編.翻轉課堂研究與實踐:翻轉課堂微課設計研究與制作指導[M].山東友誼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