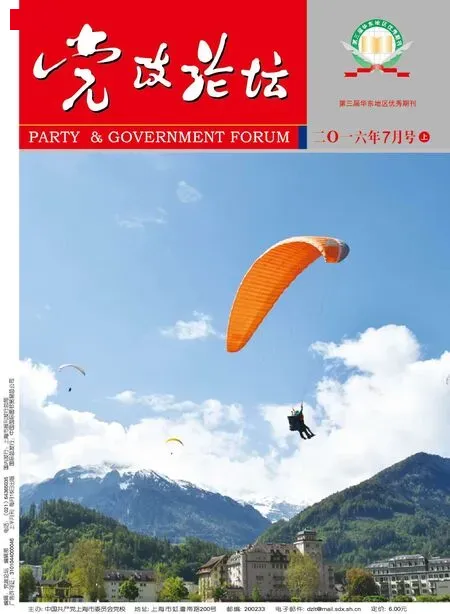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
○ 程 晨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
○ 程 晨
隨著2016年兩會的開幕,“協商民主”一詞又進入熱議話題領域。習近平同志曾在慶祝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談道:“我們要全面認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這一重大判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是針對什么而言的、體現在哪些方面、在理論層面又如何論證?本文試以通俗簡明的語言與讀者略作討論交流。
“協商民主”一詞是針對“票決民主”來說的。值得明辨的是,很多公眾將“票決民主”等同于“投票選舉”來理解并不準確。前者主要指在多個不同意見之中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確定最終方案,而后者指選民投票選舉自己認可的公共權力行使者。簡單說前者是選方案,后者是選人。選舉的問題不在協商民主與票決民主比較的范疇中。
在“選方案”這個問題上,即使是西方學術界,對協商民主(或審議民主)的優越性也達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共識。羅爾斯、哈貝馬斯等當代西方著名思想家都有過論述。然而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決策規則卻恰是以票決民主制為主要制度承載的,且頗有積重難返之勢,公共政治生活并沒有在實質意義上吸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這是因為以極端的個體自由為價值導向的自由主義民主體制,與協商民主制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邏輯悖反。
要說清這個問題需要交代一下理論的淵源。其實自由主義理論最早是在經濟領域生成的,強調的是個體產權保障前提下的充分競爭以求得市場活力和優勝劣汰,在此過程中消費者的利益卻可以實現最大化。道理最簡單不過,“貨比三家”才能找到最優選擇。應該說在經濟領域這一套確實是有效的,然而,當自由主義理論將這一套“自由競爭—自由選擇”的體制“依樣畫葫蘆”地搬到政治領域演化成票決民主制的決策規則時,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原先的設想是:政治領域不同的立法、政策主張就相當于經濟領域的產品,由不同的“政治產品”自由競爭,“政治消費者”(公民)則通過議會代表用票決民主制做出選擇就能實現優勝劣汰,也就得到了最優選擇和最大利益。這一套設想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忽略了政治領域的“公共性”絕非經濟領域可比。在進入21世紀后,遺留的漏洞尤為明顯地表現出來。
漏洞之一是,政治領域的效力普遍性與經濟領域的選擇個別性存在差異。立法、政策的效力及于社會公眾群體,而經濟領域的消費者選擇什么產品則是自己一個人的事。不同的公眾在對具體立法、政策上的偏好會有很大的不同,票決民主制、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雖然能得出最終方案,但對少數人來說,接受多數的意見畢竟在“自由”上是打了折扣的。在某些極端情形下,甚至會出現很多西方學者自己也批評的那種“多數人的暴政”。
漏洞之二是,政治領域選擇的間接性與經濟領域選擇的直接性存在差異。對立法、政策的“票決”不可能像經濟領域消費者購買產品那樣由其本人做出選擇,而只能通過政治代表(各級議會議員)來做出。這中間就會產生西方學者也承認的“代理問題”:政治代理者是否完全忠實于被代理者(選民)的意愿來做出選擇?很多西方國家的腐敗,就是因為資本通過各種方式誘使這些本該代理選民利益的代理者背離了宗旨,成了資本、權貴的代理者。資本、權貴進而控制了國家立法和大政方針。這一現象被學者們稱為“公共權力被資本俘獲”。
漏洞之三是,政治領域競爭的難以調控性與經濟領域競爭的可調控性存在差異。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優勝劣汰和保障消費者的選擇權,可這在良性、有序競爭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經濟領域的競爭如果滑向不正當競爭、惡性競爭的軌道,自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和經濟法律規范來調控糾偏。但立法、政策本身的競爭一旦有上述傾向,卻難以再找到可以調控的力量。有些西方國家黨派和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惡性競爭,甚至相互傾軋,選民卻沒有絲毫辦法。
漏洞之四是,政治領域決策的穩定性和經濟領域決定的靈活性存在差異。立法、政策一旦確定便不易更改,否則會浪費巨大的社會成本。即使有心更改,受益的政治力量也絕不會輕易容忍這種動向。而經濟領域消費者做出的選擇和決定,卻可以隨時發現問題隨時變換,這家不行馬上換另一家。這對市場主體的利潤影響是極大的,他們無法忽視這種影響,只能根據消費者的需要調整自己。所以靈活的選擇實際上意味著消費者是在以“參與者”的身份互動地影響競爭過程。這一點在政治領域無法實現,選民只是選舉者而無法變成參與者。
漏洞之五是,政治領域的價值多元性與經濟領域的經濟理性存在差異。在經濟理性的支配地位下,經濟領域的很多問題較容易達成共識,所有參與者對市場環境、交易規則、產品質量等要素的要求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而在政治領域,很難用絕對的標準來判斷立法、政策對不對、好不好,持不同價值立場的人有不同的衡量標準。一涉及價值判斷問題就很難達成共識。強行以票決民主確定最終方案,即使通過,在執行、落實層面也會因為共識缺位而陷入困難重重的境地。
上述這些漏洞,西方國家也作出過很深入的分析研究。但是在以極端化的個體自由保障為價值導向的大體制之下,很難得到根本解決。或者說在他們眼里,即便事情辦砸、決策錯誤,議會代表一人一票的票決權力代表著公民的“權利”,也是絕不容“侵犯”的。尊重議會代表的“權力”,決策遲滯甚至錯誤的風險卻要全社會來承擔。
協商民主制則能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些問題。習近平同志有一段論述總結了協商民主的優勢:“在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通過多種形式的協商,廣泛聽取意見和建議,廣泛接受批評和監督,可以廣泛達成決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識,有效克服黨派和利益集團為自己的利益相互競爭甚至相互傾軋的弊端;可以廣泛暢通各種利益要求和訴求進入決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為了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固執己見、排斥異己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發現和改正失誤和錯誤的機制,有效克服決策中情況不明、自以為是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人民群眾參與各層次管理和治理的機制,有效克服人民群眾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中無法表達、難以參與的弊端;可以廣泛凝聚全社會推進改革發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項政策和工作共識不高、無以落實的弊端。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所在。”
將上文所作的分析對照習近平同志的這段論述,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協商民主與票決民主最大的不同是,在確定最終方案之前有著充分、實效的協商過程,包含信息互換、意見交流、觀點交鋒,對分歧會有反復的解釋、說服。或許其重要性看上去不那么明顯,但其實無論是在理論邏輯上還是在實踐案例中,它的效果都有較為充分的論據。例如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西方公共管理專業學者所做的社會實驗等。此外,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還有兩項獨特之處,其一,協商是在執政黨的領導下(立法、大政方針的政治協商)或國家職能機關的主持下(社會治理事項、措施的具體協商)有序進行的。其二,除了國家權力機關之外,多數政治協商并不直接票決結論,而是由執政黨或相應職能機關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意見,做最后決定。
這樣一來:第一,充分的協商過程實現了公眾的充分參與和表達。有助于在不同勢力群體中間保持話語權的大體平衡。借由有效的信息互通和理性交換消解持不同意見者的對抗心理,最大程度追求共識。無論是在決策的可接受程度上,還是在執行的順利實施上都有益處。
第二,執政黨領導下、國家職能機關主持下的有序性有助于維持協商過程理性化。當協商過程出現不正當競爭、惡性競爭的傾向時,有足夠的力量進行糾偏,引導協商過程朝著團結、共識、有效的方向進行。
第三,多數情況下協商者不票決最終方案并不會削弱協商的有效性。將協商的“權利”和決定的“權力”作必要隔斷,既符合行政法治的權責統一原則,還能避免協商者“被資本俘獲”充當特定利益集團代表的風險。反而能夠保持協商者按照自己的真實意愿和良心建言獻策。
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國家各方面的關系都要協商”、“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周恩來同志也指出:“新民主主義的議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決,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協商和反復的討論”。習近平同志還強調:“實行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要求我們在治國理政時在人民內部各方面進行廣泛商量”“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從商量精神到協商制度再到治理實踐,歷經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探索、構建,“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論和實踐。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責任編輯 張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