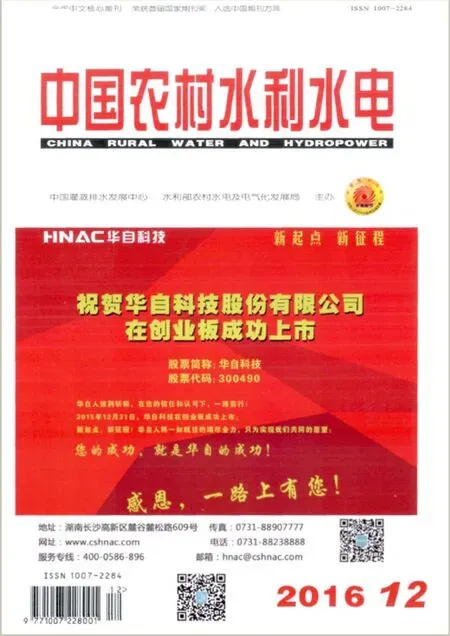汶川震后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特征及成災(zāi)機(jī)理
楊豐榮,周宏偉,霍 苗,曹 畑,梁煜峰,林珂珂(四川大學(xué)水利水電學(xué)院,成都 610065)
“5·12”汶川地震導(dǎo)致汶川震區(qū)產(chǎn)生大量的崩塌、滑坡體等松散堆積物,為泥石流的發(fā)生提供了有利條件,導(dǎo)致震后災(zāi)區(qū)泥石流頻發(fā)[1-4]。據(jù)“5·12”汶川大地震現(xiàn)場排查匯總結(jié)果可知,汶川地震后災(zāi)區(qū)新增9 000個(gè)地質(zhì)災(zāi)害點(diǎn),這些新增地質(zhì)災(zāi)害點(diǎn)以泥石流、滑坡為主,主要涵蓋8個(gè)重災(zāi)區(qū)(江油、旺蒼、綿竹、崇州、彭州、都江堰、茂縣、廣元利州區(qū))和重災(zāi)縣39個(gè),其中以汶川、北川、青川3個(gè)重災(zāi)縣最為嚴(yán)重,災(zāi)害點(diǎn)數(shù)量超過500處[4]。
現(xiàn)有的調(diào)查和研究分析表明,汶川地震前后,無論是泥石流的數(shù)量還是激發(fā)雨量都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2008-2012年5年間,汶川震區(qū)共爆發(fā)泥石流2 333處,約為震前5年間爆發(fā)泥石流總數(shù)(2003-2007年,共758處)的3倍[6]。唐川等[7]分析了北川區(qū)域泥石流震前震后泥石流發(fā)生的臨界雨量和雨強(qiáng)得出,震后泥石流啟動(dòng)的前期雨量降低了14.8%~22.1%,小時(shí)雨強(qiáng)降低25.4%~31.6%。TANG C等[8]對比北川縣泥石流爆發(fā)的雨量數(shù)據(jù)表明,震后泥石流爆發(fā)的前期累積雨量和激發(fā)雨強(qiáng)較震前分別降低了15%~22%和5%~31%。馬超等[9]對汶川地震災(zāi)區(qū)2008-2010年的暴雨泥石流雨量過程進(jìn)行分析得出34.4 mm是震后短時(shí)間內(nèi)泥石流暴發(fā)的特征雨量。
本文針對汶川地震9個(gè)地區(qū)共37條典型泥石流溝(汶川12條,清平6條,都江堰6條,北川4條,等)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事件及臨近典型泥石流溝地區(qū)的13條非泥石流溝的地形資料進(jìn)行了分析,得到了汶川震后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的地形、雨量、雨型特征,并結(jié)合汶川震后泥石流溝地形特征,物源體結(jié)構(gòu)松散,滲透性大,對降雨敏感性高的基礎(chǔ)上,認(rèn)識了汶川震后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的誘發(fā)特性及成災(zāi)機(jī)理,力求為泥石流預(yù)警預(yù)報(bào)以及防治等提供參考依據(jù)。
1 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地形特征
汶川地震后,震區(qū)內(nèi)產(chǎn)生大量的山體崩塌滑坡、植被被毀、坡體組成物質(zhì)異常松散,為震區(qū)溝道帶來大量的松散物質(zhì)(泥石流物源體),并迫使許多處在衰退期的低頻泥石流溝轉(zhuǎn)變?yōu)楦哳l泥石流溝[10],小型泥石流溝轉(zhuǎn)變?yōu)榇笮湍嗍鳒希瑥奈窗l(fā)生泥石流災(zāi)害的溝道演變成為泥石流溝[11,12]。從而導(dǎo)致汶川震后泥石流分布密度大,造成的危害十分嚴(yán)重,如震中汶川地區(qū)的映秀鎮(zhèn)、綿虒鎮(zhèn),北川地區(qū)的擂鼓鎮(zhèn)、老縣城,綿竹市地區(qū)的清平鄉(xiāng),距離震中較近的都江堰市龍池鎮(zhèn)龍溪河流域(該流域被龍門山前山、后山以及中央斷層穿過)以及彭州市龍門山鎮(zhèn)白水河流域(該流域處于龍門山斷裂帶中段與盆山的結(jié)合部,被映秀-北川斷裂帶穿過)[13-18]。為分析泥石流所在溝道的地形特點(diǎn),選取汶川震后37條典型泥石流溝,臨近典型泥石流溝地區(qū)的13條非泥石流溝作為代表,具體地形資料見表1、表2。由表1,表2可看出75.68%的典型泥石流溝主溝長度均在2~3km左右,其中宗渠溝最長達(dá)11.1 km,茂縣的大白楊溝最短僅為0.98 km,而非泥石流溝主溝長度均在14 km以上,即長度較短的溝道易于泥石流的形成。此外,相對于非泥石流溝來說,除太平驛溝與簇頭溝外,泥石流溝道流域面積均較小,94.59%在15 km2以下。由此可見汶川震區(qū)擁有泥石流形成的天然地形條件。

表1 汶川震區(qū)典型泥石流溝地形資料表Tab.1 Wenchuan earthquake zone typical debris flow gully terrain data sheet

表2 汶川震區(qū)未發(fā)生泥石流溝道地形資料表Tab.2 Wenchuan earthquake zone no debris flow gully terrain data sheet
圖1顯示了典型泥流溝的溝道流域面積和主溝平均比降。由圖1可發(fā)現(xiàn),泥石流溝道流域面積與主溝平均比降基本呈反向相關(guān)關(guān)系,即溝道平均比降越小,泥石流溝道流域面積越大,溝道平均比降越大,泥石流溝道流域面積越小,這表示溝道流域降雨量與相應(yīng)溝道比降共同導(dǎo)致了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的產(chǎn)生。由表2、表3可知,震區(qū)內(nèi)非泥石流溝比降84.61%低于10%,泥石流溝主溝比降72.97%都分布在20%~50%范圍內(nèi),與四川省泥石流爆發(fā)所需的溝床平均比降一般在10%以上[19]一致,其中以40%~50%范圍分布密度最大,占總量的27.03%,即汶川震區(qū)泥石流溝比降大,利于泥石流的誘發(fā)。
2 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雨量特征
為分析汶川震后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的雨量特征,本文搜集了汶川震后18條典型泥石流溝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事件的雨量資料,具體見表3。由表4可以看出: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所在區(qū)域年平均降雨量均較大,在1 000 mm以上高達(dá)94.4%,災(zāi)害發(fā)生時(shí)間主要集中在7-9月份,這與汶川震區(qū)降雨分布一致;84.6%的泥石流溝存在激發(fā)雨強(qiáng)小于最大1 h降雨量的現(xiàn)象,這表明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并不是小時(shí)雨強(qiáng)達(dá)到激發(fā)雨強(qiáng)便導(dǎo)致災(zāi)害產(chǎn)生,而是與豐富的前期雨量密切相關(guān),即前期累計(jì)降雨量越高,越容易引發(fā)泥石流。

圖1 汶川震區(qū)典型泥石流溝流域面積及主溝平均比降Fig.1 Wenchuan earthquake zone typical debris flow gully watershed area and main ditch average slope

表3 汶川震區(qū)典型泥石流溝分布與地形坡度的關(guān)系Tab.3 Wenchuan earthquake zone typical debris flow gully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with terrain slope

表4 汶川震后典型泥石流溝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雨量資料表Tab.4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typical debris flow ditch the rainfall data table of rainfall induced debris flow disaster
3 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雨型特征
通過分析汶川震區(qū)震后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事件降雨過程雨量資料,依照雨型特征可將汶川震區(qū)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分為3類,即暴雨突發(fā)型、大中雨激發(fā)型及連續(xù)陰雨誘發(fā)型。
(1)暴雨突發(fā)型。此類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降雨歷時(shí)最短,約6~8 h,小時(shí)降雨量非常大而密集,多在40 mm/h以上,累計(jì)雨量在短時(shí)間迅速增大,泥石流爆發(fā)突然,歷時(shí)短、約在1 h左右,暴雨突發(fā)型泥石流的發(fā)生通常出現(xiàn)在最大小時(shí)雨強(qiáng)發(fā)生時(shí)或者緊隨最大小時(shí)雨強(qiáng)前后。此類泥石流如汶川震區(qū)的八一溝(2010-08-13)和銀廠溝(2012-08-18)泥石流,具體見圖2。

圖2 汶川震后暴雨突發(fā)型泥石流典型災(zāi)害降雨過程Fig.2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storm burst type of debris flow disasters typical rainfall process
(2)大中雨激發(fā)型。此類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降雨歷時(shí)較連續(xù)陰雨誘發(fā)型短,較暴雨突發(fā)型長,約10~12 h,小時(shí)降雨量較大,多在30~40 mm/h,累計(jì)雨量增速較快,泥石流爆發(fā)突然,歷時(shí)較短約1~4 h,大中雨激發(fā)型泥石流的發(fā)生通常出現(xiàn)在最大小時(shí)雨強(qiáng)發(fā)生時(shí)或最大小時(shí)雨強(qiáng)后。此類泥石流如汶川震區(qū)的西山坡溝(2008-09-24)和文家溝(2010-08-13)泥石流,具體見圖3。

圖3 汶川震后大中雨激發(fā)型泥石流典型災(zāi)害降雨過程Fig.3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big rain excitation type debris flow disasters typical rainfall process
(3)連續(xù)陰雨誘發(fā)型。此類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降雨歷時(shí)在三者中最長,約為2~5 d,小時(shí)降雨量小,多在20 mm/h以下,累計(jì)雨量增速緩慢但雨量較大,故泥石流歷時(shí)較長約6~8 h,連續(xù)陰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的發(fā)生通常出現(xiàn)在最大小時(shí)雨強(qiáng)發(fā)生前后較長一段時(shí)間。此類泥石流如汶川震區(qū)的古溪溝(2013-07-10)和簇頭溝(2013-07-13)泥石流,具體見圖4。

圖4 汶川震后連續(xù)陰雨誘發(fā)型泥石流典型災(zāi)害降雨過程Fig.4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continuous rain induced debris flow disasters in typical rainfall process
4 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成災(zāi)機(jī)理
對于震后泥石流成災(zāi)機(jī)理,目前研究成果較多,唐川等[7]認(rèn)為暴雨過程形成的斜坡表層徑流導(dǎo)致懸掛于斜坡上的滑坡體表面和前緣松散物質(zhì)向下輸移,進(jìn)入溝道后轉(zhuǎn)化為泥石流;陳寧生等[20]通過實(shí)驗(yàn)得出地震使高含水量的土體孔壓增加,強(qiáng)度迅速降低。泥石流易發(fā)性可通過層次分析法、灰色關(guān)聯(lián)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判法和BP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法做出較為準(zhǔn)確的判別[20]。
影響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產(chǎn)生的主要因素包括:溝道地形地貌、形成區(qū)(物源區(qū))的物源體的堆積形態(tài)與物質(zhì)特性及降雨條件。由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地形特征分析可知汶川震區(qū)具備泥石流形成的地形、地貌條件,并且由于地震作用存在大量的松散物質(zhì)。物源體的堆積形態(tài)主要受形成區(qū)地形影響,經(jīng)分析,86.49%的泥石流溝形成區(qū)為“V”型河谷,89.43%泥石流溝形成區(qū)溝谷比降在25%以上,物源體堆積形態(tài)易于啟動(dòng)。主要組成物質(zhì)為地震造成的滑坡體、碎屑流及兩岸山體崩塌體,其結(jié)構(gòu)松散,滲透性大,對降雨敏感性高。那么在誘發(fā)泥石流發(fā)生的眾多因素中,降雨應(yīng)是最主要、最常見的誘發(fā)因素。“降雨誘發(fā)泥石流”僅僅是直觀的說法,嚴(yán)格來講,是降雨轉(zhuǎn)化的地下水及其與泥石流物源體之間的復(fù)雜相互作用激發(fā)了泥石流。本文在汶川震后典型泥石流災(zāi)害雨型特征分類、地形特征、物源體特征的基礎(chǔ)上,對三類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的成災(zāi)機(jī)理進(jìn)行分析。
若為暴雨突發(fā)型,降雨歷時(shí)短,小時(shí)降雨量大,累計(jì)降雨增速快。泥石流爆發(fā)以侵蝕為主,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2個(gè)方面:暴雨降落到地面,將對地面產(chǎn)生降雨侵蝕力,形成三角形沖坑,造成泥石流物源體的加速形成和失穩(wěn)破壞;來不及下滲的地表水在物原體表面形成較大積水區(qū)及滲入表層物源體使其重量增加,增大了物源體的下滑力,并且滲入的水使物源體軟化、潛蝕,導(dǎo)致其抗剪強(qiáng)度降低,最終致使松散的物源體在短時(shí)間內(nèi)形成泥石流。見圖5。

圖5 汶川震后暴雨突發(fā)型泥石流成災(zāi)機(jī)理Fig.5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type emergency mechanism of the storm burst type of debris flow
若為大中雨激發(fā)型,降雨歷時(shí)較短,小時(shí)降雨量較大,累計(jì)降雨增速較快。泥石流爆發(fā)以侵蝕和沖刷為主,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2個(gè)方面:大中雨降雨降落到地面,將對地面產(chǎn)生降雨侵蝕力,形成圓弧形沖坑,降雨強(qiáng)度較大并未完全超過土體實(shí)際入滲能力,降雨部分滲入松散物源體,使其重量增加,增大了物源體的下滑力,并且滲入的水使物源體軟化、潛蝕,導(dǎo)致其抗剪強(qiáng)度降低;隨降雨時(shí)間延續(xù),降雨形成的地表徑流對物源體表面進(jìn)行沖刷,形成表面剪切力,增大了物源體下滑力,最終致使松散的物源體在較短時(shí)間內(nèi)形成泥石流。 見圖6。

圖6 汶川震后大中雨激發(fā)型泥石流成災(zāi)機(jī)理Fig.6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type emergency mechanism of the big rain excitation type debris flow
若為連續(xù)陰雨誘發(fā)型,降雨歷時(shí)較長,小時(shí)降雨量較小,累計(jì)降雨增速較慢。泥石流爆發(fā)以下滲為主,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2個(gè)方面:泥石流爆發(fā)前一段時(shí)間,由于連續(xù)小雨持續(xù)下滲導(dǎo)致松散的物源體內(nèi)部具有豐富的含水量,使其重量增加,增大了物源體的下滑力,并且滲入的水使物源體軟化、潛蝕,導(dǎo)致其抗剪強(qiáng)度降低;累計(jì)降雨的緩慢增加致使松散的物源體飽和程度較高,并促使浸潤線水位抬高,抬高的水位對物源體產(chǎn)生浮托力,利于泥石流的起動(dòng),從而致使松散的物源體在較長時(shí)間內(nèi)形成歷時(shí)較長、規(guī)模較大的泥石流。見圖7。

圖7 汶川震后連續(xù)陰雨誘發(fā)型泥石流成災(zāi)機(jī)理Fig.7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type emergency mechanism of the continuous rain induced debris flow
5 結(jié) 語
(1)通過對汶川震區(qū)37條典型泥石流溝和臨近典型泥石流溝地區(qū)的13條非泥石流溝的調(diào)查分析得出,相對于非泥石流溝而言,泥石流溝在主溝長度、流域面積、主溝平均比降均大于非泥石流溝,即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易發(fā)生在流域面積不大(94.59%在15 km2以下)、比降不小于15%的溝谷地區(qū),泥石流溝主溝比降72.97%都分布在20%~50%范圍內(nèi),其中以40%~50%范圍分布密度最大,占總量的27.03%,泥石流溝道流域面積與主溝平均比降基本呈反向相關(guān)關(guān)系,泥石流溝道平均比降越大,溝道流域面積越小。
(2)汶川震區(qū)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災(zāi)害所在區(qū)域年平均降雨量均較大,1 000 mm以上高達(dá)94.4%,災(zāi)害發(fā)生時(shí)間主要集中在7-9月份,與汶川震區(qū)降雨分布一致;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的爆發(fā)與豐富的前期雨量密相關(guān),約84.6%的泥石流災(zāi)害激發(fā)雨強(qiáng)小于其最大1 h降雨量。
(3)通過雨型特征分析比較可將汶川震區(qū)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分為3大類,即暴雨突發(fā)型、大中雨激發(fā)型及連續(xù)陰雨誘發(fā)型。暴雨突發(fā)型泥石流具有降雨歷時(shí)短,約6~8 h、小時(shí)降雨量大,多在40 mm/h以上、累計(jì)降雨增速快,泥石流歷時(shí)短約在1 h左右的特點(diǎn)。大中雨激發(fā)型泥石流具有降雨歷時(shí)較短,約10~12 h、小時(shí)降雨量較大,多為30~40 mm/h、累計(jì)降雨增速較快、歷時(shí)較短約為1~4 h的特點(diǎn)。連續(xù)陰雨誘發(fā)型具有降雨歷時(shí)較長,約為2~5 d、小時(shí)降雨量較小,多在20 mm/h以下、累計(jì)降雨增速較慢、泥石流歷時(shí)較長約為6~8 h特點(diǎn)。
(4)通過分析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成災(zāi)的3個(gè)影響因子:溝道地形地貌、形成區(qū)物源堆積形態(tài)與物質(zhì)特性及降雨條件得出,物源體的堆積形態(tài)主要受形成區(qū)地形影響,86.49%的泥石流溝形成區(qū)為“V”型河谷,89.43%泥石流溝形成區(qū)溝谷比降在25%以上。堆積體物質(zhì)結(jié)構(gòu)松散,滲透性大,對降雨敏感性高。降雨是最重要的影響因子,通過進(jìn)一步分析3種降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的成災(zāi)機(jī)理,得出暴雨突發(fā)型泥石流爆發(fā)以侵蝕為主,大中雨激發(fā)型泥石流爆發(fā)以侵蝕和沖刷為主,連續(xù)陰雨誘發(fā)型泥石流爆發(fā)以下滲為主。
□
[1] 馬 煜,余 斌,李彩俠,等. 汶川強(qiáng)震區(qū)群發(fā)性泥石流特征研究[J]. 災(zāi)害學(xué),2014,29(3):218-223.
[2] 李大鳴,呂會(huì)嬌. 山區(qū)暴雨泥石流預(yù)報(bào)數(shù)學(xué)模型的研究[J].中國農(nóng)村水利水電,2011,(2):24-28.
[3] 崔 鵬,庒建琪,陳興長,等. 汶川震區(qū)泥石流活動(dòng)特征與防治措施[J]. 四川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工程科學(xué)版),2010,42(5):10-19.
[4] 雷發(fā)洪,胡凱衡,胡云華. 汶川地震災(zāi)區(qū)震后泥石流激發(fā)雨量研究[J]. 災(zāi)害學(xué),2014,29(5):199-203.
[5] 丁 驄.汶川大地震觸發(fā)地質(zhì)災(zāi)害的發(fā)育分布規(guī)律剖析[J]. 有色金屬文摘,2015,30(2):31-32.
[6] Huang R Q,F(xiàn)an X M. The langdslide story[J].Nature Geoscience,2013,(6):325-326.
[7] 唐 川,梁京濤. 汶川震區(qū)北川9.24暴雨泥石流特征研究[J].工程地質(zhì)學(xué)報(bào),2008,16(6):751-758.
[8] Tang C,Zhu J LI W L,et al.Rainfall-triggered debris flows following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J].Bull Eng. Geol. Environ,2009,68:187-194.
[9] 馬 超,胡凱衡,趙晉恒,等. 震后泥石流的激發(fā)雨量特征[J].災(zāi)害學(xué),2013,28(4):89-94.
[10] 阮文斌.汶川縣太平驛溝泥石流的形成機(jī)制及危險(xiǎn)性分析[J]. 四川地質(zhì)學(xué)報(bào),2014,(增34):99-106.
[11] 黃 勛,唐 川,樂茂華,等. 汶川震區(qū)銀廠溝區(qū)域8·18暴雨泥石流災(zāi)害成災(zāi)機(jī)理與特征[J]. 工程地質(zhì)學(xué)報(bào),2013,21(5):761-769.
[12] 梁京濤,王 軍,宋 云,等. 汶川震區(qū)典型泥石流動(dòng)態(tài)演變特征研究——以綿竹市走馬嶺泥石流為例[J]. 工程地質(zhì)學(xué)報(bào),2012,20(3):318-325.
[13] 張光慶,于賀艷,寇紅梅. 老街新村肖家溝泥石流形成條件與動(dòng)力學(xué)特征分析[J]. 山西建筑,2015,41(24):71-72.
[14] 嚴(yán) 炎,葛永剛,張建強(qiáng),等. 四川省汶川縣簇頭溝“7.10”泥石流災(zāi)害成因與特征分析[J]. 災(zāi)害學(xué),2014,29(3):229-234.
[15] 鐵永波,唐 川. 四川省北川暴雨泥石流的發(fā)育與汶川地震的響應(yīng)特征[J]. 災(zāi)害學(xué),2011,26(4):73-75.
[16] 趙學(xué)宏,常 鳴,黃翔超. 汶川震區(qū)清平鄉(xiāng)文家溝泥石流災(zāi)害特征分析[J]. 南水北調(diào)與水利科技,2011,9(5):107-110.
[17] 張健楠,馬 煜,張惠惠,等. 四川都江堰市大干溝地震泥石流[J]. 山地學(xué)報(bào),2010,28(5):623-627.
[18] 葛永剛,宋國虎,郭朝旭,等. 四川彭州市龍門山鎮(zhèn)8.18泥石流災(zāi)害特征與成災(zāi)模式分析[J]. 水利學(xué)報(bào),2012,43:147-154.
[19] 四川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 四川省山洪防治規(guī)劃[R]. 中國科學(xué)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災(zāi)害與環(huán)境研究所. 2004.
[20] 陳寧生,崔 鵬,王曉穎,等. 地震作用下泥石流源區(qū)礫石土體強(qiáng)度的衰減實(shí)驗(yàn)[J]. 巖石力學(xué)與工程學(xué)報(bào),2004,23(16):2 743-2 747.
[21] 池春青,徐永年,劉卉芳,等. 泥石流危險(xiǎn)性評價(jià)淺析[J]. 中國農(nóng)村水利水電,2008,(8):44-47.